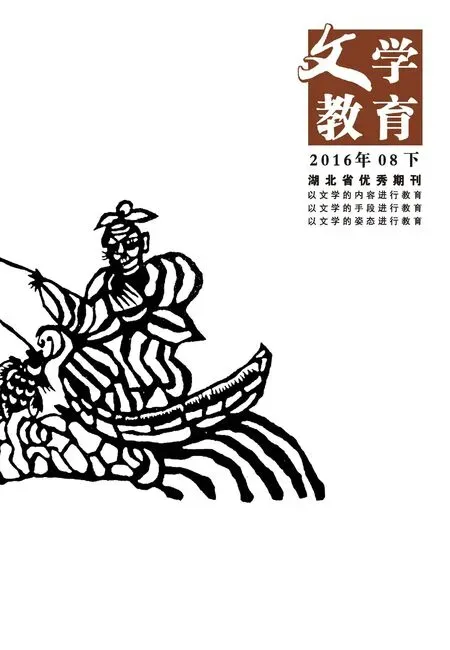關于教師語言暴力問題的分析
蘇婧雯
關于教師語言暴力問題的分析
蘇婧雯
語言作為人類交流溝通的主要工具,只有運用文明和諧的語言才能夠促進社會的文明與和諧。教師作為文明的傳播者,教師的語言要求一定要保持文明,只有這樣才能讓學生擁有一個文明、健康、積極向上的學習環境。在這幾年來,在我們的中小學校園中,教師體罰學生的現象變少了,但是教師對學生辱罵、嘲諷、當眾指責,甚至孤立漠視等現象卻是屢見不鮮。教師的語言暴力在我國的中小學已是較為普遍的了,這種畸形的教育方式對學生的身心健康有著不容忽視的危害。社會、家長、教育部門、學術界對這一問題需要給予一定的重視。
教師 語言暴力 溝通
一、概念界定
在普遍的觀念中,對于“暴力”的理解一般便是使用武力對對方的肉體上造成了一定的傷害。然而,如今西方社會對于“暴力”有著不同的理解,“暴力不必總意味著身體暴力,它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形式,可以表現為用語言傷害一個人的情感和尊嚴”那么作為日常交際的語言可以作用一種暴力的形式存在嗎?教師的語言在什么樣的程度可以成為語言暴力?本文將對此進行進一步闡述。通過對暴力及語言暴力概念的界定之后,可以得出運用暴力和語言暴力的人是在社會上或是評價體系中擁有一定的權力及地位的。而在我國悠久的師生觀中,教師作為施教者,在面對學生時,無形中便擁有了一定的權利及地位。同時,教師之所以為施教者,便是因為其在資歷上、學識上、年齡上均上高于學生的,因此教師相對處于權威的地位。雖然我國有一系列相關的教師與學生的權利及義務,亦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對未成年給予一定的保護。但是,我國在教師所行駛的權利上并沒有相關的法律以明確的限定,特別是在教師的懲戒全中,出了體罰這一項被法律明令禁止外,其他超越肉體的懲罰的方法以及界限還存在一定的盲區。因此,教師存在權力濫用的情況也多有發生。張雪梅通過列舉教師語言暴力的具體表現把它定義為:教師使用嘲笑、侮辱、誹謗、詆毀、歧視、蔑視、恐嚇、謾罵這種類型的言語,使得學生身心收到一定程度的傷害。
從語言學來看,教師的語言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有聲語言,另一類是無聲語言。有聲語言是教師教育、教學的主要媒介。眼神、表情、態度等體勢語言是一種無聲語言,是教師語言中最重要的輔助語言。因此,“惡語傷人”是一種教師語言暴力,用冷漠的眼神、態度孤立棄置學生的“冷暴力”也屬于一種教師語言暴力。
二、國內外相關研究
(一)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在教師語言暴力的研究方面以校園暴力為主。國外學者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德]哈貝馬斯著,沈清楷譯的《話語倫理學與真理問題》;法國喬治·索雷爾著,樂啟良譯的《論暴力》;英國米歇爾·艾略特著,新苗編譯小組譯的《反校園暴力101招》;美國伊文斯著,宋云偉譯的《語言虐待》等。挪威作為世界上最早關注校園暴力問題并將此上升為國家的政治層面問題的國家。挪威校園暴力事件的發生引起了全世界各類人士廣泛的關注,其中有三位學生因遭受到了校園暴力事件而自殺。這使得校園暴力成為挪威政府極度關注的問題之一。1985年的日本,16位小學生因受到校園暴力傷害而集體自殺。這個事件震驚了全世界,然人們在痛惜悲憤之余的同時也在反思校園暴力這一令人發指的問題。自此,校園暴力傷害問題已然從學校教育領域的問題上升為重大的社會問題,此后學術界也開始了進一步對校園暴力問題的研究。
(二)國內研究現狀
關于教師暴力語言的界定問題,國內也有部分學者的著作及文章作了論述。著作如徐久生的《校園暴力研究》,辛學偉的《教師語言暴力的成因及對策淺析》,胡東芳的《誰來塑造“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檀傳寶的《教師倫理學專題—教育倫理范疇研究》等。文章如王紅的《對教師“語言暴力”現象的思考》,曹虹青的《教師的語言暴力現象及根源探析》等。比較有代表性的定義如辛學偉認為:“‘語言暴力’是指用詆毀、謾罵、諷刺等歧視性語言,使他人精神層面遭到侵犯,它屬于一種精神傷害。”國內學者對于教師語言暴力的界定已較清晰、完整、全面,為本文對于教師語言暴力的界定提供了一定的理論依據。
(作者單位:延安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