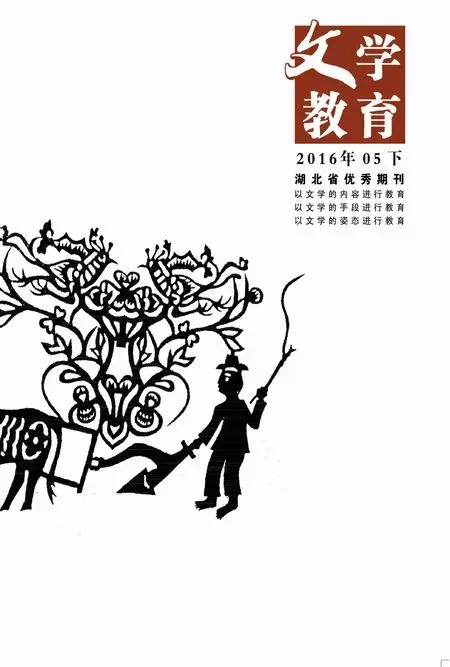試析史蒂文斯《在晴朗的葡萄季節》
周路平
?
試析史蒂文斯《在晴朗的葡萄季節》
周路平
內容摘要:作為美國現代詩歌史上的巨擘,華萊士·史蒂文斯有著對于詩歌語言形式的自覺的追求。《在晴朗的葡萄季節》以明快的意象、強烈的對比,為我們展現出語詞的魅力。在這首詩中語言不僅僅是傳情達意的工具,而且具備物質的溫度和質感,從自身延展出無窮的意蘊。本文采用文本細讀的分析方法,根據詩句中顯在的語詞張力,從三個對立層面切入文本,揭示詩篇潛在的文本動力:詞語如何呈現自身。
關鍵詞:史蒂文斯詩歌詞語
華萊士·史蒂文斯(1879-1995)是美國最著名的現代詩人之一,在美國文學史上堪與埃茲拉·龐德、T· S·艾略特、威廉·卡羅斯·威廉斯比肩的詩人。他四十四歲才發表第一部詩集《簧風琴》,而且一直供職于一家保險公司,副總裁和詩人的雙重身份,使他不得不棲身于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狀況之中。也許正是出自與商人身份互補的需要,需要在紛繁的俗世生活之中保留一塊精神的家園,華萊士·史蒂文斯一直醉心于思考和想象的詩歌國度。正如亨利·W·威爾斯在他的《華萊士·史蒂文斯導論》中所說的那樣,如果把史蒂文斯的創作比作一棵大樹,而把他的主題——藝術想象與現實的關系——比作這棵大樹的主干,那么這棵大樹的主體美主要表現在從主干長出的富有詩意的葉子上,鮮艷奪目的花朵和豐碩的果實上,而不是表現在其主干上。《在晴朗的葡萄季節》是他的一首不太為人注意的詩,但這首詩卻展現出詩人對于語詞的執著追求。本文嘗試從這首詩的文本出發,探索它的運行機制和潛在文本動力。
《在晴朗的葡萄季節》作為詩題是對于時節的把握。“晴朗”與“季節”本是抽象的概念分別對應于一種天氣狀況和時間觀念。“葡萄”一詞的介入干涉了這種空洞洞的指涉,使它不至于滑向無底、遁入純粹的虛空。天空與大地、陽光與果實,這些潛在的所指相互吸引,聚集在葡萄這個意象的周圍,它們相互照映組成一幅生動形象的立體景象,詩題因而也具有了突顯的意義,獲得了作為存在物獨自存在的權力。它夾帶著葡萄的深紫和圓潤,秋天的金色陽光,甚至農人豐收的喜悅,指向一種對于原初時間經驗的聯想。人類早期對于時的定義與度相關,“時”的意識是在與環境的協調經驗中產生的。最早人們根據天氣和大自然氣候的變化規律,選擇適宜的條件播種、采集、收獲農作物,以此為“合度”、“守時”。在這里借用與農業相關的時間感,強調早已被人忽略的人與大地的親密關系。
一、區分與融合
我們的土地和大海之間的群山——
群山和大海和土地的結合——
從前我可曾停步想起這些?
沉浸于標題流露出的田園氣息中時,第一節詩,把我們帶到了土地、大海、綿延的群山之中。“土地和大海之間的群山”——以群山為分水嶺,以此為界一邊是土地,另一邊是大海,無論是從語法,還是從語議上來講,“群山”的突出正是因其與土地和大海之間的差異。正如差異與區別產生出意義一樣,群山加強了這種區分,使它們不至于相互混淆。這種區分與“我們”相應,約定俗成做為語言產生的前提,在文字成為通行標準時,就加強了這種“事實性”(哈羅德·布魯姆在〈批評、正典結構與預言:事實性的悲哀〉一文中提到這種“事實性”,稱它為冷冰冰的事實,事實意味著本來如此,不得不如此的無奈)。原本是做為隱喻與象征的文字,最后代替了原初指涉物,最終成為塑造了我們的結構。文字以差異性為基準,難以完全表述自然之一體,然而對于“我”來說“群山和大海和土地的結合”它們走向一種融合、統一。
“從前”一詞增加了時間的意味,賦予這種突發的個人體驗以歷史感,擺脫了平行指涉的尷尬。沒有時間維度的語言爭執是虛空的,能指間的相互指涉最終只能推遲意義。能指的交錯總能產生時間序列的聯想,與其把這種對于時間的展望看作是詞語秩序的能效,還不如說正是這種原發的時間感引起了詞語的序列。“從前”一詞的現身,將“當下”納入視野,雖然說任何閱讀者是當下的,但是自覺的“當下”意識,仍然需要提醒,這種喚醒的功能是詩歌語言與日常語言之間的區別,也是“文學性”借以展現之所。由于“從前”的參與,這里的“當下”就不再是簡單的同一,而是經歷了正——反——合的辨證發展之后的更高層次上的統一。沒有經歷過區分、辨別的意識是混沌的、原始的,接受了語詞的規則之后發現它的可能性,才能到達最后的純凈:“詞的現身”(史蒂文斯稱它為最高虛構的真實)。詩人對語言的使用通常是自覺而敏感的,往往自覺地討論語言、思考語言,而不是借用語言表達、思考,語言從實用的范疇抽身而出,獨立呈現。正如馬拉美區分的:“話語的雙重狀況,即未加工的或直接的話語和本質的話語。”未加工的話語同事物的實在有關,本質的話語使事物遠離去,使它們消失,本質的語言始終是暗示式的,它向我們作提示、追憶。
二、人力與自然
維特根斯坦所謂的語言的郊區,由所謂一條條直來直往的街道,由毫不含糊,或者說是自稱毫不含糊的話語所構成:“我們的語言可以被視為一座古城;這座迷宮充滿了小街和廣場,老房子和新房子,房子上還有各個不同時期添加的東西,城四周則是大量的新區域,有著筆直規則的街道和規格一致的房子。”
語言的郊區對應與馬拉美所說“直接的話語”,它是日常話語,語詞的價值在于使用,即表明意圖,發出對話邀請,獲得有用信息的請求。語詞的魅力完全消失于使用之中,自然得幾乎讓人察覺不到詞語的存在。語言的古城對應于“本質的話語”,處處是暗道和叉路,語詞的迷宮是一個“晦暗的世界/有著永遠無法被完全表達的事物/其中你永遠不完全是你自己/也不想或不需要是”,它的目的是產生距離,而不是縮小詞與物的距離,這種距離大得足以使人驚詫于語詞本身,不需假借于物而使語詞存在。精心設計的“展覽”,就像有著明顯表達意圖的語言,它所使用的物不能做為物自身而現身,因為它服從于更高欲念:表達的需要:
當我想起土地,我想起那房子
桌子上有一大盤梨子,
青綠中泛著朱紅,擺在那兒展覽。
這里的梨子,不再是密密匝匝的果園里一棵梨樹上的果實,它也不再有果園里泥土的芬芳,不再有金秋陽光的溫暖,不再包含收獲的喜悅,不再映照樹葉的青綠。梨子的在場,成為孤寂的符碼,是“展覽”的需要,而不能揭示存在者的存在。它象征著人工的操作和人力的設定,在一個主體隱退的場景中梨子脫離了與實物的聯系,成為一個懸浮物,像一幅抽象派繪畫一樣,透視為幾種色彩的混合。“在那兒”,又是一個距離指涉詞,無意之中增加了心理距離,或者說是體驗距離。它是一個遠遠的標志物,脫離了生活的氣息,反襯出當下“此岸”生活的生動,“在那兒有非個人的存在的‘力場’。某種既非主體也非實質的東西。”
但滾動的青銅下這片粗野的藍
使那些精心選擇的涂鴉黯然失色。
更明亮的果實!陽光和月光下的一閃,
“在那兒”與“這”形成巨大的語言張力,不僅是近與遠、距離與親密之爭,更是人力與自然的較量,“精心選擇的涂鴉”不如自然造化天成,看似粗野的缺少修飾的藍,反倒成為更能代表自然本色的“果實”。自然的豐碩,自然的偉力,簡單的一種色彩就可以是無盡的表達。這里的“藍”就像維特根斯坦意義上語言古城里的一座小屋,本身的意指是含混的,甚至曖昧的,各種意義交叉,疊加,相互作用,有意推延意義,有意地掩飾和回避表達,借以擺脫淪落為工具的危險。
如果意義不過如此,但它們意味著更多
群山和大海和土地意味著更多。
霜霧的波動和狐貍的尖叫意味著更多。
這里的詩句帶有明顯的反表述特質,因為表述的最基本的要求是表情達意,這里突出的不是確切的所指,反而轉向無法言傳之物,“意味著更多”一詞重復出現加強了這種印象。“意義不過如此”,似乎還在清晰地傳達一種狀況,但語義流到此處嘎然而止,無法言傳的意義留下大片的空白,需要想象力加以填補和充實。群山、大海、土地、霜霧的波動、狐貍的尖叫,這些自然的群象,與后面的“意味”相照應,引人反復的咀嚼,并不實指現實的客觀世界。它們不是做為詞的物存在,并不與自然的現實一一對應,并不確指某處的山、土地、大海,而是作為物的詞而現身,顯示出與日常語言與日常生活的距離。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家稱之為“陌生化”,新批評稱之為“張力”,其目的都在突出詩歌語言的特質:做為詞而現身。語言的在場“這詞本身:這就是”。語詞不再是傳達意識的工具,在自身之中取得了完滿性。無論是羅蘭·巴特在《S/Z》中提出的“含蓄意指”,還是托多羅夫在《象征理論》中指出的“間接所指”它們共同的指向都是對直接意指的批評,認為文學語言中所指的推延,意義的延期與轉移,與文學作品的文學性是密不可分的。
比那意味著多得多。秋天的呼吸
被巖石的影子吊起來,
他的鼻孔把鹽噴向每一個人。
詩的結尾加強了詞語現身的力度,“意味”最后還是沒有得到澄清,大概可以說“秋天的呼吸”對應于風,秋風掃落葉,不再是春天暖融融的春風,而是勁風。巖石的陰影阻礙了光的探尋,對應于不可知之物,吊起秋風。陰影作為空間現象,不象明亮處那樣開放、敞亮,有一種凝重感,像封閉的空間一樣,在那里一切都被懸置了,甚至秋風也被吊起。“秋天的呼吸”被懸置起來,獲得非原物的存在,鼻孔成為它的代替物,把秋風的辛辣、干裂吹到每一個人臉上,仿佛在向人臉上噴灑鹽粒。這里的文字形象脫離了日常經驗,把它處理成一種想象的存在,文字與生活經驗之間的巨大張力,明顯地拒斥生活化的解讀,詞語作為獨立存在之物得以現身。
在這首名不見經傳的小詩《在晴朗的葡萄季節》中,詩人對于語詞的態度表露無遺,可以說任何一位詩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一位語言學家,但是他所向往的工作不是歸納和總結日常生活中的句法,而是創造新的語式,通過語詞的陌生感創造出新的經驗,實現新的可能性:讓世界和語言在“驚異”之中現身。
三、表述與隱義
[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吉爾﹒德勒茲“褶皺理論”研究》;目編號:2015-QN-529]
(作者單位:河南工程學院服裝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