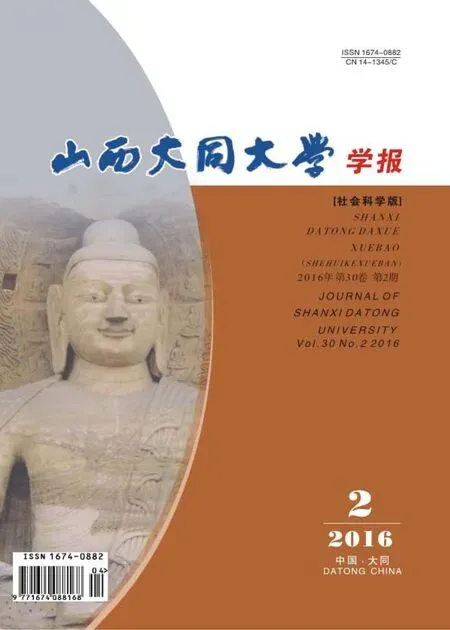都德在中國的譯介、傳播與接受
曹文剛
(淮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安徽 淮北 235000)
都德在中國的譯介、傳播與接受
曹文剛
(淮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安徽 淮北 235000)
都德初漸中國便受到各階層讀者的歡迎,文學革命倡導者借譯介都德,促進中國短篇小說的成長,鴛鴦蝴蝶派從文學趣味出發,更強調譯文的趣味性和悲情效果。1920年代對都德的接受,更多著眼于他對自然主義的反動上;1930年代及以后,中國讀者從愛國主義角度選擇都德;新時期對都德的接受轉入低谷。都德《最后一課》的中國仿作,不愿選用原作超然的反諷敘事語調與事件拉開審美距離,而是運用第三人稱敘事視角,未能與現實拉開一定距離,其藝術感染力有所下降。都德與師陀、沈從文的詩情小說都醉心于清靜、淳樸的鄉村,傾心于原始、宗法社會,表現了對人類命運深刻思索的共同精神追求。
都德;中國讀者;自然主義;《最后一課》;詩情小說;愛國主義
都德是中國讀者較為熟悉的法國作家,他在中國受到廣泛的歡迎與贊美。如果把他與另一位法國作家左拉相比較,我們會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左拉在中國毀譽參半,被中國讀者的接受程度遠遠比不上都德,中國普通讀者親近都德而疏遠左拉,然而,中國作家對這兩位法國作家的態度卻與一般的讀者截然相反。中國作家更推崇左拉,將左拉而不是都德視為自己的偶像。如何看待這一背反現象?這需要我們對都德在中國的譯介、傳播與接受作深入考察。
一、都德在中國的接受
第一位譯介都德的是胡適。1912年他譯出了都德的名篇《最后一課》,譯名為《割地》,登載于1912年9月29日的上海《大共和日報》上。后來,他又翻譯了都德的另一名作《柏林之圍》,刊登在1914年《甲寅》月刊1卷4號上。胡適當時所譯《最后一課》和《柏林之圍》,一方面是出于弘揚愛國精神的考慮,另一方面是想引進歐美短篇小說藝術,以構建中國新文學。他在《論短篇小說》中指出,短篇小說并不是字數較少,而應該是用“最經濟筆法”去寫“事實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個方面”,[1](P187)正如都德的《最后一課》,小說反映的是普法戰爭中法國的失敗,并不是按照戰爭發生的原因、進程、影響的完整寫法,而是選擇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一個無知頑童所上的最后一課,從這一側面來表現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胡適翻譯的都德的小說給中國讀者以耳目一新之感,他們習慣于有首有尾、有因有果的說書藝術,讀了這樣的翻譯小說,他們對現代短篇小說的藝術內涵、美學特征,有了直觀的認識,扭轉了中國讀者的文學趣味,促進了中國現代短篇小說的繁榮。
鴛鴦蝴蝶派作家與胡適不同,他們從文學趣味出發,對都德進行了不同的選擇,他們更注重譯文的悲情效果與趣味性,選擇了滑稽可笑的《獵帽記》,刺激情感的《妒》、《捍》等作品。他們也不像胡適那樣忠實于原作,而是采取了意譯、曲譯的方法,使原作風味蕩然無存。1920年代,《小說世界》、《東方雜志》、《小說月報》等期刊翻譯了大量都德的作品,廣大國內讀者在此時讀到了《月曜日故事》與《磨坊文札》中的大部分短篇小說。1927年,成紹宗、張人權在單篇翻譯的基礎上推出《磨坊文札》全譯本,由于都德這種詩情小說具有巨大魅力,譯本一出現,就引起強烈反響,先后多次再版,在當時的文壇上產生很大影響。
1920年代初,都德的長篇小說也開始得到翻譯。1922年,李劼人翻譯的《小東西》由中華書局出版。李劼人一直喜歡都德的作品,當他從《小說月報》上讀到《獵帽記》后,覺得都德小說很有味道,于是運用《獵帽記》中的筆調創作了文言小說《夾壩》。接下來李劼人閱讀《最后一課》與《知事下鄉》后,這樣說道,“都德的文章已是為我所愛好,乃至數年后,能夠讀法文了,故在中華民國11年,作第二部翻譯時,便選中了《小東西》這部書。”[2]1924年,李劼人又譯出《達哈士孔的狒狒》,收入《少年中國學會叢書》,這部作品卓越的諷刺藝術對李劼人以后的長篇小說創作產生了影響。
1920年代中國讀者之所以對都德感興趣,一方面出于對其小說藝術的喜愛,另一方面則出于對自然主義運動的反抗。中國讀者喜愛感傷情調和道德說教,與自然主義格格不入,對其赤裸裸寫實很反感。但他們又希望借助自然主義來救治中國文學的痼疾,所以期待自然主義與理想主義融為一體。在都德的作品中,他們找到了心理平衡。都德既屬于自然主義,又與自然主義有很多不同,他的寫實中夾雜著理想、傷感情調。在中國讀者的眼中,都德作品集寫實與浪漫、主觀與客觀之大成,調和折中,堪稱完美。事實上都德小說遠非完美,他的作品視野不開闊,缺少對人類精神世界深刻的洞察,常常流于膚淺的悲情主義,常常以犧牲作品真實與自然為代價來追求詩意與含淚的微笑。對都德作品價值人為的拔高,使都德的聲譽直線上升,卻使中國讀者難于從他作品中挖掘出更多深刻東西,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都德與左拉對中國的影響方式是不同的。
對于左拉,中國讀者主要是從理性角度來接受的。左拉的作品與中國文學傳統相抵牾,卻能救治中國文學的痼疾,通過新文學倡導者的提倡,最終匡正民族期待視野,中國讀者對于左拉實現了自覺的理性接受。而對于都德,中國讀者主要是自發的情感接受。都德親近中國文學傳統,他作品中主觀感傷情調與中國傳統審美情感是相通的,卻缺乏對衰落的中國文學的救治功效。從這個角度看,都德雖然受到中國讀者歡迎,但他卻遠遠比不上左拉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深刻。
與1920年代主要從自然主義的反動上理解都德不同,1930年代及隨后抗戰歲月中,中國讀者從愛國主義角度選擇了都德。戰爭的傷痛,中國如何面對侵略,都是讀者想從都德小說中尋找解答與寄托的。《月曜日故事》中一篇篇充滿著愛國主義激情的文字,使處于相似民族命運下的中國讀者感同身受、激動不已,正如邵燕祥所說:“都德作品最能觸發我們偷生于日本占領下的亡國之痛了。”[3]就這樣,都德作為愛國主義作家的形象被固定下來直至如今。
新時期人們對都德的熱情已經下降,他那種充滿感傷主觀情調的溫情小說已不再能引起中國讀者的興趣,譯介與研究都德由高潮轉入低谷。與都德已無可避免地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截然不同的是,隨著中國社會歷史背景的變化和讀者期待視野的變更,左拉得到了中國讀者的重新認識與解讀,他對于中國新文學的重要性遠遠在都德之上。
二、《最后一課》與其中國仿作
中國讀者對都德的名篇《最后一課》情有獨鐘,1920-1930年代出現了《最后一課》的仿作。第一篇是1922年鄭伯奇發表在《創造季刊》上的《最初之課》,它講述了一個天真的留日學生,在最初一課上受到羞辱。第二篇是1924年勁風刊登在《前鋒》雜志上的《課外一課》,講的是父親為無知男孩補上愛國一課的故事。第三篇是李輝英在1930年代創作的《最后一課》,敘述一個女孩因撕毀日本封閉學校和改上日文課的布告而被羈押。第四篇是大琨的《最后之一課》,故事是主人公在“八一三”事變之際趕到學校上好最后一節國文課。這些小說與都德的《最后一課》的相同之處是都表達了一種抗戰愛國的主題,渲染了濃厚的愛國情緒,“課”是這些小說的關鍵詞,具有象征意義,表現無知天真的少年通過一堂課而獲得愛國觀念,完成從混沌向成熟的轉變。自1912年胡適譯出《最后一課》,這篇小說便在中國得到廣泛接受,李劼人指出“及至《新青年》雜志興起,提倡自然主義,介紹左拉、莫泊桑等人,胡適之先生所譯的《最后一課》更成為人眾皆知作品……”。[2]相同的歷史境遇是中國作者對《最后一課》仿擬的最根本原因。
然而中國作者在模擬這部小說時將整部小說敘事語調完全破壞了。在都德小說中,由一個無知頑童天真的目光觀照一切,故意在亡國慘痛中加入一種輕松敘事語調,形成作品的反語結構。與都德小說相反,中國作者用第三人稱敘事視角,使原作的反語結構蕩然無存。距離能產生美,都德在小說創作上以一種超然態度與事件拉開審美距離,用一種超然的反諷敘事語調來深刻反映重大題材。與之相反,中國作家強烈的責任感和沉重的憂患意識,使他們更傾向于直接廁身于事件之中,運用第三人稱敘事,直截了當地在作品中表達自己的觀點。誠然我們能感受到作者熾烈的愛國熱情,但這種小說沒有與現實拉開一定的距離,顯得過于直露而流于口號和觀念化,其審美價值反而有所下降。通過比較都德《最后一課》與中國仿作,我們感到了中西文化的差異,也感到中國文學需要處理好藝術與生活、道理與真實的關系。
三、都德與師陀、沈從文詩情小說
都德的小說詩情洋溢,是對生活印象的詩意感受,沒有自然主義嚴峻的觀察與寫實,醉心于鄉村世界的描繪和散文氣氛的營造,這使我們想起了中國作家師陀和沈從文。他們兩人都出生于悠閑、淳樸的鄉村世界,生活于原始自然社會,他們的人格處于一種無拘無束的狀態。而他們身外的世界卻正經歷著工業文明的巨變,城市文明正吞噬著鄉村文明。他們固守自己的傳統價值觀念,與都市格格不入。朱光潛這樣評論師陀:“雖然現在算是在大城市里落了籍,他究竟是‘外來人’,在他所丟開的窮鄉僻壤里,他才真正是‘土著戶’。他徒然插足在這光彩炫目、喧聒震耳的新世界里,不免覺得局促不安;回頭看他所丟開的充滿著憂喜記憶的舊世界,不能無留念,因為它具有牧歌風味的幽閑”。[4]城市文明對人性的壓抑和扭曲,使他們眷念著鄉村。“我最愛悅的一切還是存在,它們使我靈魂安寧……坐在房間里,我耳朵永遠響的是拉船人的聲音,狗叫聲,牛角的聲音。”[5]然而,他們筆下的原始田野牧歌被工業文明所取代已是歷史的必然,他們所醉心的已屬過去時代。都德與師陀、沈從文敏感于社會對人性的異化,在作品中表達了對自然、原始的傾心,對純情鄉間的傾心。我們看到了他們對人生的關切,正是這種共同的精神追求,在都德與師陀、沈從文之間架起了溝通的橋,他們相似的藝術風格表現出了對人類命運的深刻思索。他們“將想象中的理想社會作為衡量整個外部文明的標準和道德尺度,以此與城市生活形成鮮明的對照。”[6]
四、結語
考察都德在中國的譯介、傳播與接受,會給我們帶來有意義的啟示。都德被中國讀者接納與中國當時的歷史背景、社會環境密切相關。在中國的民族矛盾尖銳的時期,中國讀者從愛國主義這一角度選擇了都德,這種單一的接受模式一直延續下來。隨著社會歷史背景的變化,人們更注重文學作品本身的審美價值、文學價值。從共時角度來看,不同人群的期待視野是不同的;從歷時角度來看,不同時期人們的期待視野也是不同的。當代翻譯理論研究認為,翻譯受到意識形態、當時的主流詩學和贊助人的左右。在時代的大潮中,普通讀者對翻譯過來的外國作家的接受往往帶有時代背景的印記,難免是片面的,不全面的,而忽視了本該引起我們重視的方面。那么,應該如何盡可能地避免這樣的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1]胡 適.論短篇小說[A].胡適譯短篇小說[C].長沙:岳麓書社,1987.
[2]李劼人.《小東西》改譯后細說由來[A].小東西[C].重慶:作家書屋,1934.
[3]邵燕祥.伴我少年時[J].外國文學評論,1992(02):127-129.
[4]劉增杰.師陀研究資料[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5]沈從文.生命的沫題記[J].現代文學,1930(01)(創刊號).
[6]唐玉清.“湘西”與“普羅旺斯”——沈從文和都德的理想世界[J].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01):60.
Translation,Communication and Acceptance of Daudet in China
CAO Wen-g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Huaibei Anhui,235000)
Daudet was very popular in China.Hu Shi translated Daudet's works to develop Chinese short novels while Mandarin Duck and Butterfly School emphasized literature interest in translation.Daudet's defiance to the Naturalism was accepted in 1920s.Chinese readers chose hi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triotism in 1930s.In new period,Daudet was not so popular.Chinese novels imitating Daudet'sThe Last Lessonwere very close to reality,so their artistic appeal declined.Daudet,Shi Tuo,and Shen Congwen's poetic novels were all keen on unsophisticated village and primitive society,reflecting their common spirit pursuit toward man's fate.
Daudet;Chinese readers;naturalism;The Last Lesson;poetic novels;patriotism
I1/7
A
1674-0882(2016)02-0048-03
2015-12-11
曹文剛(1971-),男,安徽六安人,碩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較文學、翻譯研究。
〔責任編輯 裴興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