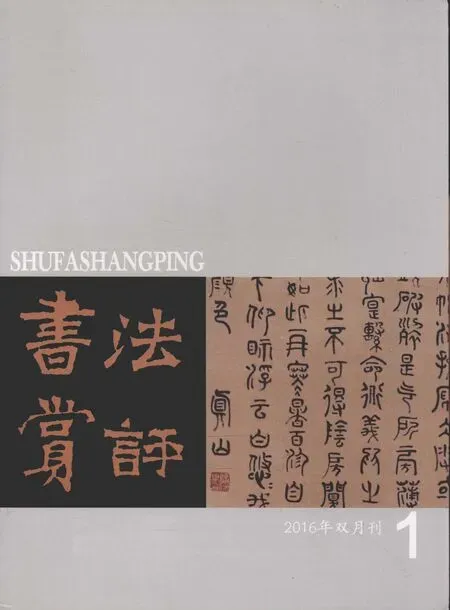魏晉時代非 “尚韻”發微
——對索靖 《草書勢》之 “勢”的思考
■李 松
魏晉時代非 “尚韻”發微
——對索靖 《草書勢》之 “勢”的思考
■李松
引言
“銀鉤蠆尾”是索靖對于自己書法字勢的評價,其傳世書論 《草書勢》在 《書苑菁華》中雖然名為 《索靖敘草書勢》,《墨池篇》作 《書勢》,而在 《晉書·索靖傳》之中,卻名為 《草書狀》。在其書論中,從邏輯理念觀之,“狀”的敘述更為明顯。這樣,就出現了 “勢”與 “狀”的不同。
“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1]
概言之意,為描述草書之狀,或者稱之為形狀更加合適。索靖將草書形容為銀鉤、驚鸞,與同時代上下許多書法理論遙相呼應。衛恒 《四體書勢》中關于古文字勢、隸書贊云:
“撅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辰,郁若云布。”[2]相比之下,衛恒顯得更加具體而微。但是,二者之間的共性還是較為突出:首先,跟中國古代書法理論一樣,都是相關性聯想,既體現出對象的可感知,又有生動想象;其次,邏輯性不強,且不需要論證,值得一提的是:其對于變化感敘述清晰,這卻是現代書法理論所欠缺的。因為即使是現代西方許多經典藝術理論,都在注重邏輯推理同時,不可避免的陷入變化的前后牽掛,絕少感性的通感式比況。從這個角度上說,中國古代書法理論,反而更有理解上的先入為主和可感性。
也是因為這樣,許多人認為中國書法理論,特別是古代書論往往是只言片語的感悟式述說。但是,這一樣難以掩蓋古代書論的偉大和精深!縱觀中國古代書法理論史,自趙壹 《非草書》,到康有為 《廣藝舟雙楫》都是如此。
一
《草書勢》始曰:
“圣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是為。蝌斗鳥篆,類物象形,睿哲變通,意巧滋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修,事業并麗。”[3]
開篇即以造字法為例,倉頡造字,無論蝌斗還是鳥篆都畫成其形,這形之中含有 “意”與 “巧”。“意”其實暗含意味深長,與宋代 “尚意”書風相合;亦或是宋代 “尚意”書風的最早論述,只是在早期書法思考中,理論性總結不夠完備。只是說,當時更加質樸,并未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反之,而 “巧”——無論技巧——藝術思想之巧思——直到現當代為止,一直是書法藝術追求的目標。但是,盡管書法技法隨著時代變遷愈加復雜和巧妙,書寫漢字字形卻變得簡化,也就是崇簡。無論是漢字發展史還是書法發展史,都是如此。這不能不是心靈的力量:
“人類有心之作用,能選擇發動情而統御之,這種心之作用叫做 ‘慮’,能運用心之作用的力量叫做‘能’”[4]
所以,索靖——“勢”——之理論從更大程度上可以理解為 “狀”更加合理。
“蓋草書之為狀也、、、、、、玄熊對踞于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4]
有趣的是:這里既有動態之勢,又有靜態之狀。動靜交叉,宛若書法創作,形成理論敘述與作品創作相互交織。只是二者中前為書法作品,后者為理論見解。那么,這種兩相交織在古代書家看來,似乎并不是不同。我們也更有理由相信:書法作品只有一件,其余皆為刻石或他者臨摹;而理論除了一件親筆書寫作品外,還有別人傳抄過去的理論文字。當然,到底是 “勢”重要,還是 “狀”更加重要?卻成為后代書家思考的命題。“銀鉤”與 “驚鸞”在舒翼與若舉中又體現出 “未發”、“復安”,顯然索靖更體會出動靜結合之美。接著依此類比,將蟲蛇與虯蟉比附為婀娜、桓桓;再推為 “逸游盼向”、“乍正乍邪”,讓讀者頭腦中出現極其豐富多姿的畫面。無疑,這是 “狀”之描摹。緊接著 “勢”出現:“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超凡想象力可見一斑。
由此上溯,漢代藝術總體卻是以 “尚勢”為主。無論是漢賦、詩歌、舞蹈、音樂,都幾乎一致以氣勢雄渾、宏闊博大為主要特色。在書法方面亦是如此。只不過,由于時代原因,漢代書法以篆隸且主要是以隸書為重。國力強盛導致文學藝術以陽剛之美為尚,隸書是漢代的主要書體,許多漢代隸書代表作如 《曹全碑》《禮器碑》《華山碑》《張遷碑》都早已經成為后代學習傳統書法之經典。
“隸體的書寫進一步激活了書家的感情機制,不同性情的驅動不僅產生了豐富多樣的書體,而且強化了書家對運筆結體的 “勢”的關注,把書法作為一種審美形式,著重表述它的審美效果。”[6]
但是,索靖畢竟是西晉時代,與兩漢的審美觀已經不同。
二
可以肯定的是:東漢崔瑗 《草書勢》是迄今所證明的最早的書法理論,其對于 “勢”之論述在古典書法美學思想中最值得關注。而且,論述與其時代風尚暗合。華人德先生對 “勢”的定義為:
章草書不同于后世的今草,尤其是大草的連綿飛舞,其最大的特征,也是最重要的關鍵是持引不發,似斷還連,靜中寓動,蓄而后泄,這就是草書的 “勢”。[7]
這樣,就出現了一個有意思的話題:后來者索靖 《草書勢》與前者崔瑗 《草書勢》是否為深化,或者是對于前者的補充。這個問題在書法理論史上有著先例:如姜夔 《續書譜》就是對前者孫過庭 《書譜》的補充與創新。除卻這些,還有值得關注的是書寫最多的 《論書》,僅僅下面例表中就有七部,還沒有包括另一些題目略微不同,而意義相近的篇目。比如陶弘景 《論書啟》,吾衍 《論篆書》,翁振翼 《論書近言》等等。“勢”在歷代書論中卻逐漸出現弱化現象,
索靖本身亦是草書家,劉濤先生將其理論名為 《草書狀》,論述為:
他用賦體寫過一篇 《草書狀》,極力贊美草書,其中文句也觸及技法原理。反映了索靖的草書理念,同樣包含著書家的書法經驗。[8]
問題是對于 “勢”的真正理解,在魏晉時代并沒有得到垂范。雖說許多書家認為論述篇章之中,皆言為 “勢”,而未及 “書法”。如果說,中國古代書法一開始并沒有叫做 “法”,那么我們有理由找到個相關稱呼。于是,最先進入視野的應該可能就是 “勢”。這個問題早已經引起了注意,但這似乎帶來了疑點。在篆書、隸書之前的古文字時期,雖然書寫工具不是毛筆,還是有草書的形式出現。例如草篆、草隸等非正式書寫形式。不過因為不夠正式和存在于鼎、玉器、石頭、摩崖等物質之上,給后世帶來尋找和研究的困難。
唐耕馀先生 《<筆陣圖>蜉化階段及其內容》曾指出:
古人未講 “書法”以前,先有 “書勢”。衛恒、索靖雖講書勢而不言法。書勢者,書論之起點,亦為形成字體之初步,更為用筆原始之動機。[9]
勢經萬古而長存,何論于時代。造語之先后,而勢之位說,遠在漢則無可疑,此則論書之最古也。[10]書家作書,無不有勢,無勢即不純。[11]
事實上,這個結論無論正確與否,都值得一讀。當然,把 “勢”作為書法之前的一種概念雖說無法定論,但是直到現在都無法證明其有失。那么,值得思考的是:先秦兩漢在書法藝術理論產生同時,書家或者是書寫者到底用什么概念作為最初的定義。這時,書法即使最初稱之為書勢,在這之前,應該還有一個或者多個命題。只是說,在有限的書法出土和傳世書論中,還有許多值得后代書家考證之處。當然,如果以 《非草書》作為書法理論的開篇作,那么這個說法就可以成立。
如果將中國歷史再往前推1000多年,中國古代文明一樣有著文字,那時的書法理論應該存在,而且并不是以書法之 “法”或者書法之 “勢”存在。因此,即使康有為也曾經提出 “古人書論以勢為先”,依然絕非的論!
三
吊詭的是:晉 “尚韻”之論斷一出,幾乎讓所有人只注意到 “二王”書風中的 “韻”之美。尚法、尚意、尚態似乎只是當時的副產品,他們置于后世的唐、宋、明清時代。 “勢”——這個出現更早的書法現象卻似乎消失,或者說是被人客觀遺忘。事實上,從書寫形制和表現材質視角分析:這類把玩在手的書寫形式 “手卷”“尺牘”“手札”似乎后來居上,成為后來書家研究魏晉時代書法的主流。但是,不應該忽視魏晉時代一樣有著大幅作品,包括題署、對聯、榜書等等,甚至題壁書法。[12]可悲的是后者隨著歲月與歷史變遷而消失殆盡,成為可以想象卻沒有實物存在的書法形式。
而遠距離觀看和欣賞的書法作品遭到忽視,其實帶來了書法理論研究之不全!
我們又在讀 《草書勢》后面部分:
“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體磊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璀璨。”[13]
索靖在這里還是繼承以往書法理論的寫作方式,采用排比的駢文文學形式,僅僅是文字就形成一種 “勢”的意味。但是,在這種 “狀”的敘述之中,出現二者也就是 “勢”與 “狀”的混合。在借助于 “玄學”“文學”背景下,書學理論并未實現超越。這就帶來 “韻”與 “勢” “狀”的某種契合,遺憾的是這種契合我們并沒有注意到。當然,聯系歷史過程,盛極而衰的兩漢時代,到了戰亂頻繁的末期以及朝代更替的魏晉時代,書法審美變化與時代變化驚人相似。因此,由 “勢” “狀”直接到 “韻”就可以理解。
最后一句為:
“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回其腕,著絕勢于紈素,垂百世之殊觀。”[14]
顯然,其文并不完整。由于時代久遠,出現流傳的偏差和一些缺憾,在書法理論史上其實也是正常現象。但是,以此類比,也可以看到 《草書勢》闡釋的 “非尚韻”傾向明顯,又再觀索靖代表作品 《月儀帖》《出師頌》《七月帖》等等,章草書法的古法濃厚、典雅、氣息神秘。
小結
魏晉書法作為對于兩漢書法的發展,在隸書繼承中實現超越。毋庸置疑,無論是禁碑還是書寫隸書活動減少,都帶來新的變化。顯然,索靖 《草書勢》與前人眼中之 “勢”不同,開啟后來者 “韻”之審美追求。不過索靖書法作品章草意味與今草大不一樣,對于今草的啟發也值得研究。出現 《草書狀》的名稱也可以理解,而且在文字中,其排比、駢文形式與前代并沒有本質差別。甚至可以說,這種文體形式在漫長歷史中影響深遠。
當然,我們對于兩漢書法既不能以 “尚勢”作為定論,也不排除魏晉時代除去 “尚韻”之外, “勢”作為書學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依然存在。那么,在現當代書法看來,展廳書法占據主流,書法主流或者說以 “尚勢”作為重要命題,以期對于以往 “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態、清尚樸”之后,對于現當代及其以后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提出 “尚勢”,再次吶喊草書時代來臨。
無疑,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命題,也值得期待!
注釋:
[1]索靖 《草書勢》,選自 《歷代書法論文選》,黃簡,上海書畫出版社,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2012年版,19頁。
[2]衛恒 《四體書勢》,選自 《歷代書法論文選》,黃簡,上海書畫出版社,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2012年版,15頁。
[3]索靖 《草書勢》,選自 《歷代書法論文選》,黃簡,上海書畫出版社,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2012年版,19頁。
[4][日]赤忠等,《中國古代文化史》,東京都:研文社,1988年版,89頁。
[5]索靖 《草書勢》,選自 《歷代書法論文選》,黃簡,上海書畫出版社,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2012年版,19—20頁。
[6]陳方既、雷志雄 《書法美學思想史》,河南美術出版社,1994年版 ,88頁
[7]華人德 《中國書法史·兩漢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199頁
[8]劉濤 《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313頁
[9]《書法叢刊》,2000年第四期。“蜉”當作 “孵”
[10]同上
[11]同上
[12]侯開嘉 《中國書法史新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77—90頁
[13]索靖 《草書勢》,選自 《歷代書法論文選》,黃簡,上海書畫出版社,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2012年版,20頁
[14]同上
作者單位:河北美術學院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