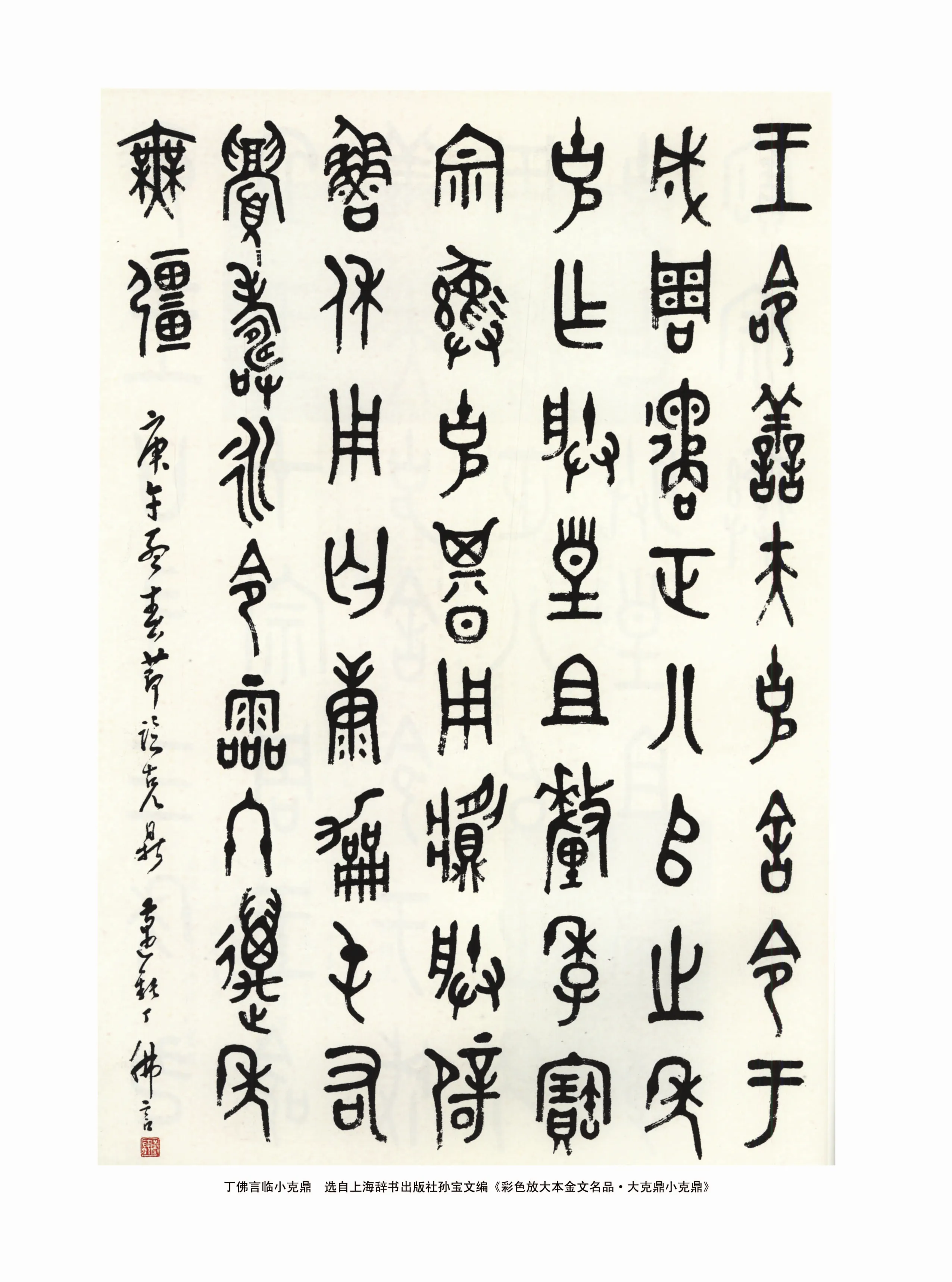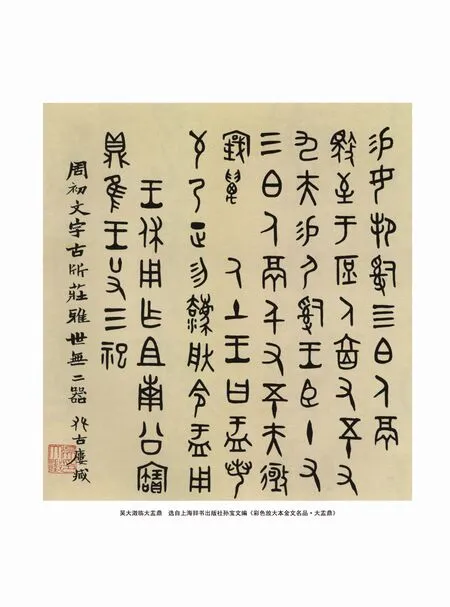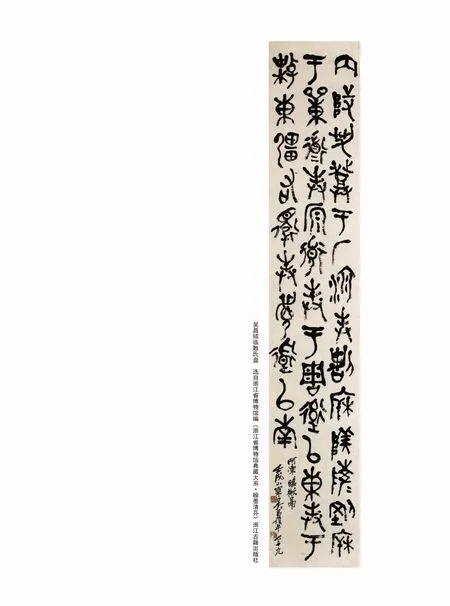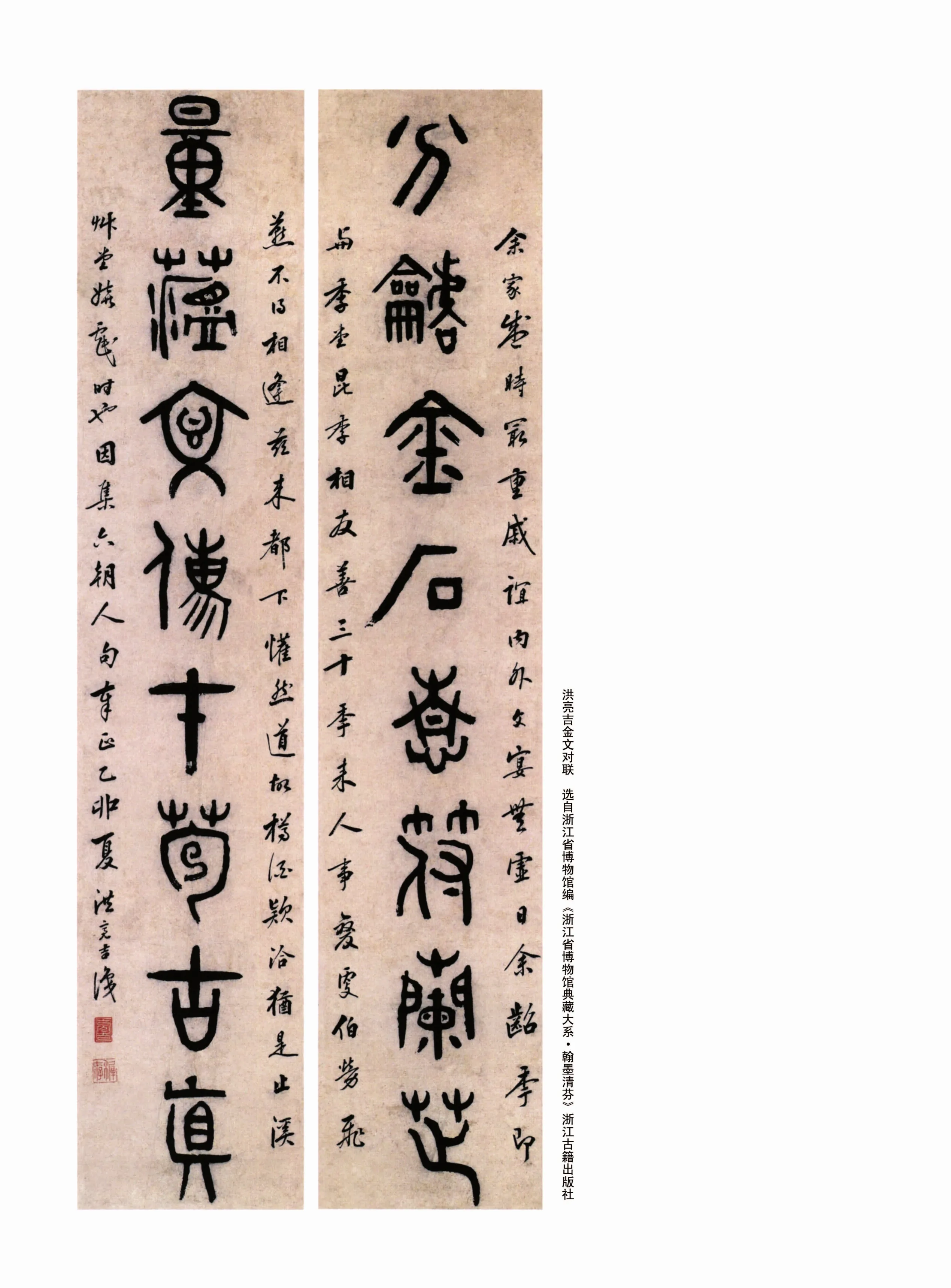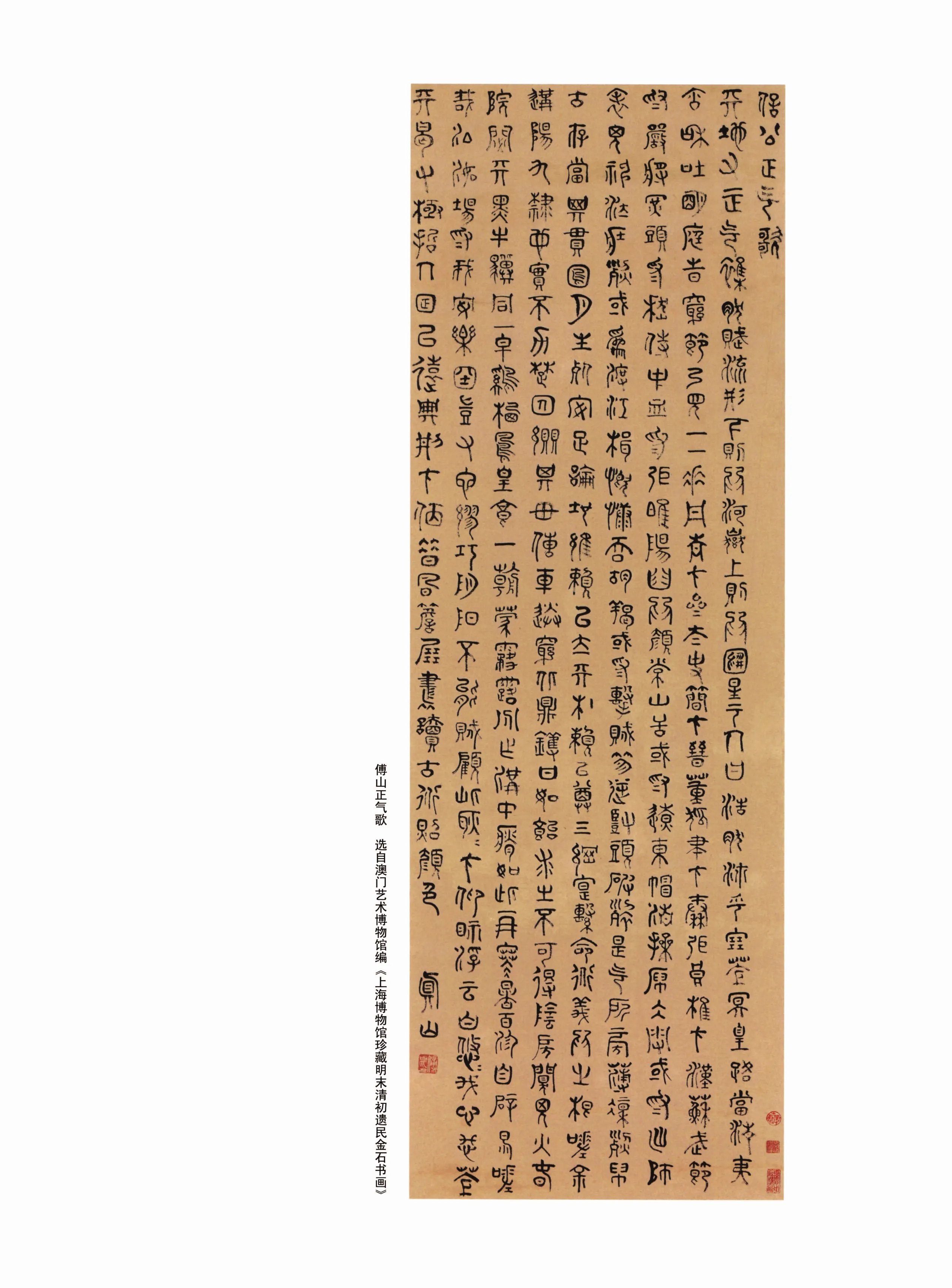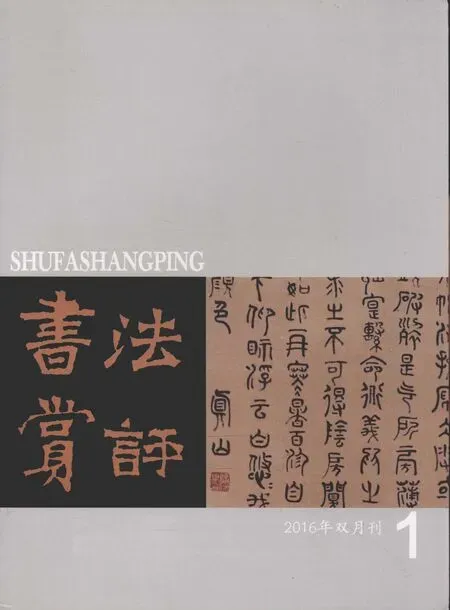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以后:以權(quán)威鑒定家為主導(dǎo)的書畫鑒定流派的形成
■林 如
書畫鑒藏
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以后:以權(quán)威鑒定家為主導(dǎo)的書畫鑒定流派的形成
■林如
中國書畫鑒定觀念在當(dāng)代轉(zhuǎn)型的第二個時期的表現(xiàn)特征,是形成了以權(quán)威鑒定家為主導(dǎo)的書畫鑒定流派。
從上世紀(jì)八九十年代至今,書畫文物市場極為活躍,書畫文物在市場上的價格不斷飚升就是一個重要的表現(xiàn)。書畫文物的價格除了決定于其本身的年代、數(shù)量、藝術(shù)水平以外,還與國內(nèi)的經(jīng)濟發(fā)展?fàn)顩r等密切相關(guān)。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也在市場活動中充當(dāng)了重要角色,那就是鑒定家。在還沒有發(fā)明一種可以完全充當(dāng)鑒定文物真?zhèn)蔚目茖W(xué)儀器以前,鑒定家的判斷就是唯一相對可信的結(jié)論。也可以說,鑒定家操縱著書畫文物的生殺大權(quán)。如今的書畫文物收藏家或經(jīng)營者都明白,他們手中的書畫文物只要擁有一紙鑒定家的鑒定書,便如同吃了一顆定心丸,而若有權(quán)威鑒定家的鑒定書,書畫文物立刻身價百倍。可見,鑒定家在整個書畫文物領(lǐng)域的影響不容小覷,尤其是當(dāng)代的權(quán)威鑒定家,他們的地位更是舉足輕重。
論當(dāng)代書畫鑒定界最具影響力的權(quán)威鑒定家,我們可以列出一批耳熟能詳?shù)摹㈨懏?dāng)當(dāng)?shù)拿郑簡⒐Α⒅x稚柳、徐邦達(dá)、劉九庵、傅熹年、楊仁愷……他們對歷代書畫的真?zhèn)舞b定結(jié)論無疑是書畫鑒定界的標(biāo)桿。隨著學(xué)者們對書畫鑒定理論的關(guān)注和深入研究,這些被人們所公認(rèn)的當(dāng)代書畫鑒定界的大師們,他們獨特的鑒定方法、鑒定思想、鑒定理論為我們提供了學(xué)習(xí)書畫鑒定的門徑,也為理論家們開拓了廣闊的書畫鑒定思想研究的領(lǐng)域。
在思想開放,各種學(xué)術(shù)理念、研究方法百花齊放的當(dāng)代學(xué)術(shù)界,流派的形成與其所產(chǎn)生的巨大影響力是一種必然,書畫鑒定學(xué)界也不例外。當(dāng)然,書畫鑒定學(xué)派的形成不是憑空而來,它經(jīng)過了二十世紀(jì)六十年代以后對書畫鑒定理論研究的積累,包括張珩最早的書畫鑒定概論性的研究著作,緊接著是謝稚柳的 《論書畫鑒別》、徐邦達(dá) 《古書畫鑒定概論》、王以坤 《書畫鑒定簡述》等,更有他們對具體書畫作品的真?zhèn)窝芯俊⑻接憽3龂椅奈镨b定小組的幾位成員以外,還有象郭沫若、張伯駒、徐森玉等國學(xué)家與文物鑒藏家的參與。在長達(dá)幾十年的鑒定學(xué)術(shù)研究和辯論當(dāng)中,一些具有鮮明個性鑒定風(fēng)格的鑒定家逐漸脫穎而出,進入我們的視野,他們在書畫鑒定界的特殊地位也逐漸顯現(xiàn)出來。可以說,沒有之前對書畫鑒定的研究歷程和研究成果的積累沉淀,以鑒定方法的不同特征而形成的書畫鑒定幾大流派就不會逐漸清晰地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目前,已經(jīng)有學(xué)者根據(jù)當(dāng)代幾位權(quán)威書畫鑒定家鑒定方法的不同,提出了代表當(dāng)代書畫鑒定領(lǐng)域的幾大鑒定流派。如以謝稚柳為代表的藝術(shù)鑒定學(xué)派;以徐邦達(dá)為代表的技術(shù)鑒定學(xué)派;以啟功為代表的學(xué)術(shù)鑒定學(xué)派等等,對鑒定家們旗幟鮮明的鑒定方法進行了比較合理的概括。[1]那么,當(dāng)代鑒定學(xué)派是如何產(chǎn)生的,它有著怎樣的契機?幾大鑒定學(xué)派的研究特色以及所帶來的影響如何?
一個學(xué)派的產(chǎn)生,需要經(jīng)過學(xué)者在某個領(lǐng)域幾十年堅持不懈地研究、積累,甚至需要幾代人付出艱辛的探索和努力。上世紀(jì)八十年代以后逐漸形成公認(rèn)的以謝稚柳、啟功、徐邦達(dá)等為代表的幾大鑒定學(xué)派,當(dāng)然也不是憑空而來,其中包含了 “天時”“地利”“人和”等多種因素在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首先是時代政策的因素。國家在承傳文化方面所必須做的重要工作,就是對古代的文化遺產(chǎn)進行搜求并加以整理和保護。新中國成立以后,政府對恢復(fù)文物事業(yè)非常重視,從二十世紀(jì)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國家文物機關(guān)開始從全國各地大力收購書畫文物,今天各大博物館的藏品,大多是解放后由民間征集而來。政府除了從藏家手中購買古書畫以外,并委派負(fù)責(zé)征集工作的專家們四處探訪、聯(lián)絡(luò)、游說,鼓勵藏家們捐贈所藏書畫文物,也有許多書畫文物收藏家出于愛國熱忱,競相將藏品捐獻給國家。如國家文物局委派徐森玉、謝稚柳收購了著名的上海龐氏虛齋所藏大批書畫;蘇州 “過云樓”顧氏,于二十世紀(jì)五十年代兩次捐獻古書畫藏品約三百來件,現(xiàn)藏上海博物館等等。各地文博單位收藏的書畫不斷增加,對古書畫的鑒定工作被日益推上日程,突飛猛進的形勢發(fā)展,需要有一流的鑒定家來從事這項繁復(fù)而艱巨的任務(wù),為國家的文物收藏、保護保駕護航。作為時代與政策的需要,高級別、高水平的權(quán)威鑒定家呼之欲出。
其次是書畫文物買賣的推動。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后,經(jīng)濟迅速發(fā)展。隨著市場的開放,文物交易也隨之興旺起來。國內(nèi)的書畫交易從八、九十年代開始,到上世紀(jì)末本世紀(jì)初,是一浪高過一浪,書畫拍賣熱一路高漲。除了國內(nèi)的買賣交易,還發(fā)展到國際間的買賣流通。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的書畫文物交易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政府指定單位如文物商店、博物館與國內(nèi)私人藏家的交易,主要是政府向民間收藏家收購書畫藏品;二是政府指定單位與國外收藏家的交易,主要是向國外收藏家出售或購回一部分書畫藏品。尤其是八十年代國內(nèi)經(jīng)濟剛剛起步,需要與國際市場進行交流接軌,國家政策允許有一部份書畫文物在國際市場流通,但是,文物法又規(guī)定重點保護文物是不允許流出國門的。因此,必須要有嚴(yán)格地把關(guān),更需要有一批鑒定家為書畫文物作真?zhèn)渭暗燃夎b定。鑒定是書畫交易以及出境許可的保障,長期的實戰(zhàn)經(jīng)驗使專業(yè)鑒定家脫穎而出,鑒定家的地位與權(quán)威同時也在書畫交易的實踐當(dāng)中逐漸樹立起來,并具有相當(dāng)?shù)挠绊懥Γ瑸槌蔀闄?quán)威級的鑒定家、為鑒定流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礎(chǔ)。
而真正確立書畫鑒定家權(quán)威地位并促使當(dāng)代幾大書畫鑒定流派形成的較為直接的原因,是八十年代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的成立和隨后的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的成立,它把一批權(quán)威鑒定家推上了一個難以撼動的崇高地位。1983年6月,經(jīng)中宣部批準(zhǔn),由文化部文物局成立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其目的和作用有四:一是查考全國各文物文化教育機關(guān)團體所存歷代書畫的情形;二是協(xié)助各單位鑒定藏品,分出精粗真?zhèn)危蝗菍Σ糠炙饺瞬仄疯b別評定;四是由此而鑒定出書畫的真?zhèn)巍⒌燃壗Y(jié)論,從而更有利于文物保護,為美術(shù)研究者提供豐富材料,提高其研究的科學(xué)性。并擬通過此舉培養(yǎng)出一部分中青年專業(yè)人員,建立起專業(yè)的書畫鑒定隊伍。
8月,在北京召開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成立大會。鑒定組由七人組成,謝稚柳任組長,組員啟功、徐邦達(dá)、楊仁愷、劉九庵、傅熹年、謝辰生。[2]其實,早在1962年,國家文物局就曾組成中國書畫鑒定組,對全國各地所藏中國古代書畫作全面系統(tǒng)地鑒定。當(dāng)時的鑒定組成員即有:張珩、謝稚柳、韓慎先。后由于韓慎先在北京病逝,增補故宮博物院劉九庵為成員。1964年,張珩病逝,謝稚柳、啟功、劉九庵又重新建組。六十年代組建的中國書畫鑒定組,曾經(jīng)在天津、黑龍江、遼寧、重慶、四川等省市巡回鑒定古書畫達(dá)萬余軸。但是后來由于文革十年動亂,鑒定工作被迫中斷,沒有一直延續(xù)下去。而從1983年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恢復(fù)工作以來,書畫鑒定組成員對北京、上海、浙江、江蘇、安徽等全國各大博物館各單位收藏共幾萬件書畫進行拉網(wǎng)式的調(diào)查、鑒定、分等級、著錄,范圍之廣、力度之大,在全國范圍影響巨大。正如謝稚柳先生所說:“這個書畫鑒定小組的成員都是中國第一流書畫鑒定專家。不但在國內(nèi),而且在全世界都具有權(quán)威性。”[3]至此,具有國家級水平的幾位權(quán)威鑒定家的地位得到了真正確立。
在全國的巡回鑒定過程中,鑒定小組成員對書畫的真?zhèn)舞b定有時會有一致性意見,有時也產(chǎn)生了一些分歧。比如對王羲之的 《上虞帖》、張旭的 《古詩四帖》的真?zhèn)魏湍甏鷨栴},都有不同的看法,鑒定家們不但各持己見互不相讓,還各自撰文進行激烈地探討。正是從這些爭論當(dāng)中,逐漸顯現(xiàn)了他們各自不同的鑒定風(fēng)格和鑒定方法。他們的這些各具特色的鑒定方法和鑒定理論也成為后人學(xué)習(xí)和借鑒的經(jīng)典范式,他們的努力為各自的鑒定學(xué)派的形成做出了極好的鋪墊。因此,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的成立可以說是鑒定學(xué)派形成的一個重要契機。
從幾大鑒定家在全國巡回書畫鑒定工作過程中、在一些古書畫的真?zhèn)渭澳甏鷨栴}的爭論中所舉的看法和理由來看,他們都有各自所注重的、極具特色的鑒定方法與風(fēng)格。將這些不同的鑒定風(fēng)格和鑒定方法相比較分析,應(yīng)該可以歸納出當(dāng)代書畫鑒定界幾個以權(quán)威鑒定家為代表的風(fēng)格鮮明的鑒定學(xué)派。即:以謝稚柳為代表的筆法風(fēng)格分析鑒定學(xué)派;以啟功為代表的文史考證鑒定學(xué)派;以傅熹年為代表的器物圖像考證鑒定學(xué)派;以徐邦達(dá)為代表的技術(shù)經(jīng)驗加著錄鑒定學(xué)派。我們試對這幾大鑒定學(xué)派代表人物的鑒定風(fēng)格和鑒定方法的形成、特色和影響作具體分析,并以此來研究這幾大鑒定學(xué)派在當(dāng)代鑒定學(xué)界的地位。
二、以謝稚柳為代表的筆墨風(fēng)格分析鑒定學(xué)派
在國家文物局古代書畫鑒定組成員中,謝稚柳名列首席。這不僅僅是因為他是解放后與張珩、韓慎先同時成為第一代專家的少數(shù)書畫鑒定家之一,也并不僅僅因為他在文革結(jié)束后倡導(dǎo)恢復(fù)中國書畫鑒定小組,并對全國各大文物單位的書畫進行巡回鑒定,對文物的整理和保護作出了至關(guān)重要的貢獻。更為重要的是他的鑒定成果的可靠性、鑒定方法的獨特性在書畫文物收藏界、鑒定界樹立起了無可置疑的權(quán)威。并且,以他為旗幟,在書畫鑒定界形成了一個特色鮮明的書畫鑒定流派——筆墨風(fēng)格分析鑒定學(xué)派。我們試對謝稚柳鑒定方法的形成、特征與影響作一分析,以期對這位叱咤風(fēng)云的當(dāng)代書畫鑒定大師有一深入認(rèn)識和準(zhǔn)確評價。能夠成為書畫鑒定家的途徑一般有幾種:一是從愛好書畫的收藏家,不斷買字畫,買經(jīng)驗而走上鑒定之路。二是買賣文物的商人,在經(jīng)營字畫的過程當(dāng)中,積累了大量的經(jīng)驗而成為鑒定家。前兩類鑒定家一般注重作品的形式、題款、印章、紙絹材料、著錄等依據(jù)。三是學(xué)問家介入書畫鑒定,把書畫鑒定作為一門學(xué)問來做。這類學(xué)者出身的鑒定家,一般重在對文獻的考訂。四是從學(xué)畫、繪畫創(chuàng)作研究轉(zhuǎn)而成為鑒定家。謝稚柳無疑屬于第四種。
謝稚柳自己曾談道:
“我當(dāng)初并不是為學(xué)鑒定而去看畫的,主要是想學(xué)習(xí)繪畫而開始研究古人的真跡。從那時候起就成了一個習(xí)慣,一有機會看真跡,就絕不會放過,而且必定一絲不茍。”[4]
因此,書畫創(chuàng)作家出身的書畫鑒定家研究鑒定的著眼點,必然是與書畫創(chuàng)作相關(guān)的幾個點,即筆墨、風(fēng)格。個人的經(jīng)歷不同,知識結(jié)構(gòu)背景不同,鑒定方法也會有所不同。謝稚柳筆墨風(fēng)格分析鑒定學(xué)派的形成,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特點。
筆墨風(fēng)格分析鑒定方法的形成,是與謝稚柳的藝術(shù)經(jīng)歷和知識結(jié)構(gòu)背景有著必然的聯(lián)系。謝稚柳的書畫創(chuàng)作經(jīng)歷為他強調(diào)以筆墨風(fēng)格分析為主的鑒定方法打下基礎(chǔ)。
謝稚柳出生在有著深厚文化背景的家庭中,父輩與長兄皆博才多學(xué)、風(fēng)雅好古。在這種家學(xué)的熏陶之下,謝稚柳從小就流露出對詩、書、畫的極大的熱情。這給他后來的書畫創(chuàng)作鋪下了路子。謝稚柳十六歲迷上了陳老蓮的書畫,從此鐘情花鳥,扎根在陳老蓮,對陳老蓮的畫風(fēng)、繪畫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取其筆墨神理,在實踐上打下了深厚的基礎(chǔ)。后來,他又對兩宋繪畫產(chǎn)生了興趣,花鳥畫追蹤宣和體,但是在對兩宋院體畫的研究中又加入了自己對筆墨的理解,取其風(fēng)神,別具一格。謝稚柳的山水畫推崇江南畫派,對江南畫派的風(fēng)格傳承、筆墨特色追蹤探索,最早從巨然入手,追溯到董源,又學(xué)王詵、范寬、郭熙、燕文貴,后來又由五代繪畫至宋并逐及元四家。通過不斷地臨摹體會,對各家的用筆、用墨、風(fēng)格形式由表及里、由點及面,了然于心。謝稚柳晚年研究 “落墨法”,通過對作品筆性、筆法、墨法的研究和實踐,證明了徐熙 《雪竹圖》的可靠性。正是由于謝稚柳本人對唐、五代、宋元繪畫的愛好、關(guān)注以及他創(chuàng)作的經(jīng)歷、經(jīng)驗,對他后來在鑒定學(xué)中擅長以筆墨、風(fēng)格形式為著眼點分析辨別唐宋書畫的真?zhèn)纹鹬鴽Q定性的作用。
其次,謝稚柳的敦煌之旅使他對繪畫的源流、時代風(fēng)格的傳承有了更為深刻的體會,為書畫鑒定方法提供了新的依據(jù)。
上世紀(jì)四十年代,謝稚柳與張大千曾一同在敦煌,對敦煌壁畫進行觀摩考察。與張大千著重臨摹壁畫不同,謝稚柳把研究重點放在對每個佛窟的測量、記錄、考證上,對壁畫風(fēng)格的差異、來源進行比較,并整理成了 《敦煌藝術(shù)敘錄》一書。通過考察研究,對中國歷代繪畫風(fēng)格的整體演變過程以及特點有了深刻的理解,確立了繪畫的時代性,為繪畫史的分期確立了坐標(biāo)。對敦煌壁畫的研究不僅為原有中國繪畫史的研究添上了濃重的一筆,并且對繪畫鑒定研究中以個性與時代性為鑒定書畫的重要內(nèi)容提供了依據(jù)。正如薛永年教授的評價:
“不僅 《敦煌藝術(shù)敘錄》是我國學(xué)者研究敦煌藝術(shù)的開山之作,而且謝先生還是很早就用石窟壁畫與卷軸畫互相參證以說明繪畫源流及其時代的先行者。他對于唐代興起的水墨畫及其源流派別的精辟論述,既清晰地理出了美術(shù)史發(fā)展的線索脈絡(luò),又為鑒定書畫者認(rèn)識時代性與個性的關(guān)系指示了門徑。”[5]
可見,敦煌之旅對他以時代風(fēng)格與個人風(fēng)格分析為主的鑒定方法的形成有至關(guān)重要的影響。
筆墨風(fēng)格分析鑒定方法的形成,還和謝稚柳與畫家鑒藏家的交游有著重要關(guān)系。
為謝稚柳以筆墨風(fēng)格形式為主的鑒定方法打下堅實基礎(chǔ)的,除了他本身的學(xué)習(xí)創(chuàng)作經(jīng)歷以外,還和他與吳湖帆、張大千、徐悲鴻、于右任、沈尹默等優(yōu)秀畫家的交往有關(guān)。吳湖帆、張大千、徐悲鴻等不僅是偉大的創(chuàng)作家,他們還都是著名的收藏家和鑒定家,只是收藏家和鑒定家的名聲被他們的畫名所掩蓋而已。與吳、張、徐等人的交往,不僅對謝稚柳的創(chuàng)作帶來長足進展,也對他的鑒識眼光補益良深。并且他們經(jīng)常聚集在一起,評論自己最近的畫作,探討創(chuàng)作心得。同時,也對自己所收的藏品進行研究,評優(yōu)劣,判真?zhèn)巍漠嫾业囊暯莵砥吩u作品真?zhèn)蝺?yōu)劣,自然是注重對作品的時代風(fēng)格、個人風(fēng)格、筆墨特性的分析,這對謝稚柳后來的風(fēng)格分析鑒定學(xué)派的形成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與其他鑒定學(xué)派相比,謝稚柳的鑒定方法和觀念有著與眾不同的非常鮮明的特征,就是以書畫本身的筆墨特點、風(fēng)格形式的比較分析為最本質(zhì)的鑒定方法。他還特別指出,從印章、題跋、著錄、別字、款識等作為鑒別所依據(jù)的種種,其根本缺點在于拋開了書畫本身,而完全以利用書畫的外圍因素為主。
“鑒別的原理,是唯物辨證的,既然鑒別的是書畫,就不應(yīng)拋開書畫本身為它的先決條件,而聽任旁證來獨立作戰(zhàn)。不掌握書畫的內(nèi)部規(guī)律,反映書畫的本質(zhì),這個鑒別的方法所產(chǎn)生的結(jié)果,是書畫不可認(rèn)識論。”[6]
對書畫本身的認(rèn)識,他認(rèn)為:
“從古典書畫的筆墨、個性、流派等方面來認(rèn)識它的體貌與風(fēng)格,是完全從鑒別的角度出發(fā)的。”[7]
“畫法歷代都有發(fā)展和不同,使用這些畫法有不同的側(cè)重點和愛好,各個畫家有不同的風(fēng)格面貌。鑒定就是要了解、剖析其不同的風(fēng)格特點。每個鑒定者對于作品的某種技巧及精神內(nèi)涵各有不同的感受,但都可以加以歸納和保留。鑒定與欣賞的不同在于前者不單以審美上的好惡評判作品的高下,而是對作品進行仔細(xì)的考察、研究,并由此持久地保存對作品的理解和感受。反復(fù)地重溫感覺,在深入研究并形成感覺后,鑒定者就能獲得鑒定的基礎(chǔ)。在書畫鑒定中,形成感覺的基本因素有:筆墨、個性、流派和時代性。”[8]
對于以上謝稚柳的鑒定方法理論,我們可以從他在鑒定古書畫的具體實例中加以印證。
一是對張旭草書 《古詩四帖》的鑒定。經(jīng)過謝稚柳的研究,他贊同明代董其昌的觀點,認(rèn)為 《古詩四帖》為唐張旭真跡。并為此著文 《唐張旭草書<古詩四帖>》和 《宋黃山谷<諸上座帖>與張旭<古詩四帖>》,論證了他的判斷。他所憑借的論據(jù)就是:首先從筆法看,以典籍中所記張旭之筆法,他對董其昌所認(rèn)為的 《古詩四帖》與張旭所書 《煙條詩》《宛陵 (溪)詩》為同一筆法持贊同態(tài)度。看謝稚柳對此所作的分析:
“按歷來對張旭草書的敘說,如 《宣和書譜》所記:‘其草書雖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無一點劃不該規(guī)矩。’而杜甫的 《張旭草書歌》:‘鏘鏘鳴玉動,落落長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這些形容的詩句,‘玉動’指書勢的快慢有節(jié),‘松直’指風(fēng)骨蒼勁矯健,‘連山’指形態(tài)回旋起伏,‘溟漲’指筆力波瀾壯闊。
“以論這一卷 (按張旭 《古詩四帖》)的書體,在用筆上直立筆端逆折地使鋒埋在筆畫之中,波瀾不平的提按,抑揚頓挫的轉(zhuǎn)折,導(dǎo)致結(jié)體的動蕩多變。而腕的運轉(zhuǎn),從容舒展,疾徐有節(jié),如垂天鵬翼在乘風(fēng)回翔。以上述的一些論說來互相引證,都是異常親切的。
“董其昌提出的 《宛陵詩》與 《煙條詩》,在明詹景鳳 《東圖玄覽》中有明確的論述,他對 《宛陵詩》寫道:‘字大者如拳,小者徑寸……其筆法圓健,字勢飛動,迅疾之內(nèi),優(yōu)閑者在;豪縱之中,古雅者寓。以故落筆沈著,無張皇倉卒習(xí)氣,雖大小從心,而行款斐然不亂,非功夫天至烏能。’以這樣的敘說來引證這一卷的風(fēng)骨情采,真是如出一轍了。”[9]
其次是從張旭新的草書風(fēng)格對顏真卿、懷素、楊凝式、黃山谷等后學(xué)的影響來看,謝稚柳從黃山谷 《諸上座帖》的風(fēng)格中找出了與張旭 《古詩四帖》風(fēng)格的承接之處,從而證明了 《古詩四帖》確為張旭所書。在對 《古詩四帖》與懷素狂草 《自序帖》和顏真卿 《劉中使帖》筆勢結(jié)體的比較分析中,也非常具體地體現(xiàn)了謝稚柳以筆墨形式風(fēng)格分析為主的鑒定方法:
“從顏、素的法書來辨證與這一卷 (按:張旭 《古詩四帖》)的相互關(guān)系,似不失為探索張旭消息的另一途徑。懷素的筆跡,除一些簡短的書札而外,從能使人窺見全貌的狂草 《自序》卷,可以領(lǐng)略到那種細(xì)勁如鷺鷥般的風(fēng)格,與此卷是截然殊途,然而其中如 ‘五’字、‘煙’字則與此卷中的 ‘五’字、‘煙’字是同一結(jié)體,同一筆勢。而 ‘兩’字,是從這卷的 ‘南’字而來,至于筆勢,很多地方都與這卷脈絡(luò)相連,條貫相通,明確地顯示了兩者之間的淵源關(guān)系。而顏真卿行書,如 《祭侄文稿》也與此卷的形體不同。獨有 《劉中使帖》卻與 《祭侄文稿》情勢有別,它的特異之點在于運用的是逆筆如 ‘足’字,完全證實與此卷書勢之一脈相通。而在 ‘耳’字和 ‘又’字的起筆,與此卷中的 ‘難’字和 ‘老’字的起筆,不僅形體上,即在意態(tài)上也是完全一致的。這種形體和意態(tài),從未在晉唐之際的其他書體中見過。董其昌所援引的 《煙條詩》《宛陵詩》已絕跡人間,懷素 《自序》卷和顏真卿 《劉中使帖》從淵源而言,顯示了它追風(fēng)接武、血脈相連的關(guān)系,以之辨證此卷為張旭真筆,是唯一的實證。”10
最后從張旭草書的時代風(fēng)格特征來進一步論證其可靠性。謝稚柳提到:
“從晉唐以來的書體發(fā)展來看,這一卷的時代性,絕不是唐以前所有,而筆勢與形體,也不為晉以來所有。從王羲之一直到孫過庭的書風(fēng)都與這一卷大相懸殊,迥異其趣,這一流派的特征,在于逆折的筆勢所產(chǎn)生的奇氣橫溢的體態(tài),顯示了上下千載特立獨行的風(fēng)規(guī)。”[11]
我們看到,在以上所引征的三點判斷依據(jù)中,謝稚柳反復(fù)提到的就是筆法、風(fēng)格、形式。這里的筆法、風(fēng)格的淵源關(guān)系和時代風(fēng)格特征,就是謝稚柳在書畫鑒定中所倚重的書畫本身的內(nèi)容。它反映出畫家鑒定家審視書畫真?zhèn)蔚莫毺匾暯牵渤浞煮w現(xiàn)了謝稚柳與其他鑒定家所用鑒定方法的巨大差異。足以體現(xiàn)這種不同之處的典型實例,是曾有過關(guān)于張旭 《古詩四帖》真?zhèn)蔚闹x、啟之爭。啟功的鑒定方法注重的是文獻考證,根據(jù)文獻史籍中的記載,對帖中“丹”“絳”二字等等的考證,認(rèn)為此帖是宋人作品而非唐代張旭所作。從兩位最為權(quán)威的書畫鑒定專家對 《古詩四帖》的判斷依據(jù)中,可以比較清晰地顯示出謝稚柳的鑒定風(fēng)格特征。
二是對唐柳公權(quán) 《蒙詔帖》的鑒定。有鑒定家認(rèn)為 《蒙詔帖》是偽作的依據(jù)是 “出守翰林”“職在閑冷”兩句與事實不符。謝稚柳不僅從文獻中找出證據(jù)對這兩句加以合理解釋,更指出以文字內(nèi)容作為判定法書真?zhèn)蔚臎Q定性要點而無視法書的筆法本身,乃至以文字的解釋來決定法書本身的真?zhèn)问遣豢扇〉摹T谒?《唐柳公權(quán)蒙詔帖與紫絲靸帖》一文中提到:
“認(rèn)識書體的時代風(fēng)格,是認(rèn)識書體的個別風(fēng)格的前提。傳世墨跡如李太白的 《上陽臺帖》,盡管我們對于李太白的書體完全生疏,也可以確定它是偽跡,因為它的時代風(fēng)格不是唐。顏真卿的《湖州帖》,盡管它的書勢與顏真卿近似,也可以確定它是臨本,因為它的時代風(fēng)格是唐以后的。我們不僅從 《紫絲靸帖》文字內(nèi)容的荒謬胡扯,并從書體的荒蕪虛偽這兩者來斷定它是出于偽造。”[12]
謝稚柳以書畫本身的時代風(fēng)格為依據(jù)來論證書畫真?zhèn)蔚蔫b定方法,在 《蒙詔帖》之判真與 《紫絲靸帖》之判偽之間也得到充分的展現(xiàn)。
第三個實例是對徐熙 《雪竹圖》的論證。1954年,謝稚柳在寫 《水墨畫》一書時,就把 “徐熙落墨”當(dāng)作一個專題來論述。他在 《徐熙落墨兼論<雪竹圖>》一文中通過 《宣和畫譜》《夢溪筆談》《圖畫見聞志》等著錄中所述徐熙落墨的特點,用色的習(xí)慣,根據(jù)對落墨的實踐感受所得,判斷 《雪竹圖》完全符合徐熙 “落墨”的規(guī)律,以 “落墨”的技巧風(fēng)格為關(guān)鍵憑證,證明 《雪竹圖》為徐熙僅存的畫筆。
關(guān)于對 “落墨”兩字的理解,還曾引發(fā)了一場謝、徐之爭。徐邦達(dá)認(rèn)為 “落墨”即 “落筆”,論畫都以 “筆墨”合稱,只有明白這點才能理解所謂落墨應(yīng)是一種怎樣的風(fēng)格面貌的花卉畫了。徐氏還以繪畫材料的尺幅大小來證明 《雪竹圖》起碼是南宋以后的作品了。謝稚柳后來寫了 《再論徐熙落墨——答徐邦達(dá)先生<徐熙落墨畫法試探>》一文從風(fēng)格、技法上加以反駁。由此可見,謝稚柳和徐邦達(dá)的鑒定風(fēng)格各有其著眼點。徐邦達(dá)是在目鑒的基礎(chǔ)上相對注重著錄、印章、紙絹等繪畫的外部條件,而謝稚柳則毫無異議地注重書畫本身的筆墨、風(fēng)格。他強調(diào):
“繪畫之至者是風(fēng)格,所以形成風(fēng)格是一幅畫的整體,所以形成畫的整體的是技法,所以形成技法的是筆墨。因而,不能認(rèn)識歷代的繪畫,就不能認(rèn)識一代的繪畫……安心于著錄、印章、紙絹等等的重圍,就不能豁然去認(rèn)識畫派的個人風(fēng)格與各個時代風(fēng)格,不從研究繪畫藝術(shù)本身去找尋規(guī)律這一正道,就只覺其是,看不到其失,若憑此來認(rèn)識繪畫,真所謂舍正道而弗由了。”[13]
在謝稚柳的鑒定成果當(dāng)中,還有對歷來被認(rèn)為是李成作品的 《茂林遠(yuǎn)岫圖》其實為燕文貴畫筆的判斷及論證。對王羲之、懷素、周昉作品的判斷及研究,都表現(xiàn)了他獨特的鑒定方法。根據(jù)他在書畫鑒定中特別注重對筆墨、風(fēng)格特征分析的特點,我們可以將他的鑒定方法歸為筆墨風(fēng)格分析鑒定學(xué)派。
筆墨風(fēng)格是書畫最本質(zhì)的內(nèi)容。能夠通過本質(zhì)來解決書畫的真?zhèn)螁栴},是最理想的方法也是最高的境界。但筆墨、氣息的把握是最本質(zhì)的,同時也是最難、最玄的。我們知道,在書畫創(chuàng)作中,同一個人在不同年齡、不同創(chuàng)作狀態(tài)下的風(fēng)格、水準(zhǔn)都是有差異的,更何況當(dāng)時人的代筆、作偽和后人的作偽情況如此復(fù)雜,僅僅憑作品風(fēng)格、筆墨的感覺,“望氣”就能做出斷定,則需要過目大量古代書畫作品,對歷代書畫有極為深刻的理解才能做到。而謝稚柳完全具備這樣的素質(zhì),他的鑒定方法并不僅僅是靠感覺,而是加上對筆墨風(fēng)格極為透徹的理性分析。從以上幾個實例的分析可以看出,以謝稚柳為代表的筆墨風(fēng)格鑒定學(xué)派的幾個顯著特征:
第一,謝稚柳本身是一個書畫創(chuàng)作實踐家,對筆墨悟性極高。古代書畫鑒定家一般都是優(yōu)秀的書畫家,書畫家認(rèn)為書畫創(chuàng)作的最高境界是筆墨的精湛、氣息的高古。因此,在書畫鑒定中,傳統(tǒng)的 “望氣”的方法歷來是鑒定家津津樂道、奉為正宗的。謝稚柳的鑒定方法也根基于此。他立足于自身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和對筆墨的體會、理解,以書畫本身的規(guī)律,即書畫家本身的各種性格,包括筆墨表現(xiàn)方法、個性、流派和時代性特征等為鑒定書畫的主要手段,理解之精到,判斷之準(zhǔn)確在鑒定界首屈一指。王遽常對謝稚柳書畫鑒定之神奇是這樣評價的:
“君之鑒別古跡真贗,往往望氣而知神遇于牝牡驪黃之外。鑒即定,如南山之不可移,人或不信,但久而后,君言卒驗,予曰君古跡之九方皋也。”[14]
通過 “望氣”的方法能得出準(zhǔn)確的結(jié)論,要有超一流的書畫創(chuàng)作水平才能做到。而在現(xiàn)代的書畫鑒定家中,很少有人能具備這種特殊的條件,因此,所謂 “望氣”的結(jié)論可信度往往頗為可疑。謝稚柳是個特例,他的書畫創(chuàng)作造詣之精深在書畫創(chuàng)作界是被公認(rèn)的,不談謝稚柳在書畫鑒定界的地位,僅僅是作為一位一流的書畫創(chuàng)作家,他也是當(dāng)之無愧的。因此,書畫創(chuàng)作的經(jīng)歷和水平為謝稚柳書畫鑒定帶來的優(yōu)勢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謝稚柳又是一位繪畫史和繪畫理論研究家,對理論的證明能力極強。如果謝稚柳僅僅是一位繪畫實踐家,僅僅從繪畫創(chuàng)作技法分析來鑒定書畫,顯然會缺乏理論上的邏輯證明,從而使結(jié)論不可信。但謝稚柳恰恰又是一位繪畫史家和理論家。在鑒定書畫過程中,他運用繪畫技法史、風(fēng)格史的研究內(nèi)容,在理論上進行邏輯證明和推理演繹。謝稚柳運用時代風(fēng)格與個人風(fēng)格的特征判斷書畫的年代與作者,其實是借鑒了繪畫史研究中的內(nèi)容,特別是利用了繪畫史中的風(fēng)格學(xué)說,從繪畫風(fēng)格流派的因革承變中找到鑒定的依據(jù)。體現(xiàn)在他的許多理論著作上,如 《鑒余雜稿》《中國古代書畫十論》中的許多散論文章、《論書畫鑒別》等,這些理論研究成果表明:他的筆墨風(fēng)格分析方法有著學(xué)理上的支撐和證明。
筆墨風(fēng)格分析方法其實代表了兩層含義,一是實踐意義上的具體筆墨風(fēng)格,二是理論意義上的技法史、風(fēng)格史與筆墨風(fēng)格史。要具備這兩層含義的筆墨風(fēng)格鑒定法,僅僅是書畫家或僅僅是繪畫史論家都不能做到,而謝稚柳的獨特之處在于兼有兩者之長,這使他的筆墨風(fēng)格鑒定法具有了旁人無法達(dá)到的優(yōu)勢。
第三,謝稚柳的想象力與推演能力極為豐富,鑒定書畫具有 “無中生有”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其它流派的書畫鑒定家鑒定書畫,一般首先在心目中確立一個樣板,以樣板來套具體畫作,符合樣板即為真,反之為假,這是首先設(shè)立外框再往里做的方法。謝稚柳則不然,他是從繪畫史文獻中記載的對筆墨技法的說明,結(jié)合自身的實踐,接著提出一個創(chuàng)造性的學(xué)說,并且用理論來證明這一說法。如用 “落墨法”證明徐熙作品,古人有 “落墨法”一說,其實誰也沒有見過真正的 “落墨法”,但謝稚柳通過繪畫史中關(guān)于落墨法的記載、演變特征和實踐研究作出推理判斷,證明了什么是 “落墨法”。并且用邏輯推理證明了 《雪竹圖》即為徐熙落墨法的典型代表作。這是從創(chuàng)作元素中的一個點推出一種樣板,是從里往外做的方式。與其他鑒定家相比,謝稚柳鑒定書畫堪稱是最有想象力的,是思維的敏銳和藝術(shù)家的創(chuàng)造性格,使他的書畫鑒定不同凡響。
謝稚柳以繪畫史學(xué)的立場切入到書畫鑒定中,與啟功以歷史學(xué)、文獻學(xué)的立場切入書畫鑒定,雖然切入的點不同,但他們都不僅是站在鑒定實踐的圈子里研究鑒定學(xué),而是從大歷史、大文化的角度和高度對書畫鑒定學(xué)進行研究,這相對于一般的經(jīng)驗鑒定家的目鑒,顯然更具有理論高度,思考各種問題更有深度,其鑒定方法更有標(biāo)志性和個性特征。謝稚柳的筆墨風(fēng)格分析鑒定法是后學(xué)者在實踐中必然借鑒、在鑒定理論研究中也必然繞不開的對象。他的成就對整個鑒定學(xué)界產(chǎn)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對今后的鑒定實踐研究與理論研究都具有指導(dǎo)性意義。
三、以啟功為代表的文史文獻考證鑒定學(xué)派
在現(xiàn)當(dāng)代古書畫鑒定的研究領(lǐng)域里,啟功算得上是一位舉足輕重的代表人物。因為精通書畫,早在20世紀(jì)40年代,就經(jīng)沈兼士先生推薦,被故宮博物院聘為專門委員,負(fù)責(zé)鑒定故宮收購的古書畫。解放以后,鄭振鐸先生主持籌建了國家文物局,當(dāng)時邀請的書畫文物鑒定方面的專家有張珩、謝稚柳、徐邦達(dá)、朱家濟,在北京特別邀請了啟功參加專家組從事古代字畫的鑒定工作。80年代以后,啟功成為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七位專家之一,并被文化部聘為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可見,啟功的大半生都在從事古代書畫的鑒定工作,他不僅以他的真知灼見判定了諸多歷史上關(guān)于古書畫真?zhèn)蔚膽野敢砂福⑶覟閲遗囵B(yǎng)了許多鑒定文物的人才,使他們成為今天文物界的骨干力量。可以說,啟功對于中國古書畫文物鑒定的卓著貢獻和在當(dāng)今文物界的影響與地位是無可爭議的。
書畫鑒定這門學(xué)問涉及的知識領(lǐng)域非常廣,沒有對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有深入廣博的研究是根本無法駕馭它的。啟功知識面很廣,所掌握的文史文獻信息很多,對如何處理這些信息也非常有方法。在鑒定一件作品的時候,他并不只是憑感覺對作品進行一般的真?zhèn)闻袛啵巧朴谶\用他對古文字學(xué)、古典文學(xué)、歷史學(xué)、文獻學(xué)、目錄學(xué)、考據(jù)學(xué),對書法史、繪畫史等各方面的研究,綜合分析,得出正確的判斷。這種充分利用相關(guān)文史文獻信息的鑒定方法的形成,與啟功的學(xué)習(xí)經(jīng)歷和他所掌握的知識結(jié)構(gòu)背景分不開,是他經(jīng)過數(shù)十年的勤奮學(xué)習(xí)積累而成的。
啟功從十幾歲就拜賈羲民先生和吳鏡汀先生為師學(xué)習(xí)書畫,跟隨戴姜福先生學(xué)習(xí)古典文學(xué)。戴先生的教導(dǎo)使啟功從小便在中國古典文獻和歷史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chǔ)。吳先生對啟功繪畫技法方面的教授使他的作畫技巧突飛猛進。賈先生博通書史,并且對書畫鑒賞方面有非凡的見識。啟功經(jīng)常隨賈先生和一些前輩到故宮博物院看陳列的古字畫,前輩們對古字畫的隨意評論,使啟功對書畫鑒賞方面的知識有了了解和啟發(fā),為他后來的書畫鑒定鋪下了基石。啟功曾說:
“我現(xiàn)在也忝在 ‘鑒定家’行列中算一名小卒,姑不論我的眼力、學(xué)識上夠多少分,即使在及格線下,也是來之不易的。這應(yīng)當(dāng)歸功于當(dāng)時故宮博物院經(jīng)常的陳列和每月的更換,更難得的是我的許多師長和前輩們的品評議論……最得益處是聽他們對某件書畫的評論,有時他們發(fā)生不同的意見,互相辯駁,我們可以從中得知許多千金難買的學(xué)問。如果有不能理解的問題,向老輩問一下,得到的答案即使是淡淡一句 ‘甲某處是,乙某處非’,便使自己的疑難迎刃而解……”[15]
而對啟功影響最深的是他的恩師陳垣先生。經(jīng)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版本、目錄、校勘學(xué)家和大藏書家傅增湘先生的推薦,啟功認(rèn)識了當(dāng)時輔仁大學(xué)的校長陳垣先生。跟隨陳垣先生的這段時間,無論是在事業(yè)上還是在學(xué)習(xí)上,對啟功來說都是一個人生至為關(guān)鍵的轉(zhuǎn)折點。對啟功書畫鑒定方面的學(xué)習(xí)和研究也是如此。陳垣先生對書畫鑒定并沒有做過專門的研究,但他將曾精心研究過的文字避諱問題運用到了書畫鑒定中,這對啟功鑒定書畫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可以說,啟功后來所用的文獻考證的鑒定方法得益于此,只是他又能將老師的方法進一步領(lǐng)會,舉一反三地將所積累的歷史、文學(xué)、書畫中的有關(guān)文獻運用到書畫鑒定中來,從而青出于藍(lán)更勝于藍(lán)。
陳垣先生曾在他的 《史諱舉例》中指出 “避諱可以辨別古文書之真?zhèn)渭皶r代”,所以他在鑒定古書畫的時候,往往不憑借作品的風(fēng)格筆法,而是著重憑借對歷史文獻的掌握,從一個字?jǐn)喽ü艜嫷恼鎮(zhèn)巍1热纾愒壬吹竭^一位收藏家購買的吳漁山摹古畫一冊,共有八頁,題名為 《仿古山水八幀》,畫法細(xì)密,技法相當(dāng)?shù)轿弧F渲械谄邘悄∥宕捅彼沃H的畫家李成的,題款為 “李營邱渡秋圖”,第八幀的末款題 “丙戌年冬至”。陳垣先生立刻斷定這本畫冊是偽作,理由是,歷代對孔子的字都不避諱,直到清代雍正四年 (1726年)才下令避諱 “丘”字,凡是寫 “丘”字,均加 “邑”旁作 “邱”,此前都沒有這種寫法。吳漁山生于明崇禎五年 (1632年),卒于清康熙五十七年 (1718年),在雍正以前,他不可能預(yù)知要如何避諱,而丙戌年冬至是康熙四十五年 (1706年),也不可能預(yù)知要避誰的諱,所以盡管這本畫冊筆墨精良,但僅以這點,偽作的馬腳就立刻暴露了。這個例子告訴啟功,熟練掌握豐富的歷史文獻也是鑒定書畫文物的一個有效的方法,這對啟功的影響很大。
除了少時打下的童子功,啟功在輔仁大學(xué)直到后來的北京師范大學(xué)里的教學(xué)生涯也為他的書畫鑒定方法的形成提供了條件。啟功鑒定書畫最注重文獻考證,在古書畫鑒定領(lǐng)域中可謂獨樹一幟。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他在大學(xué)里一直擔(dān)任中文系的古典文學(xué)、古典文獻學(xué)的教學(xué)工作,教授文史典籍、歷代韻文、敦煌變文等,內(nèi)容涉及到文字、音韻、訓(xùn)詁、目錄、版本、校勘、官制、地理、典章、習(xí)俗等,范圍相當(dāng)廣。在八十年代,啟功還創(chuàng)立了北京師范大學(xué)古典文獻專業(yè)碩士點、博士點。他的許多研究都是從他長期從事的教學(xué)實踐中發(fā)展起來的。以一位教授、學(xué)者的身份,以他擅長的古典文獻學(xué)方面的廣博知識為背景和立足點介入到書畫鑒定中,他的視角必定會與眾不同。他不是憑感覺地判斷某件作品對或不對,而是提出以文史記載為依據(jù)的方式,有理有據(jù),這也往往能夠在鑒定書畫中出奇制勝,令人信服。
在從事古書畫鑒定的幾十年時間里,啟功充分運用他在古典文獻、古文字等方面的深厚積累,總結(jié)出了不少關(guān)于古書畫鑒定的經(jīng)驗和心得,發(fā)表了不少頗有見解的關(guān)于書畫鑒定的文章,如 《〈平復(fù)帖〉說并釋文》《〈蘭亭帖〉考》《舊題張旭草書古詩帖辨》《孫過庭 〈書譜〉考》《從 〈戲鴻堂帖〉看董其昌對法書的鑒定》《董其昌書畫代筆人考》、《談南宋院畫上題字的 ‘楊妹子’》等等,給了我們很多提示,也使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啟功以文史文獻考證為主的鑒定方法和鑒定觀念。我們可以舉實例來分析說明啟功的書畫鑒定方法的特色。
在啟功的 《鑒定書畫二三例》一文中,舉米芾的 《寶章待訪錄》和張即之寫的 《汪氏報本庵記》為例,啟功判斷這兩件的破綻,并非筆墨風(fēng)格或其它,而是文字中的一個 “某”字。他談道:
“(《寶章待訪錄》)這卷墨跡,我沒見到過,但從張丑抄錄的文詞看,可以斷定是一件偽作。理由是,其中凡米芾提到自己處,都不作 ‘芾’,而作 ‘某’。我們今天看到許多米芾的真跡,凡自稱名處,全都作 ‘黻’或 ‘芾’,他記錄所見書畫的零條札記,流傳的有墨跡也有石刻,石刻如 《英光堂帖》《群玉堂帖》等,都沒有自己稱名作 ‘某’字的。可知這卷墨跡必是出自米氏子孫手所抄……然而卷尾還有一行 ‘元祐丙寅八月九日米芾元章撰’,這便壞了,從卷中自避其名,而卷尾忽署名與字這點上看,也是自相矛盾的。”[16]
這是典型的以作品文字的考證來作為鑒偽手段的方法。還有用對古畫名款的考證來判斷真?zhèn)蔚摹R苑秾挒槔瑩?jù)郭若虛 《圖畫見聞志》中所記,“寬”是范中正之諢號,因為自己不可能落自己諢號的款,那么在作品的名款上署 “臣范寬制”顯然有問題,但如果是從畫法上來看,確是與范寬風(fēng)格相符。那么,從對名款的考證中,這件署名范寬的作品最多是宋代范派的畫而非范寬本人所作。
在考證中,還有許多以背景文史資料為鑒定依據(jù)的例子。最具代表性的是啟功的 《董其昌書畫代筆人考》,其中就以大量的文史文獻依據(jù),如前人手札、跋文、隨筆雜記、文集詩集、書論畫論,來證明董其昌有多少如趙左、沈士充這樣的代筆者。從文史文獻的考證中分析他們與董氏繪畫的相同與相異之處,從而對作品作出客觀判斷。
啟功總結(jié)出了他多年的研究經(jīng)驗,同時也對其它的鑒定依據(jù)提出了一些看法。如啟功對歷代以著錄為依據(jù)來鑒定書畫真?zhèn)蔚姆椒ㄌ岢龅馁|(zhì)疑。他說:
“在攝影印刷技術(shù)沒有發(fā)達(dá)之前,古書畫全憑文字記載,稱為 ‘著錄’。見于著名收藏鑒賞家著錄的作品,有時聲價十倍。其實著錄中也不知誤收多少偽作品、或冤屈了多少好作品。如 《寶章待訪錄》,如果看到原件,印證末行款字是否后人妄加,它可能不失為一件宋代米氏后人傳錄之本;《汪氏報本庵記》如果僅憑 《石渠寶笈》和 《墨妙軒帖》,它便成了偽作……”
“古代書畫不是一個 ‘真’字或一個 ‘假’字所能概括;‘著錄’書也在可憑不可憑之間;古書畫的鑒定,有許多問題是在書畫本身以外的。”[17]
啟功所說的書畫本身以外的許多問題,從他的實際操作方法中可見,大多從對作品文字、題款和相關(guān)文史文獻等各方面的考證中得來,而并非偏重歷代著錄或偏重對書畫作品藝術(shù)風(fēng)格的分析和感受。由此,還可以引出啟功與其他鑒定家運用不同的鑒定方法,在鑒定同一件作品時所產(chǎn)生的分歧,從而進一步展現(xiàn)了啟功在書畫鑒定研究中的獨特之處,并與其他鑒定家的鑒定方式形成鮮明對比。
值得一提的就是啟功、謝稚柳、楊仁愷三家對張旭 《古詩四帖》的鑒定,以及從而引發(fā)的一場真?zhèn)伪鎰e的爭論。謝稚柳認(rèn)為 《古詩四帖》為唐張旭真跡,并為此著文 《唐張旭草書<古詩四帖>》和 《宋黃山谷<諸上座帖>與張旭<古詩四帖>》,論證了他的判斷。他所憑借的論據(jù)是筆法、個人風(fēng)格和時代風(fēng)格。謝稚柳以歷來對張旭草書的敘說,如杜甫的 《張旭草書歌》:“鏘鏘鳴玉動,落落長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等對張旭筆法的形容與 《古詩四帖》筆勢相印證;并從對 《古詩四帖》與懷素狂草 《自序帖》和顏真卿 《劉中使帖》筆勢結(jié)體的具體比較分析中,證明 《古詩四帖》確為張旭所書。謝稚柳反復(fù)提到的就是筆法、風(fēng)格、形式,這非常具體地體現(xiàn)了他以筆墨形式風(fēng)格分析為主的鑒定方法。
楊仁愷也認(rèn)定 《古詩四帖》是張旭的真跡,他對草書發(fā)展的各個歷史階段、時代背景作了綜合分析考察,從顏真卿的 《祭侄稿》、懷素 《苦筍帖》、《自敘帖》到五代楊凝式的 《神仙起居帖》、北宋人黃庭堅 《諸上座》等直接或間接受張旭影響的后代草書家作品真跡進行對照和分析,論證了張旭此卷的特點。他認(rèn)為:
“(顏真卿 《祭侄稿》等)所有這些真跡,都與 《古詩四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其中最突出之點,就是用筆。我在文章的開頭就提到過盛唐以后書法之風(fēng)為之一變,草書始于張旭,正楷定于顏真卿,不僅是風(fēng)貌有別,而且運筆方法都具有劃時代的標(biāo)志。從盛唐上溯到東晉,運筆有一個普遍的法則,無論是真、行、草、隸的橫筆豎畫,基本上是方頭側(cè)入,自然形成橫筆筆鋒在上,豎畫筆鋒在左的狀態(tài),以此去考察這一時期的字跡,不致有多大的差誤。到了盛唐以后,運筆改用圓頭逆入,筆鋒居于橫豎畫的正中,近于篆書筆法。《古詩四帖》是這樣,《苦筍帖》《自敘帖》《祭侄稿》也莫不是如此。如果硬是不承認(rèn)這種運筆法則始于張旭,那么顏真卿、懷素新的運筆法又是從何而來?再說 《古詩四帖》用圓筆運筆是那樣的明顯,如錐畫沙,無往不收,內(nèi)擫的筆勢,又處處與右軍相默契,是亞棲、彥修之輩無從想象的!”[18]
在此,楊仁愷也提到主要以用筆、風(fēng)格的特征來判斷此卷的真?zhèn)危旧鲜歉鶕?jù)本人經(jīng)驗對某個時代的筆法特征加以籠統(tǒng)概括,多方比較之后得出結(jié)論。與謝稚柳對某字的用筆、結(jié)構(gòu)、筆勢、風(fēng)格作具體分析還有所不同。應(yīng)該說楊仁愷的鑒定方法比較綜合,但特點不是很顯著,而謝稚柳的筆墨風(fēng)格分析法則旗幟更為鮮明。
啟功的鑒定方法同樣是旗幟鮮明的——文史考證法,只是最后得出的結(jié)論卻是和謝、楊兩家截然不同。他對作品的跋文和關(guān)于此卷記載的疑點作了詳細(xì)考證,包括項元汴、豐坊、董其昌等人的跋文,還有 《宣和書譜》和王世貞 《王弇州四部稿》中所記,啟功還特別對董其昌的鑒定提出了質(zhì)疑。最后他闡述了自己對此帖的一番見解:
“這卷字跡本身究竟是什么時候人所寫的?算不算張旭真跡?我的回答如下:按古代排列五行方位和顏色,是東方甲乙木,青色;南方丙丁火,赤色;西方庚辛金,白色;北方壬癸水,黑色;中央戊己土,黃色。庾信原句 ‘北闕臨玄水,南宮生絳云’,玄即是黑,絳即是紅,北方黑水,南方紅云,一一相對。宋真宗自稱夢見他的始祖名叫 ‘玄朗’,命令天下諱這兩字,凡 ‘玄’改為‘元’或 ‘真’, ‘朗’改為 ‘明’,或缺其點畫。這事發(fā)表在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見 (宋李攸《宋朝事實》卷七)所見宋人臨文所寫,除了按照規(guī)定改寫之外也有改寫其他字的,如紹興御書院所寫 《千字文》,改 ‘朗曜’為 ‘晃曜’,即其一例。這里 ‘玄水’寫作 ‘丹水’,分明是由于避改,也就不管方位顏色以及南北同紅的重復(fù)。那么這卷的書寫時間,下限不會超過宣和入藏,《宣和書譜》編訂的時間;而上限則不會超過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19]
雖然啟功根據(jù) “玄水”改 “丹水”所得出的結(jié)論遭到了楊仁愷等人的質(zhì)疑,但對于他的依據(jù),卻并沒有來自正面的辯駁,它表明啟功的立論是不輕率的,有分量的。這樣的例子一多,啟功的文史考證鑒定方法逐漸得到了許多鑒定家和學(xué)者的認(rèn)可,從而成為當(dāng)今鑒定學(xué)界的一個典型代表。
與另外幾家具有典型特征的鑒定流派的鑒定方式相比,啟功以文史文獻考據(jù)為主要特色的鑒定方式獨樹一幟。總結(jié)啟功書畫鑒定方法的特點,有以下幾點:
第一,對 “似是而非”的望氣方法的批判最自覺,最強調(diào)書畫鑒定中的 “證據(jù)說”。在古代的書畫鑒定理論中敘述的鑒定書畫的方法,一般都以 “望氣”或一般的以經(jīng)驗式筆墨分析的方法,憑經(jīng)驗下結(jié)論,當(dāng)代大多數(shù)鑒定家仍沿用這種傳統(tǒng)的方法。“望氣”的鑒定方法,雖然涉及的是所謂的書畫本身,但感覺的成分還是占主導(dǎo)地位,筆墨風(fēng)格的對比相對抽象,各人有各人的感覺和理解,變化指數(shù)很大,除非是對書畫有很深的造詣,飽覽歷代書畫名跡,對歷代書畫作品進行過深刻對比和理解的一流畫家鑒定家才能做到準(zhǔn)確把握。否則,感覺的不確定因素將是筆墨風(fēng)格鑒定法的最大困擾:它無法被證明。因此,啟功對 “望氣”法的批判非常直接:
“鑒定方法,在近代確實有很大的進步……比起前代 ‘鑒賞家’那套玄虛的理論、‘望氣’的辦法,無疑進了幾大步……”[20]
他認(rèn)為在書畫鑒定中最不可靠的就是 “似是而非”的望氣,鑒定應(yīng)講求證據(jù),以文史文獻中確切的事實、信息為依據(jù)進行推理驗證,因為文史文獻是有記載、有確切根據(jù)的,它的信息比較固定,因此也最可靠。當(dāng)然,文史文獻考證鑒定方法需要大量文史知識的積累,證據(jù)越豐富,結(jié)論更有說服力。
第二,關(guān)于書畫鑒定的科學(xué)性,啟功的方法顯示出的特征最強。這主要表現(xiàn)在鑒定依據(jù)與證明過程的科學(xué)性,“望氣”的方法依據(jù)的是經(jīng)驗和感覺,經(jīng)驗和感覺的偏差會造成鑒定家對鑒定依據(jù)的各持己見互不相讓,而文史文獻的推理實證過程,它的依據(jù)是最無疑義的。有歷史和文獻為證,推理的過程也表現(xiàn)出邏輯力量的強大,具有相當(dāng)?shù)目煽啃浴⒖芍院涂茖W(xué)性。
第三,文史文獻實證的鑒定方法與通過科技鑒定書畫屬同一邏輯要求,兩種方法在邏輯上最為相通,因此,啟功對高科技鑒定書畫的觀念接受能力最強。除了文史考證的鑒定方法以外,啟功非常認(rèn)同現(xiàn)代科技方法對書畫鑒定帶來的影響和作用。他在 《書畫鑒定三議》一文中提到:
“鑒定怎樣才更科學(xué)?我個人覺得首先是辯證法的深入掌握。其次是電腦的發(fā)展,必然可以用到書畫鑒定方法的研究上。例如用筆的壓力,行筆習(xí)慣的側(cè)重方向,字的行距,畫的構(gòu)圖以及印章的校對等等,如果通過電腦來比較,自比肉眼和人腦要準(zhǔn)確得多。已知的還有用電腦測視種種圖象的技術(shù)……人的經(jīng)驗又可與科學(xué)工具相輔相成。不妨說,人的經(jīng)驗是軟件,或說軟件是據(jù)人的經(jīng)驗制定的,而工具是硬件,若干不同的軟件方案所得的結(jié)論,再經(jīng)比較,那結(jié)論一定會更科學(xué)。從這個角度說,‘肉眼一觀’、‘人腦一想’,是否 ‘萬無一失’,自是不言可喻的!”[21]
對科學(xué)鑒定方法的認(rèn)同,也從另一個側(cè)面體現(xiàn)了啟功一貫認(rèn)為的鑒定并不能僅僅憑經(jīng)驗,更不可憑空臆測,而必須講求實證的科學(xué)的鑒定觀念。從今后書畫鑒定會逐漸更多地依靠科技手段的發(fā)展趨勢看,啟功對高科技鑒定書畫的預(yù)測和認(rèn)同,也充分顯示了文史文獻考證的方法在邏輯上最易轉(zhuǎn)向高科技書畫鑒定法的可能性,和他作為大師級人物對所從事的事業(yè)的高瞻遠(yuǎn)矚。
第四,啟功鑒定書畫是學(xué)問與書畫鑒定相結(jié)合的典型。啟功鑒定書畫是在深厚的傳統(tǒng)文化基礎(chǔ)上進行,這是一般的鑒定家很難企及的。文物鑒定最終解決的雖然是真?zhèn)螌﹀e的科學(xué)問題,但它的過程卻是和文化、歷史、藝術(shù)、審美等緊緊聯(lián)系。啟功首先是一位學(xué)問家,他對考古發(fā)掘資料、文學(xué)、藝術(shù)史料的研究和學(xué)術(shù)觀點,充分體現(xiàn)在他的書畫鑒定上,表達(dá)在他的許多題跋和題書畫詩上,并迅速判斷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是不可信的。啟功又是一位教育家、書畫家,以他多年的書畫創(chuàng)作實踐和教學(xué)積累為基礎(chǔ),以深厚的文化素養(yǎng)和歷史知識作為書畫鑒定的支撐,因為這許多綜合條件,他才能成為獨具慧眼的書畫文物鑒定家,成為當(dāng)代書畫鑒定界中文史考證鑒定學(xué)派的代表。
啟功自謙地認(rèn)為書畫鑒定于他來說只是文人的 “余事”,在書畫鑒定家的行列里只能算一名 “小卒”。在啟功所馳騁的各個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里,書畫鑒定也許真是如他所說的 “余事”,但他所謂的 “余事”在書畫鑒定領(lǐng)域里,卻是一塊金字招牌。實際上,他并非書畫鑒定家行列里的 “小卒”,而是不折不扣的大師。原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楊新先生這樣評價啟功:“啟功先生是傳統(tǒng)文化一個時代的總結(jié),標(biāo)志著一個時代的高峰,他的去世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結(jié)束……”[22]
四、 以傅熹年為代表的實物圖像考證鑒定學(xué)派
從1983年重新成立的中國古代書畫鑒定七人小組名單上,可以看到一位鑒定家:傅熹年。與謝稚柳、啟功、楊仁愷、徐邦達(dá)等當(dāng)代最受關(guān)注的幾大權(quán)威鑒定家相比,傅熹年可以說不那么引人注目。在書畫鑒定領(lǐng)域,關(guān)于他的介紹和研究文章相對并不多,研究他的書畫鑒定理論和方法則更少。也許是因為研究建筑學(xué)的出身,以古代建筑史介入古書畫鑒定,而不是從通常人們所看重的筆法、風(fēng)格、題款等書畫作品本身的內(nèi)容來研究書畫鑒定,因此容易被忽視。但即便如此,傅熹年對中國古書畫鑒定所作的巨大貢獻仍然是眾口一詞,有目共睹。或許正相反,正因為他獨特的知識結(jié)構(gòu)背景,使他對書畫鑒定有著有異于別家的最獨特的視角。為書畫鑒定的研究提供了以書畫本身為主的鑒定方法之外的又一種研究方法和鑒定風(fēng)格。而他以書畫圈外人之所以能成為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小組的寥寥幾位鑒定家之一,可能也正因為此。
實際上,傅熹年涉獵的研究領(lǐng)域非常廣,這對古書畫鑒定而言有百利而無一害。除了書畫藝術(shù)本身的筆墨、風(fēng)格、氣韻外,書畫鑒定還涉及到題跋印章中透露出來的文史文獻信息、作品的裝潢和材質(zhì)、畫面所描繪的建筑物和服飾、器物等方方面面的內(nèi)容,任何一個細(xì)小環(huán)節(jié)的漏洞都會左右古書畫的真?zhèn)闻袛嘟Y(jié)論。因此,掌握各方面的知識越多,判斷書畫真?zhèn)蔚囊罁?jù)也越多,結(jié)論也更可靠。
傅熹年出身于文博世家。祖父傅增湘先生是著名的古籍版本目錄學(xué)家和大藏書家,父親傅忠謨是一位古器物學(xué)家,對古代玉雕藝術(shù)頗有研究。傅熹年受先輩影響,在業(yè)余時間進行古籍版本目錄學(xué)與古器物學(xué)方面的研究,先后整理了其祖父傅增湘與父親傅忠謨遺稿,出版 《藏園群書經(jīng)眼錄》 《藏園群書題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古玉精英》《古玉掇英》等書,對古籍方面的整理頗有貢獻。
傅熹年是建筑學(xué)領(lǐng)域出身,1955年畢業(yè)于清華大學(xué)建筑系,先后為梁思成教授、劉敦楨教授助手,從事中國古代和近代建筑史研究。后來側(cè)重進行已不存在的歷史上重要建筑物的復(fù)原研究。出版了 《傅熹年建筑史論文集》《古建騰輝——傅熹年建筑畫選》《北京古建筑》《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史》等專著,在建筑學(xué)研究領(lǐng)域頗有建樹。
傅熹年也同時從事繪畫史的研究,曾主編 《中國美術(shù)全集·繪畫編》中的 《北宋繪畫》《南宋繪畫》《元代繪畫》三卷,對古代繪畫史的見解頗有獨到之處。
對古籍與古文物的研究和積累為他的古書畫鑒定研究奠定了一個非常堅實的基礎(chǔ)。對古代建筑史與古代書畫史的雙重研究,可以兩者結(jié)合,以對繪畫中古建筑的考證分析切入到書畫鑒定中,從而為他的古書畫鑒定的研究方法樹立不同的視角,在古書畫鑒定領(lǐng)域中偏師獨出。
我們來分析一下傅熹年古書畫鑒定方法的特點。
一是運用考古學(xué)中的類型學(xué),建立可供鑒定參考的比較系列。
首先列出傳世作品中公認(rèn)的各個時代的作品,以時代風(fēng)格、畫派、畫家為三個層次的內(nèi)容,建立一個 “標(biāo)準(zhǔn)品”系列,作為鑒定工作中比較分析的標(biāo)準(zhǔn)。其次對于元、明、清以后傳世作品較多的,這個標(biāo)準(zhǔn)系列的內(nèi)容還可以再細(xì)分。比如重要書畫家可以分人編年,以五年或一個階段為間隔選擇標(biāo)準(zhǔn)品,對作品的題材、風(fēng)格、筆法、署名和鈐印的階段性特點等,結(jié)合其生平進行考察,得出一個較為可靠的標(biāo)準(zhǔn)可供鑒定時參考。
正如他自己所說:
“建立這個供比較用的系列是很細(xì)致的工作,要注意到各種細(xì)節(jié),以期更為準(zhǔn)確。它多少有點近似于考古學(xué)中的類型學(xué)。在做這項細(xì)致工作的同時,由于反復(fù)、大量地接觸書畫,熟能生巧,又自然而然地會逐漸形成一個源于具體例證又脫離具體例證的對時代、流派、風(fēng)格的綜合概念。這比通過瀏覽所得的初步的印象又深入了一步,是建立在逐項細(xì)致分析研究基礎(chǔ)上的,更為可信。有意識地把綜合概念與細(xì)致的比較分析結(jié)合起來,可以使鑒定水平大大提高一步……”[23]
考古學(xué)中類型學(xué)的方法,是建立一個參考比對系列,也就是把鑒定家平時腦子里積累的經(jīng)驗分類型量化、具體化、數(shù)據(jù)化,把原本感性的、模糊的感覺和直覺的東西清晰化。這與后來主張以高科技介入書畫鑒定的研究者提出的利用電腦做成書畫鑒定的數(shù)據(jù)庫是同一個道理。傅熹年提出的建立一個可供比較的系列,就相當(dāng)于為這個電腦數(shù)據(jù)庫提供細(xì)致的項目框架。這個參照系列的有效性,證明了書畫鑒定并非人們想象的如此玄奧和遙不可及。同時,有了這個參照系列,也可以檢驗書畫鑒定家的經(jīng)驗判斷是否萬無一失,它的科學(xué)性格不言而喻。
二是引入建筑史研究中的比較分析方法,并運用古代建筑圖像和器物、服飾圖像的比較分析作為書畫鑒定的依據(jù)。
傅熹年曾說:
“我的本職工作是研究建筑歷史,這在西方屬美術(shù)史范圍,并有一二百年以上的歷史,有一套比較科學(xué)的嚴(yán)格的研究方法,在利用比較分析方法作斷代研究上頗為成熟。在這方面我又有幸分別在梁思成教授、劉敦楨教授這幾位中國建筑史學(xué)的開拓者指導(dǎo)下工作過,他們在利用比較分析和文獻考證研究中國古代建筑方面,取得極高的成就,也在運用比較分析方法上給我很多教誨。所以我在研究古代書畫史時是有目的地引入了在建筑史研究中使用的比較分析方法的。”[24]
在對具體的繪畫作品作鑒定時,他特別注重利用古代建筑圖像、器物與服飾等圖像的比較、分析、考證作為書畫鑒定的主要依據(jù)。以 《關(guān)于展子虔<游春圖>年代的探討》一文為例,可以看出傅熹年的鑒定方法。
歷代對 《游春圖》的時代和真?zhèn)螁栴}都是有爭議的。明代以后的鑒賞家如文嘉、詹景鳳等對此畫都有極高評價,清代著名的鑒藏家安岐也稱其奇古,乃六朝人手筆。唯有元代鑒藏家周密對此畫的真?zhèn)翁岢霎愖h,但他們都沒有舉出或真或偽的具體理由。傅熹年認(rèn)為北宋以前的古畫,因為年代久遠(yuǎn),絕大多數(shù)作品沒有款識,又往往是孤本,所以對作品時代的確定,難度很高,但它又是鑒定中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對作品的斷代,利用畫中的圖像特點來分析應(yīng)該是最有效也是最可信的方法。他在文中說道:
“《游春圖》是山水畫,畫中又有人物、鞍馬、建筑物。如果僅僅從山水畫的風(fēng)格特點來分析,目前可資比較的只有敦煌石窟中一些隋代壁畫。但二者除了地域上的懸隔之外,還有壁畫與絹素畫的差別,論者可以各執(zhí)一詞,不容易取得一致意見。如果從畫中所表現(xiàn)出的人物服飾和建筑物的特點來分析,則較易達(dá)到目的。因為前代人不能穿后代人的衣冠,不能住后代形式的房子,這是十分淺顯的道理。唐張彥遠(yuǎn) 《歷代名畫記》中說:‘詳辨古今之物,商較土風(fēng)之宜,指事繪形,可驗時代。’這說明我國自古以來就有利用畫中所反映出的衣冠宮室制度、風(fēng)俗習(xí)慣、地區(qū)特色等來驗證繪畫的時代和地域特點的傳統(tǒng)。”[25]
傅熹年從分析 《游春圖》中所畫人物頭上的幞頭和建筑物的斗拱、鴟尾的形制來驗證它是否符合隋代的特點。首先是服飾中的幞頭。詳細(xì)對比文獻記載與在近年考古發(fā)掘工作中發(fā)現(xiàn)的隋唐各時期的幞頭形制,以圖像的形式一一描繪排列,文獻與實物相結(jié)合,確定 《游春圖》中所畫幞頭不符合隋及初唐形制,而接近于敦煌144窟晚唐供養(yǎng)人像的幞頭。就此而論,可以證明 《游春圖》的時代上限不會超過晚唐。
其次是建筑物中的斗拱、鴟尾與獸頭。傅熹年運用古代建筑史料記載,將 《游春圖》描繪的建筑物上的斗拱特點與隋至唐末近三百年間的斗拱做法對照,得出它的時代不能早于晚唐,而與隋制相差甚遠(yuǎn);同樣,從古代建筑史發(fā)展中鴟尾的演變過程和文獻記載來看,《游春圖》中的鴟尾具有典型的北宋鴟尾特點,這一點又將 《游春圖》的時代上限下降到了北宋;獸頭的對比得出的結(jié)論同樣是不會早于北宋初或五代末年。以上的分析雖然不能完全斷定此畫準(zhǔn)確的時代上限,但至少證明這幅 《游春圖》肯定非隋代之物,這對書畫鑒定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貢獻。
除了關(guān)于 《游春圖》的年代探討,傅熹年還運用建筑、器物圖像考證的方法做了大量的書畫鑒定方面的研究。如 《王希孟<千里江山圖>中的北宋建筑》《宋趙佶<瑞鶴圖>和它所表現(xiàn)的北宋汴梁宮城正門宣德門》《論幾幅傳為李思訓(xùn)畫派金碧山水的繪制時代》等。
與啟功的文史文獻鑒定方法一樣的是,傅熹年也注重考證,從不憑經(jīng)驗下結(jié)論,兩者的鑒定方法都需要學(xué)術(shù)文獻的支撐。不同之處在于,啟功考證的是書畫作品中的文史內(nèi)容,而傅熹年考證的是書畫作品中的建筑物、器物等實物圖像內(nèi)容。細(xì)分之下,兩個流派之間的差異還是頗為明顯的。以建筑物、器物與服飾的比較考證對古書畫的斷代是非常準(zhǔn)確有效的手段,通過實物圖像考證判斷時代可以直接與筆墨風(fēng)格鑒定法中的書畫時代風(fēng)格相印證,并且,只有對書畫的時代風(fēng)格有準(zhǔn)確的定位,才能進一步分析判斷書畫家的個人風(fēng)格。當(dāng)然如果要確定是某家某派的作品,還需要對繪畫風(fēng)格或題跋印章等等更細(xì)內(nèi)容的考證才能作出判斷,傅熹年也贊成在書畫鑒定中利用多方面的手段推理考證。但是,實物圖像考證法是能與其它鑒定方法相互印證的最有力的手段,它無疑是傅熹年書畫鑒定的最具特色的閃光點,是其他鑒定家的知識結(jié)構(gòu)中不具備的。這一點足以表明:他從另外一個角度為古書畫鑒定增添了一種最具說服力的方法和手段。
同樣在書畫鑒定中擅長以實物圖像考證為主要方法的,還有文學(xué)家、文物學(xué)家沈從文。與傅熹年注重作品建筑物圖像的考證不同的是,沈從文更加偏向于對繪畫作品中服飾圖像的考證。
新中國成立以后,沈從文從一位優(yōu)秀的作家轉(zhuǎn)行成為文物研究專家,在中國歷史博物館渡過他后半人生。沈從文先是對出土文物中的紙絹、絲織綢緞材料做過精心研究,撰寫了 《談金花箋》《談染纈》《江陵楚墓出土的絲織品》等多篇學(xué)術(shù)論文。通過對絲綢等材料的研究繼而研究中國歷代服飾的花紋和基本圖案,這為服飾圖像考證的書畫鑒定方法研究提供了基礎(chǔ)。
在書畫鑒定中,以歷代服飾為著眼點,重實物輕文獻的實證方法是沈從文一貫提倡的,他曾提到:
“照過去的習(xí)慣,我們多以為對漢唐文物已知道的實在還太少。例如在文獻上雖常常提及唐代婦女的服飾,但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實并不明確。因為文獻只有相對可靠性,不夠全面。那么,現(xiàn)在不甚費力就能分辨出初唐、盛唐、晚唐婦女服飾基本上的不同。所以這些研究從大處說,不僅可以充實我們對于中國民族文化史的知識,從小處說,也可以幫助我們糾正對許多有名的畫跡、畫冊在年代上的鑒定。”[26]
運用繪畫作品中服飾的考證,沈從文對歷來被許多書畫鑒定家公認(rèn)為真跡的名作提出了置疑,并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最為有名的是傳為顧愷之作品的 《洛神賦圖》:
“傳世有名的 《洛神賦圖》,全中國教美術(shù)史的、寫美術(shù)史的,都人云亦云,以為是東晉顧愷之作品,從沒有人敢于懷疑。其實若果其中有個人肯學(xué)學(xué)服裝,有點歷史常識,一看曹植身邊侍從穿戴,全是北朝時人制度;兩個船夫,也是北朝時勞動人民穿著;二駙馬騎士,戴典型北朝漆紗籠冠……從這些物證一加核對,則 《洛神賦圖》最早不出展子虔等手筆,比顧愷之晚許多年,哪宜舉例為顧的代表作?”[27]
從 《洛神賦圖》的人物著裝中,證明其年代應(yīng)該不早于北朝與隋唐,而絕非顧愷之之作,這是沈從文鑒定書畫作品的主要依據(jù)。
此外,在對被認(rèn)為是隋展子虔作品的 《游春圖》的鑒定中,沈從文與傅熹年都認(rèn)為其年代不能早于晚唐,但與傅熹年側(cè)重作品中建筑物圖像的考證不同,沈從文的考證依據(jù)是服裝冠巾與馬匹裝備的衍變特征。他最后得出的鑒定結(jié)論是衣冠似晚唐,馬似晚唐,不大可能出自展子虔之手。[28]
以歷代服飾的衍變特征作為最主要的書畫鑒定依據(jù),也是屬于實物圖像考證的一個重要內(nèi)容,是鑒定書畫的一個獨特視點,它同樣能夠?qū)嬜髌返臄啻鷨栴}提出實物圖像上的可靠依據(jù),可以作為一種可證明的科學(xué)鑒定方法。因此,沈從文亦可被視為實物圖像考證學(xué)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五、以徐邦達(dá)為代表的技術(shù)經(jīng)驗加著錄鑒定學(xué)派
在當(dāng)代中國古書畫鑒定界屈指可數(shù)的幾位權(quán)威鑒定家中,徐邦達(dá)應(yīng)該算是年事最高、資歷最老的一位了。徐邦達(dá)先生舉辦九十壽辰時,曾得到了當(dāng)時的國家領(lǐng)導(dǎo)人李瑞環(huán)、李嵐清和文化部、文物局的最高領(lǐng)導(dǎo)的祝賀,這充分顯示了徐邦達(dá)對中國文物事業(yè)的卓著貢獻。他的名字是和國寶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他的一生都在從事著古書畫鑒定的工作,從來沒有停止過。
徐邦達(dá)書畫鑒定的方法是最典型的博物館研究專業(yè)人員研究書畫的方式,細(xì)致,技術(shù)上的可操作性強是其主要特點。徐邦達(dá)大半生都呆在故宮博物院,他的鑒定技術(shù)和經(jīng)驗就是從不斷地看畫實踐中得來,從鑒定實踐中來,到鑒定實踐中去,這與謝稚柳、啟功、傅熹年具有美術(shù)史、文學(xué)史、建筑史等的相關(guān)知識結(jié)構(gòu)背景的影響有著顯著的不同。
徐邦達(dá)早年也是繪畫創(chuàng)作出身,十幾歲師從蘇州畫家李醉石學(xué)習(xí)繪畫創(chuàng)作,在二十世紀(jì)四十年代曾在上海舉辦過個人畫展。同時,由于家中富有,父輩喜歡收藏書畫,耳濡目染之下,為培養(yǎng)判別書畫的真?zhèn)蝺?yōu)劣能力打下了些許基礎(chǔ)。而真正使他對書畫鑒定產(chǎn)生興趣并使書畫鑒定成為他畢生奮斗的職業(yè)的,是與著名古文物鑒定家兼書畫家趙叔孺、吳湖帆、馮超然、王己千等人的交往,正是他們,逐漸將徐邦達(dá)引入了古書畫鑒定的領(lǐng)域中來。趙叔孺是清末民國海上著名的金石書畫家,富收藏,擅鑒別,當(dāng)時海上一些有名的商人收藏家都請他為自己的書畫收藏 “掌眼”,[29]鑒別之名聞于海上。吳湖帆 “梅影書屋”的書畫收藏更是宏富,遠(yuǎn)近聞名,他本人見多識廣,精于鑒藏。吳湖帆又與當(dāng)時與其合稱為海上山水畫派代表 “三吳一馮”的馮超然毗鄰而居,時相往來,吳通過馮定交趙叔孺;王己千又是吳湖帆門下弟子。徐邦達(dá)先后拜趙叔孺、吳湖帆為師,學(xué)畫、學(xué)書畫鑒別,又經(jīng)常與他們的朋友、弟子一起研討和切磋藝技、鑒賞書畫。在這樣的環(huán)境熏染下,逐漸培養(yǎng)起了他鑒定古書畫的興趣和能力。因此,徐邦達(dá)在而立之年就以能辨別古書畫的真?zhèn)味谏瓿牵瑥亩呱狭斯艜嬭b定的專業(yè)之路。
徐邦達(dá)經(jīng)常目睹趙叔孺、吳湖帆、馮超然等人在一起討論書畫,孰是孰非,孰好孰壞。在不斷地爭論中,他們鑒別書畫的方法對徐邦達(dá)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趙、吳、馮等人都是書畫家出身,在鑒定當(dāng)中應(yīng)該比較注重畫的筆墨、技法,以藝術(shù)特點來作為判斷書畫真?zhèn)蔚淖钪饕侄巍P彀钸_(dá)受他們影響,早年又學(xué)畫,照理說應(yīng)該也對筆墨風(fēng)格較為注重,然而我們看徐邦達(dá)后來的鑒定方法,對以畫家立場為出發(fā)點,關(guān)注書畫作品筆墨真贗的分析倒是不多,而相反對作品的題跋、印章、形制等技術(shù)性的問題,還有對歷代著錄研究極稱深刻而到位,這似乎有些出人意料。我以為與他的后半生置身于故宮博物館,且棄筆多年有關(guān)。
全國解放后,徐邦達(dá)因為有書畫鑒定方面的特長從上海調(diào)到北京,先是在文化部文物局負(fù)責(zé)接收從各方面送來的古書畫,后來跟隨這些古書畫到了故宮博物院。自從調(diào)入北京故宮博物院以后,因為工作的需要和個人的擅長、喜愛,徐邦達(dá)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古書畫的收集、整理、研究和鑒定上,于書畫創(chuàng)作幾乎輟筆三四十年,直到晚年才重新拾筆,偶爾作畫。然而作畫的目的也大多出于幫助鑒定書畫的角度,與書畫家的心境和追求不能等同。博物館的工作是細(xì)致而繁瑣的,徐邦達(dá)在故宮博物院所做的工作一是繼續(xù)收購古書畫,二是對藏品作歸檔整理工作。這需要對每件作品的質(zhì)地、尺寸、款字、來源進行登記,對收藏印鑒、題跋進行識別,最后對作品的真?zhèn)巍⑺囆g(shù)水平作評價,查出作品流傳的文獻記錄等。長期從事這些看似博物館里最最基礎(chǔ)性的工作內(nèi)容,對他作為鑒定家的眼光、鑒定風(fēng)格的形成,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
徐邦達(dá)鑒定書畫第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技術(shù)全面。對于鑒定書畫中任何能夠涉及的方方面面要素,都進行詳細(xì)的分析和考證,比如畫家生平、師承、繪畫技法、落款、題跋、印章、材料、裝潢形制,任何一個小細(xì)節(jié)都可以成為他論證真?zhèn)蔚囊罁?jù)與出發(fā)點。《古書畫鑒定概論》比較全面地闡釋了他的鑒定思想和鑒定方法。如在談到鑒別古書畫應(yīng)注意的各點時,他指出書畫本身是第一點,其中分為書畫創(chuàng)作中的基本組織;書法作品中的文字考訂;繪畫中建筑物和服飾用品形制的考訂三部分。第一書畫創(chuàng)作中的基本組織談的是筆法、墨和色、結(jié)構(gòu)和剪裁,書畫本身的筆法僅占一小點,并且對筆法本身略作分析后就轉(zhuǎn)到不同的筆作為工具對書畫創(chuàng)作的影響,包括后面的墨、色、結(jié)構(gòu)、剪裁都是從技術(shù)的層面作闡述,而并非以書畫創(chuàng)作藝術(shù)本身的角度來作分析。這顯然與謝稚柳的書畫創(chuàng)作積累尤其是包含筆墨、流派、個人風(fēng)格與時代風(fēng)格等豐富內(nèi)容有著相當(dāng)大的差別。第二文字考訂與第三建筑物和服飾用品形制的考訂,也是從操作層面上講避諱字、錯訛字、建筑物、服飾是書畫鑒定中必須注意的點,而并非象啟功、傅熹年,是從更專業(yè)的文史、歷史、建筑史上的發(fā)展特點作為背景引伸到書畫鑒定中。當(dāng)然,徐邦達(dá)能把畫家各個時期用筆、用墨、題款、用印、作偽情況等特征作大量分析,細(xì)致推理,總結(jié)出常規(guī)和特例,并把他人鑒定書畫所側(cè)重的各點集于一處進行綜合分析,是他作為綜合性人物的長處。
以 《古摹懷素食魚帖的發(fā)現(xiàn)》一文為例。[30]古摹懷素 《食魚帖》是徐邦達(dá)從青島市博物館未清理好的書畫中發(fā)現(xiàn)的,有北宋宣和間吳喆之題跋。經(jīng)過徐邦達(dá)考證,認(rèn)為此乃北宋以前之摹本。理由有幾點:
其一,徐邦達(dá)認(rèn)為:
“此帖墨色濃潤,神采不失……書法高華圓潤,放逸而不狂怪,風(fēng)格在真跡 《苦筍帖》、宋拓本《律公帖》等之間,結(jié)字亦近有來歷的宋人臨本 《自敘帖》,但細(xì)看筆劃稍嫌滯澀,在枯筆中又見有徐徐補描之跡,必是勾廓半臨半摹之本。其勾摹技巧的高超,所見只有唐摹 《萬歲通天進王帖》等,堪與比擬。雖不能如 《苦筍帖》那樣的流暢自如,但結(jié)體筆劃保持懷素書法一定的面目,可謂 ‘下真跡一等’,更非刻拓本可及。”[31]
這是根據(jù)作品的筆法、結(jié)字、風(fēng)格等所謂的書畫本身與相關(guān)其它作品的風(fēng)格對應(yīng)比較,作為判斷的依據(jù),得出結(jié)論。
其二,著重對北宋人吳喆的題跋情況進行反推理,附以項元汴題字、何元英等人的跋文與歷代的收藏印章,鞏固得出的結(jié)論:
“懷素本帖今既定為摹搨,那么,吳喆跋一紙是否從原跡上移來呢?否則為什么他竟稱為真本呢?我認(rèn)為北宋人雖離中唐為近,但他已講到 ‘士大夫家所藏,罕有完者’,可見藏真之跡,在當(dāng)時已經(jīng)相當(dāng)稀少;同時吳氏也不是有名的鑒賞家,此本摹得又如此之精好,吳氏信以為真也是有可能的。再則元明以前的一些鑒賞家對有來歷的勾摹善本,在他們的鑒定題跋中的措辭往往同題真跡一樣,他們不一定不知道這些作品原是摹本。但從唐代以來,鑒賞家習(xí)慣對摹搨本幾乎同真跡一樣的重視,而且當(dāng)時有的也實非作偽,而是為了流傳久遠(yuǎn),所以題跋時就不再加以嚴(yán)格區(qū)分……”[32]
并且徐邦達(dá)指出此卷從跋、印上看,自北宋、元、明、清以來,流傳有序。這是根據(jù)作品的題跋分析推理與印章的流傳情況作為判斷依據(jù)。
其三,查出此卷曾錄于民國初年上海 《神州國光集》,為丁氏韻香館所藏。又對比明人李日華 《六研齋三筆》中所載 《魚肉帖》,除吳跋外,加了李璜、張晏、沈右跋,并從后者的沈右跋文判斷其必為偽作。沈右跋文署為 “延祐五年十月”,徐邦達(dá)考證:
“按沈右生于元末,與錢良右之子錢逵 (伯行)、陳植 (叔方)、陳基 (敬初)等為友,他們都是元末明初的人,因此沈氏不可能在延祐中已能為人題跋。所以此件墨跡雖未目睹,也能斷其必偽。”[33]
又考李日華 《六研齋三筆》、清顧復(fù) 《平生壯觀》、卞永譽 《式古堂書畫匯考》、吳升 《大觀錄》都記載有包括沈氏偽跋在內(nèi)的四跋,因此斷定此 “四記本”可能是據(jù) “丁本”再次摹寫的重摹本。這是借助著錄中記載的跋文內(nèi)容信息,對寫跋者的生平和活動狀況的考證作為判斷依據(jù)之一。
其四,對比 《平生壯觀》《墨緣匯觀》《石渠寶笈》中所記懷素 《論書帖》卷,其中印文與 《食魚帖》上所見全同,跋紙高也大致相等,其后有張晏、趙孟頫跋,兩者均為真跡,而趙跋的內(nèi)容完全同于偽沈右跋。由此可以推斷: “丁本”《食魚帖》后,本有北宋吳喆、李璜、張晏、趙孟頫四跋,大約在明季,被人將李、張、趙三跋拆割去,張、趙二真跋,被配于 《論書帖》中。這些推斷是根據(jù)作品形制和作偽中拆配手段的研究所下的結(jié)論。
最后,徐邦達(dá)評價元代張晏是一位收藏古法書墨跡較多而又有眼光的鑒賞家,他推斷這幅 “丁本”《食魚帖》為唐代臨摹本。又此本所用紙紙面無毛,纖維束較粗,確為麻料,此也可為北宋以前物之一證。這又是以作品的材質(zhì)年代作為斷代的依據(jù)。
從以上徐邦達(dá)對古摹懷素 《食魚帖》的幾點考證,從筆法、題跋、印章、著錄、生平、作偽、作品材質(zhì)等多方面進行對比證明,徐邦達(dá)鑒定書畫的技術(shù)全面細(xì)致可見一斑。
徐邦達(dá)還特別擅長明清書畫作品的鑒定,正如他自己所認(rèn)為的一樣:
“對明清名家作品之真?zhèn)伪鎰e較有把握,因為年代近,且存世作品多,容易掌握,而在此之前的名家作品識辨難度較大……”[34]
對明清書畫的鑒定是徐邦達(dá)的強項,明清書畫留下來的材料和信息相對比較全面,這對徐邦達(dá)技術(shù)全面的鑒定特點來說是最符合的,也是他最得心應(yīng)手的。如 《明清三家繪畫鑒考》,就對王時敏、王鑒、惲壽平三人的生平、各個時期的繪畫風(fēng)格、著錄中對他們的評價一一說明,并列舉考辨三家的諸多作品,包括印章、題跋、筆法、著錄等情況,所收作品之詳細(xì),考證之全面令人嘆為觀止。
注重著錄對書畫鑒定的作用是徐邦達(dá)鑒定書畫的第二個顯著特點。主要表現(xiàn)在:
第一,充分利用歷代著錄書中的記載作為鑒定書畫的依據(jù)。歷代著錄對鑒定書畫的作用有兩個方面,一是可以利用前人著錄中對書畫作者的藝術(shù)面貌和水平高下的評論作為確立的樣板,比較是否與所見書畫相符合,從而為真?zhèn)闻袛嗵峁┮罁?jù)。二是從著錄中可以查到歷代鑒賞家對作品有無詳細(xì)記錄情況,為鑒定提供流傳有序的佐證。徐邦達(dá)在鑒定古書畫時,總是會引出作品在歷代著錄中的記載,然后將著錄中記載的評述與作品相比對,加以細(xì)致的考辨,再提出可信之處與可疑之處并闡述自己的觀點。如 《古書畫偽訛考辨》,引用大量著錄,并將其進行排比、甄別、演繹,顯示了他對歷代著錄的博覽程度和駕馭能力。 《南宋帝后題畫書考辨》,以著錄為核心,把有南宋皇帝皇后題字的繪畫作品分別排出,一一詳細(xì)注明它們所在的著錄,并作考證,列舉的著錄之詳細(xì),考證之精到,充分說明他對歷代著錄的掌握了然于心。著錄雖然只作為書畫鑒定的輔助依據(jù),但徐邦達(dá)已將它運用到了極致。當(dāng)然,徐邦達(dá)雖然在鑒定書畫的實際操作中把著錄放在較為重要的位置,但在理論上也有非常理性的闡述:
“對待著錄也要和對待題跋、鑒藏印記一樣,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著錄中所載,不但傳記未必都確實,即所錄作品中更多有偽跡,不能盡信也不可輕信。古語云: ‘盡信書不如無書’,書并非全不可信,不過我們必須慎加識別與抉擇,以免上當(dāng)。”[35]
這就是徐邦達(dá)考慮問題的全面和謹(jǐn)慎之處。
第二,表現(xiàn)在他本人親身編著的諸多關(guān)于書畫著錄的成果上。《古書畫鑒定概論》中附 《明清書畫著錄書編年表》全面收集記錄了明清的書畫著錄書、作者、編寫年代情況;《重訂清故宮舊藏書畫錄》,把自己過目的故宮書畫按朝代編輯成冊,注明作者、品名、質(zhì)地、藏處,特別詳細(xì)標(biāo)明每件作品的著錄情況,并加以簡單的評語,包括是非真?zhèn)蔚葌€人的見解。這些都是運用著錄鑒定書畫的寶貴資料。《古書畫過眼要錄》[36]記錄了故宮博物院院藏的部分作品,這只是徐邦達(dá)所做的初步工作,他的目標(biāo)是對全國各省市博物館、文管會、文物商店等單位所藏的古書畫,作一次全面考察,編一部內(nèi)容豐富,資料詳實的古書畫著錄書。目前出版的 《古書畫過眼要錄》共分五冊,法書三冊,繪畫二冊,收錄在 《徐邦達(dá)論古書畫匯集》的第二輯中。這部著錄書的規(guī)模與質(zhì)量相對歷代任何一部私家著錄而言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除了編寫書畫著錄,徐邦達(dá)還對古代著錄進行考辨和對比研究。《兩種有關(guān)書畫書錄考辨》對米芾 《山林集拾遺》與 《寶晉英光集》的年代、卷數(shù)、篇目、編次、序跋等作對比考證,證明 《寶晉英光集》乃從 《山林集拾遺》剽竊而來的結(jié)論。另考證了 《宋中興館閣儲藏圖畫記》為 《南宋館閣續(xù)錄》中儲藏欄的內(nèi)容,并非專為一書等等,以為后人運用著錄時提供借鑒。這些兼有資料性和學(xué)術(shù)性的著作,為研究書畫鑒定提供了這個時代的寶貴資料,顯示了徐邦達(dá)在書畫著錄研究方面的特長,是同時代的任何其他鑒定家所不及的。
從幾位中國當(dāng)代權(quán)威鑒定家的鑒定風(fēng)格來看,謝稚柳的筆墨風(fēng)格分析法,啟功的文史文獻考證法和傅熹年的器物圖像考證法都有特殊的傾向性,并把各自的傾向性內(nèi)容做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盡管如此,因為書畫鑒定包含許多領(lǐng)域的知識內(nèi)容,這種帶有傾向個性的鑒定方法總是會顧此失彼,遭受質(zhì)疑。徐邦達(dá)鑒定書畫的手段相對來說是最豐富的,角度和依據(jù)也最多,技術(shù)的全面往往使得大家雖然對鑒定的結(jié)果會有分歧,但他提出的論證過程卻很難讓別人找出破綻,這是令人佩服的一點。但同時,相對其他幾大鑒定家鑒定風(fēng)格的個性鮮明、角度清晰,徐邦達(dá)的鑒定方法也應(yīng)該說是最缺乏個性和最不具想象力的一種。徐邦達(dá)的研究方式要首先確立一個樣板,再一一對應(yīng)作品反映出的信息是否符合,考證符合或不符合的原因,得出解釋。一旦心目中的樣板有偏差或者作品反映出的信息很少,就很難有一個令人信服的圓滿的解釋。這不同于謝稚柳的鑒定方法,即使作品表面表達(dá)的信息很少,他也會通過藝術(shù)家的想象力,合理地生發(fā)出許多依據(jù)和解釋,并自圓其說。對比之下,這是徐邦達(dá)在鑒定研究中所缺乏的。
鑒定家在研究中所表現(xiàn)出的差異——優(yōu)勢和劣勢,其中的原因當(dāng)然與前面所提到的,研究方法的差異與鑒定家所處的環(huán)境影響和個人的知識結(jié)構(gòu)背景息息相關(guān)。謝稚柳雖然為上海博物館的書畫收藏和鑒定作出過卓越貢獻,但他始終沒有完全進入上海博物館的編制,他的工作單位一直屬于上海中國畫院,其實他的真正身份應(yīng)該是一位藝術(shù)家。而啟功的主要身份是北京師范大學(xué)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傅熹年則是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建筑技術(shù)研究院建筑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他們與博物館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但他們都不處在博物館的環(huán)境中。唯有徐邦達(dá)一直在博物館從事專職的書畫鑒定工作將近半個世紀(jì),他的方法是最典型的博物館式的研究。與國外博物館的普遍研究方式一樣,有博物館背景的研究員側(cè)重技術(shù)型的研究,接觸的實物資料多,技術(shù)工作做得扎實,考證詳實,但往往從比較微觀、具體的角度考慮和研究問題,而不象有著藝術(shù)學(xué)、教育學(xué)、歷史學(xué)、建筑學(xué)背景的謝、啟、傅那樣,不僅僅只站在鑒定的本身,而是抽身于書畫鑒定本身之外關(guān)注鑒定之學(xué)。從更為宏觀的視角審視書畫鑒定之學(xué),會得出技術(shù)型操作難以達(dá)到的客觀效果,這是被實踐證明了的,也是許多研究者現(xiàn)在正在逐漸意識到的。
當(dāng)然,任何一種鑒定研究方法都有其長處與缺陷,在沒有找到更為科學(xué)的鑒定方法以前,博物館式的技術(shù)操作型的研究方法還是值得認(rèn)真學(xué)習(xí)的主要方式之一。而以徐邦達(dá)為典型代表的技術(shù)經(jīng)驗加著錄鑒定學(xué)派,也是矗立于眾多當(dāng)代書畫鑒定學(xué)派中的一支最重要的水平標(biāo)桿。
六、書畫鑒定流派特征的比較及與書畫鑒定觀念轉(zhuǎn)型之關(guān)系
由多個處于同一地域或?qū)W術(shù)理念、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研究風(fēng)格相近的個體組成的群體,可以稱之為流派或?qū)W派,此外,一個有著鮮明學(xué)術(shù)觀念和研究風(fēng)格并在相關(guān)領(lǐng)域里得到多數(shù)人認(rèn)可、具有相當(dāng)影響力的個體,也可以形成相應(yīng)的學(xué)派。我們在此處總結(jié)出的當(dāng)代書畫鑒定最有代表性的四大流派,基本上是一個代表人物撐起一個學(xué)派,他們與眾不同的鑒定經(jīng)歷與知識背景,個性鮮明的鑒定風(fēng)格,以及運用各自的鑒定方法解開歷史遺留的疑難雜案的眾多范例,足可以讓他們在中國書畫鑒定史上留下輝煌的一筆。雖然在 “斷案”過程中相互會有爭議,或者因為時代的局限性,他們所作的結(jié)論也會有所偏頗,引起爭議,但他們作為當(dāng)今鑒定界的大師是無可爭議的。當(dāng)然,在這里,我們只以四位鑒定風(fēng)格對比性比較強的流派和鑒定家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其實在當(dāng)代,還有象楊仁愷、劉九庵、王世襄、朱家溍等等各有建樹的書畫鑒定家,本來也都應(yīng)該成為很好的研究對象。
在遼寧博物館工作了半個世紀(jì)的楊仁愷,是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古書畫鑒定組的主要成員,張擇端 《清明上河圖》和米芾 《苕溪詩》得以重見天日,楊仁愷居功甚偉。在鑒定理論研究上,不僅有象 《國寶沉浮錄》等對許多散失的古書畫珍貴資料進行整理而成的著作,還有類似 《簪花仕女圖》等個案的研究文章,更為可貴的,他的理論研究有一個學(xué)術(shù)性較強的體系和框架,從他的力作 《中國書畫鑒定學(xué)稿》中可以略窺一二。《中國書畫鑒定學(xué)稿》的體系,除了其他鑒定家都在研究的鑒別書畫的主要依據(jù)、輔助依據(jù)、書畫作偽等內(nèi)容,還對書畫鑒藏史和歷代書畫鑒定使用的方法作了整理分析,這在一般概論類的書畫鑒定著述中是不多見的。但更值得一提的是,楊仁愷還特別對 “書畫鑒定學(xué)”的概念作了進一步的探討,對 “書畫鑒定學(xué)”進行界說,論述 “書畫鑒定學(xué)”形成的過程、科學(xué)鑒定學(xué)的現(xiàn)實意義等。有這樣一種 “學(xué)”的宏觀的研究視野,在以關(guān)注具體書畫真?zhèn)螢橹饕康牡蔫b定家群體當(dāng)中是難能可貴的,雖然他提出的 “鑒定學(xué)”的概念,還不能等同于現(xiàn)代學(xué)科立場上的 “鑒定學(xué)”,但他的研究思路對將來的建設(shè)書畫鑒定學(xué)科已具有相當(dāng)?shù)囊龑?dǎo)性。這不能不說是楊仁愷對書畫鑒定界學(xué)術(shù)研究的一大貢獻。
楊仁愷之外,在二十世紀(jì)六十年代就與張珩、謝稚柳同為書畫鑒定小組成員的劉九庵,也是當(dāng)代書畫鑒定界的大師級人物。他對書畫鑒定經(jīng)驗豐富,掌握資料周全,觀察細(xì)致,考證嚴(yán)謹(jǐn)精微,曾撰寫發(fā)表了三十余篇學(xué)術(shù)論文,編著了 《劉九庵書畫鑒定集》,涉及如考鑒明人吳卯仿偽祝允明的大量書法作品,對八大山人書畫的研究,張大千偽作名人書畫等,以及在書畫鑒定界最權(quán)威的對明清尺牘的鑒定和研究,都是突破性的學(xué)術(shù)成果。還有王世襄和他的 《錦灰堆》,王世襄在鑒定界是屬于名副其實的雜家,《錦灰堆》匯集了家具、工藝品、雕塑、飲食、雜稿、詩詞等各種內(nèi)容,研究范圍涉及廣且并非泛泛之言,其中對書畫的鑒定研究也頗為精到。王世襄既是雜家,也是公認(rèn)的鑒定專家。與之同時代的鑒定歷代碑帖拓本的權(quán)威朱家溍,也是一位身懷絕技的頂極人物。他們的名字和他們的鑒定思想、鑒定業(yè)績,都在這個時代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
在致力于中國古書畫鑒定研究的專家里,還包括一批臺灣和海外的華裔書畫鑒定家,他們較早地接觸并接受了西方先進的科學(xué)技術(shù)、理論研究方法和觀念,并將其引入中國古書畫鑒定研究中,產(chǎn)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其中頗有代表性的人物有李霖燦 (臺灣)、方聞 (美國)、傅申 (美國)等人。與謝稚柳一樣,李霖燦也是畫家出身,畢業(yè)于杭州藝術(shù)專科學(xué)校,之后又曾從事語言文字學(xué)研究,曾任臺灣故宮博物院院長。在書畫鑒定中,著力于從傳世名跡的技法特征和承傳中尋找斷代的依據(jù),運用科學(xué)的方法,講求以科學(xué)方法系統(tǒng)梳理,鑒定方法具體、操作性強。其著作 《中國畫斷代研究例》《中國墨竹畫法斷代研究》等,都充分證明他在書畫鑒定實踐中對科學(xué)方法的探索,其個案研究成果得到了業(yè)內(nèi)廣泛的關(guān)注和肯定,影響不容忽視。
畢業(yè)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xué)美術(shù)與考古系的方聞,受西方美術(shù)史研究方法的影響和訓(xùn)練,將西方美術(shù)史研究方法引入中國古書畫鑒定中,以風(fēng)格形式分析為著眼點,在古書畫鑒定的斷代分期方面作出了相當(dāng)大的貢獻。他較早提出將繪畫本身的形式結(jié)構(gòu)變化作為斷代的內(nèi)在依據(jù),款識、題跋、印章和著錄為外在依據(jù),這與張珩 “主輔依據(jù)”說頗為接近。但他又同時提出以考古發(fā)現(xiàn)的年代確鑿的繪畫作品作為風(fēng)格比較的第一依據(jù),其方法則更具科學(xué)性。這在其論文與著作中都有所體現(xiàn),如 《論中國畫的研究方法》《心印》《山水畫結(jié)構(gòu)分析》等等。方聞的鑒定方法在個案研究中也得到了深入論證,如對董源 《夏山圖》等的具體案例分析,都充分突出其鑒定方法的獨特性和科學(xué)性。[37]傅申是方聞的學(xué)生,先后任職于美國耶魯大學(xué)和弗利爾沙可樂藝術(shù)博物館,他的書畫鑒定方法在方聞關(guān)注形式與結(jié)構(gòu)的風(fēng)格分析基礎(chǔ)上,更注重筆法在鑒定中的意義,將西方繪畫理論與中國傳統(tǒng)社會文化、畫家文化素養(yǎng)相結(jié)合,找到了理解 “筆性”的科學(xué)依據(jù),這在其著作 《鑒定研究》[38]《海外書跡研究》等等中都有充分表現(xiàn),大大豐富了中國書畫鑒定的方法和語言。
海外的華裔書畫鑒定家雖然在研究方法和影響上尚未達(dá)到諸如謝稚柳、啟功等書畫鑒定大師們開宗立派的程度,但他們的研究成果不僅在應(yīng)用層面上具有廣泛影響,其鑒定方法也顯示出一定程度的科學(xué)性和獨特性,值得普遍關(guān)注與借鑒。
綜觀現(xiàn)當(dāng)代對古書畫鑒定的研究,在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統(tǒng)性方面比前人有了很大的進步。前人在對一件古書畫作品作真?zhèn)闻卸ǖ臅r候,往往只憑感覺講對錯,講依據(jù)時也往往是只字片語,提不出具體可以論證的理由。直到二十世紀(jì)六十年代,才有了相對系統(tǒng)的研究文章,張珩于1964年發(fā)表的理論研究成果 《怎樣鑒定書畫》,可以說是書畫鑒定理論走向系統(tǒng)化和科學(xué)化的轉(zhuǎn)折點。后來謝稚柳、徐邦達(dá)等概論類的鑒定理論又由此基礎(chǔ)深入發(fā)展,不同的書畫鑒定研究方法在他們個案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發(fā)揮和展示。謝稚柳、啟功、傅熹年、徐邦達(dá)等的出現(xiàn),標(biāo)志著當(dāng)代書畫鑒定流派時代的崛起,鑒定流派的形成是二十世紀(jì)八九十年代轉(zhuǎn)型的一個重要標(biāo)志。諸位鑒定大家與所代表的鑒定流派之對于書畫鑒定的觀念以及鑒定方法,與張珩以前的吳湖帆、黃賓虹、張大千時代的差異在于:吳湖帆、黃賓虹、張大千們還是和古代書畫家或書畫鑒定家一樣,將書畫鑒定置于傳統(tǒng)書論、畫論里,與其他如人物品評、作品優(yōu)劣品評混淆在一起,因此它的理論表現(xiàn)形式也是隨筆札記式的,如吳湖帆的 《丑簃談藝錄》、黃賓虹的 《故宮審畫錄》中關(guān)于書畫鑒定的內(nèi)容,都是感悟性的真?zhèn)卧u判語詞,或者對所見書畫的資料記錄再加以簡單地評判真?zhèn)巍_@種鑒定理論觀念和方法,與宋元明清以來涉及書畫鑒定的書畫理論如出一轍,在形式和體例上并沒有突破,沒有時代的標(biāo)志性內(nèi)容。而謝稚柳、啟功、徐邦達(dá)們已經(jīng)通過他們的努力,證明了書畫鑒定研究可以成為不依附于任何書畫理論的一門專業(yè)。無論是書畫鑒定概論類的研究還是具體作品的個案研究,或者是書畫鑒定方法論的獨立探討,把它作為一個獨立的學(xué)科,與其它學(xué)科如美術(shù)學(xué)、考古學(xué)進行相互比較、相互借鑒,都標(biāo)明了書畫鑒定學(xué)在當(dāng)代人的觀念里面逐漸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專業(yè)、獨立的學(xué)科。當(dāng)然,這首先要歸于張珩的篳路藍(lán)縷之功,他率先提出了 “書畫鑒定之學(xué)”這個概念,試圖用科學(xué)的方法來分析、辨別古代書畫的真?zhèn)巍R钥茖W(xué)的鑒定意識取代審美的鑒賞意識,是中國書畫鑒定觀念轉(zhuǎn)型的標(biāo)志之一。然而,張珩時代還只是書畫鑒定觀念轉(zhuǎn)型的始發(fā)期或者說是過渡期。因為張珩時代整個社會對書畫收藏、交易的熱度以及社會認(rèn)同度相對不高,對書畫鑒定還不夠重視,業(yè)內(nèi)人士也沒有意識到書畫鑒定在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的重要性。大多數(shù)同時代的人對張珩超前的鑒定理論不能完全理解和認(rèn)同。在當(dāng)時,也沒有幾大家運用自己的鑒定方法對一件作品進行激烈爭論的學(xué)術(shù)平臺,沒有經(jīng)過眾多學(xué)者對鑒定方法論的深入探討。這些,只有在謝稚柳、啟功、徐邦達(dá)的流派時代才真正得以發(fā)揮,因此,我們才認(rèn)為:走向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的書畫鑒定流派時代,是書畫鑒定觀念的真正轉(zhuǎn)型時期。
謝稚柳、啟功、傅熹年、徐邦達(dá)的書畫鑒定流派時期所呈現(xiàn)出的觀念形態(tài),不同于張珩時代和吳湖帆、黃賓虹、張大千時代的書畫鑒定觀念,當(dāng)然也會不同于未來的書畫鑒定觀念和鑒定方法。書畫鑒定流派紛呈是當(dāng)今時代的產(chǎn)物,它只屬于這個時代。從目前對書畫鑒定人才的培養(yǎng)方式來看,今后的書畫鑒定研究者可能大多是經(jīng)歷過科班的專業(yè)培養(yǎng),學(xué)習(xí)相關(guān)的鑒定知識、全面的鑒定理論和相關(guān)的美術(shù)學(xué)、文獻學(xué)方面的知識。處在同一個時代的相同的知識結(jié)構(gòu)背景,鑒定觀念不會有太大的差異。因此今后的專業(yè)人才不再會象謝稚柳、啟功、徐邦達(dá)們一樣集文博、收藏、鑒定、詩文、詞曲、書法、繪畫等諸多傳統(tǒng)文化領(lǐng)域的突出成就于一身,也不會有他們那樣不同的藝術(shù)背景、學(xué)術(shù)背景和鑒定經(jīng)歷,以及凸現(xiàn)出時代烙印的個性鮮明的書畫鑒定方法和鑒定模式。當(dāng)然,今后的書畫鑒定也會有自己的時代特征,但無論如何,處在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的流派時代的鑒定模式,無論是與之前或之后的鑒定模式相比,都堪稱是空前絕后的,它是由鑒定大師們撐起的書畫鑒定時代,或許可以更進一步推論:流派時代的過去也將意味著大師時代的過去。
流派的形成標(biāo)志著對書畫的鑒定逐漸由辨識真?zhèn)蔚慕诩夹g(shù)性工作上升到學(xué)術(shù)研究水平,這是書畫鑒定觀念轉(zhuǎn)型的一個重要方面。觀念的轉(zhuǎn)型是符合這個時代的要求的,因此是進步的。但在轉(zhuǎn)型的過程中也會顯示出這個領(lǐng)域本身的時代局限性。比如:
將書畫鑒定家與同時代的其它領(lǐng)域的專家學(xué)者相比較,我們會發(fā)現(xiàn)無論是政治學(xué)家、經(jīng)濟學(xué)家、社會學(xué)家、文學(xué)家、科學(xué)家,或是藝術(shù)學(xué)科的其它門類的大師級人物,大多是學(xué)貫中西,既有深厚的傳統(tǒng)文化基礎(chǔ),又接受過體系完整的西式教育和西學(xué)思想的熏染。但鑒定界的大師們卻大多沒有接受過正規(guī)學(xué)校教育,而是靠多年的實踐經(jīng)驗逐漸確立專業(yè)地位。因此,他們的知識結(jié)構(gòu)相對比較單一,思維的局限性較大,很難從一個宏觀的角度來考慮書畫鑒定學(xué)科的構(gòu)建問題。
此外,由于書畫鑒定的實用技術(shù)功能,導(dǎo)致理論研究者必須以實踐經(jīng)驗的積累為前提,即鑒定理論家首先必須懂得如何鑒定具體的書畫,必須具備鑒定書畫的能力才能在理論研究領(lǐng)域有一席之地。這就使鑒定理論研究的范圍始終囿于以實踐為前提,最終又以實踐為目的的樊籬中,張珩、謝稚柳、啟功、徐邦達(dá)等等都不例外。在這個領(lǐng)域,還缺乏具有學(xué)理性視野與學(xué)術(shù)展開能力的純粹的理論家,因此,哪怕是幾個鑒定學(xué)派的研究成果相加或進行組合,還是難以構(gòu)成一個學(xué)科概念的完整的理論體系。
那么,由此我們可以總結(jié)書畫鑒定在這個時代所具有的成果,以反映權(quán)威鑒定家為主導(dǎo)的書畫鑒定流派時期的總體特征:二十世紀(jì)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是中國書畫鑒定以權(quán)威鑒定家的個人魅力為主導(dǎo),以鑒定家的實踐成就和成果為支撐的時代。
因為時代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大環(huán)境的制約,以及書畫鑒定本身的復(fù)雜性和實踐操作的高難度,決定了它并非人人都可以參與的金字塔尖上的一門專業(yè),能被稱為書畫鑒定家的可謂鳳毛麟角,而他們的學(xué)術(shù)背景和鑒定才能也可謂名至實歸。這個時代的書畫鑒定,實質(zhì)上就是圍繞著這些權(quán)威鑒定家的鑒定活動和鑒定學(xué)術(shù)研究而展開的,他們引領(lǐng)著整個時代的書畫鑒定的發(fā)展方向。
另外,書畫鑒定在這個時期的相關(guān)研究主要體現(xiàn)在鑒定家的鑒定實踐成就,以及在理論研究上的多項學(xué)術(shù)成果。包括為國家文物部門征集、搜集民間的古書畫和幾次全國性的古書畫巡回鑒定,不僅為國家保存了大量的文物古跡,而且為博物館和文物單位的書畫文物確定了真?zhèn)魏偷燃墶R詫嵺`活動為平臺,理論研究學(xué)術(shù)成果層出不窮:對作品真?zhèn)蔚奶骄俊ψ髌氛鎮(zhèn)蔚臓幷摗嬭b定方法的討論……可以說,這些純粹的實踐活動和學(xué)術(shù)研究內(nèi)容,基本上代表了此時書畫鑒定的主要性質(zhì)和生存狀態(tài)。
正規(guī)、高端的書畫鑒定實踐活動為書畫鑒定研究的發(fā)展帶來的積極影響,是為鑒定家們的書畫鑒定理論研究和爭論探討提供了絕佳的學(xué)術(shù)氛圍和平臺。不難發(fā)現(xiàn),我們提出的上述幾大鑒定家的不同鑒定方法以及以此形成的鑒定流派,是在對同一件作品的爭論中才得以顯現(xiàn)。其結(jié)果是,只有在真槍實劍的學(xué)術(shù)爭論中,為了證明己方結(jié)論的可靠性和學(xué)術(shù)研究的嚴(yán)肅性,鑒定家們會竭盡所能列舉出各自的鑒定依據(jù)、鑒定理由、鑒定方法。而在平常的書畫鑒定中,此時的鑒定家們還是與古代鑒定家一樣,以傳統(tǒng)目驗的方法,憑感覺而作出真?zhèn)谓Y(jié)論。盡管憑依據(jù)、講證明的書畫鑒定觀念還無法成為這一時期的普遍定勢,但是,我們已經(jīng)在書畫鑒定的研究成果中尋找到了強烈的科學(xué)意識與理論要求。科學(xué)意識表現(xiàn)在:不是憑主觀感覺和臆測,而是對過程有科學(xué)的因果推理,對依據(jù)和結(jié)論有充分、有據(jù)的考證和證明。理論要求表現(xiàn)在:不是零散、隨意的敘述,而是有嚴(yán)謹(jǐn)?shù)睦碚摻Y(jié)構(gòu)、有系統(tǒng)的邏輯構(gòu)架的科學(xué)論述方式。這對于現(xiàn)代書畫鑒定研究來說是很好的開端,是書畫鑒定觀念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重要標(biāo)志。
[1]鄭奇、金丹 《三大鑒定家與書畫鑒定學(xué)》,見 《榮寶齋》,2003年,第5期。
[2]沈士君 《巨眼行天下——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始末》,見 《收藏》,2003年10月,總第130期。
[3]同上。
[4]鄭重著 《中國文博名家畫傳之謝稚柳》,文物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34頁。
[5]鄭重著 《壯暮堂——與大師談藝之謝稚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第2頁。
[6]謝稚柳著 《中國古代書畫研究十論》,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5月,第5頁。
[7]同上,第14頁。
[8]謝稚柳主編《中國書畫鑒定》,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1月,第194頁。
[9]謝稚柳著 《中國古代書畫研究十論》,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5月,第42、43頁。
[10]謝稚柳著 《中國古代書畫研究十論》,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5月,第44頁。
[11]同上,第44、45頁。
[12]同上,第55頁。
[13]謝稚柳著 《中國古代書畫研究十論》,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5月,第155、156頁。
[14]鄭重著 《謝稚柳系年錄》,王遽常序,上海書店出版社,1991年。
[15]侯剛著 《中國文博名家畫傳——啟功》,文物出版社,2003年12月,第22頁。
[16]啟功著《啟功叢稿·題跋卷》,中華書局,1999年7月,第89頁。
[17]同上,第92頁。
[18]楊仁愷著 《楊仁愷書畫鑒定集·唐張旭的書風(fēng)和他的 〈古詩四帖〉》,河南美術(shù)出版社,1999年4月。
[19]啟功著 《啟功叢稿·論文卷》,中華書局,1999年7月,第79、80頁。
[20]啟功著 《啟功叢稿·題跋卷》,中華書局,1999年7月,第94頁。
[21]同上。
[22]朱威、王征 《啟功辭世:揮別漸行漸遠(yuǎn)的大師時代》,《文物天地》,2005年8月。
[23]傅熹年 《淺談做書畫鑒定工作的體會》,見 《傅熹年書畫鑒定集》,第9頁。
[24]《談?wù)勛鰰嬭b定工作的體會》,傅熹年著 《傅熹年書畫鑒定集》,河南美術(shù)出版社,1999年4月。
[25]傅熹年著 《傅熹年書畫鑒定集》,河南美術(shù)出版社,1999年4月。
[26]沈從文 《從新文學(xué)轉(zhuǎn)到歷史文物》,載自 《花花朵朵壇壇罐罐》,江蘇美術(shù)出版社,2002年8月。
[27]沈從文 《我為什么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載自 《花花朵朵壇壇罐罐》,江蘇美術(shù)出版社,2002年8月。
[28]同上。
[29]民國時期上海著名的紅頂商人周湘云的書畫收藏大部分都是由趙叔孺 “掌眼”,因為趙叔孺學(xué)識淵博,品格又高,所以周家古代書畫收藏之富、檔次和格調(diào)之高都是頗有聲名的。(見鄭重著 《海上收藏世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1月)
[30]《文物》,1979年,第2期。
[31]《文物》,1979年,第2期,第11頁。
[32]同上,第12頁。
[33]同上,第13頁。
[34]朱明堯 《鑒定大家徐邦達(dá)》,《榮寶齋》,2003年7月。
[35]徐邦達(dá) 《古書畫鑒定概論》,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10月。
[36]已出版書法二冊,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1987年。
[37]WenFang,SummerMountains,TheMetrolitanMuseumofArt,1975。
[38]ShenFuandMarilyn,FuStudiesinConnoisseurship,PrincetiontheArtofMuseum,PrincetionUniversity,1973。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