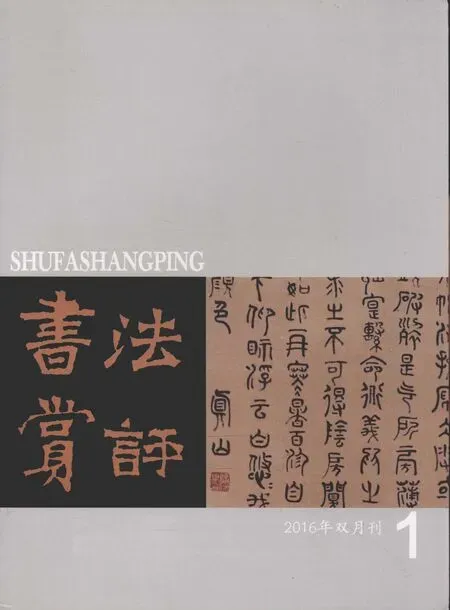唐代 “尚法”書風(fēng)的形成及其表現(xiàn)形式
■張福朋
唐代 “尚法”書風(fēng)的形成及其表現(xiàn)形式
■張福朋
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玄學(xué)占據(jù)了統(tǒng)治地位,崇尚 “清談之風(fēng)”。士大夫們的藝事品評(píng)圍繞著 “二王”而展開構(gòu)成了藝術(shù)品評(píng)觀。唐太宗時(shí)期重視 “大王”書風(fēng),全國(guó)自上而下形成了崇王的熱潮。南北書風(fēng)的合流促使了唐代尚法的確立。自魏晉南北朝以來,楷書書體的演變逐漸穩(wěn)定,同時(shí)唐代科舉考試要求 “楷法遒美”“皆得正詳”。以及唐代重要書家如歐、虞、褚、薛的推動(dòng),促使唐代書法 “尚法”風(fēng)格形成。唐 “法”是一種特指,它是唐代人追求和建立起來的書法藝術(shù)法度,構(gòu)成唐代書法藝術(shù)學(xué)習(xí)與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形式。
一、唐代尚法書風(fēng)的形成
1.隋代書法的沿襲
隋代為時(shí)雖短,但從北周開始經(jīng)隋,書法已出現(xiàn)了南北書風(fēng)統(tǒng)一的趨勢(shì)。初唐書家歐、虞大半生生活在陳,經(jīng)北周、隋入唐,書名始顯,從而成為將北周、隋開始的南北書風(fēng)融合傾向向唐延伸的傳遞者。隋之南北書風(fēng)的融合主要由北趨南為指向,其中,楷書體現(xiàn)得最為明顯。南北朝時(shí)北方主要以奇崛剛健、質(zhì)樸中帶有某種粗獷之趣為書法的主要特征。至隋,北方楷書亦由質(zhì)趨文,標(biāo)志著楷書已形成了完全成熟的技法和審美定勢(shì)。徐利明說:“縱觀隋代書法的發(fā)展大勢(shì),無論從刻石方面考察,還是從墨跡作品中研析,都表現(xiàn)為在集南北朝書法之大成的同時(shí),對(duì)王書筆勢(shì)類型的今體書法加以整理,使之在兼容南北有所變化的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規(guī)范化、法度化。”[1]隋代為唐代 “尚法”書風(fēng)做了鋪墊。
“唐代書法風(fēng)格多種多樣,但有代表性和典型意義的唐代書風(fēng),則是指正大雄強(qiáng)、法度嚴(yán)謹(jǐn)、直抒胸臆的風(fēng)格。這個(gè)書風(fēng)的形成經(jīng)歷了從無到有、從微到顯的過程。而此過程的開端是在隋朝。”[2]從而為唐成為中國(guó)書史上最恢弘的時(shí)代奠定了基礎(chǔ)。
2.“二王”書法的傳承
唐代書法風(fēng)貌是在崇尚王羲之為代表的晉人風(fēng)尚基礎(chǔ)上形成的。“二王”的行草書具有實(shí)用和藝術(shù)的審美價(jià)值,王字 “中和之美”能適應(yīng)最廣泛的社會(huì)需求。此后兩千多年,漢字的結(jié)構(gòu)、形態(tài)都無法脫離王羲之的影響。“大王書筆致清勁而血脈通暢,輕而不薄,秀兒不弱,玉光內(nèi)蘊(yùn)。小王書雪柔豐腴,行筆轉(zhuǎn)折幅度較大,顯得八面來風(fēng),左右逢源,神旺氣足,金彩外敷。二王書法正好相輔相成,具備了領(lǐng)導(dǎo)書壇兩千年的強(qiáng)大生命力。”[3]隋代的智永是 “二王”書法的忠實(shí)繼承者,他曾臨寫 《真草千字文》800本,對(duì)傳播王氏書法起到了極大地推動(dòng)作用。他將書法技藝傳給虞世南,啟發(fā)了唐代書法的第一代人物。至盛中唐之交,才以顏真卿為標(biāo)志,在創(chuàng)作上有一個(gè)較大的突破。在行草書方面,主要受王派書法的影響,但又有不同程度的改變,虞世南草書和孫過庭 《書譜》,其用筆不及羲之渾厚豐滿,在氣勢(shì)上顯然加強(qiáng)了奔騰急速的運(yùn)動(dòng)節(jié)奏,顯示唐草走向酣暢浪漫書風(fēng)的跡象。至賀知章、張旭、顏真卿、懷素,唐代的浪漫寫意書風(fēng)得到充分的展現(xiàn)。
3.時(shí)代因素的影響
唐王李世民,他以開國(guó)君主的地位大力提倡書法。他親自撰寫 《王羲之傳》,為書壇樹立了典型。貞觀元年,詔設(shè)弘文館,設(shè)書法一科,規(guī)定 “貞觀元年,勒見任京官、文武職事五品以上,有性愛學(xué)書及有書性者,聽于館內(nèi)學(xué)書”。[4]由歐陽詢、虞世南執(zhí)教,不僅迅速提高了唐代書家的素質(zhì),更振奮了全社會(huì)學(xué)習(xí)書法的風(fēng)氣,提高了書法在諸多藝術(shù)門類中的地位。
同時(shí),唐代在翰林院設(shè)有侍書學(xué)博士,國(guó)子監(jiān)亦有書學(xué)博士。唐代科舉考試中,設(shè)有書科,“常貢之科有秀才,有明經(jīng),有進(jìn)士,有明法,有書、算”;[5]在唐代的官吏選拔中,“凡擇人之法有四,即身言書判”,[6]其中 “書”的要求就是 “楷法遒美”,唐朝書法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學(xué)習(xí)的基本方向。在科舉考試大背景下,書法成為朝庭選用人才的標(biāo)準(zhǔn),從而導(dǎo)致干祿字書盛行,刺激了唐代書法的發(fā)展。科舉考試更進(jìn)一步通過書法教育促進(jìn)了 “法”的規(guī)范化。因此,唐代書法的興盛超過以往的任何一個(gè)時(shí)代,“舊時(shí)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書法成了人人得而習(xí)之的一項(xiàng)技能,唐代書法成為一種自覺的藝術(shù)深入到人們的生活當(dāng)中,成為大家所接受的藝術(shù)。
二、唐代尚法書風(fēng)的表現(xiàn)形式
1.楷書法則的奠定
“唐立國(guó)之初,書壇呈興盛趨勢(shì),其時(shí)書壇執(zhí)牛耳者有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其楷書結(jié)字以斜畫緊結(jié)為主體,歐陽詢父子脫胎于北魏顯得峻嚴(yán)方飭,虞世南則平正和美,與智永、丁道護(hù)一脈相承,褚遂良上溯北齊《龍藏寺》變?yōu)槠疆媽捊Y(jié)。”
唐代的科舉制及相應(yīng)提出的對(duì)文字字形規(guī)范的端正的要求,改變了人們的書法審美標(biāo)準(zhǔn),法度成為人們衡量書法的主要標(biāo)尺。“所謂的 ‘法’,就是指客觀造形規(guī)律。在這一點(diǎn)上,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虞字的凝練、歐字的嚴(yán)謹(jǐn)、褚字的疏朗,都表現(xiàn)出平衡的美、次序的美,都是努力追求客觀規(guī)律的。”[7]其中歐陽詢?yōu)樽钔怀龅拇恚瑲W體書法的成就在于 “正”和 “險(xiǎn)”,“四面停勻、八邊具備、短長(zhǎng)合度、粗細(xì)折中。心眼準(zhǔn)程、疏密欹正。筋骨精神,隨其大小。不能頭輕尾重,無準(zhǔn)程、疏密欹正。筋骨精神,隨其大小。不可頭輕尾重,無令左短右長(zhǎng),上稱下載,東西映帶,氣宇交融,精神灑落。”[8]歐陽詢的 《九成宮》,不僅間架結(jié)構(gòu)高度穩(wěn)定,而且點(diǎn)畫筆法也日臻成熟,為唐代楷書奠定了基礎(chǔ)。他的字成為千百年來漢字講求端正的無可非議的典范,以至宋以后將歐字刻成字模,成為標(biāo)準(zhǔn)印刷體。黃庭堅(jiān) 《山谷題跋》:“回視歐虞褚薛、徐浩、沈傳師輩,皆為法度所窘。”繼歐虞之后,與褚薛、顏柳一起并稱 “唐楷六大家”,把唐代的楷書推向了高潮。
2.“顏筋柳骨”成為唐法典范
唐代的楷書發(fā)展到鼎盛時(shí)期,其用筆講究、風(fēng)格剛健,達(dá)到書法形式與內(nèi)容的完滿融合。顏真卿的早期楷書《多寶塔》《東方朔畫贊碑》,用筆起落頓按分明,橫線稍細(xì)而呈弧勢(shì),豎畫較粗而取直,筆勢(shì)稍內(nèi)。結(jié)體則注重疏密開合的參差,其時(shí)已顯示出筆勢(shì)雄渾、體勢(shì)寬博的最初跡象。中后期的楷書體勢(shì)相向,字之空間擺布力求勻稱,創(chuàng)造了內(nèi)疏外密的結(jié)字法,形成了質(zhì)樸、敦厚、體勢(shì)雄放的獨(dú)特風(fēng)格,重氣象、求氣勢(shì)的典型風(fēng)格完備。顏真卿的楷書 “穩(wěn)實(shí)而利民用”“左右基本對(duì)稱,出之以正面形象,渾厚剛健,方正莊嚴(yán),齊整大度”“納古法于新意,生新意于古法之外”,打破了王羲之的標(biāo)準(zhǔn),創(chuàng)造了雄強(qiáng)奇?zhèn)ァ⒊梁衲氐目瑫裾{(diào)。郝經(jīng):“書至于顏魯公,魯公之書又至于 《中興頌》,故為書家規(guī)矩準(zhǔn)繩之大匠。”柳公權(quán)楷書師法顏真卿,其字結(jié)體瘦長(zhǎng),棱角分明,方折峻麗,以勁健為主,趨于清瘦一路,被后世稱為 “顏筋柳骨”,在形式和技巧上確立了唐法典范,表現(xiàn)了雍容、寬博的時(shí)代特征。唐代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quán)三大楷書家創(chuàng)作的書體,應(yīng)該說是現(xiàn)代規(guī)范漢字的前身,是官方對(duì) “法”的規(guī)范和引導(dǎo)的具體表現(xiàn)。
3.狂草 “法”與 “情”的結(jié)合
張旭和懷素的狂草書代表唐代行草書的最高成就,有 “張顛醉素”之稱。盡管其真書和草書在表現(xiàn)特征上有極為懸殊的差別,但其筆法在本質(zhì)上卻是一致的。張旭草書一改唐人風(fēng)貌,大量使用連筆,從而使章法、結(jié)體、墨法發(fā)生連續(xù)性的變化,展現(xiàn)出連綿不絕的壯美氣勢(shì)。懷素用筆純以中鋒,筆法高度凝練,點(diǎn)劃盡量減少形態(tài)上的細(xì)節(jié),而將線條的奔縱放逸氣勢(shì)作為審美的第一要素。筆法的高度凝練要以深厚的功力為基礎(chǔ),可知?jiǎng)?chuàng)作者早年必經(jīng)過長(zhǎng)期的真書訓(xùn)練。貫休 《觀懷素草書歌》云 “固宜須冷 (令)笑逸少,爭(zhēng)得不心醉伯英”,懷素雖取法 “二王”但卻絲毫不受約束,取法 “二王”而又遠(yuǎn)超 “二王”之外。張旭 “揮毫落紙如云煙”,懷素 “滿壁縱橫千萬字”。二人同處尚法時(shí)代,其狂草 “醉不失態(tài)”、“顛不越度”,草而不失法度。張旭以狂草書的歷史意義更多地表現(xiàn)在對(duì) “二王”草書的 “破”,而懷素草書的歷史意義則更多地體現(xiàn)在對(duì)狂草模式法度的“立”。二人將書法的內(nèi)在藝術(shù)規(guī)律在書法創(chuàng)作中得到了充分的運(yùn)用和體現(xiàn),“尚法”與 “尚情”完美結(jié)合,成為今草書的極端形式,從而創(chuàng)立了狂草的基本法度。
4.“尚法”在書法理論中的體現(xiàn)
隨著書法藝術(shù)的繁榮,帝王的大力提倡,唐朝書法理論也隨之有了更大的發(fā)展。唐朝書法理論中確實(shí)存在很多關(guān)于書寫技法、結(jié)構(gòu)方法的要求。如張懷瓘 《玉堂禁經(jīng)》談?dòng)霉P、筆勢(shì)、結(jié)構(gòu)問題,韓方明 《授筆要說》、盧攜 《臨池訣》、林蘊(yùn) 《撥燈序》是關(guān)于執(zhí)筆方法的探討。
唐代的技法理論已相當(dāng)完備、精細(xì),尤其是楷書技法,與唐代楷書在書史上輝煌的一頁(yè)相呼應(yīng)。如歐陽詢的《三十六法》詳述了書法中漢字的框架及筆勢(shì)。中庸,合度,和諧,平衡,這是唐人 “重法”的目的。歐字法度嚴(yán)謹(jǐn),一絲不茍,唐人尚法,歐陽詢更為典型。張懷瓘的 《書斷》在審美觀上也將晉人瀟灑飄逸之風(fēng)轉(zhuǎn)變?yōu)闉⒚摫家荨⒒趾雽挷鈩?shì)和博大氣象。孫過庭 《書譜》已有相當(dāng)可觀的創(chuàng)作論框架,它涉及到創(chuàng)作思維、創(chuàng)作過程、內(nèi)容與形式、形質(zhì)與神采、繼承與創(chuàng)新等內(nèi)容。從唐開始,書法評(píng)論中以自然無相作比喻的方式日益減少,而對(duì)技法和書法自身形象的理解與評(píng)價(jià),乃至?xí)覀€(gè)人氣質(zhì)的審視及在書法中的體現(xiàn),成為書法批評(píng)的重要內(nèi)容。
總之,唐人尚法書風(fēng)的形成,不僅提高了中國(guó)書法的社會(huì)地位,而且是一種標(biāo)志。“法”作為一種規(guī)定、法則、標(biāo)準(zhǔn),為后人提供了長(zhǎng)久學(xué)習(xí)和仿效的范本。學(xué)習(xí)書法必需懂得書法藝術(shù)的基本特征和普遍法則。既要在書法繼承中思索,更要在書法借鑒中思索。
[1]張福朋,女,呂梁學(xué)院。
[2]徐利明.中國(guó)書法風(fēng)格史 [M].北京: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09。
[3]中國(guó)書法發(fā)展史.中國(guó)教育學(xué)會(huì)書法教育專業(yè)委員會(huì)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4]蕭元.中國(guó)書法五千年 [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
[5]朱關(guān)田.中國(guó)書法史 (七卷本)隋唐五代卷 [M].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
[6]朱關(guān)田.中國(guó)書法史 (七卷本)隋唐五代卷 [M].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
[7]朱關(guān)田.中國(guó)書法史 (七卷本)隋唐五代卷 [M].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
[8]黃敦、李昌集、莊熙祖.《書法篆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9]熊秉明.中國(guó)書法理論體系 [M].北京: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
[9]潘文告.中國(guó)歷代書論選 (上下)[M].長(zhǎng)沙: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2007。
作者單位:呂梁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