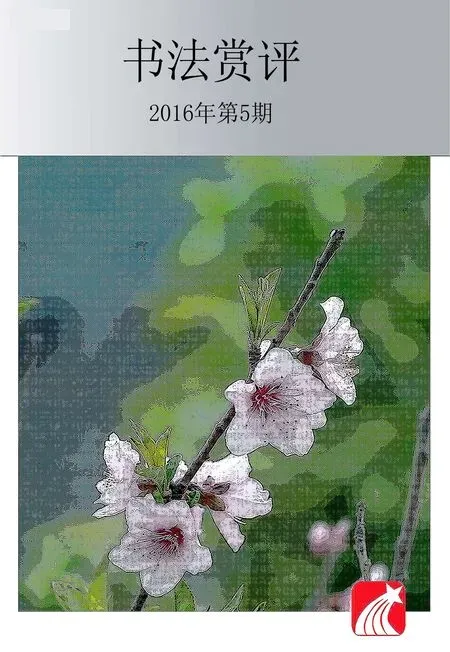疑古與復古
——宋代士人學術風氣與唐宋草書流變
■吳旭春
疑古與復古
——宋代士人學術風氣與唐宋草書流變
■吳旭春
唐、宋是草書發展的重要時期。唐代草書在“顛張醉素”的引領下,被推向激情奔放、狂逸宏博的藝術境界,達到抒情寫意的最高峰,使書法成為了具有強烈抒情性的藝術門類。而至宋代,草書無論是筆法、風格亦或是草書理論都有了很大的轉變,由唐草外向性的宣情達意轉向了內省式的理性表達,使草書獲得了新的面目和內涵,并影響了后人對草書的理解,改變了后世草書發展的方向。
唐宋草書流變與唐宋社會變革、書法自身發展、社會審美風尚等諸多因素密切相關,而宋代士人“疑古”與“復古”這兩股學術風氣的興盛轉變,也對唐宋草書流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促進了草書的變革。
一
文化的轉型往往會帶動士人疑古思潮的勃興。文化轉型過程中舊的學術逐漸表現出內在的矛盾和局限,與新興的學術思想日益格格不入,從而萌發士人開拓思路、大膽疑古的風氣。唐宋文化轉型過程中更是如此,文化的轉型促進了宋代士人疑古思潮的興盛。唐中后期開始,以柳宗元為代表疑古思潮開始產生,學術不再謹守儒家經學的義疏,而是大膽疑辨,自我思考,對古書、古史進行新的詮釋。到了宋代,學術界的疑古辨偽思潮蔚然成風。開創宋代疑古新學風的是歐陽修,他不墨守漢唐注疏,力排舊說,提出自己的見解。如其曾云“自秦漢以來,諸儒所述,荒虛怪誕,無所不有”,[1]否定先儒注疏的曲解及牽強附會之處,而強調從經義本身進行理解。在歐陽修的引領下,宋代出現了大批疑古辨偽學者,如王安石、蘇軾、鄭樵、朱熹等,疑古辨偽成為學術界盛行的風氣。
宋代士人的疑古風氣對草書發展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宋書家不拘泥經典,不盲從經典,以疑古的精神對宋之前的經典法帖進行理性的分析,在習書方法、作品取法、作品風格、作品真偽等多個方面都進行理性的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
如黃庭堅曾云:“蘭亭雖是真行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劃以為準,譬如周公孔子不能無小過,過而不害其聰明睿圣,所以為圣人。不善學者,即圣人之過處而學之,故蔽于一曲。今世學蘭亭者,多此也。”[2]宋人崇晉,以晉人書法為宗,《蘭亭序》在宋人眼中具有較高的地位。對于這樣的經典,黃庭堅仍不盲從,以辯證理性的態度來對待。
在對待草書作品的真偽上,宋人也充分體現了疑古理性的學術風氣。如黃庭堅《跋懷素千字文》云:“此《千文》用筆不實,決非素所作,書尾題字亦非君謨書。然此書亦不可棄,亞棲所不及也。”[3]黃庭堅從用筆斷定此作為偽作,君謨題字亦為偽作,然而黃庭堅并沒有因為是偽作而忽視其藝術價值,仍然以“亞棲所不及”之語對其藝術價值作了恰如其分的評價定位。
再如黃庭堅對張旭作品真偽的辨別,亦有其獨特、理性的看法。如其云“張長史行草帖多出于贗作。人聞張顛,未嘗見其筆墨,遂妄作狂蹶之書托之長史。其實張公姿性顛逸,其書字字入法度中也。”[4]又云:“顏太師稱張長史雖姿性顛佚,而書法極入規矩也。故能以此終其身而名后世。如京洛間人傳摹狂怪字,不入右軍父子繩墨者,皆非長史筆跡也。”[5]他對作品真偽有著清晰而理智的辨別標準。
而疑古風氣在書法上最突出的表現在于宋書家對唐草的復雜態度上。唐代大草將草書的情感表現及自由精神發展到極致,狂放、宣情成為唐代草書的主要特征,唐代草書成為草書發展史上最奔放的一頁,而張旭、懷素草書無疑成為大草的典范。然而隨著社會文化的轉型,在疑古風氣的影響下,北宋書家對唐大草書風卻較多批評抨擊之辭,對張旭、懷素也表現出較為復雜的態度。
如蘇東坡雖曾夸贊張旭:“張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6]但是其又有詩云:“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鐘,妄自粉飾欺盲聾。有如市娼抹青紅,妖歌漫舞眩兒童。”[7]諷刺了張旭、懷素顛狂、做作的創作狀態,可以看出他對唐草的真實想法。而米芾在《論草書帖》中的批評更為激烈:“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辯光尤可憎也。”在米芾眼中,懷素尚能稍到天成,張旭則是變亂古法的典型,高閑之流更是令人憎惡,米芾從筆法傳承的角度對唐草書家進行了質疑和抨擊。又云:“公權丑怪惡札祖,從茲古法蕩無遺。張顛與柳頗同罪,鼓吹俗子其亂離。懷素簶獠小解事,僅趨平淡如盲醫。”將張旭和柳公權作為變亂古法的代表。再如黃伯思云:“草法之壞,肇張長史……此諸人書非不工也,而缺古人之淵源。”[8]與米芾的“變亂古法”之說如出一轍。
作為宋草代表書家的黃庭堅,其草書取法懷素,對旭素草書較多稱贊,沒有非議之句。但其草書疑古思想與蘇軾、米芾是相通的。縱觀黃庭堅論書,對張旭草書的稱贊主要集中在顛逸而入規矩、雖縱逸而法度森嚴這一方面,如其所云“蓋其姿性顛逸,故謂之張顛,然其書極端正,字字入古法。”[9]但是在尊崇張旭的同時,他對另一位草書家亞棲則提出了強烈的批評。如“蓋草書法壞于亞棲也”、[10]“書尾小字,唯余與永州醉僧能之,若亞棲輩見當羞死”[11]等。亞棲為晚唐五代草書僧,其論書以求變為要,黃庭堅將其作為典型猛烈批評了晚唐之后狂怪猖獗的草書之風。由黃庭堅的尊張旭貶亞棲之論可以看出其對唐草書風的理性辯證思考,他所尊崇的不是大草的狂放,而是大草的法度。因此他以宋人的意趣和理性對顛狂的唐草進行了改造,以冷靜理性的安排經營消解了唐草的激情狂野,賦予了大草平和簡靜之氣,以自己的草書實踐改變了大草的發展趨向。
北宋書家對唐草尚能持著褒貶不一的復雜態度,對唐草書風亦是有接受的批評。而至南宋,士人對唐草則采取了更為偏激的批評態度。如趙孟堅所云:“晉賢草體,虛淡蕭散,此為至妙。唯大令綰秋蛇,為文皇所譏。至唐旭、素,方作連綿之筆,此黃伯思、簡齋、堯章所不取也。今人但見爛然如藤纏者,為草書之妙,要之晉人之妙不在此,法度端嚴中,閑散為勝耳。”[12]此論在南宋書論中頗具典型性,對旭素為代表的唐代大草的“連綿”“藤纏”的大寫意風格進行了全面的否定,而將虛淡蕭散、法度端嚴作為草書的最佳境界。趙孟堅的評論過于偏頗,但實際反映了疑古風氣下南宋士人對唐代草書經典的懷疑態度。
疑古的學術風氣使宋人對草書保持著理性的創作與研究態度,打破唐草書風的發展定勢,為草書發展開拓了新的發展方向,促使草書由感性朝著理性的方向轉變,推動了唐宋草書的流變轉型。疑古風氣對唐宋草書流變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其一,創作精神的轉變。唐大草書家將草書作為情感宣泄的途徑,以奔放的情感和豪邁的氣勢打動人心,追求顛狂怪異的書寫狀態,追求草書創作的表演性,無論是草書作品還是草書創作狀態都具有極強的表現力,使唐大草達到書法抒情寫意的最高峰。但宋草書家并未因循唐草的這種創作精神,而是強烈批評了唐草狂怪做作的創作精神和狀態,以理性的思維、適意的狀態來創作草書,強調情感表現的適度。“于靜中坐,自是一樂事”[13]成為宋人草書創作的普遍狀態,如蘇東坡云:“何用草書夸神速,君有此病何能瘳,自言其中有至樂,適意無異逍遙游。”[14]文人將草書作為消閑自娛的雅好,與唐草的表現性、表演性相比,宋人草書是內向性、書齋式的藝術,講求內心的自省、自娛與自適。
其二,創作風格的轉變。中晚唐大草重在情感宣泄,筆法、空間布局等要素都成為情感表現的附屬品而不被重視。隨著晚唐五代大草的一味狂怪,過于追求顛狂的創作狀態以致草法盡失,一味纏繞,以至于宋初“士大夫作字,尚華藻而筆不實,以風墻陣馬為痛快,以插花舞女為姿媚,殊不知古人用筆也。”[15]在這樣的情況下,蘇軾、米芾、黃庭堅等北宋書家對唐以來大草發展狀況進行了大膽的反思和探索,對草書筆法、意趣、空間布局等要素進行了理性的分析與研究,扭轉了草書發展的方向。如黃庭堅早年學草跟隨時風,以周越為師,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其后仔細研習張旭、懷素、高閑草書墨跡,“乃窺筆法之妙”。在筆法方面,黃庭堅不隨時風、不拘經典,耗盡一生盡力對草書筆法進行了理性的探索與研究。如他曾反思其早期草書“用筆亦不知起倒”“用筆不知禽縱,故‘字中無筆’”;紹圣年間又得草書三昧“覺前所作太露芒角”;[16]他從懷素的草書中看到了“用筆皆如以勁鐵畫鋼木”,[17]按自己的思考對懷素草書進行了取舍和變法,將懷素線條的迅捷圓勁改為自己的遲澀蒼勁加以發展,并夾雜篆意,形成山谷獨特的草書線質。在布局方面,黃庭堅放棄了唐草的迅捷快速,放慢書寫速度,以理性的態度經營位置,打破結構程式,精心安排點線位置和結構章法,充分營造正側收放等結構關系,精心構筑作品的空間布局。
因此黃庭堅等宋草書家雖取法唐人,于唐人得益最多,但卻不因循守舊,大膽疑古,對唐草進行了理性的分析
與取舍,在唐草這座高峰下另辟新路,開拓新風,對后世草書創作與研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二
與疑古思潮相伴產生的是復古之風。有宋以來,為了改變晚唐五代思想衰亂的局面,重建儒家正統思想體系,以直追圣古、復興儒學為目的的復古之風興盛,成為唐宋轉型中重要的思想潮流,“復圣古”的思想得到了北宋上層統治階級及士人的普遍認同。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宋代的復古之風在政治、制度、禮樂、藝術、審美風尚等諸多層次都得到體現。如在禮制上,太祖命御史撰《開寶通禮》,并以聶崇義所著《三禮圖》為樣本,制禮作樂,以正宗廟祭儀,復三代之盛,在禮器的采用制作上也力求復三代之古。而在禮樂制度中,北宋朝以“復古”“正雅”為出發點,以古圣經書為據,嚴斥胡夷音聲,多次改樂以求合于理想化的三代雅樂傳統,形成雅樂制作的復古風氣。再如政治體制上王安石提出恢復周禮的理念,倡復井田制,以實現其政治變法主張,亦體現了士人復古的思想觀念。
在宋士人的復古思潮影響下,宋代書壇也存在著一股復古之風。崇尚魏晉古法風韻是宋代書法復古運動的核心觀念,這一復古運動貫穿了從北宋到南宋整個宋代書法的發展,從未間斷,對唐宋草書的變革發展亦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北宋書壇從太宗時期已開始了復古之風的萌芽。米芾《書史》記:“本朝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盡之間,天縱好古之性,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書無對,飛白入神,一時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學鐘王。”太宗的崇晉思想使宋初書壇“悉學鐘王”成為風氣。宋太宗還詔天下購募鐘王真跡,命王著編次十卷《淳化閣帖》,模刻以賜群臣,其中六至十卷皆為二王書跡,約222件,占總數一半以上,可見對魏晉風韻的推崇。閣帖之后宋代刻帖蔚然成風,帖學大興。二王書跡在眾多刻帖中皆占有較大比重,這為草書由崇唐轉為師法魏晉提供了物質基礎,對整個宋代草書向魏晉古法的回歸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歐陽修、蔡襄則是北宋中期復古書風的中堅推動力量。歐陽修嗜古好古,曾云:“予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18]而其歷時十八年收集金石拓本一千卷而成《集古錄》,即是其踐行復古思想、改變書法風氣的重要舉措。蔡襄與歐陽修觀點頗為一致,其《論書》中云:“晉人書,雖非名家,亦自奕奕,有一種風流蘊藉之氣。”
其后北宋晚期蘇、黃、米等書家將崇古尚晉的復古之風推向高潮,都標榜魏晉風韻,將古法晉韻作為書法追求的終極目標。蘇軾云:“予嘗論書,以謂鐘、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對晉人書法的自然、平淡、幽遠之境較為向往。米芾《草書帖》中說得更為直接:“草書若不入晉人格轍,徒成下品。”米芾將“晉人格轍”作為草書的根本,草書的創作與審美應當以晉人風格為模范。米芾自宋元豐五年三十二歲始“專學晉人”,并將自己書房命名為“寶晉齋”,“入晉魏平淡”是其終身追求。黃庭堅亦云:“觀魏晉間人論事,皆語少而意密,大都猶有古人風澤,略可想見。論人物要是韻勝,最為難得。蓄書者能以韻觀之,當得仿佛。”[19]黃庭堅受瀟散簡遠的魏晉風度啟發并加以拓展,在其書法及書論中將“韻勝”作為最高審美標準。
南宋時期盡管草書式微,蘇、黃、米書風風行天下,但在北宋的復古慣性下,書家仍將魏晉風韻作為內心的向往與尊崇。如高宗、孝宗、光宗、理宗等帝王皆以復歸二王書風為目標,而在帝王的影響下,范成大、陸游、朱熹等眾多書家學者都將古法晉韻作為最高的審美理想。
求古崇晉的復古風氣改變了宋人草書的創作狀態、創作精神及審美追求,使唐草與宋草在本質上產生了極大的變化。在復古風氣影響下,宋草書家皆以蕭散簡遠的魏晉風韻為審美追求,以王羲之為代表的自然、中和、平淡之美成為宋草書家普遍遵循的審美法則。故而中晚唐五代以情感宣泄為主的大草書風因有違于魏晉風韻的審美標準,在宋代失去了持續發展的生命力。宋代草書則走上講求法度、注重含蓄內斂意趣的發展方向。
三
“疑古”與“復古”兩股學術思潮看似是矛盾對立的,實則在宋人草書發展里得到了有機的統一。
“疑古”思想是一種對舊有經典的反思與懷疑精神,從反思中打破舊有的定勢規則與價值標準。宋草書家“疑古”風氣的產生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晚唐五代大草取法旭素,刻意求變,一味求怪求狂,內涵愈趨簡單,逐漸喪失了作品中深層的意蘊,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卑俗。以至宋初草書一味纏繞,古法盡失,偏離了書法的本質。在這樣的背景下,宋書家將疑古的矛頭指向以旭素為代表的唐大草,對唐草書風進行理性的反思,通過對唐草的反叛與抨擊試圖瓦解唐草的發展定勢與審美體系,摒棄唐草對宋草發展的影響,扭轉草書發展的方向。而“復古”之風則是在“疑古”的基礎上重建傳統,復魏晉古法,以魏晉筆法與風韻為指歸,重建新的價值體系。在宋人眼中,以旭素為代表的唐草筆法是對魏晉古法的異化與誤讀,正如米芾批評張旭“變亂古法”,張旭所變的即是魏晉古法。宋人需要以正統的魏晉古法為典范,解除唐人對古法的異化與誤讀,直接上溯魏晉,
引領草書回復到蕭散淡遠的魏晉風韻中去。
因此宋人疑的是唐人之古,而復的是晉人之古。“疑古”與“復古”是宋人改革草書的兩個層面,“疑古”為破,“復古”為立,兩種思潮交互作用、融為一體。而在宋草發展中,疑古思想又使得宋人在復古過程中保持冷靜理性的態度。宋人雖追求魏晉風韻,但又不對王羲之亦步亦趨,顯示出在經典面前冷靜思考、自我獨立的態度。
但是受時代所限,宋人對晉人書法的理解仍然有所偏頗,只注重晉人蕭散簡遠的意趣,而忽視古拙簡樸之質。而其對唐草的反叛又使宋草弱化了豪放激昂之氣,走向另一個極端,使得宋草大部分作品都過于理性與平淡,缺少草書應有的激情氣勢與表現力。
綜上所述,“疑古”與“復古”兩種思潮的交互作用,使宋代草書擺脫了唐草發展的定勢與桎梏,在尚情寫意的唐草之外開創了一條新的發展方向。雖然在唐草輝煌成就的遮掩下,宋草并未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宋人對草書的思考與探索卻豐富了草書的內涵,改變了草書的發展方向,對后世草書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看,唐宋草書的流變在書法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宋代草書的成就不容忽視。
[1]《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中國書店1986年版,第330頁
[2][3][4][5][9][10][11][15][16][17][19]黃庭堅《山谷題跋》,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版,第96頁、303頁、123頁、152頁、230頁、152頁、195頁、186頁、144頁、303頁、108頁
[6]《唐宋八大家散文總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497頁
[7]《蘇東坡詩集》,珠海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2頁
[8][12]崔爾平《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頁、159頁
[13]《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版,第309頁
[14]《蘇軾詩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頁
[18]歐陽修《集古錄跋尾》,人民美術出版社2010年版,第91頁
本文為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唐宋文化轉型視野下的唐宋草書流變研究”成果,項目批準號:2012SJD760027。
作者單位:南通大學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