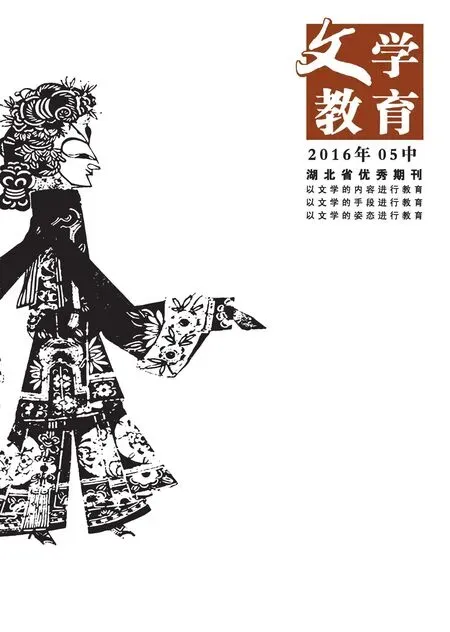論《等待戈多》的時間與等待
秦佩佩
論《等待戈多》的時間與等待
秦佩佩
在《等待戈多》整部戲劇中,時間對于荒誕人所呈現出來的特點便是對過去的否定,以及對將來的不加以定義,于是,人的存在只能收縮到現在。也是由于此,而使人面臨的處境便是:身后靠的是一堵厚鐵墻,而前方面對的是茫茫黑夜,于是在前后都無法行進之時,等待成為了人存在的唯一明智選擇。
《等待戈多》 時間性特征 等待
回顧往昔,當眾人被存在主義的虛無觀擊中,而渴求于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尋回生活的意義時,卻不曾想過,貝克特的這部戲劇,只是對現代人狀態的一種呈現,而生活的意義在這部戲劇中依然被加以破解。
一.荒誕人的“過去”與等待
整部戲劇中對過去的描繪是很深刻的,它的具體表現就是:一旦事情發生過后,對于這件事曾經存在與否確定不了了。比如在劇中,當愛斯特拉岡和弗拉基米爾談到昨天是不是也來過此地時,他們倆越是討論越是確定不了到底有沒有來過。到了后面,就在波卓和幸運兒走后不久,他們倆對于認不認識這對主仆又產生了疑惑。似乎事情一發生過后,就被忘掉了。
一切曾經存在過的事情,一旦發生,成為過去中的一部分,就會被忘掉。這樣的時間特性所表現出來的特征其實就是一個荒誕人典型的標志。因為作為一個荒誕人,他認識到了人的理性對于把控事物的無效性,也就是尼采所說的:“本是熟悉的世界,卻被剝奪了幻覺與光明”[1]。
那么這種否定會產生怎樣的結果呢?最直接結果就是時間的延續性被打斷了。過去就在事情完成的那一霎那完結了,不再會對接下來的時間段,即現在,產生任何影響了。而這就是所謂的立足于當下,過去的全然消解。
二.荒誕人的“將來”與等待
將來這個時間段,在《等待戈多》中又呈現出怎樣的特征呢?我們首先來看看戲劇中涉及將來的具體內容——在戲劇開始后不久,當愛斯特拉岡和弗拉基米爾確定要等戈多時,愛斯特拉岡提出了疑問:“萬一他不來呢?”然后弗拉基米爾非常堅定地說:“咱們明天再來”,接著的對話就是“然后,后天再來”“老這樣下去”“直等到他來了為止”。毫無疑問,戲劇里的明天成為了將來的代名詞。由此便可分析將來的特征了。
首先,由上面第一點的分析可以知道,在這部戲劇中,由于過去的全然消解而使時間失去了它的過去性,所以,當立足于此刻的這天過去,到達原本許以的明天時,對過去的忘記使他又站在了另一個此刻中,而明天又是一個夜晚之后的事情了。也就是薩特在《存在與虛無》中所說的:“而將來,則是現在朝著它超越的可能,它永遠在人的前方,等待他去實現。”[2]由此便可以知,將來將一直綿延而呈現出無限性。
而無限性的背后便意味著,一切許以明天的東西,將不確定會不會在你所期望的那個時間點出現。將來變得不可加以預想,前途是一片不可知的黑暗。
三.荒誕人的“現在”與等待
對于現在時間的呈現,在整部戲劇中,也表現出了不確定性。在第一幕中第二節的開頭,愛斯特拉岡就不斷在獨白:“今天是不是星期六?今天難道不可能是星期天!或者星期一?或者星期五?”從這里就可以看出,貝克特給出的現在的定義也是不確定的。同樣,這也是因為荒誕人認識到了人類所獲得的所有認知,包括今天是星期幾,都不能完全真實地反映事物本身,一切的“自以為是”都變成了虛無。所以現在的時刻可以是星期一,星期二,甚至是任何的日期。
那么,整部戲劇對待現在的態度是否也像過去那般是全部否定,或是像對待將來那樣無比無奈呢?答案當然不是的。貝克特在《等待戈多》中否定掉的只是人給予現在這個時間的外衣而已,也就是人們用以量化的表現形式,即具體的星期幾或者日期。但是對于現在本身,即原始真實、客觀存在著的,不需要人加以認識的現在這種世間狀態是加以肯定的。因為,縱觀全劇可以看到,貝克特極力呈現的動作和場景都只發生在此刻,就如愛斯特拉岡和弗拉基米爾在不確定到底是星期幾時,仍決定要等待戈多,他們要做的只是于此刻等待,而不是去關注于時間的外在變現形式。
縱觀《等待戈多》整部戲劇,時間對于荒誕人來說就是對過去的否定,以及對將來的不加以定義,于是,人的存在只能收縮到現在。也是由于此,而使人面臨的處境便是:身后靠的是一堵厚鐵墻,而前方面對的是茫茫黑夜,于是在前后都無法行進之時,等待成為了人存在的唯一明智選擇。而這,正如英國人馬丁·艾斯林在《論荒誕派戲劇》中對《等待戈多》的評價:“當我們處于主動狀態時,我們可能忘記時光的流逝,于是我們超越了時間;而當我們純粹被動地等待時,我們將面對時間流逝本身。”
[1](德)尼采.《悲劇的誕生》[M],周國平譯.江蘇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53.
[2](法)薩特.《存在于虛無》[M],陳宜良譯.北京:三聯書店,2014.172-173.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