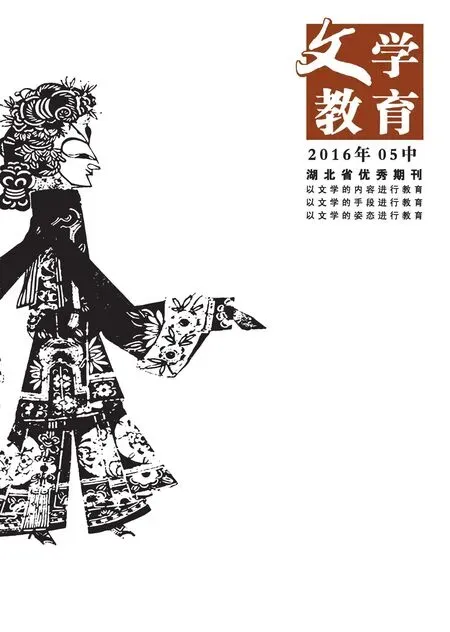詩歌中的意象之美
周新穎
詩歌中的意象之美
周新穎
詩歌是文學殿堂里的桂冠。古今中外,這種文學形式備受人們推崇和關注。五千年中國文化,洋洋灑灑一路走來的是詩三百、楚辭、漢樂府、唐詩、宋詞、元曲這些具有時代特征的詩歌形式。在我們的文化傳承里,詩歌記載了我們祖先的印跡。我們從一首詩里,可以解讀某個時代,某個歷史事件,某個歷史人物,甚至某個凄美動人的愛情故事。基于文化素養的不足,有很多同學在學習詩歌尤其是古典詩歌時總不能夠很好地解讀,有同學甚至對古典詩歌可以說是完完全全懵然無知。因而,激發學生對詩歌尤其是古代詩歌的 學習興趣,就要有一個恰當的切入點,意象是解讀詩歌的一把鑰匙。
何謂“意象”?意象,即意中之像。“意象”一詞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一個重要概念。古人以為“意”是內在的抽象的心意,“象”是外在的具體的物象:源于內心并借助于像來表達,“象”其實是“意”的寄托物。從大文化的角度講,意象是一個哲學的范疇。《周易》提出了“立象以盡意”“觀物以取象”的命題。古代的哲學家們已經注意到了人與外部自然的關系。孔子提出“智者樂水,仁者樂山”這種“比德”的山水觀。“登東山而小魯,等泰山而小天下”“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孔子把厚重不移的山當作他崇拜的“仁者”形象,用周流不滯的水喻有智慧的人的通達事理。這種以山水喻人的哲學思想對后世產生了無限深廣的影響,深深浸透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當然,先哲們的美學觀念也深深地影響了詩歌。文學作品必須通過具體可感的人物事件來表現內容,詩歌的語言是高度凝練的,它形象化的內容必須借助意象來表達。而詩歌的意象是浸染了作者特有情感的具體形象,這個形象一般指某個特定景物如明月、山水、浮云、歸雁、楊柳等,也可以指某個事件甚至物件。因而意象成為詩人情感的宣泄點,把握了意象,就能很好地解讀詩歌。
一.離別詩
此類詩,多抒寫離愁別緒,抒發別離之苦,多表達親友依依惜別之情。李白的《送友人》:“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青。輝手茲茲去,蕭蕭班馬鳴。”太陽下山,徐徐而落,多像詩人對朋友依依不舍的惜別之情啊。不愿離開同伴。離別詩寫的濃情之至當數柳永的《雨霖鈴》“寒蟬”“驟雨”“長亭”這些具體意象很好地渲染了離別的凄苦之情。“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主人公的暗淡心情給天容水色涂上了陰影;“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進一步寫出了主人公的孤零愁苦,情味不盡,意韻無窮,歷來為人所傳誦。
二.愛情詩
人間第一美好情感首推愛情,因而有關愛情的詩篇歷來表現內容最豐富,意象的運用也最為精當。古樂府詩《上邪》“上邪!我欲與君長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從這首詩里我們可以感受到一位女子大膽的愛情表白。詩人借五種自然現象表明自己矢志不移的愛情信念。情感熾烈,意象鮮明,震撼人心。元稹的《離思》“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借滄海之水、巫山之云表達詩人對愛情的忠貞專一,可謂千古絕唱。
三.思鄉詩
故土之情是中華文化傳統里的特有情愫。在中國文化傳統意象里“月亮”“白云”“落日”“斜陽”幾乎成了思鄉的代名詞。這一類的詩歌意象舉不勝舉,北宋詞人范仲淹的《蘇幕遮》:“碧云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碧云”“黃葉”“翠煙”這些意象襯托了鄉魂旅思和相思,上闋所描繪的秋景,是歷來詞家多次重復過的意象,卻依然能給人比較新鮮的感受。
四.懷古傷今詩
借古喻今,在古代文學作品中是常見的筆法,自然,在古典詩歌當中,詩人也常常借助于歷史典故和人物抒寫懷古傷今之幽思。作者憑吊古跡,或是諷喻當今,或是感慨自身,或是抒發對某事的看法。這些歷史的事件、人物與眼前的景物構成了宣泄詩人情感的意象。杜甫的《蜀相》詩人徘徊于丞相祠堂前,情思遠接,感慨不已:“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作者英雄難酬心志的情感表達得淋漓盡致。
五.言志詩
此類詩歌,詩人借物明志,有感而發。從分析意象入手,就能理解詩人的志向、意趣和情感。屈原在他所有的詩篇當中,都借香花和蘭草寄托自己高潔的品行。在《離騷》中,“制支荷以為衣,集芙蓉以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以荷葉荷花為衣,把自己裝扮成峨冠博帶的形象,是詩人“舉世皆濁我獨醒”的具體展現,因而詩人的品格就被刻畫得異常崇高。
以上從意象的角度對詩歌進行粗略分類與賞析,可以說意象是解讀詩歌的關鍵,把握了意象也就抓住了詩歌的意境、風格及作者蘊含其中的思想感情。只有對意象有了清晰而深刻的認識,我們才能對詩歌產生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和把握,才會產生審美情感。當然,對一首古詩的理解與把握僅就意象來分析是不夠的,但至少我們可以由此深入詩歌的幽林深處,做好了這一步,相信,我們離古典詩歌的殿堂已不遠了。
(作者單位:威海職業技術學院基礎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