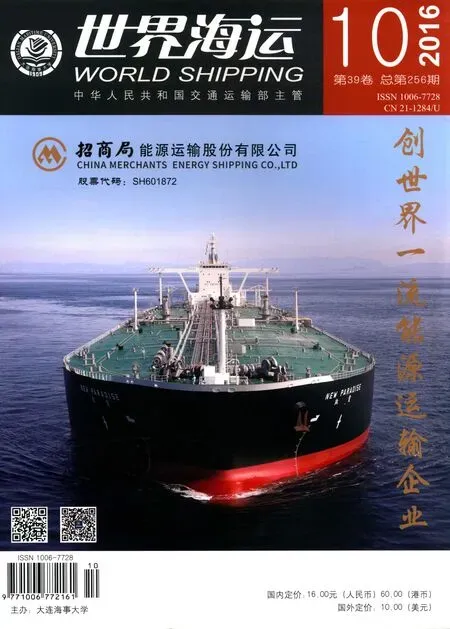水運貨損金額認定難點
廈門海事法院 鄧金剛
水運貨損金額認定難點
廈門海事法院 鄧金剛
我國境內港口之間的水路貨物運輸貨損如何進行認定,實踐中仍然存在一些常見的難點,如增值稅損失問題、貨損狀況的判斷問題、貨物原值和殘值的確定問題等。從一起已生效的水路貨物運輸糾紛案例出發,結合相關法律規定,對前述難點問題進行分析,以期為問題的解決提出可能的答案。
貨損;認定;難點
一、案例情況
原告江某。
被告:廈門A船運公司(下稱A公司)。
被告:廈門B集裝箱班輪公司(下稱B公司)。
被告:C貨輪公司(下稱C公司)。
某貿易公司接受原告委托辦理一批陶瓷從廣東運往上海等地的業務,原告預付了運費8 100元。為此,貿易公司將前述貨物委托B公司運輸。此后,案涉貨物分別裝于3個集裝箱內,于2011年8月21日裝上“甲”輪,由廣東黃埔港運往上海港。2011年8月26日,“甲”輪在上海吳淞口附近水域與“乙”輪發生碰撞,造成“甲”輪傾斜擱淺并導致案涉貨物發生了貨損。
2011年10月9日、27日,丙保險公估有限公司和丁保險公估有限公司委派的人員共同對箱號為TGHU1539102、CXDU1050630、FCIU4173642的貨物進行檢驗。結果為:箱號為TGHU1539102的貨物,58箱灰磚、27箱黑聚晶破損,地磚變色;箱號為CXDU1050630的貨物破損52箱,地磚變色;箱號為FCIU4173642的貨物,僅有約700箱貨物卸出,共有9箱破損,其余均發現串色,所有貨物全部裝回箱子并重新鉛封。
2011年10月27日,江某向B公司等出具說明,陳述箱號為FCIU4173642的貨物無法銷售,拒絕接收,保留索賠權。
丙保險公估有限公司接受某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廣東省分公司的委托,對案涉貨物進行了檢驗和公估,并于2012年10月16日出具了檢驗報告。該報告記載:貨方按全損索賠貨物損失270 370元及運費損失8 100元,與貨物實際損壞情況不符。合理的損失金額為:貨物實際損失+清洗和重新包裝費+材料費,合計為53 567.82元。該報告所附的產品調撥單、銷售單與原告所提供的一致。該產品調撥單記載,開單時間2011年8月16日,收貨單位江某,腳線1 000箱,柜號1050630,貨值82 200元。該銷售單記載,開單時間2011年8月16日,收貨單位江某,600A灰磚1 050箱,每箱單價88元;800A灰磚380箱,每箱單價144元;黑聚晶300箱,每箱單價135元,柜號4173642裝1050箱600A灰磚,柜號1539102裝680箱800A灰磚和黑聚晶,貨值188 170元。
2012年8月21日,法院作出民事裁定,準許原告就被告A公司、B公司設立之責任限制基金以及被告C公司設立之責任限制基金的債權登記申請。
A公司為“甲”輪的船舶所有人,B公司為該輪期租承租人,C公司為“乙”輪的船舶所有人;案涉“甲”輪與“乙”輪的碰撞責任比例為“乙”輪承擔碰撞事故責任的60%,“甲”輪承擔碰撞責任事故責任的40%。
原告江某請求法院判令:三被告按其應承擔的碰撞責任比例連帶賠償原告貨物損失278 470元及其利息。
被告C公司辯稱:
一、原告要求連帶賠償其所謂的貨物損失不符合海商法的規定。二、原告所述的貨物損失是在碰撞后發生的,與船舶碰撞沒有因果關系。三、原告未能提供涉案貨物的買賣合同、付款憑證、裝箱單等證明其是涉案貨物的所有人,沒有索賠權。四、根據丙保險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檢驗報告,即使原告有證據證明其所述的貨損清單的內容是真實的,涉案貨物的損失也僅為53 567.82元。
被告A公司、B公司共同辯稱:
一、原告的債權只能依法從設立的基金中分配。二、其僅按“甲”輪在本次事故中的碰撞責任比例承擔賠償責任。三、原告未能提交充分的證據證明其損失,應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
法院認為:
一、關于原告的訴訟主體資格
法院認為,原告系案涉3個集裝箱的發貨人,金華通公司接受原告委托后,又將貨物委托B公司運輸,在沒有相反證據證明案涉貨物的所有權已經轉移至收貨人的情況下,原告作為貨物的所有權人,有權向船舶碰撞的各方主張侵權損害賠償。
二、關于案涉貨損是否系因碰撞引起
法院認為,在案涉碰撞發生前,案涉貨物完好裝載于“甲”輪,案涉3個集裝箱的貨物損失系由于碰撞事故發生后產生的,即使如被告所言,貨損并非碰撞直接導致的,但在碰撞事故發生后,碰撞雙方之間對案涉貨物在交付前仍負有保管責任,故應根據碰撞責任比例承擔賠償責任。
三、關于貨損的金額
法院認為,該爭議焦點涉及的具體爭議項目為:案涉貨物是否全損;貨物的價值是多少;是否應扣除17%的增值稅;貨物的殘值;運費8 100元是否屬于原告損失。
關于案涉貨物是否全損的問題。法院認為,在案證據集裝箱現場檢驗記錄顯示貨物并未全部破損,只是部分貨物存在色差,而原告又無證據證明案涉殘余貨物經過公開處理也無法變現,因此原告關于貨物構成全損的主張,因無證據證明,依法不能予以支持。
關于貨物的價值是多少的問題。法院認為,被告雖否認原告據以證明貨物價值的證據產品調撥單、銷售單,但被告C公司所提交的檢驗報告附件中也提交了該證據,并且系該報告結論的依據之一,因此該產品調撥單、銷售單的真實性應予以確認,案涉貨物的價值可以據此認定為270 370元。
關于貨物的價值是否應扣除17%的增值稅問題。法院認為,本案中貨物的價值系根據產品調撥單、銷售單的記載予以認定的,被告主張該銷售的價值包含了17%的增值稅,但沒有提供證據予以證明,因此前述認定的案涉貨物的價值不應再扣除17%的增值稅。
關于貨物的殘值問題。法院認為,原告沒有提供證據證明貨物已構成全損,因此貨物的殘值宜以被告提交的檢驗報告中公估公司認為的60%的殘值率進行認定。
關于運費8 100元是否屬于原告損失問題。法院認為,在原告已支付了運費8 100元,且該費用不可能得到退還的情況下,該款項應視為原告的損失。
綜上,原告所受到的損失為箱號為FCIU4173642的貨物,損失92 400元;加上箱號為CXDU1050630的貨物破損52箱,損失4 274.4元,地磚變色貶值損失948箱乘以82.2乘以0.4,數額為31 170.24元;加上箱號為TGHU1539102的貨物,58箱灰磚,損失8 352元,27箱黑聚晶破損損失3 645元,地磚變色貶值損失,黑聚晶部分14 742元(273箱乘以135乘以0.4的得數),灰磚部分18 547.2元(322箱乘以144乘以0.4的得數);加上運費損失8 100元,原告因貨損產生的損失合計為181 230.84元。
法院判決:一、被告A公司、B公司連帶賠償原告72 492.34元及利息;二、被告C公司立即賠償原告108 738.5元及利息;三、原告上述債權在被告A公司、B公司以及C公司在廈門海事法院設立的海事賠償責任限制基金中分配;四、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
二、爭議問題的分析
前述案例中,法院對于雙方爭議的增值稅金額扣除問題,貨損狀況、貨物原值和殘值等問題作出了認定,一審宣判后,各方均未上訴。下文中,筆者針對這些難點問題進行進一步的探討。
(一)增值稅的扣除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十一條規定,銷售退回或者折讓貨款可以從應納稅額中予以相應的扣減。因此,如果貨物發生貨損,收貨人拒收貨物,托運人進行索賠時,承運人往往以前述條款為由,主張貨損賠償中應扣除17%的增值稅數額。
是否應該扣除,實踐中存在不同的看法。
有人認為,貨損發生時,根據合同法的規定,如雙方沒有約定賠償標準,則依照目的地的市場價格進行賠償,該市場價格本身就是含稅的價格,因此承運人的賠償標準不應扣除增值稅數額。
筆者認為,前述觀點恐怕不能成立,理由是:一則合同法對于市場價格是否為含稅價格并無明確的界定,根據個人的理解來認為市場價格就為含稅價格不足為憑;二則既然是市場價格就應尊重交易雙方的自由意志,所以市場交易的價格有時為含稅價,有時為不含稅價;三則從損失賠償原理看,存在損失是賠償的前提,因此實際損失的存在是賠償義務人賠償的法理基礎,任何的損失賠償規則不能脫離該基本法理基礎;四則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民申字第454號廈門聚億電氣設備有限公司(下稱聚億公司)與庫柏電氣(上海)有限公司(下稱庫柏公司)一般買賣合同糾紛申請再審民事裁定書中認為,根據國家稅務總局2006年10月17日修訂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使用規定》第十四條第一款,“一般納稅人取得專用發票后,發生銷貨退回、開票有誤等情形但不符合作廢條件的,或者因銷貨部分退回及發生銷售折讓的,購買方應向主管稅務機關填報《開具紅字增值稅專用發票申請單》(以下簡稱《申請單》,附件3)”及第二款“《申請單》所對應的藍字專用發票應經稅務機關認證”的規定,本案中庫柏公司多開的增值稅發票因沒有實際發生交易,可以通過相應的稅務程序解決,以避免損失的發生。二審判決在雙方未經稅務退票處理的情形下,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取得防偽稅控系統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進項稅額抵扣問題的通知》第一條的規定,直接認定聚億公司應向庫柏公司賠償相應損失,適用法律不當。故不管是從法律條文的理解上,還是從損失賠償的原理看,還是從最高法院的裁判看,一般情形下,發生貨物損失時,經過相應的稅務處理可以得到退回的稅款,不應成為索賠的內容。
在水路貨物運輸貨損糾紛中,增值稅是否扣除的問題存在各種不同的情形。
其一,收貨人作為索賠主體時,因收貨人已支付的價款中已包含了增值稅,故不存在是否應扣除稅款的問題。
其二,托運人提供了增值稅完稅發票時,一般應根據稅票上記載的稅款金額扣減承運人應賠償的數額。理由之一,依照前述條款,未完成的銷售依法可以扣減稅款。理由之二,實踐中,作為托運人的賣方,在發生貨損的貨物銷售未完成時,往往可以另行發貨,并套用發生貨損的增值稅發票;或者在今后的銷售中,套用已開具的增值稅發票。理由之三,即使托運人不是貨物的賣方,增值稅問題亦可層層追溯至賣方進行調整,雖然具體糾紛中,作為托運人的貨代處于商業考慮或者不清楚可以扣除,已賠付了貨物賣方包括增值稅在內的全部貨款,但不能成為其有權向承運人索賠的理由。
其三,托運人未提供增值稅發票時,如買賣合同中已明確約定了銷售價款為不含稅時,則承運人應賠償的款項不存在還須扣除增值稅款項的問題,只是需審查該銷售價款與市場上同類產品的含稅價格是否大致相同,以避免托運人為索賠故意不提供增值稅發票。如果托運人主張的不含稅價與市場含稅價基本相同,且托運人不能提供合理的解釋,那么從貿易的常識出發,還應認定該價款為含稅價,承運人的賠償數額應扣除稅款。從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看,托運人提出的不含稅價與市場含稅價是否相同的舉證責任在于承運人。前述案例中,承運人未能舉證證明原告主張的價格與市場含稅價相同,故法院未予支持。
(二)貨損狀況的判斷
(1)協商一致。如有雙方的書面確認,一般以雙方的書面協議為準。
(2)未協商一致。如無雙方聯合檢驗的書面共同確認,則提出索賠的貨主需要舉證證明貨物在目的港接收時的損壞狀況。貨物損壞的狀況,如果有相應的港口卸貨方、公估機構等參與確定,則除非承運人有相反地證據予以推翻,否則對損失的狀況可以根據貨物運輸相關方參與確定的損失情況來確定貨損狀況。實踐中,承運人往往提出其未獲得機會參與共同檢驗,但多數是一種托詞,大部分情況下,貨主都會通知承運人派人參與,只是承運人有時不愿參與或者參與后不愿簽字確認。即使承運人未獲得通知,但在法律沒有規定承運人必須參與,否則就不能確認貨損的情況下,只要根據證據,貨損的情況可以確定,仍應根據證據體現的事實,確認貨損狀況。
(3)鑒定情形。此外,有的貨主單方委托鑒定機構對貨物的損壞狀況進行鑒定。此時需要綜合鑒定機構的資質、被鑒定的貨物是否為爭議貨物、鑒定結論的依據是否充分等因素來判斷鑒定結論能否作為認定貨損狀況的依據。如果是在訴訟過程中,一方申請貨損鑒定,雙方共同選擇一家鑒定機構或者由法院指定一家鑒定機構進行鑒定,那么除非鑒定的結論明顯不符合事實,否則該鑒定結論一般可作為認定貨損狀況的依據。
(4)注意事項。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貨物損壞的狀況如何,與貨損金額之間并非可以直接等同。如貨物部分損壞后,導致整批的特殊定制的貨物無法使用,沒有市場價值;或者某些密封包裝的貨物,雖然品質沒有發生變化,但因為受過海水浸泡或者其他污染,市場價值已大為貶損等。只是該特殊貶值的舉證責任在于貨主,即貨主須提交證據證明貨物的市場價格實際發生了貶值。
案例中,雙方對于貨物的損壞狀況進行了聯合檢驗,并共同予以確認,故檢驗的情況可以予以直接確認。
(三)公允價值的判斷即貨物原值和殘值的確定
關于貨物的原值。如果有相應的增值稅發票及付款憑證予以證明,那么貨物的銷售價格構成貨物的原值;如果未有增值稅發票,那么貨物的實際銷售價格構成貨物的原值,但貨主應提供買賣合同(或類似的供貨單等),并提供支付憑證;如果貨主提供的證明貨物銷售或購買價格的證據薄弱,如無書面合同,只是賣方或買方的一個證明,那么應結合市場價格對該證明的證明力進行認定,如與市場價格基本一致,就予以認定,如明顯超出市場價格,貨主又無法予以解釋,就以市場價格認定貨物的原值。
關于殘值的確定。最便捷的方式是,船貨雙方一致認可,但實踐中,此種情形極為少見,因為船貨雙方的利益方向是對立的。為解決該對立,出現了幾種殘值的確定方式。
(1)保險公估方式。該方式最為普遍,主要原因是,貨主一般都投保了貨物運輸保險,因此一旦發生貨損,會立即報險,保險公司則立即指派保險公估公司進行查勘。該方式的優點是,快速、專業、高效、鎖定證據、較為公允;缺點是,系單方委托的機構作出,公正性不免受到懷疑。司法實踐中,對于貨主的保險公司提出的公估報告,除非承運人提出相反的證據予以推翻,或者公估的結論明顯不符合常理,否則多認可其證明力。理由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一百二十九條,“保險活動當事人可以委托保險公估機構等依法設立的獨立評估機構或者具有專業知識的人員,對保險事故進行評估和鑒定”的規定,保險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后可以單方委托具有公估資質的獨立評估機構對涉案貨物損失進行評估和鑒定,其并無通知事故責任人參與保險公估機構的選定及公估過程的法定義務。而且,作為保險貨物理賠程序中的一個環節,如要求保險人或被保險人在保險公估階段通知所有的責任人或身份尚不明確的責任人參與公估機構的選定及公估過程過于苛刻甚至難以為之。如果以責任人未參與公估機構的選定或評估過程為由,直接否定保險公估報告的效力,保險公估機構將失去存在的意義。但需要特別予以提及的是,如果是貨主自行委托的保險公估機構所作出的報告,并不符合前述法律規定,出于審慎原則,應對其公正性予以更加認真的審查。公估報告中,對于貨物原值或者殘值的認定,如果與其他證據所體現的事實不符的,則應以增值稅發票體現的貨物價格或者公開拍賣或變賣貨物得到的貨物殘值為準。
(2)公開拍賣方式。該方式的優點是公開、公正,證明力強,貨物通過公開拍賣所得到的價款(扣除合理費用后)可以作為貨物的殘值進行認定。但拍賣是否構成公開、公正,還須審查拍賣的程序,如拍賣的公示范圍、方式、時間,參加拍賣的限制條件,是否通知承運人等相關主體參加等。如果已及時通知承運人或其代理人或其貨物的保險人等參加拍賣會,那么拍賣的結果,一般應予以認可,即使承運人不派人參加,因為承運人等如認為拍賣的價格過低,其可以通過提高報價的方式來接收殘余貨物,以減少損失。如果未通知承運人或其代理人或其貨物的保險人等參加拍賣會,那么拍賣的結果,須要通過嚴格審查拍賣是否公開、公正、公允進行判斷,如是否存在故意不通知承運人的情形,拍賣程序是否合理,拍賣結果與市場正常價格的對比情況等進行綜合判斷。
(3)變賣處理方式。該方式的優點是簡便、快速、高效、節約,缺點是變賣的處理結果易受到質疑。公開拍賣的方式雖然易得到各方認可,但程序繁瑣,耗時較長,費用高,變賣方式可以通過聯系市場的潛在客戶即時進行以減少處理費用。由于其優點突出,該方式在貨損事故中,較為常見。變賣的對象通常有貨物的買方,或者市場的其他潛在客戶。變賣方式處理的結果,扣除合理的費用后,即為貨物的殘值,除非承運人有相反的證據證明變賣的價格明顯低于市場價格,或者變賣價系貨主與買方惡意串通的結果。如果變賣前已及時通知承運人參加,那么變賣的結果通常被認為是公允的,應予以認可;如未通知承運人參加,則須依照前述規則進行認真審查;如故意不通知承運人參加,則應加強對變賣價格是否符合市場價格進行著重審查。
(4)貶值處理方式。該方式貨物貶值處理的接受方為收貨人,故其優點是簡便、快捷,但缺點是公允性易受到質疑。實踐中,一般以貨主是否給予承運人知情權和救濟權作為該貶值處理是否適當的重要考量因素。如貨主在貶值處理前,已提前告知承運人并給予其不同意該貶值處理的救濟權,那么,除非貶值處理明顯違背市場規律,否則應予以認可。如貨主未給予承運人知情權和救濟權,或者只給予承運人知情權,未給救濟權,那么該貶值是否合理,需要通過審查同類商品在相似情形下的市場價格情況來進行判斷。一旦該貶值處理的價格與市場情形明顯不同,則不應予以確認。
案例中,在原告證據不足以證明其損失情況下,法院巧妙運用了被告方提交的保險公估報告中附件的材料與原告方證據一致的情形,以及該報告所認定的殘值情況來認定貨物的原值及殘值,符合法理、情理。
郵發代號:8-32
10.16176/j.cnki.21-1284.2016.10.010
鄧金剛(1974—),男,碩士,高級法官,E-mail:djg082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