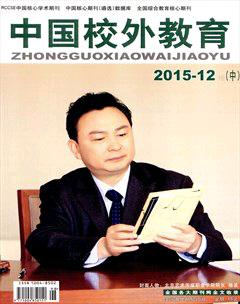用新批評的細讀法解讀李商隱的《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
和玉清
摘要:借助新批評這一文學流派中的細讀法,從詞義、句義、修辭、意象等方面,對李商隱的《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進行分析,深層推敲,挖掘詩句的言外之意,發現其新的美點、亮點和意境。
關鍵詞:李商隱 七律《無題》 細讀法
李商隱是晚唐詩壇上一顆寧靜而明亮的巨星,他將唐詩推上了又一個高峰,在他才華橫溢的超越前人的詩作中,最具藝術獨創性,引起千百年來無數讀者賞悅不已的,是他抒情詩中的七律《無題》。李商隱用靈魂、詩心和才情寫就的這些詩篇,在古典詩歌的百花園中散發著穿越世紀的芬芳。他的詩歌創作常以清詞麗句構造優美的形象,寄情深微,意蘊幽隱,富有朦朧婉曲之美。詩以《無題》命名,是李商隱的獨創。這類詩作并非成于一時一地,多數是描寫愛情,其內容或因不便明言,或很難用一個恰當的題目表現,所以命為“無題”。李商隱的無題詩寫得意境要眇,情思婉轉,辭藻精麗,聲調和美且能疏密相間,讀來令人回腸蕩氣。
無題李商隱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曉鏡但愁云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根據細讀法,這首詩的復雜含義遠遠超過字面本身的意思,它是隱蔽的,深藏于作品的有機結構之中。很顯然,簡單的分析是無法揭示這樣一個復雜的客體的。需對作品進行耐心仔細的分析推敲,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對作品的詞義、句法、隱喻、象征等,加以分析,從而揭示作品內在的全部含義。
新批評(New Chriticism)作為一種文學評論的流派,出現于20世紀的三四十年代,它認為:作者生平與創作意圖及作品內容與價值之間不存在必然聯系。而文本細讀法是英美新批評所提倡的一種批評方法。它強調對文學文本全封閉式的精細閱讀。排除文本生成研究和讀者情緒反應研究,將目標集中于文本,對文本進行多重回溯性閱讀,尋找其中詞語的隱微含義,如詞句中的言外之意和暗示,聯想意義;仔細分析作品中所應用的各種修辭手段,如隱喻和擬人等。另外,應用細讀法,可想象文本具有戲劇沖突性,將文本視為充滿矛盾和張力的有機統一體,分析語言的含混、悖論、隱喻、反諷、象征等要素,以及由于這些要素的作用所形成的詩歌的復雜意義和闡釋空間,從而在矛盾沖突中形成詩歌和諧統一的具有張力的整體結構。
本文借助細讀法對李商隱的《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從以下幾方面進行深層領會。
一、詞義
通過細讀發現有些詞富有特定的表現力和極其豐富的情感。本首詩中出現的“東風”“殘”“絲”“蠟炬”“云鬢”“夜吟”“青鳥”等一系列詞給人以深層的想象,無盡的情意。東風指春風,絲比喻思,思念相思之意。蠟炬即蠟燭。淚,指蠟淚,隱喻相思淚水。云鬢,青年女子的頭發,代指青春年華。青鳥,傳說中為西王母傳遞信息的神鳥,在本文中是使者的代稱。全詩以首句“別”字為通篇主眼,闡述相見不易,離別尤難。多種修辭交替使用,表達了雙層互動的情思,細細品讀,別有意境。
二、句義
全詩共四聯,每聯都有自己在全詩中的層次定位,聯內又有自己的小層次;他們共同組成了全詩表現真愛的感人境界。同時,七律詩細讀起來可領會到特有的情感和韻味。開頭兩句,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寫愛情的不幸遭遇和抒情主人公的心境:由于受到某種力量的阻隔,一對情人已經難以相會,分離的痛苦使她不堪忍受。“別”情“離”緒之苦加倍的訴述相見之難。“東風無力百花殘”一句,既是自然環境的寫實,也是抒情者心境的反映,物我交融,心靈與自然取得了精微的契合。寫實與象征融為一體,賦予感情以可以感觸的外在形態,從而作到“寓情于景”。
三、四兩句,將“相見時難”而“別亦難”的感情,表現得更為曲折入微。“春蠶到死絲方盡”中的“絲”倒出了自己對于對方的思念,如同春蠶吐絲,到死方休,仿佛蠟淚直到蠟燭燒成了灰,方始流盡一樣。思念不止,像在無窮地循環,難以求其端緒;又仿佛組成一個多面的立體,光從一個角度是不能見其全貌的。詩人只用兩個比喻就圓滿地表現了如此復雜的心理狀態。“春蠶”句首先是人的眷戀感情之纏綿同春蠶吐絲綿綿不盡之間的聯想,又從蠶吐絲到“死”方止而推移到人的感情之生死不渝,因此寫出了“到死絲方盡”,使這一形象具有了多種比喻的意義。
以上四句著重揭示人物內心的感情活動,使難以言說的復雜感情具體化。五六句轉入寫外向的意念活動。上句寫自己,次句想象對方。夜晚輾轉不能成眠,以至于鬢發脫落,容顏憔悴。總之,是為愛情而憔悴,痛苦、抑郁。“夜吟”句則推己及人,想象對方和自己一樣痛苦。揣想對方大概也將夜不成寐,常常吟詩遣懷,但是愁懷深重,無從排遣,所以愈發感到環境凄清,月光寒冷,心情也隨之更趨暗淡。“應覺月光寒”是借生理上冷的感覺反映心理上的凄涼之感。
結尾兩句,以仙侶比喻情侶,將蓬山比作仙山,而以青鳥作為抒情主人公的使者出現。這個寄希望于使者的結尾,并沒有改變“相見時難”的痛苦境遇,不過是無望中的希望,前途依舊渺茫。
這首詩,從頭至尾都融鑄著痛苦、失望而又纏綿、執著的凄婉之情,詩中每一聯都是這種感情狀態的反映,但是各聯的具體意境又彼此有別。這樣的抒情,聯綿往復,細微精深,成功地再現了隱藏在心底的綿邈深情,讓人嘆為觀止。
三、修辭
《無題》詩中運用多種修辭法,仔細品味其達意生動,情感傳神。
隱喻。新批評流派把文學作品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對象加以研究,在研究中又特別重視語言技巧,尤其重視隱喻。布魯克斯曾用一句話概括現代詩歌的技巧:重新發現并充分應用隱喻。對隱喻的極端重視是新批評派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特征。李商隱的《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詩共四聯,從第一聯起,描寫一個隱喻性的意象,構成一個主題。四組的意象各不相同,但都表達了“難”的特點。
艾倫·退特在《論詩的張力》中提出了張力的概念。退特說:“詩的意義就是它的張力,即我們從詩所能發現的全部外延和內涵的有機整體。”可見,外延是指一個詞的詞典意義,即字面意,指稱意;內涵指暗指意義,或附屬于文詞上的感情色彩,即暗示喻,比喻意。詩歌語言既要有內涵,也要有外延;既要有明晰的概念意義,也要有豐富的聯想意義,是兩種的統一體所構成的張力。新批評認為沒有張力的詩是沒有詩韻和詩味的詩,不能打動讀者的心靈。李商隱的《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詩,是一首充滿張力的詩。詩的意象凝聚在一個含蓄的命題下:一對情人相見難,別更難,兩個靈魂的統一是一個非空間的實體,因而是分不開的。詩的特點是將整體的非空間的心靈容納在一個空間形象的邏輯矛盾:“春蠶到死”“蠟炬成灰”。這種有限形象,在外延上和這個形象所表示的內涵意義在邏輯上相互矛盾,但這種矛盾并不會使這種內涵意義失去作用;春蠶、蠟炬所表示的內涵意義“堅韌”和“永恒”,共同表達了情人之間的情感意蘊,念情不斷的離恨與摯愛構成了詩歌的張力。故有人評論說“言情至此,真可以驚天地而泣鬼神。”這首《無題》詩,正是將比喻、隱喻、借代、張力等修辭手法自如使用,才使得文本達意生動而傳神。
四、意象
借助細讀,通過寫作技巧,領會《無題 ·相見時難別亦難》中的想象空間、情感氛圍和藝術境界。
意象是我國詩學的一個重要美學范疇,與意境同為衡量詩歌優劣的標準。竊以為,意象即意中之象,是詩人感官接觸外物后所引起的想象、體驗、知覺形成于心中的圖象。李商隱的《無題 ·相見時難別亦難》風格獨具,意境朦朧、深邃、含蓄。詩中的形象初讀使人產生恍惚迷離之感。但如果仔細吟讀這首詩,就會給人不同的感受,那種意象會把人的情感情不自禁地引向一個特定的方向,盡興陶醉,啟人遐想,回味無窮。同時,詩中意象的含蓄有著巨大的張力,給讀者留下極大的想象空間,感情細膩而朦朧,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愈咀嚼,味愈甘,意愈深遠。
這首膾炙人口的《無題》中,“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為世人所樂道和傳誦。春蠶、絲盡、蠟炬、淚干等意象,不僅憑藝術的苦思,雕鑿所得到,而是詩人與愛妻無限恩愛之情的結晶,坎坷愛情生活的濃縮。“春蠶”“蠟炬”既有著纏綿無盡的思念,又有著忠貞不渝的執著;既有著對美好愛情的歌頌,又有著痛失愛妻的嘆挽。雖無驚風雨的境界,卻有泣鬼神的魅力。
再如,詩中的“東風”意象,在古人筆下多是示現喜情的。而在《無題》中遂成了悲痛的象征。“東風無力百花殘”,催動萬物生長的東風,變得軟弱無力,春光已逝,百花調殘,景語皆情語,深含痛失愛妻的嘆息和無奈。再如詩中“蓬山”“青鳥”意象,二者皆為仙界景物,愛妻到了人間的另一頭——蓬山,但愿生活更美好。人間天上難以溝通,只好請殷勤的青鳥互相傳遞情意消息。這雖為想象之詞,卻凝聚了深深的愛意。
詩歌是心靈的窗口,是情緒的表現,心靈情緒本來是無序的,是一個謎團,只是為了表現才苦思冥想給了它秩序;意象是心中之象,多種意象的交叉組合,才有可能揭示心中的謎團,疏通淤積于心中的情緒之癥結。李商隱這首《無題》詩中,通過比興、象征、暗示、等多種表現手法創造出朦朧、含蓄雋永的意象之美。
五、結論
本文通過新批評這一文學流派的細讀法,將李商隱的《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詩句所含蓋的知識點全方位、系統的細讀咀嚼,深層推敲,挖掘詩句的言外之意,發現其新的美點、亮點和意境。
參考文獻:
[1]邱運華.文學批評方法與案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64-167.
[2]劉學鍇,于恕誠.李商隱詩選[M].北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93.265-267.
[3]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