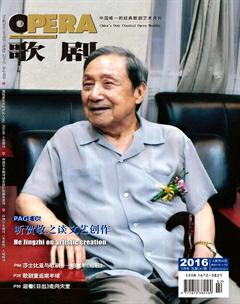感恩久遠


金湘是我所敬愛的老師。有人說,教作曲就那么回事——“師傅引進門,修行在個人”,上滿45分鐘即可,學生能學到什么,那是他自己的事了。這種說法無大錯,亦無大意義。但我遇到的不是普通的作曲老師,而是以傳道授業解惑為宗旨并將作曲理論與實踐高度結合的大家、著名的作曲家金湘先生,能成為金湘老師較早的學生,跟他學作曲,感受深切、感悟良多。
掌握不同的樂器“語言”
記得剛進師門,金湘老師讓我分別為中外各種樂器寫50-60個主題。我曾在民樂隊中拉過二胡,在管弦樂隊中拉過中提琴,因而完成這樣的作業并不難。一周后去回課,金老師看完后沒有我所期待的夸獎,也沒有批評,而是問我,高胡、京胡、板胡的性格有什么區別,小提琴、長笛的氣質有什么不同等,而后對逐個樂器進行介紹與分析,讓我知道,它們的“語言”各不相同,當然修辭風格也就完全不同了,應該“各說各的話”。這讓我想起一位非職業作曲,試圖寫一首長笛獨奏曲,寫著寫著就超出了長笛的最低音,于是乎就改成了單簧管獨奏了,出來的效果也許還湊合,但仔細琢磨,就不夠講究了。有一次上課,在處理一個連接部分時,金湘老師問了我好幾次問題出在哪,我都說不知道。金老師生氣了,讓我去洗菜,他接著去給另一位同學上課。我在洗菜時突然想到,可能是那個*f的時值不妥,于是告訴老師,他會心地笑了,并留我在家里吃飯。從金湘老師這里,我深深感受到:學習作曲是個艱難復雜的過程,多細都不為過。
注重建立“多聲思維”
跟金湘學作曲最重要的收獲,是他幫助我建立起了“多聲思維”。從那50多個中外樂器的主題中,篩選提煉出了8個,又從這8個主題中選了3個,從單三部的前奏曲直至寫到復三部和奏鳴曲。整個過程就是打碎原有的平面概念,逐步建立起多聲、立體、樂隊的思維。應該說專業作曲與非專業作曲的分界線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掌握的“多聲思維”是否豐富上。1984年,我去西藏采風后向他說起收獲與心得,并想寫點什么,后來在金湘老師的悉心建議與潛心指導下,我寫出了鋼琴組曲《西藏素描》。在這首組曲的寫作過程中,金湘老師不厭其煩地多次幫助我修改與調整,使其趨于成熟,后來,該曲在全國第四屆音樂評獎中獲獎,并被鮑蕙蕎、李民鐸、陳崇學等鋼琴家們作為保留曲目經常上演以及錄制CD并出版。這部作品正是在金湘老師給我進行了大量的“多聲思維”訓練后的結果。
由微觀到宏觀,金湘老師將他的“多聲思維”“立體結構”等觀念,在他的《原野》等優秀的歌劇作品中作了更加充分和恰當的展現,如劉烈雄說的“他以《原野》的創作實現了中國歌劇思維由‘平面向‘立體的復述轉變,使得戲劇性、交響性和民族性有機地滲透和交融,形成渾然一體的復述語言體系,使得聲樂、器樂、戲劇動作、民俗音樂體例等都成為歌劇的語匯元素,并協調而交錯,形成一種強大的歌劇功能,為歌劇所表達的思想、主題及戲劇的最高任務服務”。
讓總譜充滿陽光和空氣
從學校畢業后,我和金湘老師見面的機會隨之減少,但每次我拿著總譜去找他,金湘老師仍然熱情滿滿、興致勃發。我曾經寫了一個圓號與樂隊的《西志哈志》交與他看,他仔細看了總譜后大發議論,除了表揚外,他建議我進行修改補充的地方多達十幾處,其中最讓我心服口服的是對第一樂章樂隊呈示部的織體處理,弦樂如何遞次加厚,打擊樂如何進行點描,他都講解得很是精到。金老師在指導的過程中似乎總在提醒我們:不要以為你什么都考慮到了,什么都能記住,寫總譜要全面地推進,速度記號、強弱記號、表情記號都要寫一遍即過,否則,某一小節上的特別想法與處理就會轉瞬即逝。同時,鑒于對我早期的一些樂隊作品寫的比較滿意,金湘老師多次向我提醒:“總譜里要充滿陽光和空氣”,現在回想這句話的韻味:真是形象而生動的比喻!
2006年,山西運城曾找金湘老師創作音樂劇《娘啊娘》,他推薦我來作曲,這是我第一次與師母李稻川導演合作,大家合作得都很愉快。2012年,我的作品集準備付梓出版,金湘老師非常熱情地為我寫了跋,并對我鼓勵有加:“作曲家出版自己的作品集是大事,也是喜事,隨著音樂教育的普及與提升,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閱讀總譜,閱讀中國作曲家的總譜,包括崔炳元的。”
金湘老師的歌劇音樂會、交響音樂會、《原野》的兩個版本我都看過。《日出》上演前,我探望老師時看到鋼琴譜,后來陪同金湘老師看了B組的《日出》。聽音響與看總譜的“感官互換”(或者叫“通感”)正是在金湘老師指引下,逐步培養出來的。
恩師外表的堅硬,此刻回想起來都是親切與溫暖;恩師內心的柔軟,此刻更是讓人倍感心酸;恩師的獨立自恃,是我精神上的旗幟;恩師的諄諄教誨,更讓我不敢懈怠、緩緩向前。能有幸成為金湘的學生,感慨萬千、感恩久遠!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