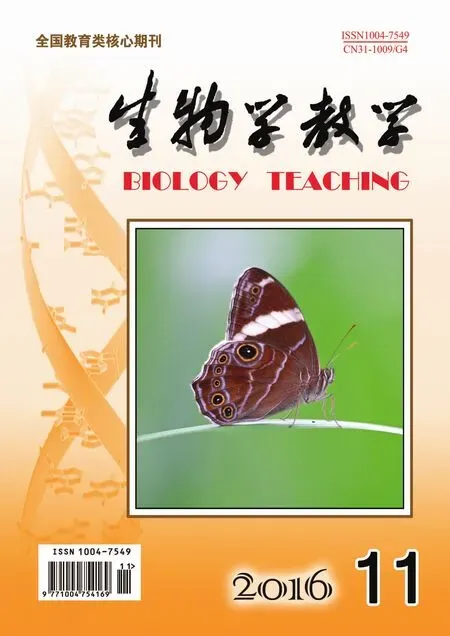線粒體的發(fā)現(xiàn)和起源假說
劉 銳
(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大學(xué)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 合肥 230026)
1 線粒體的發(fā)現(xiàn)過程
自19世紀以來,解剖學(xué)迅速發(fā)展,生物器官的結(jié)構(gòu)以及相應(yīng)功能的研究得到科學(xué)界的重視。這一時代有一位杰出的德國生物學(xué)家、解剖學(xué)家寇里克(Rudolph Kolliker)在這一研究領(lǐng)域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寇里克出生于瑞士蘇黎世,21歲之前一直在家鄉(xiāng)生活學(xué)習(xí),并順利讀完高中。1838年,他來到波恩大學(xué)學(xué)習(xí)生理學(xué),畢業(yè)后一直從事解剖學(xué)研究。他在動物學(xué)方面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詣,他解剖了脊椎動物中的哺乳綱和兩棲綱動物的橫紋肌、平滑肌、骨頭、皮膚、血管等各種組織,并且詳細地記錄了實驗結(jié)果[1]。1850年,他在實驗中觀察到昆蟲的橫紋肌中具有許多顆粒結(jié)構(gòu),并將這些顆粒進行了分離研究。根據(jù)實驗,寇里克推測它們被半透性的膜包被著,這些小顆粒其實就是當時未認識的線粒體。寇里克第一個描述了線粒體,但他當時并沒有對這些顆粒進行命名,因為他還無法窺測到線粒體內(nèi)部的亞顯微結(jié)構(gòu),無從得知這些細胞器的具體功能,因而無法根據(jù)結(jié)構(gòu)或功能上的特點對其命名。
在實驗中,寇里克所解剖的都是一些需要能量較多的組織,包括平滑肌、橫紋肌和心肌等。這些組織都與運動緊密相關(guān),需要大量的能量供給,而線粒體正是細胞中的動力工廠,因此這些組織中的線粒體數(shù)量相對其他組織要多很多,這也讓寇里克有機會發(fā)現(xiàn)它們。
由于當時生物學(xué)界對細胞的微觀結(jié)構(gòu)并沒有達成共識,同時顯微鏡也剛剛應(yīng)用到生物學(xué)的研究中,所以對新發(fā)現(xiàn)的細胞器大多數(shù)是停留在外觀形狀的描述,并沒有了解它們的具體功能和亞細胞結(jié)構(gòu)。寇里克也僅僅是描述了線粒體的形狀和大小,他無法去驗證線粒體的具體功能和內(nèi)部結(jié)構(gòu),只是大膽猜測這種數(shù)量眾多的顆粒可能會有著極為重要的生理學(xué)功能。
1880年左右,顯微手段有了質(zhì)的飛躍,出現(xiàn)了多個鏡片組合在一起的復(fù)合顯微鏡,使得顯微鏡的放大倍數(shù)提高到了2000倍,分辨率也相應(yīng)地提高到1 μm的水平,從而使生物學(xué)家得以深入研究細胞的亞顯微結(jié)構(gòu)。德國病理學(xué)家及組織學(xué)家理查德·阿爾特曼(Richard Altman)在研究細胞的亞顯微結(jié)構(gòu)時,在需能組織附近發(fā)現(xiàn)了大量的顆粒聚集,他決定將這種“原生粒”與細胞中的其他結(jié)構(gòu)區(qū)分開來[2]。阿爾特曼1886年發(fā)明了一種鑒別這些顆粒的染色法,據(jù)此可以在顯微鏡下清楚地看到這些顆粒在細胞中的分布情況。阿爾特曼猜測這些顆粒可能并不是細胞自身的組成部分,而是與細胞具有共生關(guān)系的細菌。他將觀察到的這些顆粒命名為“原生粒”(bioblast)。1890年,生物學(xué)家帕特斯(Petzius)將觀察到的同樣的小顆粒命名為肌粒(sarcosome),因為它在肌肉細胞中的數(shù)量較多。同年,生物學(xué)家理查德·阿爾特曼又將這些顆粒命名為細胞質(zhì)活粒(bioblast),認為這些顆粒并不是細胞的組成部分,而是獨立的與細胞有共生關(guān)系的細菌[3]。
直到1897年,德國生物學(xué)家卡爾·本達(Carle Benda)首次正式將這種顆粒命名為線粒體(mitochondrion)。他在研究中發(fā)現(xiàn),這些原生粒數(shù)量眾多,且形態(tài)多變,有時候呈線狀、有時呈顆粒狀,所以他用希臘語中“線”和“顆粒”對應(yīng)的兩個詞“mitos”和“chondros”組成“mitochondrion”為這種結(jié)構(gòu)命名。至此,“線粒體”的名稱才正式被科學(xué)界所采納。從1850年線粒體被描述,到對它正式命名整整經(jīng)歷了漫長的半個世紀的時間[4]。
在線粒體被發(fā)現(xiàn)和命名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它在細胞中的具體功能依然是個謎,直到20世紀初關(guān)于線粒體功能的研究才有所突破。
1899年,美國化學(xué)家萊昂諾爾·米歇利斯(Leonor Michaelis)開發(fā)出具有還原性的詹姆斯綠染液,并且利用這種染液為肝細胞中的線粒體染色。他通過顏色的變化,推斷線粒體參與了細胞中的某些氧化反應(yīng)。該實驗成功的關(guān)鍵是實驗素材選擇了肝臟細胞。由于肝臟在人體中擔(dān)負了解毒的重要作用,而解毒需要大量的能量,因此其中線粒體的數(shù)量也較其他組織更為豐富,染色后容易被清楚地觀察。米歇利斯發(fā)現(xiàn),在細胞耗氧后,被染色的線粒體顏色會逐漸變淡,從而提示線粒體具有氧化還原反應(yīng)的作用。經(jīng)過反復(fù)的實驗驗證,1900年米歇利斯公布了這一方法,隨后很多生物學(xué)家開始不斷嘗試使用這種方法去觀察線粒體。美國細胞學(xué)家埃德蒙·文森特·考德里(Edmund Vincent Cowdery)對米歇利斯的方法進行了大力推廣,并在此基礎(chǔ)上進行了改良,使得線粒體的結(jié)構(gòu)能夠更清楚地展示在顯微鏡下。隨后,德國生物化學(xué)家奧托·海因里希·沃伯格(Otto Heinrich Warburg)在對線粒體進行標志性染色后,成功完成了線粒體的粗提取,繼而從中分離得到一些催化有氧呼吸反應(yīng)的酶,并提出了這些酶能被氫氰酸等氰化物抑制的猜想。沿著這一思路,科學(xué)家逐步證明線粒體是細胞中發(fā)生克雷布斯循環(huán)、電子傳遞、氧化磷酸化作用的場所,從而確定了線粒體是真核生物細胞進行能量轉(zhuǎn)換的主要部位。
2 線粒體的起源假說
關(guān)于線粒體的起源,生物學(xué)界一直沒有形成統(tǒng)一的觀點,迄今為止,依然存有爭論。目前主要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假說,其一是內(nèi)共生起源學(xué)說(endosymbiosis theory);其二是非共生起源學(xué)說(noendosymbiosis theory)。這兩種假說相互對立,又各自有著支持論據(jù)。
2.1 內(nèi)共生起源學(xué)說 內(nèi)共生起源學(xué)說認為,線粒體是由被細胞吞入的細菌演化而來。這一學(xué)說最早的雛形來自于幾位俄羅斯科學(xué)家,其中起關(guān)鍵作用的是生物學(xué)家安德雷·謝爾蓋耶維奇·法明茨恩(Andrei Sergeevich Famintsyn)。他著手從植物的細胞中將重要細胞器葉綠體分離出來,并試圖讓它在離體的狀態(tài)下生長。他的想法代表著內(nèi)共生學(xué)說最原始的萌芽:假如能夠證明葉綠體能夠在離體的環(huán)境下獨立生長,就可以從側(cè)面反映葉綠體可能是來自于被細胞吞入的細菌,它與細胞之間是共生的關(guān)系。隨后,另一位生物學(xué)家康斯坦丁·謝爾蓋耶維奇·梅里日可夫斯基(Constantine Sergeevich Merrykovsky)提出了“雙原生質(zhì)”(twoplasm)理論,他認為細胞器來自于細胞內(nèi)部的新細胞,葉綠體起源于一種特殊的藍綠藻。這種理論實際上也認為葉綠體與細胞可能存在共生的關(guān)系。第三位生物學(xué)家波利斯·米哈伊洛維奇·庫佐·波利延斯基(Boris M. Kozo-Polyansky)則認為細胞的游動性源于共生。當時這三位生物學(xué)家在俄羅斯學(xué)術(shù)界享有很高的聲譽,他們的觀點在俄羅斯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但是當時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的西方科學(xué)界對這些理論并不以為然。1905年,克斯坦丁·麥斯克沃斯基(Konstantin Mereschkowsky)最先提出葉綠體是由原先的內(nèi)共生體形成的。隨后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學(xué)者伊萬·沃林(Ivan Wallin)在哥倫比亞大學(xué)做“推測細胞成分”的主題匯報時,提出線粒體由原先的內(nèi)共生體形成,而這些共生體具有與細胞器相同的功能。但是,這個在當時頗具前瞻性的學(xué)說卻遭到與會者的嘲笑與抵制。而最終完整提出內(nèi)共生學(xué)說的是美國生物學(xué)家馬古利斯(LynnMargulis),她在1970年出版了《真核細胞的起源》一書,在書中她第一次提出了較為完善的內(nèi)共生學(xué)說。她認為原核生物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吞入了一些好氧的細菌,這些細菌在長期與原核生物共存的情況下逐步發(fā)展演化起來,并且沒有被分解與消化,而是與寄主之間達到了一種默契,產(chǎn)生相互適應(yīng)的關(guān)系,形成一種互利共生的狀態(tài),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進化成線粒體。她的這一學(xué)說包含了幾條重要的觀點:原線粒體是線粒體的祖先,它屬于一種革蘭氏陰性菌,它可以進行三羧酸循環(huán)和電子傳遞;原線粒體可以與寄生的宿主產(chǎn)生相互依賴的共生關(guān)系,兩者是互利共生的;宿主可以給原線粒體提供豐富的營養(yǎng),原線粒體的氧化分解可以給宿主提供生命活動所必須的能量[5]。
馬古利斯提出的線粒體起源于內(nèi)共生細菌的假說,獲得了學(xué)術(shù)同行的大力支持。首先,線粒體與它的宿主細胞一樣,均具有各自獨立的遺傳物質(zhì)——線粒體脫氧核糖核酸和線粒體核糖核酸;第二,細胞在進行自身繁殖的同時,線粒體等細胞器也同時進行增殖和分配,保留了獨立性和連續(xù)性;第三,現(xiàn)存生命有機體中依然存在著類似的現(xiàn)象,例如,低等動物草履蟲中含有藍藻共生體,水螅中含有綠藻共生體等。這些證據(jù)都可用來作為線粒體起源于需氧的細菌的證據(jù),也成為支持馬古利斯內(nèi)共生起源學(xué)說的依據(jù)。
2.2 非共生起源學(xué)說 有關(guān)線粒體起源的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理論是非共生起源學(xué)說。這種學(xué)說認為,細胞本身就來源于一種好氧的細菌,伴隨著生物的不斷進化,某些具有呼吸作用的細胞膜逐步內(nèi)陷,并包裹住部分遺傳物質(zhì),如DNA或RNA等,逐漸形成了既具有獨立遺傳物質(zhì)、又有著呼吸功能和膜結(jié)構(gòu)的線粒體。
非共生起源學(xué)說的產(chǎn)生是內(nèi)共生起源學(xué)說的反對者集思廣益的產(chǎn)物,是在不斷反駁馬古利斯觀點的基礎(chǔ)上綜合起來的[6]。
非共生起源學(xué)說的內(nèi)容主要包括三點:第一,現(xiàn)今存在的一部分原始的好氧細菌中具有擬線粒體結(jié)構(gòu),這種結(jié)構(gòu)是由細胞質(zhì)膜的內(nèi)陷和折疊形成的,具有呼吸功能;第二,原核細胞中具有呼吸功能和光合作用功能的結(jié)構(gòu)可以分別看成是線粒體和葉綠體的雛形,現(xiàn)今細胞的這兩種細胞器都是在原核細胞中逐步進化而來的,而不是由細菌共生轉(zhuǎn)化而成的;第三,在驗證內(nèi)共生學(xué)說的實驗中,通過對真核細胞連續(xù)切片發(fā)現(xiàn)核膜與各種細胞器膜的連續(xù)關(guān)系,由此有力地證明了這些細胞器與細胞核具有更為親密的關(guān)系,很可能是起源自自身內(nèi)膜系統(tǒng)的內(nèi)陷,而非外來共生的細菌。
2.3 兩種起源學(xué)說的比較分析 目前這兩種學(xué)說都有著各自的理論和實驗證據(jù),但是究竟孰是孰非至今尚無定論。但是相比較而言,由于共生是生物界的普遍現(xiàn)象,所以內(nèi)共生學(xué)說的支持依據(jù)相對較多。
例如,近年發(fā)現(xiàn)的灰孢藻本身并無葉綠素,但有許多葉藍小體生活在其體內(nèi)并進行光合作用,這是對內(nèi)共生起源學(xué)說的有力支持。此外,葉綠體和線粒體都有各自獨特的DNA,可以自行復(fù)制,且不完全受細胞核DNA的控制。線粒體和葉綠體的DNA同細胞核DNA有很大差別,但同藍藻和細菌的DNA卻很相似。這些事實都說明細菌和線粒體、藍藻和葉綠體可能是同源的,也就是存在著共生的關(guān)系。同時,抗生素可以分別抑制真核生物細胞的線粒體和葉綠體以及細菌和藍藻的現(xiàn)象,也從另一個角度提示這兩種胞器與細菌和藍藻之間可能有著共同的起源。再從細胞膜的角度來看,線粒體和葉綠體的內(nèi)、外膜有顯著差異,并且內(nèi)、外膜的化學(xué)成分是不同的。外膜與宿主的膜基本一致,特別是與內(nèi)質(zhì)網(wǎng)膜很相似,而內(nèi)膜則同細菌和藍藻的膜相似。這些證據(jù)都有力地支持著內(nèi)共生起源假說。
雖然有著很多的證據(jù)支持,但是迄今為止關(guān)于內(nèi)共生起源學(xué)說的爭議依然存在。最大的爭議來自于它與進化思想的矛盾。按照進化論的觀點,在內(nèi)共生過程中,擁有先進氧化代謝途徑的好氧細菌無疑應(yīng)該占優(yōu)勢,但是馬古利斯的內(nèi)共生學(xué)說卻認為好氧細菌反而逐步喪失了獨立自主性并將其遺傳信息成批地轉(zhuǎn)移到了宿主細胞中,這顯然是不符合進化論思想的。同時,內(nèi)共生起源學(xué)說也不能清楚地解釋細胞核這樣一個控制生命活動最主要的細胞器是如何起源的。因此,內(nèi)共生起源假說依然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有更加合理和完善的學(xué)說出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