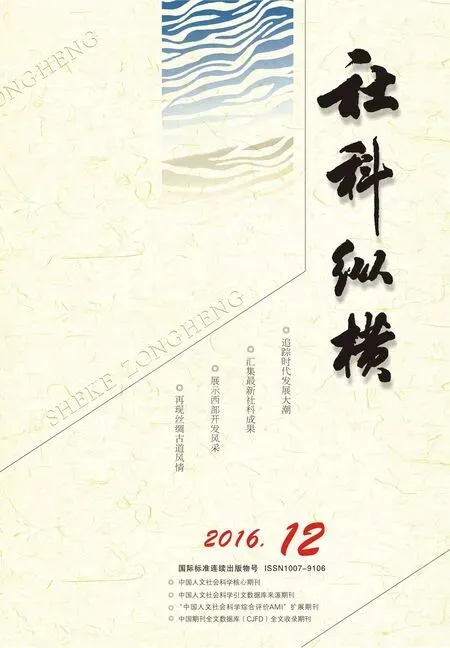河西寶卷對走廊文化的注解及其當代價值
哈建軍 張有道 李奕婷
(1.復旦大學民族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2.蘭州交通大學 甘肅 蘭州 730070;3.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
·文化研究·
河西寶卷對走廊文化的注解及其當代價值
哈建軍1張有道2李奕婷3
(1.復旦大學民族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2.蘭州交通大學 甘肅 蘭州 730070;3.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
河西民俗傳統、民間信仰、家園觀念等民間文化都是時代主流文化在河西地區不斷沉積的結果,歷史鑄造了河西是一個多元文化“共生”的環境;河西寶卷是在河西這一特殊地域中經歷了文化“潮汐”傳承下來的,給我們的認識經驗是:傳承華夏文明即要延續家園向往的保障力,創新華夏文明不能將地方和中央分離,正如不能將“人”和國家分割為面對面的“個體”,而是知行合一的“共同體”,要真切把握文化之中的“人”的切實需求。
河西寶卷地域歷史文化共生文明意識
絲綢之路上文化豐富多樣,傳播了華夏文化、西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也積淀了走廊文明的樣態。河西寶卷是流傳于河西走廊的民間寶卷文本及其念唱活動,也是河西的一種特殊的民間曲藝活動,更是多元文化在河西地區沉潛的文化。寶卷活動在此繁衍,既與宗教信仰活動有關,還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調適慣性有緊密聯系。從人類學的觀察來看,文化是在調適中接續傳統完成傳承的,也是在調適中教化新人、培育年輕人的。河西寶卷在“五四”時期的疑古、批古的思潮中,逐漸走向了沒落,但是作為民間的一種教化儀式、文娛活動,卻保留在了老百姓的生活記憶中。至今,河西農村還有不少農家在家中留藏有寶卷抄本,偶爾在農閑時間會有“念卷”活動。他們舍不得扔棄這些已經有些破舊的寶卷卷本,是因為這些卷本曾是崇羨“文化人”的時代里祖輩、父輩或自己在當年謄抄或收藏的“文化”。在往昔的時代,能“抄卷”“念卷”“起卷”的人都可被老百姓視為是“有文化的人”,而且認為在祁連山腳下、在這狹長的“山夾”之中,能有“文化”已實為不易。一定程度上說,河西寶卷詮釋了河西人民的宿命,也注解了河西人民的家園觀和家園文化,這與河西所在地理位置、地形特點和歷史景觀有很多關聯。
一、河西走廊文化的“潮汐”與沉潛
河西走廊在歷史上就是建構家園的基點。在新石器時代①,河西就有了人類生活的遺跡,這從1989年在河西走廊西北端馬鬃山區明水鄉霍勒扎德蓋河谷地區發現的三件打制石器可以說明。而新石器時代及其以后的文化遺跡在河西走廊卻星羅棋布,學界對此分類有好幾種,其中,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四壩文化和沙井文化代表性地說明了河西走廊歷史上的生命轍跡。
在早期的地理學著作《山海經》以及《尚書禹貢》中,有些記述已經涉及三危、合黎、黑水、弱水等這些河西地段的山川地理狀況。據《穆天子傳》中記載,西周時期周穆王西巡時經過河西走廊,而且在當時河西已為中原所知曉。戰國時期,河西走廊主要是月氏、烏孫、羌人和匈奴等游牧民族居息游動,且月氏、烏孫和羌人均“與匈奴同俗”,兼行牧業和農業。匈奴的金屬與皮革加工、陶器與木器制作、紡織等技術水平已經很高,在河西地區就有傳用跡象。
秦末漢初,匈奴趁中原戰亂之機,重新控制了大漠南北、河西、河湟及西域地區,匈奴與漢朝在這一帶進行了長達數年的“拉鋸戰”。此時漢高祖為恢復經濟、提升抗爭實力,采取了與匈奴“和親”的策略,以求得漢朝邊境的安寧。這種通過“和親”以安穩邊境局勢的做法延續到漢惠帝、文景時代,直到漢武帝初年,“和親”都是首選的“定邊”策略。漢武帝繼位前后國力空前強盛,改變了漢高祖以來對匈奴“和親”的羈縻政策為武力征伐,同時招募能使者如張騫等出使西域,欲溝通大月氏以夾擊匈奴。從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90年的40多年里,漢朝先后調集200多萬的兵力,派衛青、霍去病等將,進行了22次與匈奴的戰事,漢初以來匈奴強而漢弱的局面發生逆轉。公元前121年,漢武帝派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進兵河西,過焉支山而突襲匈奴右部。在此次漢朝反擊匈奴的重大行動中,匈奴休屠王因降漢之心不堅而被渾邪王所殺,渾邪王降漢后被封侯,其部眾降漢后被分別安置在西北邊五郡塞外,與當地漢族混居,河西自此正式歸入漢朝版圖,漢族中原文化以主流形態形塑了河西地區的文化。漢朝占據河西以向西域推進,所以對河西的治理主要采取了筑城設郡的方式,修筑長城烽燧,駐軍屯田、移民實邊,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積蓄實力、穩固西北而設置新縣。漢朝歷史中,河西地區各族人民就在戰亂與遷徙中感受到了在民族融合、文化交融中穩定家園的必要性,原有的畜牧業、農業生產方式都發生了變更,逐漸使河西地區出現“殷富”景象。
東漢時期,匈奴分為南北兩部,南匈奴附漢后與漢文化融合漸深。東漢國勢衰微,加之政治中心東移,在西北邊疆的政策也由漢武帝時期的積極進攻、主動進取變成了消極防御、被動退守。東漢中后期政治黑暗腐朽,羌族部眾大量內遷且起義不斷,與西域關系曾有“三絕三通”,朝廷中曾有三次“棄涼”之議[1](P130-134)。西北局勢動蕩不安,河西經濟遭受大沖擊而呈衰退之勢,加之自然災害頻繁發生,漢安帝初年發生了“涼州大饑,人相食”的現象,人心惶惶而家園“虛耗”[2]。直到曹魏時期,經過張既、徐邈、倉慈、皇甫隆等地方官員的勵精圖治,河西社會才逐漸恢復到安定生活和經濟發展中。
西晉的“八王之亂”后,匈奴、鮮卑、羯、氐、羌所謂“五胡”相繼內遷而逐鹿中原。司馬氏建立東晉政權后,北方陷入“十六國”分裂狀態,其間漢族張氏主政的前涼政權、氐族呂氏主政的后涼政權、鮮卑禿發氏主政的南涼政權、漢族李氏主政的西涼政權、匈奴沮渠氏主政的北涼政權相后主政河西大地,史稱“五涼”。“五涼”統治者謹修內政、保境安民,使偏遠的河西保持了一百多年相對安定的平穩時期。公元439年,北魏滅北涼,結束了北方分裂割據的局面,河西也重新與中原連為一體。北魏統治者重視對河西的開發,采取因地制宜、農牧并舉的策略,促動河西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北魏分裂后河西歸屬西魏,后西魏被北周所取代,北周時期以關隴集團為政治核心的統治者注重務實的社會改革措施,在河西普遍推行均田制,繼續推動河西的經濟社會發展。
隋朝建立后,突厥和吐谷渾常常抄略酒泉、武威、金城、天水、延安等地,使得河西走廊、天水、延安一代“六畜咸盡”,絲路交通數次被截斷。為了進一步解除北方草原民族結成的聯盟對中原政權的威脅,為了保障與西域的商貿往來,隋朝政府采取“內綏外御”“遠交近攻”“離強合弱”“以夷攻夷”等措施,一邊安輯諸“夷”,一邊開通西域,促動絲路貿易。隋朝政府將河西作為重要的戰略基地,加強了河西政權建設以完善邊防保障體系,同時大興屯田,發展農牧,開展互市,并倡導民族團結,取得了顯著成效,河西得到了又一個發展的高峰期。特別是隋煬帝在公元609年結束了對吐谷渾的戰事后西巡張掖,在張掖焉支山迎接西域二十七國首領,陳設了可拆卸可組裝的活動宮殿“觀風行殿”,與各國國王和使節一道宴飲,同賞“九部樂”與“魚龍戲”。隋煬帝與西域國賓共賞的“九部樂”中的西涼樂、龜茲樂、天竺樂、康國樂、疏勒樂、安國樂均是十六國以來從西域各國傳入的,隋煬帝時整理后被定為宮廷樂,顯示了隋朝與西域密切的關系。由于漢武帝時代及以后,河西就有來自西域的移民,隋煬帝上演“九部樂”也顯示了隋朝社會與西域各族、中國北方各民族共享文化、共系家園的姿態和視野。隋煬帝西巡事件,表征了中原民族政權、北方民族政權、西域民族政權以及西南民族政
權圍繞家園問題在河西走廊進行了一次求趨“共識”的對話,針對“家園(land,領地)”文化進行了一系列銜接保障的工作。因此說,隋煬帝西巡聚會對于隋朝在河西及西域統治的加強、保障絲綢之路的暢通、促進河西及中原經濟文化的發展都起到了積極作用。最終將近青海、新疆南部等廣大地域納入到了鞏固家園文化的版圖中。
唐朝建立以后便著手進行統一全國的戰爭。為消滅割據秦隴的薛舉,公元618年,唐帝李淵遣使至涼州與坐擁河西的李軌拉攏關系以聯合夾擊薛舉,之后進一步招撫河西。而“盡有河西五郡之地”的李軌于618年12月自稱“皇從弟大涼皇帝”,建元安樂,設置官署,“連好吐谷渾,結援于突厥”[3],拒絕接受唐朝官爵。于是唐朝政府又積極聯絡河南南部的吐谷渾共擊李軌,請涼州胡商首領安興貴招撫李軌而附唐。之后河西又經歷了幾年的反叛事件和與突厥、吐谷渾的紛爭后才穩于唐朝的統治之中。唐朝于711年設立河西節度使——唐朝設立最早、力量最強的節度使之一,并著力發展農牧業經濟,很快河西成為唐朝最富庶的地區之一。“安史之亂”后,唐朝將駐守西北的勁銳兵卒調往中原平叛,致使河西防務空虛,吐蕃乘機占領了河西、隴右之地。吐蕃統治河西近達百年,其間發生過敦煌人張義超率領沙洲人民反抗吐蕃統治而歸義唐朝的起義。
至五代北宋時期,中原王朝失去了對河西的有效控制。河西繼吐蕃統治以后,瓜沙歸義軍、甘州回鶻、西涼六谷族、西夏黨項族等都同時或相繼在河西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并將勢力不斷向今陜甘寧一代擴展,河西仍然是東、西、北三股勢力殫力爭奪的地區之一。黨項族建立的西夏政權在河西的統治延續了近兩個世紀,1226年,成吉思汗的蒙古漢國在攻取西夏時取得了河西,河西再次進入草原游牧文化的濡染之中。
明朝領有河西后,采取了設置衛所、修筑長城和屯田移民等措施,設立陜西西行都指揮使司和衛所,以及巡撫、總兵官等官職,而且接連派遣重臣巡視河西或專督兵馬,以此來管理河西。清代是我國多民族國家鞏固和發展的重要時期,隨著清王朝平準戰爭的勝利,河西不再像明代那樣屬于邊地,而完全成了內地。河西地位的變化和清王朝對河西的經營,使河西社會經濟再次出現了繁榮景象,滿族文化又成為河西地區的主流話語。但由于經濟重心的南移,陸上絲綢之路也已衰落。
辛亥革命及“五四”之后的民國期間,河西地區隸屬甘涼道和安肅道,實行過保甲制度,幾個公署轄區臨界地帶在行政區劃上有過多次的變動,譬如將永登劃歸蘭州市,將內蒙古阿拉善右旗劃入武威,后又劃分到內蒙古自治區,將景泰劃歸白銀市等。新中國建立后,河西地區的行政區劃基于穩定,實行了土地改革,個別縣區在武威市、張掖市、酒泉市的市轄范圍內有微調。國家在河西地區除了發展農牧、水利、電力、交通、商業,還大力發展工業,建立了玉門油田、金川銅鎳工業、酒泉鋼鐵工業等,都曾是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重點項目,從中培育出了中國的“鐵山精神”、“玉門精神”、“鐵人精神”。酒泉東風航天城的建立,成了中國在國際競爭中部署“空間戰略”的“航天基地”,發射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神舟夢”。改革開放之后,沿海地帶和中心城市所在省區首先從“經濟開發區”“經濟特區”逐漸發展成了“經濟發達地區”,河西地區落入了“欠發達地區”,甚至是“待開發”的落后地區,亦或者列入“扶貧”和“精準扶貧”的對象。
這種文化的“潮汐”交替雖說演繹了時代潮聲,同時形成了河西民俗傳統、民間信仰、家園觀念等民間文化的土壤,鑄就了多元文化“淘洗”和積淀的“共生”環境,也決定了河西地域文明、寶卷文化的傳承機遇。也充分表明,河西走廊作為山川—綠洲—沙漠—戈壁的復合系統,歷史上是“華夏”與“西域”的一大交集地帶,也是中西文化交匯交融的關鍵地區。這一系統中族群生態和地質地形復雜,人民生活方式多樣,是當代諸多文化的“沉積帶”和源頭。
二、河西寶卷對河西走廊文化的闡釋與延伸
河西寶卷是在敦煌俗文學的深刻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反映的是人民群眾切身的社會生活,寄托著人民群眾發自內心的喜怒哀樂,深深地植根于群眾之中,世代相傳,經久不衰。其傳播的價值導向、思想內容、方式方法,對河西走廊文化的體系
形成,都有很好的支撐和注解。
1.對價值導向的注解
寶卷以“如何做人”、提倡“行善事”“做善人”為落腳點,宣揚了維護家園和諧平安、家國同構、認同國家之主題,著重宣揚了如下幾種價值觀念。(1)“善”為立人之本,“善”為弘德之基。善可養性,亦可安心;善可積德,也可立信;善可節欲,善可敞明。無善難固本,無本做人難。篤善之人天護佑,揚善之事天地尊。人在天地之間要誠心向善、給養大德,是為本分。(2)人之為人要尚“信”。無論信天、信地,信神、信佛,信長者、信古訓,人要尚信,信可守安、信可有善報。(3)守人倫而重“禮節”,但有“節”才有“禮”。人的欲望出于性,發乎情,但欲無止境,欲壑難平。(4)公正和平等。論多平凡的人都有對光明和正義的渴望,無論多卑微的人,所行之善都會得到神明的褒彰。(5)人與人的命運在現實生活中都是互有聯系、相互影響的,彼此之間是維特根斯坦式“繩索共同體”。(6)讀書會明理,做事要顧人。生活事相見人心,事件之中顯人品。生活之中有大“道”,寶卷之中有箴言。求是實干轉命運,傷天害理難為人。多行善事廣積德,成事留名有因果。(7)表現“家國同構”和“國家認同”的覺悟。(8)表現了“有序”則“可控”,維護家園生態的理性。這些價值,有力地支撐了河西走廊歷史文化遺產中蘊含的本地區民族特有的精神價值、思維方式和想象力。
2.對文化思想的豐富
河西走廊文化豐富多樣,包含域外文化、敦煌佛教文化、漢唐以來儒釋道合一的“三教”文化,還包括西北各民族的藏蒙回文化、河西歷史神話傳說、邊塞文學與民歌民謠、曲藝等多維內容。河西寶卷是絲綢之路上的河西文化與佛教思想結合的直接衍生產物。這種邊地俗文化藝術形式及其文本,絕對是絲綢之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4]
河西寶卷大體上可分為四類:一是反映社會日常生活的,如《鸚鴿寶卷》《紅燈寶卷》等。如《烙碗計寶卷》《丁郎尋母寶卷》《繼母狠寶卷》等,這類寶卷數量很多,質量也好,是最基本的一類。二是反映宗教的題材,它們是唐代變文和宋代說經的沿襲和衍化,如《目連三世寶卷》《灶君寶卷》;記敘佛教活動的,如《唐王游地獄寶卷》《目蓮救母寶卷》《劉全進瓜寶卷》等。三是根據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說改編的,如《孟姜女寶卷》《白玉樓掛畫寶卷》;如《天仙配寶卷》《劈山救母寶卷》《張四姐大鬧東京寶卷》《何仙姑寶卷》等,這類寶卷基本上是從民間傳說故事中改編,神話色彩很濃,聽起來委婉有趣,感染力很強。表述寓言和童話故事的,如《老鼠寶卷》《鸚哥寶卷》《義犬救主寶卷》等。四是表達歷史人物傳奇的,如《昭君和北番寶卷》《康熙私訪山東寶卷》《包公寶卷》等。這些內容豐富了民間社會的知識、理性和經驗,也豐富了老百姓的精神世界。
3.對文化傳播方式的完善
寶卷也是河西走廊家族教育和基層教化的主要方式之一。寶卷中的神靈崇拜思想、倫理秩序思想、家國“共同體”思想、懲惡揚善思想、品德修為思想以及家園建構意識都是寶卷傳播中的重要內容,交融滲透在或長或短的寶卷文本中,因此有的文本較長。越長的文本中,寶卷中的思想內容演繹得越齊備,交叉重疊之處越多。
寶卷的文本形式有的是木刻版,也有少數是石印本。在老百姓的家里傳抄的多是“手抄本”,筆記、字體、用紙等都各不一樣,體現著家庭中的經濟狀況。寶卷活動中的“起卷”和“抄卷”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地域文化、宗教信仰文化等的傳播方式及其范圍。總體上來說,寶卷的傳播形式主要有兩種:一是文字傳播,二是口頭流傳。口頭傳卷一是宣揚寶卷的故事大概和寶卷的趣味性,二是宣揚民間的習慣和規范。因為在老百姓看來,寶卷就是“有文化的人”“遺留”下來的“文化”。老百姓對“遺留”的認可,意味著尊重傳統、尊重先輩經驗,也意味著對前輩、先人之文化理念的認同與接受。因此,寶卷的傳播是民間“立信”的最基本方式。聚鄰宣講寶卷中的故事和義理,抄卷、藏卷在河西人民看來是積功德,所以有文化的人也樂意為之。那些不識字的人則請人抄,有一種說法是家中有卷(寶卷)便可以鎮妖避邪。
總體看來,河西人民傳抄寶卷、藏存寶卷、宣講寶卷都是在傳播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宗教信仰文化、地域民俗文化,也是在傳承教育文化、家園文化,甚至在傳承國家和民族的制度文化、慣習
規范。寶卷的傳播裹挾了老百姓對秩序和社會發展的體悟,寶卷的傳播又是一種自發行為,是一種不怎么受媒體和介質限制的交流行為,因此,河西寶卷的傳播傳承彌補了國家文化傳播體系中的虛漏之處,一定程度說也是對國家文化、民族文化的一種自覺完善。
三、對建構“共同體”意識的啟示
一直以來的河西地區“輪屬”于來自不同方位之民族的“家園”中,在民族政權之間擴展疆域、競占領土時,河西往往就成了“必爭之地”或者“戰略要地”。河西地區交替地被來自不同區域的文化覆蓋著、沖刷著,河西酷似一片“潮汐”中的沙灘,其中的富庶、貧瘠、繁華、寂寥如同沙灘上的潮來潮往,其主流文化形態如同中央政權對其“重要性”的認識保持了某種程度的一致性,也是“此消彼長”。
河西一度作為文人作家抒懷言志的基點,曾是不同時期“邊塞”詩人、作家抒情言志的重要意象。“家園”在進入文學層面時,就成了理想或意象。“家園”不僅有“土地”之意,還有“領地”之意;不僅是一種物權、財權,還是一種精神空間;不僅指向某一“個體”的訴求,還指向融合了其血脈關系、人情關系的“群體”的向往。當民族之間在對權力等級、地位差異、榮譽安危等的認識上發生較大的分歧時,家園意識就有可能以“民族意識”的面目凸顯出來。河西寶卷正是在這種文化“潮汐”和政治博弈中注解了河西大地上的家園意識、國家共同體意識的選擇。
河西寶卷在2006年被列入中國“非遺”后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同時,很多人在如何保護和開發利用河西寶卷這一“非遺”的問題上表現出了被動和迷惘,也有很多人在如何傳承和創新文明這一問題上表現出了一種無從下手的惶惑。這可能是當我們在討論“文化遺產”時,我們并沒有在關于文化的概念和功能問題上總是保持一致的看法,而且我們的話語對接中已經把寶卷看成了一種物質性的對象,而且看成了一種外在于自己的對象。政府在宣傳和推行“文藝遺產”保護時,政府扮演了一個主導者角色,將老百姓擺置在了“執行者”的角色。
這種被動、惶惑和“產業化”的設計中,意識上似乎潛藏著若干個“二元”分割結構。即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真實的“個體”,國家也便成了一個更大的“個體”,而且是一個靠文化匯集起來的“個體”。如此,老百姓會將自己和政府視為有等級距離的“二元”,也將人和文化視為了面對面的“二元”。這種分割的一個結果就是人往往把自己分離到了文化之外,人們對文化的推動就弱化其主體性,強化外力干預的接受認同。這樣,文化的演進和創新就有了依賴“他者”的思維模式。
“文化共同體”首先是一個榮譽、利益和精神向往的“共體”。哈佛大學人類學家赫茲費爾德(Michael Herzfeld)教授認為,一個國家最關鍵的是它的文化,我們在理解文化這個概念時,不應該用“這個文化”或“那個文化”指稱文化,文化是一個過程,不是一個東西。從赫茲費爾德的文化過程論出發,我們反觀河西寶卷的保護與開發和華夏文明的創新,就會覺得我們應該審視寶卷所映射的人們的生活過程和生命進程中的訴求,而不是去討論一個似乎外在于人的生命歷程的物質性的東西。這樣的視角倒不是為了呼應赫茲費爾德的理論,而是期望我們在保護和開發文化遺產時更多地考慮文化對于文化者享受的實際需要,注重文化遺產對于實施保護和開發者的真實需求。
注釋:
①以下史料梳理參見高榮主編.河西通史[M].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12).
[1]高榮.河西通史[M].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12):130-134.
[2]參閱《后漢書》卷五《安帝紀》、卷八七《西羌傳》.
[3]參閱《舊唐書》卷五《李軌傳》.
[4]程國君.論絲路河西寶卷的文化形態、文體特征與文化價值[J].甘肅社會科學,2016(2).
I207.7;G127
A
1007-9106(2016)12-0137-05
*本文為甘肅省社科規劃項目“基于PV-GPG理論的華夏文明創新區績效指標體系研究”(項目編號:YB059);河西學院校長基金項目“河西寶卷的當代文化價值研究”(XZ2012-17)成果。
哈建軍,復旦大學民族研究中心博士后,河西學院復旦—甘肅絲綢之路經濟協同發展研究院副教授;張有道,蘭州交通大學副教授;李奕婷,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研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