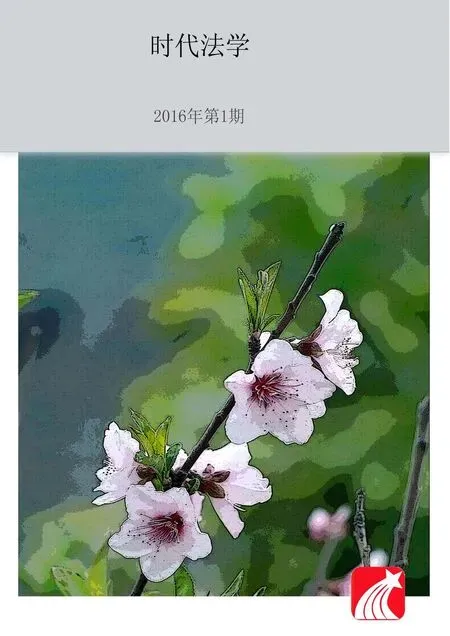論預防接種異常反應損害的社會法救濟*
賈小龍
(蘭州理工大學法學院,甘肅 蘭州 730050)
論預防接種異常反應損害的社會法救濟*
賈小龍
(蘭州理工大學法學院,甘肅 蘭州 730050)
從發生、影響對象及解決途徑看,預防接種異常反應致害是典型的社會問題,需要通過有別于傳統損害賠償制度的特殊機制補償受害者。我國現行立法規范位階較低,補償項目地方差異較大,救濟程序繁雜。為此,應在借鑒比較法經驗的基礎上,重構預防接種異常反應致害救濟程序,實現對受害者的便利、高效救濟。
預防接種;異常反應;社會問題;社會法;救濟程序
國務院《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第40條規定,預防接種異常反應,是指合格的疫苗在實施規范接種過程中或者實施規范接種后造成受種者機體組織器官、功能損害,相關各方均無過錯的藥品不良反應。發生異常反應,不但會對受種者個體造成損害,從而影響其本人和家庭正常生產生活,而且還可能引發群體性恐慌,阻礙國家計劃免疫制度的實施。因而,完善的預防接種異常反應損害補償制度,是國家計劃免疫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然而,從立法來看,我國迄今尚未建立起統一的預防接種異常反應補償制度,學說探討亦較匱乏。為此,理論上亟需回答下列問題:接、受種各方對于預防接種異常反應損害的發生均無過錯,然則受害者應當獲得救濟、抑或是讓損害停留發生之地?傳統公、私法救濟制度能否勝任對此種損害的救濟?另行救濟制度設計應當秉承何種原則?
一、異常反應損害的社會問題本質與救濟的正當性
(一)異常反應損害是典型的社會問題
社會問題是一個和人類社會一樣古老的歷史范疇,是社會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伴隨物和代價*袁華音.社會問題論綱[J].社會學研究,1994,(2):56.。其內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前者泛指一切與社會有關的問題,后者則主要指社會的病態或失調,并由此對全體或部分社會成員的共同生活形成障礙,需要動員社會力量加以干預的特殊社會現象*〔3〕劉成斌,雷洪.社會問題的社會性[J].理論月刊,2002,(1):48.。社會問題的本質特征是其具有社會性。從形成看,它不是源自于特定的生物結構或心理構成,即非少數人的責任所致,而是根植于社會系統的運行本身〔3〕。通常是因為社會在運行中發生了各系統之間的失調所致。從內容和直接作用對象看,它超越了特定的個體,指向不特定的多數人。從解決途徑看,受影響者的分散使得個別行為要么難以應對,要么其應對措施反而會抵消公共政策效果、甚至引發新的社會問題,因而需要動用社會的集體力量加以系統解決。由是觀之,異常反應損害是典型的社會問題。
首先,異常反應損害直接源于預防接種的實際發生,而不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預防接種都是社會維護整體安全的有意安排,構成社會運行的一部分。正如《關于進一步做好預防接種異常反應處置工作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所言,預防接種是貫徹黨和政府執政為民、促進社會和諧發展、保障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工作。《衛生部關于加強預防接種工作的通知》也指出,預防接種是政府提供的一項重要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又是一項社會性非常強的公共衛生工作,……。預防接種異常反應損害的發生,正是這一特定社會運行中各系統之間的失調,并由此給不特定個體帶來了損害。
其次,異常反應損害的發生具有不可控性。此處所謂不可控性,是指對于實際發生的損害,當事人無法控制和預見。就此而言,任何損害在某種程度上都有不可控性。以侵犯人身權為例,受害人無法控制損害是通常之事。而從加害人角度看,疏忽大意之加害人主觀上也沒有實際預見損害的發生,因而就損害的實際發生而言,他也無法控制;即便在行為人故意致害或因過于自信的過失而致損害發生的情形下,雖然其可以控制致害行為,但對于行為所致之實際致害程度,行為人無法準確預知和控制同樣是通常之事。異常反應致害的不可控性,與前述例證所表明的情況既有相同之處,也有其獨特性。相同之處表現在,接種方和受種方對于異常反應所致損害的程度往往也是不能預見和控制的。比較而言,獨特性更為突出:一是接種方和受種方充其量只能在概括意義上預知異常反應發生的可能性,而對于異常反應是否會發生、何時發生、幾率幾何,都無法具體預知,相應的,因發生異常反應致害的范圍、程度更加無法預測。二是除非不接受預防接種,否則并不能通過任何責任歸咎機制或方法的預設而降低異常反應發生的可能。這一點與因加害人過錯侵害他人權利情形存在顯著不同,在過錯侵害他人權利案件中,通過個人責任機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遏制損害發生的效果。
第三,異常反應損害的解決,不能也不應依靠單個人的行為。就我國而言,預防接種具有強制性。盡管現行法律、法規并未明確規定無正當理由拒絕接受預防接種的法律責任,但從《條例》第26條、第27條規范精神和實踐來看,個人、特別是兒童,除非不接受國家義務教育,對于第一類疫苗的接種沒有選擇權。既然對于是否接種沒有選擇權,相應的意味著兒童及其監護人對于異常反應的發生無法控制。從積極的方面來說,預防接種的受益者既包括了受種者本人,也惠及了社會整體。準確地說,大規模預防接種的首要目標是群體免疫*Stephanie Pywell,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Recent and Impending Changes to the Law of Statutory Compensation for Vaccine Damage”, J.P.I. Law, 2000, 4, p.247.。既然全社會都從個體普遍接受預防接種中受益,則其理應承擔單個預防接種之不利后果。反過來說,單個人解決異常反應致害的最可靠途徑莫過于拒絕受種。這樣,難免抵消社會推行普遍預防接種計劃的效果。
(二)損害恢復是社會生活的內在準則
幾個世紀以來,先賢們從不同角度揭示了社會的產生及其與個人之間的關系。柏拉圖認為,社會是“大寫的人”,內部和諧、并有其獨特的平衡規律。亞里士多德指出,不是人產生了社會,而是社會產生了人,離開社會,人實際上不可能存在*[俄]弗蘭克.社會的精神基礎[M].王永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38-39.。17、18世紀的主流學說則認為,社會產生自個人之間的協定。在孔德和斯賓塞的功能主義視角下,社會與生物有機體相似,是由在功能上滿足整體需要從而維持社會穩定的各部分所構成的一個復雜系統。這一系統的粘合劑正是個體所共享的價值觀*〔8〕〔9〕[美]戴維·波普諾.社會學[M].李強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108.102-103.。俄羅斯學者弗蘭克在批判社會個原主義和社會普濟主義的基礎上指出,社會存在本質上是作為人的內部精神生活與其外部體現兩者的統一*[俄]弗蘭克.社會的精神基礎[M].王永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90.。美國學者戴維·波普諾指出,“社會是有著相互認同、團結感和集體目標的人的集合。”〔8〕這個社會性集合包含了滿足人類基本需要的所有社會設置。為了滿足人的需要,社會要建立其獲取和分配經濟等資源的程序和機制〔9〕。盡管前列各中主張之間差異明顯,但均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社會具有滿足個體需要的天然使命。從相反的方面來說,唯有存在普遍認同的資源分配機制和個人損害恢復機制,社會才能因個體之認同而存在。
二、異常反應損害發生的無過錯性與公、私法損害救濟的失靈
根據《條例》規定,構成異常反應損害需要具備如下條件:受種質量合格;接種規范的疫苗產生了異常反應;受種者實際遭受了損害;損害與異常反應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相關各方對于異常反應的發生均無過錯。按照《條例》第2條對疫苗的分類管理,表面上看,不論是《條例》規定的哪一類疫苗,直接參與的當事人都是接種者(如計劃免疫部門、醫療機構)和受種者,但兩類疫苗接種中所涉及的法律關系性質有所不同。就第一類疫苗而言,接種者和受種者之間形成行政法律關系。接種者系受委托執行國家計劃免疫,受種者則是履行接受預防接種之法律義務。從行政行為分類上說,預防接種相當于針對人的一般命令*[德]哈特穆特·毛雷爾.行政法學總論[M].高家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97.,命令義務的承擔者是根據某種一般特征、類別確定的人群,如一定年齡階段的兒童。就第二類疫苗而言,公民就是否接種享有完全的自主決定權,當事人之間形成典型的民事法律關系。相應的,發生異常反應致害時,受害者可能適用的救濟依據也應有所不同:第一類疫苗對應國家賠償制度,第二類疫苗對應侵權法律制度。
盡管如此,但因異常反應致害是一種“加害方”或“接種方”無過錯的行為,不論是國家賠償制度,還是侵權法律制度,都難以適用。以第二類疫苗為例,理論上說,《侵權責任法》所規定的醫療損害責任包括兩個大的類型:醫療過錯責任、侵害隱私權責任、不必要檢查所致的責任以及醫療領域內的特殊產品責任*王利明.侵權責任法研究(下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368.。前者的構成需以醫療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存在過錯為必要,后者是一種嚴格責任,其構成需以藥品、消毒藥劑、醫療器械存在缺陷,或者用于診療的血液屬于不合格產品為必要。由前文敘述可知,有關各方對于預防接種發生異常反應均無過錯,僅僅是因為疫苗本身的生物性質、而非缺陷所造成。據此,受害者難以依據《侵權責任法》來獲得必要救濟。同理,由于欠缺行政命令及其執行過程中的違法性,第一類疫苗異常反應受害者無法通過《國家賠償法》獲得救濟。
三、異常反應損害社會法救濟的正當性
(一)社會法以解決社會問題為根本使命
社會問題與社會以及人的社會本質形影不離。社會問題的存在,也即社會準則與社會現實之間的顯著不一致*[美]默頓.社會研究與社會政策[M].林聚任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53.,推動了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縱觀人類文明史,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的不斷創新是人類解決既有社會問題的主要依托。
然而,以立法、公共政策為主要載體的社會制度與受自然及人力資源狀況、科學技術主導的生產方式變化相比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和被動性,因而,生產方式的變化總會帶來新的社會問題。特別是人類工業文明的發展,加劇了一般社會價值與社會現實之間的不一致,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大工業生產中的職業損害、現代生產和運輸工具的不可抗拒風險損害、各種原因所引發的恐暴損害等等,都給遭受不幸者的生存帶來了極大威脅。發達于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傳統私法規則不但難以有效應對,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社會的結構性矛盾。民法通過抽象法律人格將具體的、個殊的人締造成為了虛幻的超人,由此,在契約自由和機會平等之下,現實中的一些人始終無法擺脫生存危機。同樣,在自己責任原則之下,一些損害將難以獲得救濟,而只能歸咎于個人之不幸。在此背景下,以勞動法為代表的一系列旨在解決大工業帶來的社會問題的立法應運而生。與民法不同,這些立法以具體人為規范對象、關注其生存困境改善需求,而非以無差別人為依托、追求整體增長;視集群性、普遍性、不可預知性受害為修復重點,而非將其默示為個人不幸。上世紀后半葉以來,學者們將這些立法統稱為社會法。簡言之,社會法以解決社會問題為根本使命。
(二)在公、私法之外救濟異常反應受害者是各主要國家的普遍做法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英國、美國先后建立了專門的異常反應損害救濟制度。盡管各國在補償經費來源、補償范圍和標準、具體程序設計等方面存在不同,但共同點在于,它們所確立的補償制度與傳統公私法損害賠償制度都有明顯不同。
1.日本
日本于上世紀70年代確立了對疫苗接種損害進行救濟的制度。根據1970年7月31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的《預防接種事故處理措施》,預防接種損害通過行政補償進行救濟。該措施確立了救濟的結果責任原則,即只要認定損害系由預防接種行為所致,就給予財產補償。該措施所確定的救濟機制與傳統的民法救濟和典型的行政救濟均表現出了明顯不同:它不論預防接種性質之法律性質,弱化損害與行為之間因果關系的認證標準,明確了國家的補償義務。及至1976年日本《預防接種法》修改,國會效法《預防接種事故處理措施》,于該法中增設了預防接種損害救濟條款,明確規定政府應對此給予法定的金錢救濟*杜儀方.日本預防接種行政與國家責任制變遷[J].行政法學研究,2014,(3):28-29.。盡管在此后的“東京訴訟”中,法院認定了厚生大臣政策制定中存在過失,并確認了預防接種中國家賠償責任的存在,而且,此后的日本《預防接種法》還全面廢除了強制接種制度,但其所實施的通過動用全社會力量來補償異常反應受害者這一制度的根本面貌仍然沒有發生質的改變,它在性質上仍然有別于傳統民法及典型行政違法損害救濟制度。
2.英國
英國于1979年頒布了《疫苗損害補償法》(Vaccine Damage Payments Act),旨在為因預防接種導致嚴重殘疾者提供公款(public funds)補償。從該法制定背景來看,它源自于1972年英國組建的個人損害賠償與民事責任皇家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 on Civil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for Personal Injury)的報告,而該委員會則是政府在撒利多胺鎮靜劑(Thalidomide)悲劇后做出響應的一個重要部分。該委員會報告雖未打算全面接受普遍意義上適用無過錯責任的方案,但是卻建議對于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推薦接種疫苗引起的損害,應當引入嚴格責任*Stephanie Pywell,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Recent and Impending Changes to the Law of Statutory Compensation for Vaccine Damage”, J.P.I. Law, 2000, 4, pp.249-250.。在該法最初草案的議會辯論中,議員們從兒童預防接種主要服務于社會利益目的的角度指出,社會負擔起預防接種失誤中的責任是正當的。有的議員還將預防接種受害者比作戰爭傷亡者,以此來論證為受害兒童進行賠償的應然性。該法實施后,疫苗損害受害者理論上可通過兩種途徑獲得經濟補償:通過《疫苗損害補償法》提起補償請求和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但學者指出,自Loveday v. Renton案之后,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受害者事實上沒能通過民事訴訟成功獲得賠償。因而,疫苗損害受害者唯一有效的途徑是根據《疫苗損害補償法》提起補償請求*Stephanie Pywell, “The Vaccine Damage Payment Scheme: A Proposal for Radical Reform”, J.S.S.L. 2002, 9(2), p.74.。從內容看,該法所確立的疫苗損害救濟制度也與傳統民事侵權救濟制度存在許多明顯不同。例如,補償金來自公款,而不是像侵權法中一樣由具體加害人支付;設定了法定補償金額,且只與損害事實有關;確立了不同于民事訴訟的特別程序等。
3.美國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之前,美國各界對于疫苗致害時的侵權救濟模式表達了普遍關注。許多疫苗生產商認為,較高的侵權成本將阻礙研究和創新。而消費者群體認為,在侵權救濟模式下,取得疫苗損害賠償之前受害兒童父母需要證明生產商存在過錯的要求具有道德錯誤。經過了幾年討論之后,美國于1986年通過《國家兒童疫苗損害法》(The National Childhood Vaccine Injury Act)對此進行了回應。與日本立法有所不同,該法確立了一個兩層次的損害救濟制度:第一層是強制無過錯補償方案,第二層是侵權責任制度。因該法制定的目標是要設置一個替代傳統侵權救濟制度的更為迅捷和更為確定的救濟方案,所以其所規定的強制無過錯補償方案的適用具有前置性,通過侵權訴訟獲得賠償只是最后選擇。也就是說,如果人們認為受到了該法所覆蓋的疫苗損害,他在向疫苗生產商提出侵權訴訟之前必須先經過無過錯補償程序。在無過錯程序之后,如果損害被認定為與疫苗有關,索賠者在接受補償金與向疫苗生產商提起民事訴訟之間享有選擇權。當然,在民事程序中,生產商承擔侵權責任的條件與其他產品侵權責任沒有本質區別。若受害者不接受補償金,而選擇通過民事訴訟追究生產商的侵權責任,就有義務證明生產商存在過錯、損害與預防接種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美國《國家兒童疫苗損害法》所確立的異常反應致害救濟制度的特殊性在于,其所確立的國家疫苗損害補償計劃是一個優先適用的、無過錯、非侵權損害賠償替代計劃。詳言之,它具有不同于傳統侵權民事訴訟的特殊程序,補償程序便捷;補償金來自于依法所建立的信托基金;證明標準較低,聯邦地方法院決定是否給予補償的唯一焦點是損害是否與疫苗有關等等。這些都表明,涉及疫苗不可避免的風險所造成的損害應當通過無過錯賠償計劃而不是侵權制度加以解決*Victor E. Schwarts, Liberty Mahshigian, “National Childhood Vaccine Injury Act of 1986: An Ad Hoc Remedy or a Window for the Future?” Ohio St. L.J., 1987, 48, p.392.。學者指出,相比較侵權賠償制度而言,國家疫苗補償計劃的優越性表現在:它是對實踐證明無法有效應對疫苗損害救濟的侵權制度的必要替代;它規定社會作為整體來承擔不可避免的疫苗損害成本,向遭受損害的受種者提供了一個公平的補償計劃;它向疫苗生產商營造了一個更為安定的訴訟氛圍,大大降低了重要疫苗供給不足的危險*Mary Beth Neraas, “The National Childhood Vaccine Injury Act of 1986: A Solution to the Vaccine Liability Crisis?” Wash. L. Rev., 1988, 63, p.158.。
四、我國異常反應損害社會法救濟機制的建立
行政法規、政府規章構成了我國當前異常反應損害救濟制度的基本框架。總的來看,現行制度存在規范位階較低、補償項目地方差異加大、程序設計繁瑣、行政與司法程序銜接不暢等問題。然而,除了各方對于損害發生均無過錯外,便捷高效、非對抗的程序規則是社會法救濟有別于傳統公私法救濟的基本面。這自然也是完善我國異常反應損害救濟制度的當然要求。
(一)提高立法位階,統一補償項目,實現救濟的確定性與平等性
雖然《傳染病防治法》明確了預防接種的類型,但其未涉及異常反應及其損害救濟問題,因而,異常反應損害救濟所能依據的制度規范只是《條例》及政府規章的規定。而《條例》、《指導意見》等中央文件等僅規定了對于異常反應損害應給予一次性補償,但并未明確具體補償項目。公開資料顯示,各省份的補償辦法在補償資金、補償標準和補償程序方面存在明顯差別*如《四川省預防接種異常反應補償辦法》明確規定,除一次性經濟補償外,不再另行支付醫療費、誤工費、殘疾生活補助費、殘疾用具費、交通費、喪葬費等其他費用。在《北京市預防接種異常反應補償辦法(試行)》中,補償金額的項目中覆蓋了醫療費、誤工費、護理費、殘疾生活補助費、殘疾生活輔助具費、其他與異常反應調查診斷、鑒定有關的檢查檢驗費用、異常反應鑒定費、損害程度等級評定費;異常反應造成受種者死亡的,還包括死亡補償金、喪葬費、尸檢費用。在《上海市預防接種異常反應補償辦法(試行)》中,補償項目更為廣泛,還包括了交通費、鑒定費等。與此類似的還有廣東省、安徽省的規定。。
基于異常反應致害的特殊性,對其救濟既不屬于傳統私法救濟范疇,也難以歸入公法救濟之下。盡管在比較法上,各國并未將此種損害救濟冠以社會法救濟之名,但從整體制度設計來看,已形成了迥異于傳統公私法救濟形式的特殊救濟機制。異常反應損害是典型的社會問題,應當從理念上將其納入社會法救濟范疇之列,從而為建立符合此種損害救濟實際需要的特別程序奠定基礎。此外,對比傳統公私法救濟的制度設計以及比較法上的經驗可知,異常反應損害救濟基本制度設計應由法律來確定。當然,由于計劃接種疫苗、異常反應、致害補償標準等都有一定的變動性,應由行政法規、規章來細化。
補償項目各地差異較大是現行救濟中存在的另一問題,應當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統一。基于異常反應損害的性質,補償范圍原則上只限于實際發生的、不能通過醫療保險等補償的費用,不應包含精神損害賠償。其中,對于證據收集、聘請律師的合理支出,應當區別對待:若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認定損害系異常反應所致,則應當一并給予合理補償;若損害與異常反應無關,且屬于善意申請并有合理基礎,則應給予適當補償,否則,則不應補償。異常反應損害補償應系一次性補償,在具體數額上,可依據省、自治區、直轄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實際差異。對于前述之外的與受害者健康恢復無關的其他費用,原則上不應補償。
(二)設置補償明細表,實現救濟的便捷性
設置補償明細表,既能夠簡化異常反應鑒定程序,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受理機關的自由裁量權做出合理制約,大大提高異常反應鑒定程序效率;同時,能夠避免當事人提出明顯缺乏事實根據的申請,防止補償程序被濫用,從而造成行政資源浪費。因而,設置補償明細表,是各主要國家的通例。美國《國家兒童疫苗損害法》附設疫苗表,其中包含了應獲補償的異常反應類型及其持續的最低期限。英國《疫苗損害補償法》第1條也列舉了所應補償的疫苗種類及損害程度。當然,在明細表所應包含的疫苗種類、異常反應類型方面,應當保持開放性,允許當事人舉證證明盡管特定損害類型尚未規定在明細表中,但卻系國家計劃接種的疫苗所致。
補償明細表的設立,還能夠必要地簡化舉證責任。從申請者提出申請時應提交的證明材料來看,現行規定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各地規定不完全一致;與異常反應整體處理程序存在明顯的分段,加重了受害者負擔。為便利救濟受害者,應當將本階段融入異常反應處理中。換言之,發生異常反應致害后,受害者只需要向當地衛生主管部門提出補償申請即可,至于現行程序中前置的鑒定程序的完成及其結論,不應當成為申請人提交補償申請的前置條件。事實上,在現行立法上,異常反應鑒定權限具有專屬性,而且,從預防接種管理角度看,發生疑似異常反應的,管理部門也需依職權進行鑒定。因而,程序融合后,不會給管理部門帶來不必要的負擔,但卻可以便利受害者。
(三)明確和簡化受理機關職責,體現救濟程序的非對抗性
《條例》第42條規定了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和接種單位及其醫療衛生人員及時處理異常反應的義務;第44條規定了縣級人民政府衛生主管部門有權受理接種單位和受種方就異常反應發生的爭議。根據《鑒定辦法》,發生異常反應、疑似異常反應的,受理機關是各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組織成立的調查診斷專家組。若各方對調查診斷專家組調查診斷結論有爭議,則可以在規定期限內向接種單位所在地設區的市級醫學會申請進行異常反應鑒定,對其鑒定結論不服的,在規定期限內向省級醫學會申請再鑒定。衛生行政部門、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等有關部門發現鑒定違反該辦法有關規定的,可以要求醫學會重新組織鑒定。顯然,《鑒定辦法》旨在通過多層次鑒定機會設置,做到準確鑒定異常反應,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若從受害者角度看,確定所受損害是否源于異常反應,則最多的情況下需要經過一次調查診斷、兩次鑒定。而從第一類疫苗的接種者角度看,若考慮到衛生行政部門的因素,則何時能夠確定、需要經過多少次鑒定以及重新鑒定,至少從程序本身來說沒有定數。對于異常反應致害的補償,僅僅規定了補償費用的來源,具體受理機關在該條例中并未明確。當然,許多地方政府規章彌補了這一不足,普遍規定人民政府衛生主管部門為補償申請受理機關。盡管如此,但從異常反應損害救濟角度看,仍然較為繁雜。
事實上,從現行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衛生主管部門的架構來看,有必要將此職權統一賦予地方政府衛生主管部門。傳染病預防控制屬于衛生主管部門的法定職責范疇,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是在衛生主管部門領導下協助做好疾病預防、控制的事業單位。如此,賦予衛生主管部門全面處理異常反應問題是適當的。與此同時,異常反應專業性較強,從效率和便利受害者角度看,還應當通過明確受理機關職責來簡化救濟程序。詳言之,發生異常反應后,受害者或有關權利人只需要向有管轄權的衛生主管部門提出一次申請,是否符合應當補償的損害標準、如何補償等問題,都應由衛生主管部門依職權完成。衛生主管部門應當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做出是否補償的決定。當然,申請人有義務提供必要證據或證明材料。
如此規定,不僅與社會法救濟有別于具有對抗性的傳統公私法救濟特色相吻合,而且,也有比較法上的成熟經驗依據。按照美國《國家兒童疫苗損害法》規定,美國衛生和公共服務部部長是所有賠償申請的應答人,其他任何人都不會成為補償程序的當事人。收到申請后,美國聯邦地方法院會指定一個特別專家,協助提取證據、信息和證詞,指導聽訊,準備事實裁定和法律適用的建議方案并向地方法院提交。聯邦地方法院收到建議方案后,決定是否給予賠償。從做出決定的時間上來看,從申請到做出決定的整個程序,都應當是盡可能快捷,無論如何,都不應當超過一年。英國《疫苗損害賠償法》也有相似規定。
(四)順暢銜接行政與司法程序,兼顧救濟效率與公平
《鑒定辦法》將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作為了醫學會不受理異常反應鑒定申請的事由之一。若從文義解釋角度分析,其中所涉及的行政程序與司法程序之間是相互排斥關系,包括專家組調查診斷及任何一級鑒定程序,都不具有相對于司法程序的優先性。據此,發生異常反應時,受害者既可以直接尋求司法救濟,也可以先通過行政程序,而在行政程序進行中的任何階段都可以尋求司法救濟。誠然,這種設置的確為受害者賦予了更多選擇權,但卻沒有顧及到行政程序與司法程序之間的正常銜接關系。無論異常反應所致損害相比較傳統侵權行為而言如何特殊,從公共資源節約、公共權力正常運行角度看,異常反應損害救濟中行政程序與司法程序之間同樣需要有機銜接。在損害補償方面,《條例》只是規定當事人“可以”申請接種單位所在地有管轄權的衛生主管部門處理,并未提及當事人是否同樣可以選擇司法救濟。在各地施行的補償辦法中,該問題不但沒有得到明確,反而因各地規定之間的差異*如《上海市預防接種異常反應補償辦法(試行)》中并未涉及申請人不同意補償內容時的救濟途徑,而《北京辦法》則明確規定,不同意接受補償的,申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已經提起訴訟的,補償程序終止。《河北省預防接種異常反應補償辦法》也規定,申請人拒絕簽署一次性補償協議的,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衛生行政部門不再受理一次性補償申請。《廣東省預防接種異常反應補償辦法(試行)》規定的補償支付程序自動中止事由包括兩種情形:(1)受種者對預防接種異常反應診斷結果有異議提請地級市以上醫學會鑒定的;(2)已提請民事或刑事訴訟且人民法院已經受理者。,使得救濟程序顯得更加模糊。
為兼顧救濟的公平與效率,現行規定中所存的行政程序與司法程序銜接不暢的問題應一并完善。對于縣級衛生主管部門做出的補償決定,申請人享有申請行政救濟和司法救濟的權利。詳言之,申請人不服縣級衛生主管部門決定的,可以依法向有管轄權的機關提請行政復議,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對于行政復議決定不服的,也可以提起行政訴訟。從異常反應損害救濟的性質來看,縣級衛生主管部門的決定具有前置性,應當規定為必經程序。在縣級衛生主管部門做出決定前,申請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的,人民法院不應受理。當然,受害人可以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接種單位、疫苗生產商承擔侵權損害賠償責任。提起民事訴訟的,適用《侵權責任法》關于醫療損害責任的有關規定。為節約公共資源,受害者提起民事訴訟還應具有阻卻所有行政程序進行的作用,即受害者選擇通過民事訴訟途徑請求侵權損害賠償,則正在進行的行政程序應作結案處理,且不得再行提起行政處理申請。
此外,還應明確申請主體。明確申請主體資格是異常反應損害救濟程序的基本組成部分。有的地方政府規章對此進行了明確*參見《上海市預防接種異常反應補償辦法(試行)》第11條,《北京市預防接種異常反應補償辦法(試行)》第9條等。。而在《條例》及有的地方政府規章中,只是籠統地使用了“受種方”的表述。從便利法律適用角度看,未來立法中應當進行統一和明確。同時,現行規定中享有申請權的主體范圍還不夠全面。在比較法上,對于胎兒通過母體實施預防接種發生異常反應導致出生后存在損害的,也應有權申請補償;第三人因接觸或接近受種者而感染異常反應導致損害的,有權像接種者一樣獲得補償*參見英國《疫苗損害補償法》第1條之(3)。。
On Relieving Damages Result from Immune Vaccination Adverse Reactions by Social Law
sJIA Xiao-long
(LawSchool,LanzhouUniversityofTechnology,Lanzhou,Gansu730050,China)
Damages result from immune vaccination adverse reactions is a typical social problem from its emergence, influential objects and solving measures,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compensate these injured victims by a special systems not like traditional damage recovery system. Our current legislation has a lower legislative rates and a large disparity in compensatory items in different areas, the relieving procedure provided is to some extent miscellaneous. So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briefly and efficiently relieving injured victims, we should rebuilt our relieving procedure for compensating injured victims resulted from vaccination adverse reactions based on lessons from comparative law.
immune vaccination; adverse reactions; social problem; social law; relief procedure
2015-09-25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西部項目“社會法基本范疇研究”(項目編號12XFX02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賈小龍,男,蘭州理工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侵權法,知識產權法。
DF522
A
1672-769X(2016)01-002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