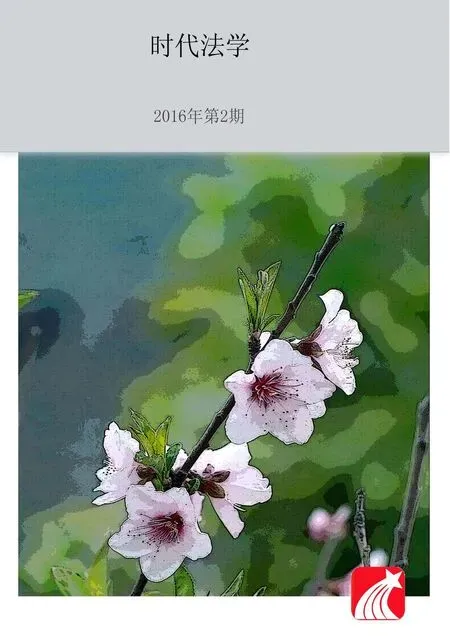直接適用法的正當性考察*
楊 華
(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 湖南 長沙 410081)
直接適用法的正當性考察*
楊 華
(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 湖南 長沙 410081)
直接適用法所體現的單邊主義立場,已經突破了薩維尼的理論預設。直接適用法的興起并非偶然,它是歐陸國際私法發展到一定階段順應時代潮流所做的一種自我反省和調適,也是歐陸傳統國際私法面對生存困境所做的一種自我救贖和完善。國際私法的范式的轉換、價值取向的嬗變、功能主義的勃興,以及公共秩序的式微,共同為直接適用法的產生提供了正當性理據。
直接適用法;范式;價值取向;功能主義;公共秩序
直接適用法對沖突規范的限制作用,較之反致、禁止法律規避、公共秩序保留等傳統工具或手段更加直接和有效率,它完全拋棄了沖突規范,這決定了其在國際私法中的“強勢”地位。而且,直接適用法因其表現出的強烈的法院地法傾向而被認為是單邊主義的復興,這與歐陸傳統國際私法溫文爾雅的中立態度形成鮮明的反差,但正所謂“存在即合理”,直接適用法的產生與興起自有其某種合理性或正當性。目前國內對直接適用法正當性的論證較少,而從國際私法角度來探討的則更是鳳毛麟角,為此本文擬著眼于國際私法的晚近發展趨勢,從范式的轉換、價值取向的嬗變、功能主義的勃興和公共秩序的式微四方面對直接適用法的正當性進行全方位的論證。
一、國際私法范式的轉換
有學者指出,迄今為止,國際私法經歷了由主體性范式到主體間性范式再到社會性范式的進化之旅*張春良.沖突法的范式進化論[J].法律科學,2010,(4):40-51.。這三種范式的立足點或出發點各不相同,主體性范式立足于涉外私法關系中彼此對立的雙方主體及其歸屬的法律體系,試圖通過特定的主體因素分析來優先保障某一特定主體方的法律適用來實現法律沖突之消解,從而容易導致主體雙方的失衡。唐朝《永征律》中“化外人相犯”的規定和巴托魯斯的法則區別說就是這一范式的代表。與主體性范式不同,主體間性范式要求法官站在中立立場,通過平等兼顧主體雙方利益以實現法律沖突的解決,如薩維尼的法律關系本座說。無論是主體性范式還是主體間性范式,都是市民社會的產物,是建立在純粹“市民法”的基礎之上,關注焦點是主體雙方的私益,前提是國家與社會、公法與私法的分立。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傳統的憲政國家觀念漸被民主—法制國家觀念取代,國家與社會、公法與私法的界線逐漸模糊,呈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態勢,不再像以前那樣非此即彼、涇渭分明。情勢的變化和前提的喪失使國際私法的既有范式陷入危機,促使其在對既有范式揚棄的基礎上尋求符合時代情勢的新范式,社會性范式由此應運而生。與前兩種范式都將關注焦點放在涉外私法關系的主體雙方不同,社會性范式的視域更為寬廣,它在關注沖突雙方的同時,更加強調透過沖突所依托的整體背景來尋求沖突的積極消解,使涉外私法案件的處理能回應沖突雙方、社會背景乃至整個國際民商秩序的要求。克格爾的利益法學即是這一范式的典型。
社會性范式拓展了國際私法的深度,使之不再只是純粹關注涉外私法法律關系當事人之間的私益糾葛,而真正成為擔綱構建國際民商新秩序的“基本法”。過去那種將法律沖突的解決奉為國際私法最高的和唯一正當責任的觀點越來越不符合時代的要求,國際私法的社會責任重新被拾起。它要求法院審理涉外私法案件時,不僅應著眼于法律沖突的解決,還應滲透到法律及沖突背后的整個生活世界以尋求沖突的積極消解;它要求法院在構建沖突消解方案時應綜合考慮涉外案件所涉的各種因素,選擇案件公正合理解決的最佳法律,以便在國際社會責任、國內社會責任、政府利益責任和當事人利益責任之間尋找一個合理的平衡點,使這四者之間的矛盾得到完美統一。國際私法的社會化也使其淡化了對當事人利益的關懷,并引起個人法律地位的弱化,散發出濃郁的“重公輕私”(即公共益優于私人私益)氣息。以上這些,不僅為法院于涉外私法關系直接適用實體法的實踐提供了正當理由,也為直接適用法理論的產生提供了哲理依據。
二、國際私法價值取向的嬗變
國際私法對正義價值的追求經歷了從形式正義(沖突正義)到實質正義的轉變。傳統國際私法立足于主權國家林立、多元法律體系并存的國際社會,以承認、尊重和平等對待諸國法律體系為要旨,在維護既有法律沖突有效的前提下調整涉外私法法律關系、解決法律沖突問題(而非徹底消除法律沖突),實現多元法律體系的和諧共存。它要求法官在各法律體系之間保持中立立場,排除一切價值取向,根據既有的沖突規范結合案情平等地選擇法律。這種平等對待各國法律體系的態度正是沖突正義的主題。巴托魯斯的法則區別說首先抓住了法律的域內域外效力這個法律沖突的根本點,并首次擺脫之前的法律適用屬地法傳統,開始自覺地站在普遍主義立場上對待諸城邦的特別法,據此探討法律沖突的解決問題。可以說,法則區別說一開始就毫不掩飾地表達出對沖突正義的關注,這種情懷一直延續到薩維尼并在后者手中達到極致。薩氏以諸國法律體系構成的“國際法律共同體”為出發點,從法律關系的性質入手,通過尋求其應隸屬的地域的法律,即所謂的“本座”來解決各種不同法律關系應適用的法律。薩維尼精心打造的法律關系本座說,強調平等對待內外國人和內外國法,以恢弘嚴謹的體系將對沖突正義的強調提高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度,一舉奠定了現代國際社會法律適用的基調。作為傳統國際私法經典理論的法則區別說和法律關系本座說雖然在解決法律沖突的方法上截然不同,前者是從法律或法則自身的性質來探討法律沖突的解決方法,而后者則是從法律關系本身的屬性來確定應適用的法律,但二者均不約而同地將沖突正義作為追求目標,“傳統的、古典的國際私法基于一個最基本的假設,即國際私法的職能在于保證適用于每一起多國法律爭議的法律與該爭議存在‘最適當’的聯系。長期以來,關于界定、衡量這種‘適當性’的觀點因法律體系和主題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然而,盡管存在上述差異,所有的古典學派的觀點仍然迷戀于選擇準據法所屬國,而不是直接尋找適當的法律,更不是要尋找適當的案件結果。”*Symeon C. Symeonide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Progress of Regres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0, pp.43-44.簡言之,傳統國際私法將“適當國家的法律=適當的法”奉為圭臬,法律選擇只是對立法管轄權或法律淵源的正確選擇,而不是依據準據法內容的正當性來確定。
傳統國際私法以其公式化的法律規則和嚴謹的形式推理確保了從適當國家中獲得準據法和法律適用的一致,但并不承諾追求(更不談上實現)實質正義。這種獨崇沖突正義的做法在主權國家并立、多元法律體系并存和國際統一實體法有限的現實背景下,較之其他法律選擇方法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其正當性顯而易見,因為它保證了對諸國法律體系的平等對待,而這一點更加有利于在無損于主權的前提下發展平等互利的涉外私法關系,符合當代國際社會實際。可以預言,只要這種狀況不從根本上改變,沖突法這種傳統的法律選擇方法在國際私法中將一直占據“主角”地位,而其他方法只能對沖突法起補充或者矯正的作用,充當“配角”。正因如此,美國沖突法革命中的一些激進者全面否定沖突法、主張徹底拋棄整個沖突法制度的極端做法最后只是曇花一現,后革命時代的美國沖突法又掀起“重返沖突規則”的思潮*Ralf Michael, After the Revolution—Decline and Return of U.S. Conflicts of Laws, Yearbook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vol. 11(2009), p.30.。美國新理論對歐陸國際私法的影響更為有限,其對以薩氏學說為基礎的沖突法規則體系并無太大的沖擊力,歐陸國際私法“原有的基本理念仍然難以撼動”*Gerhard Kegel, The Crisis of Conflict of Laws, Recueil des Cours 112(1964-II), p.91.。
沖突正義的正當性難掩傳統法律選擇方法的先天性缺陷,對實質正義的漠視即是其中之一。在涉外私法案件的處理中,沖突正義要求平等對待不同的法律體系,而實質正義要求對涉外案件作出公平正義的裁決。在沖突正義與實質正義之間,案件在實質上的公正處理應當是國際私法的終極目標,沖突正義不過是達至實質正義的必要手段,而傳統解決方式將沖突正義作為唯一關切而完全忽視實質正義的舍本求末做法,致使國際私法陷入一種抱殘守缺的狀態,嚴重束縛了國際私法的發展。美國革命所體現出的對實質正義的關注促使歐陸國際私法開始從沖突正義轉向實質正義,“歐洲沖突法不再生活在‘沖突正義’的‘真空’當中”*Friedrich K. Juenger, American and European Conflicts Law,Bologna Symposium, Am.J. Comp.L.30 (1982),p.117.。這種轉變的主要標志之一就是將承載著正義價值的實體法規則優先于沖突規范而得到適用(這些優先適用的實體法規則就是直接適用法),通過對沖突規范的限制來實現實質正義。
三、國際私法功能主義的勃興
按照美國法律現實主義者的傳統觀點,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與“形式主義”(formalism),歐陸諸國稱“概念主義”(conceptualism),是相互對立的兩種法理學觀點。法律形式主義是美國19世紀后期和20世紀早期的主流法律思維模式,其要旨是:法官是發現而非創制法律,判決源于不可變的正義原則*G.Aichele, Legal Realism and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Jurisprudence: The Changing Consensus,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0, p.4.,法官就像一臺自動售貨機,只要依據先例和正義原則就可作出任何案件的判決;作為科學的法律,是由一些原則或原理構成的;在龐雜的判例法中,必要的和有用的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根據這些判例就可以歸納出類似于幾何學原理的少數法律基本原理,而精通法律原理的法科生憑借法學教授們總結出的規則便可馳騁天下*C. Langdell, A Selection of Cases on the Law of Contract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1871,pp.vi-vii,“Preface”.。在此觀點下,立法者的規則體系成為所有法學研究的中心,裁判者不過是戴著腳鐐的舞者。一些激進的形式主義者甚至提出,判斷司法判決合法性的唯一尺度,在于裁判者嚴格地遵循既有規則的程度*[美]丹尼爾· A. 法伯.法律形式主義舉隅[J].劉秀華譯.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學院,2001,(1):49.。
在國際私法領域,自巴托魯斯以來,形式主義長期以來都占據著主導地位。國際私法曾經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一個很強大的公式化法律體系*[澳]邁克爾·J.溫考普,瑪麗·凱斯.沖突法中的政策與實用主義[M].閻愚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2.。
美國曾經是英國殖民地,沒有本土的沖突法理論淵源。美國沖突法理論的真正建構始于斯托雷和比爾,而他們的理論都是在吸收歐陸學者的理論基礎上完成的。斯托雷的理論是在歐陸“國際禮讓說”的基礎上創立的,而比爾則是借鑒了戴西的觀點,創建了既得權理論。因此,早期美國的沖突法與歐洲十分近似。1934年,以比爾為主報告人,美國法學會出版了《沖突法第一次重述》。該示范法為了使外國的權利根據國際禮讓原則在美國法院得到承認,以既得權理論為指導思想,設計了一套形式主義國際私法觀的沖突法規則體系,通過抽象的連結因素將權利固定于特定的地域,形成了一種依靠概念化的系屬公式和固定的沖突規范解決法律選擇問題的方法。對此我們不難發現,第一次重述的法理學基礎為法律形式主義,其指導原則是形而上的,其具體內容是規則定向的*Jeffrey M. Shaman, The Vicissitudes of Choice of Law: The Restatement(First, Second) and Interest Analysis, buffalo L. Rev. 45(1997), pp.329-330.。這一點,與以薩維尼方法為基礎的歐陸傳統國際私法十分相似,無怪乎有學者說,美國傳統沖突法是“美國法中少有的具有大陸法系傳統的法律部門之一”*Symeon C. Symeonides, Wendy Collins Perdne, Arthur T. Von Mehren, Conflict of Laws: America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1998, p.12.。
第一次重述滿足了司法界對規則明確性和穩定性的需求,加之美國法學會的權威影響,這套規則體系得到法院的普遍接受,“幾乎具有法令的尊嚴和效力”*Symeon C. Symeonide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Progress of Regres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0, p.22.。比爾為闡述這套規則而撰寫的《沖突法專論》也獲得巨大成功,被譽為“權威和劃時代的作品”*A. Harding, Joseph Henry Beale: Pioneer, Missouri,L. Rev, 2(1937), p.131.。但是,比爾的規則和理論存在內在的矛盾和缺陷,這在合同和侵權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比爾規則和理論的內在矛盾和缺陷主要有以下幾點:一、少部分規則并非是從判例法中歸納出來的,而是比爾根據其既得權理論推出來的,這些規則與司法實踐脫節,如合同締結地法規則;二、一些規則是比爾放棄理論而順從實踐的結果,這些規則與既得權理論之間存在矛盾,如反致制度;三、既得權理論內部存在難以克服的矛盾,例如比爾一方面認為法院地并不把外國法看作法律,這種觀點符合美國法律界對外國法的一貫態度,另一方面卻把外國法看做法律一樣用來判斷既得權的存在與性質;四、比爾規則強調法律形式主義的穩定性和確定性,但作為既得權理論根據的比爾法律思想是法律現實主義的法律動態性觀點,這種騎墻立場是《沖突法第一次重述》中的規則標準不一的重要根源。許慶坤.美國沖突法理論嬗變的法理——從法律形式主義到法律現實主義[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54-59,71-78.,這兩個領域理所當然成為后來沖突法革命批判舊理論的主陣地。而且,第一次重述可謂生不逢時,因為那時形式主義已經風光不再,法律現實主義開始在美國法學界占據主導地位。
20世紀20年代,庫克、英特馬(Yntema)和勞倫岑(Lorenzen)等法律現實主義者開始將矛頭指向沖突法領域,并最終摒棄了比爾的法律選擇體系,為沖突法革命搭建了舞臺。進入20世紀60年代后,以柯里、卡弗斯、艾倫茨威格、萊弗拉爾等人為代表的美國沖突法學者秉承了法律現實主義的觀點,對傳統沖突法通過“機械”、“僵硬”的規則“盲目”選擇法律而忽視實體法所體現的公共利益和社會政策以及個案的公正解決的做法進行了猛烈抨擊,主張徹底推翻以第一次重述為代表的美國傳統沖突法規則體系,代之以靈活的法律選擇“方法”,從而掀起了一場對舊理論的革命。他們將法律現實主義的功能主義觀點引入沖突法領域,運用功能分析方法(functional approach)分析法律沖突,并根據自己的理解提出不同的法律選擇方法,形成各種現代沖突法學說*法律現實主義者使用“功能主義”一詞,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現實世界中法律的功能,是指通過靈活的標準以平衡各種不同因素和利益,從而實現個案的公正解決。其觀點可以簡要歸結為規則懷疑主義(rule-skepticism)、實用主義(pragmatism)和結果主義(consequentialism)。功能主義是法律現實主義核心理念,因此有學者認為法律現實主義不過是“功能主義的一種形式”,是“功能分析方法的一個結果”。See Joseph William Singer, Legal Realism Now, Calif.L.Rev.76(1988),p.468; Martin P. Golding, Realism and Functionalism in the Legal Thought of Felix S. Cohen, Cornell L. Rev.66(1981),p.1055;Glenn S. Koppel, The Functional and Dysfunctional Role of Formalism in Federalism: Shady Grove Versus Nicastro, 16 Lewis & Clark L.Rev.905(2012), pp.928-929.。
國際私法上的功能主義,就是運用功能分析方法解決法律選擇的問題。古德認為,功能分析方法是指法官對可能適用于涉外私法案件的實體規則所進行的一種政策定向(police-oriented)分析,該分析是通過對具體規則的內容與目的的分析解釋以確定其空間適用范圍*Thomas G. Guedj, The Theory of the Lois de Police, A Functional Trend in Continental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A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Modern American Theories, 39 Am.J.Comp.L.661(1991),p.664.。溫特勞布(Weintraub)認為對法律沖突的功能分析是一個過程,該過程可以分為兩步,首先是將關注點放在與當事人和交易相關的明顯存在沖突的兩個或多個法域的內國實體規則上,下一步是探求各個實體規則所隱含的政策,以確定哪國的政策明顯應當通過適用其本國法而得以實現*Russell J. Weintraub, The Impact of a Functional Analysis upon the “Pervasive Problems” of the Conflict of Laws, UCLA L.Rev.15(1968),p.817.。這兩種定義雖然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基本含義是一致的,即國際私法語境下的功能分析方法是對涉外私法案件所涉各法域的實體規則的內容與目的的闡釋,探求發掘潛藏于規則之下的政策與利益,以確定應當適用的法律。因此,功能分析方法也可以說是一種政策定向的方法。這種法律選擇方法與歐陸以薩維尼理論為基礎的傳統空間定向(spatially-oriented)或地域定向(territorially-orientation)的方法存在較大的區別。首先是出發點不同,前者是從實體規則本身入手,通過對可能適用于個案的實體規則的內容與目的之解釋,發掘隱藏在規則背后的政策與利益來確定該規則的空間效力范圍;而后者是從法律關系本身的性質入手,將每一種法律關系分配到其“本座”所屬的法律體系,通過特定的空間連結因素將法律關系或事實與特定的地域聯系起來,以確定它們應適用的法律。其次是目的不同,前者或者以實現各州公共利益為目標(如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說”),或者以個案的公正解決為目標(如卡弗斯的“優先選擇原則說”),或者在二者之間采取折中主義(如萊弗拉爾的“法律選擇五點考慮”),雖然各自取向有所不同,但均不以判決一致作為其既定目標;而后者追求的是法律適用的確定性、可預見性以及判決結果的一致,從而保證相同案件相同處理,阻止當事人挑選法院。
美國學者創制的各種替代傳統規則的法律選擇方法,引起歐洲學者的高度關注與熱烈討論。他們普遍擔心這些完全排斥確定性的方法會鼓勵挑選法院并降低可預見性,因而認為這些革命性理論已誤入歧途*Vitta, The Impact in Europe of the American “Conflicts Revolution“, Am.J.Comp.L.30(1982),pp.3-6.。出于以上擔憂,歐陸國際私法并沒有發生像美國一樣的對傳統理論的顛覆性“革命”,在“規則”與“方法”之間,歐陸國家無一例外地選擇了“規則”。然而,他們也清醒地認識到傳統國際私法所面臨的困境。薩維尼所倡導的方法依靠其嚴謹的形式邏輯和機械的法律適用規則以希冀實現法律適用的大一統。然而,這些看上去堪稱完美的法律適用技巧,如同作繭自縛一般,使歐陸傳統國際私法日益脫離實踐。實現判決一致的目標也因為識別、先決問題、反致、公共秩序、禁止法律規避、外國法查明等制度或策略的運用而很難實現。傳統方法使用一種特殊的表示地理位置的詞語來指示涉外案件應當適用的內外國法,而置實體法的內容以及所體現的政策和利益于不顧,就如同一種“盲目的實驗”*D. Cavers, A Critique of the Choice-of-Law Problem, Harvard Law Review, 47(1933), p.173.,是無法求得個案的公正解決。因此,他們并沒有將美國的新理論完全拒之于門外,而是對其進行了揚棄,吸取了其中的合理因素特別是功能分析的方法,對原有的沖突規范進行了修正與改良。
直接適用法正是歐陸國際私法從形式主義向功能主義方向發展的結果,是功能分析方法與傳統法域選擇規則相互融合的產物。首先從適用基礎上看,法院審理涉外案件時,在決定是否直接適用實體規則之前,應當對該實體規則的內容與目的進行考察,從中探尋立法者對適用其法律的意愿及其所體現的國家政策或公共利益,并據此決定是否必須強制適用于特定涉外民商事關系。這種以法律背后所體現的政策或利益作為基礎與核心的準據法選擇方法,其本質就是對實體規則所作的一種“政策定向”分析。其次從適用對象上看,直接適用法只能適用于特定的涉外民商事關系,這些法律關系通常關乎一國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等重大利益,立法者制定的調整這些重要法律關系的法律必須得到強制適用方能維護和實現其政策或利益,而無論法院地沖突規范是如何規定的。直接適用法的采用是建立在個案基礎之上的,它只能通過“逐案”(case by case)的方式進行,這符合功能主義的內涵和本意。因為功能分析方法并不像傳統法律選擇方法那樣可以建立一套具有普適效力和可供反復適用的沖突法規則體系,只能依賴法官于個案中個別審酌。再從適用效力上看,直接適用法調整涉外私法關系時,不必經過沖突規范的指引,從而排除了法院地沖突規范的運用,這與美國學者要求以“方法”代替“規則”的主張是一致的。只不過后者走得更遠,它完全推翻了原有的體系。相比之下,歐陸學者要溫和得多,他們只是將直接適用法作為一種輔助或補充手段,部分取代沖突規范,沖突規范在歐陸國際私法中依舊占據著主導地位。最后從適用后果上看,直接適用法促成了單邊主義在歐陸國際私法的復興。由于直接適用法具有“公法”性質,傳統國際私法基于國家主權原則,認為公法具有嚴格的域內效力,因而排除外國公法的適用,這就是“公法禁止原則”。根據該原則,早期的直接適用法都是以法院地法為中心,對于外國(包括準據法國和第三國)的直接適用法一般不予適用。以弗朗西斯卡基斯的學說為例,他在提出“直接適用法”概念時,只是討論了法國法院不經過沖突規范指引直接適用法國實體法的現象,后來他發現這些直接適用的法國法常為《法國民法典》第三條第一款所規定的“有關警察與公共治安的法律”,遂將“直接適用法”改稱為“警察法”(lois d’police),以統稱他所闡述的“法官所直接適用的實體法規則”概念。因此,直接適用法與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方法一樣,都有鮮明的“返家趨勢”(homeward trend),極易無節制擴大法院地法的適用,二者共同促成了單邊主義在歐美的復興。這種狀況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公法禁止原則”的解禁而有所改觀,晚近歐陸國際私法開始逐漸接受外國直接適用法的適用,這標志著直接適用法已由單純的“單邊主義”方法向“多邊主義”邁出了一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法院地法至上”逐漸向“平等對待內外國法”的轉變,符合經濟全球化時代國際民商事交往發展的新要求。但是,在對待第三國的直接適用法上,各國均持審慎態度,表現在對適用第三國的直接適用法設定了嚴格的條件限制,例如要求第三國直接適用法與案件有密切聯系。并且要求法院在確定是否適用時,應當考慮該法的性質、目的及其適用與不適用的法律后果。因此,承認外國直接適用法的可適用性難以從根本上改變直接適用法的單邊性。另外,在決定是否適用第三國直接適用法時所采用的“最密切聯系”的標準和利益衡量的方法,也折射出功能分析方法對歐陸國際私法的深刻影響。
四、國際私法公共秩序的式微
從本質上講,公共秩序是從兩方面來實現其排除外國法適用的功能的:一方面,它起著一種對外國法的防范或否定的作用,即安全閥的作用。因為在原則上,依據法院地的沖突規范,有關涉外民商事關系本應適用外國法作為準據法,但現在由于其適用會與法院地的公共秩序相抵觸而不予適用。此即公共秩序的消極功能;另一方面,它還起著一種對內國法的積極或肯定的作用,即對于某些涉外私法案件,法院在援用公共秩序時,并不首先表明依據沖突規范本應適用外國法,而是直接認定由于該案件與法院地有著某種重要的聯系,因而它的某些體現公共秩序的法律是必須直接適用的。此時,法院便可對自己的沖突規范完全棄置不顧。此即公共秩序的積極功能。這種“二分法”思想源于薩維尼。薩氏根據其提出的“法律關系本座說”,主張在一般情形下,法律關系的“本座”在什么地方就應當適用什么地方的法律,而不管它是內國法還是外國法,這是法律適用的原則。但他同時承認,這個原則是有例外的。他將這種適用外國法的例外情形歸納為兩類,第一種例外是強行性的實在法,在薩維尼看來,這類強行法又可分為兩個部分,即一部分強行法只是為了保護所有者利益,這類規則并不包括在例外情況之內,因為因此產生的沖突可以用法律中存在的最大量的共同原則來很好地解決。而另一部分強行法不僅僅是為了保護所有者的利益,它還具有自己的道德或公共利益基礎,這類規則具有絕對排除外國法適用的效力。第二種例外是凡屬內國法不了解的外國法律制度,不能得到德國法院的保護*[德]薩維尼.法律沖突與法律規則的地域和時間范圍[M].李雙元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7-20.。薩維尼把這兩種例外相提并論,為公共秩序的產生及其與直接適用法的混同埋下了伏筆。
公共秩序的消極功能(又稱“消極的公共秩序”)就來源于上述第二種例外,這也是古典公共秩序的基本含義。關于這一點,從早期有關公共秩序的論述和立法即可得出。例如,巴托魯斯所論及的“令人厭惡的法則”被認為是公共秩序觀念的萌芽。他將法則分為人法和物法,并認為物法只有域內效力,而人法還具有域外效力,但人法中那些“令人厭惡的法則”不具有域外效力,因而可以排除其在域內的適用。胡伯依據“禮讓”的觀點指出,外國法律如果會“損害法院國政府或其臣民的權利或權力”,禮讓就不要求法院地對之予以承認*E. Lorenzen, Selected Article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1947, p.164.。斯托雷重申了這一思想,他認為,那些試圖壓迫鄰國的優越權和特權是不幸的或無力的,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很難說這些國家必須執行那些與他們自己的道德、正義、利益或政策相違背的法律、制度或者習慣*J.Story, Commentarie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1st.ed.,1834, p.26.。從這些早期的論述可以看出,公共秩序的原始的、基本的概念只是消極意義上的。之后的里斯教授更是形象地指出,公共政策在沖突法上可當作“盾”來適當使用,但絕不能當作“劍”來用*In De conflictu legum (Mélanges Offerhaus)1962,p.395. cited by Hilding Eek, Peremptory Norms and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Recueil des Cours,139(1973), p.20.。多林格也認為,傳統上的公共秩序只是一項防御性的、消極的原則*J.Dolinger, Resolving Conflicts in Contracts and Torts, Recueil des Cours 283(2000), p.317.。
從立法實踐看,那些較早以立法形式規定公共秩序的,如1856年《希臘民法典》、1865年《意大利民法典》和1896年《德國民法施行法》,都只規定了消極的公共秩序*1856年《希臘民法典》第8條:希臘法院禁止適用那些違背公共秩序或者不被希臘法律認識的外國法律制度。該條規定顯然是受到薩維尼觀點的影響。1865年的《意大利民法典》第12條:無論前面作何規定,凡外國的法律、行為或判決,以及個人的處分與契約,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與王國關于私人所有制或行為的法律相背離,均不得與任何被認為是公共秩序或良好道德的法律相背離。該條規定在1942年修訂時變得更為簡潔:違反公共秩序的外國法不應予以適用。(第16條第1項)1896年《德國民法施行法》第30條:外國法之適用,如違背善良風俗或德國法之目的時,則不予適用。。唯一例外是1804年《法國民法典》只規定了積極的公共秩序*1804年《法國民法典》是最早直接規定“公共秩序”條款的法典,但只在第3條第1款規定了“積極的公共秩序”:有關警察與公共治安的法律對于居住在法國境內的居民均有強行力。第6條規定:個人不得以特別約定,違反有關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法律。這項規定原本只適用于國內契約關系,后來在審判實踐中擴大適用于外國法的排除的,即發展成為“消極的公共秩序”。,究其原因,應當是法國民法典是世界第一部資產階級性質的民法典,里面包含許多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定,如法國人都享有平等的民事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動產與不動產的所有人對物享有絕對無限制的使用、收益與處分的權利,以及契約自由等等,這些規定必須借助積極的公共秩序這種強有力的手段才能得到有效執行。在當時的條件下,《法國民法典》作此規定,是完全出于保護已奪得政權的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和經濟利益之目的的。
孟西尼對公共秩序的重視程度要遠遠超過薩維尼,他并沒有將公共秩序僅僅視為“安全閥”,而是加以拓展,把薩維尼提到的第一種例外也納入其中,使原本僅有“事后排除”消極功能的古典公共秩序成為集“事后排除”與“事前防御”于一身的現代公共秩序。此外,他還把公共秩序提到了國際私法三大基本原則之一的高度*后人將孟西尼國際私法學說概括為三大原則:國籍原則——本國法原則,主權原則——公共秩序原則,自由原則——契約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這與薩維尼只把公共秩序看作國際私法基本原則的例外完全不同。
誠如一位前蘇聯學者所言:“有關公共秩序的保留中既有進步的成分,也有反動的成分。”*[蘇]科列茨基.英美國際私法的理論和實踐綱要[M].莫斯科,1948:102.轉引自[蘇]隆茨,馬雷舍娃,沙迪科夫.國際私法[M].袁振民,劉若文譯.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87.62.公共秩序本身具有的不確定的特性和潛在的易被濫用性,使其成為“一匹桀驁不馴的馬,一旦騎上它就無法預知它會把你帶往何處”*Richardson v. Mellish, 130 Eng. Rep.294,303 (Ex.1824).,孟西尼的觀點更是不適當地助長了這種趨勢。當今大部分學者仍傾向于消極意義上的公共秩序,并將其視為一種例外。而且,現在大多數國家對消極公共秩序的運用也持謹慎態度,適用的條件越來越嚴格,適用的機率越來越少,公共秩序的式微已是大勢所趨。各國的做法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一般方法,即以各種方式對公共秩序加以界定,例如通過積極規定有關事項的方式對公共秩序的內涵進行限制,強調只有在外國法的適用明顯與法院地公共秩序相抵觸時,才可以排除外國法的效力,像德國、土耳其、委內瑞拉等國采取的就是這種方法*德國舊民法施行法第30條:外國法之適用,如違背善良風俗或德國法之目的時,則不予適用。新民法施行法第6條修改為:外國法之適用,如將導致與德國法的根本原則明顯不相容的結果,則不予適用。尤其當該法律的適用違背基本權利時,不予適用。土耳其國際私法第5條規定:如果適用于特定案件的外國法的規定,明顯違背土耳其的公共秩序,則不予適用;此時,如有必要,適用土耳其法律。委內瑞拉國際私法第8條規定:依照本法本應適用的外國法規定,僅在其適用將產生與委內瑞拉的公共秩序的基本原則明顯相抵觸的結果時方予以排除適用。。一些國家則是通過判例對公共秩序予以限制性解釋。卡多佐很早就指出,紐約法院只有適用某外國法將會與正義的重大原則、道德基本觀念或事關大眾福祉的傳統相抵觸時,才可以拒絕執行之*Louchs v. Standard Oil Co., 224 N. Y. 99, 111, 120, N. E. 198, 202(1918).;波蘭法院多次強調,只有在適用外國法的結果使波蘭法律無法忍受時方可適用公共秩序,而在評價其適用結果時必須根據波蘭法律的根本原則,公共秩序只是排除那些與波蘭公共秩序不符的外國法規則,對于該外國法的其他規則應盡可能地繼續適用*Tomasz Pajor, Polish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Progress or Regress?, cited by Symeon C.Symeonide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Progress or Regress? Kluer Law International,(2000),pp.344-345.。另一類是特殊方法,即將公共秩序的積極功能予以剝離,形成排除外國法適用的一種新方法。具體地講,就是將那些帶有公法性質的私法法律關系直接視為具有公法性質的法律關系,不考慮法律選擇問題,直接適用法院地法或該問題所屬的外國法。這種通過直接排除沖突規范的運用達到間接排除外國法適用的方法,就是直接適用法。這種方法至少有三方面益處:一是可以還公共秩序的本來面目,即起著一種對外國法的防范的、否定的安全閥作用,也即消極意義上的公共秩序,這樣可以有效地減少濫用公共秩序的機會;二是可以為法院地國適用直接適用法正名,無須再借公共秩序之名而無限制地排除外國法的適用,這是因為直接適用法的適用需要法官探尋每條直接適用法背后隱藏著的立法政策(通常由立法者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作出),而不像公共秩序的適用那樣完全依賴法官的自由裁量,此外,隨著越來越多國際、國內立法對適用外國直接適用法持開放態度,這也可以有效減少內國直接適用法的濫用,從而增加外國法的適用機會;三是在越來越多國家主張對公共秩序的運用加以嚴格限制的背景下*現在大多數國家主張對公共秩序制度的運用應加以嚴格的限制,外國法律只胡在其適用明顯與法院國公共秩序相抵觸的情況下,法院國才可以排除該外國法的效力。參見李雙元,鄭遠民,呂國民.關于建立國際民商新秩序的法律思考——國際私法基本功能的深層考察[J].法學研究,1997,(2):122.,直接適用法為法院地國提供了一個為新的利益保護手段,故直接適用法一經提出,即受各國之追捧,亦在情理之中。
On the Legitimacy of Lois D’application Immédiate
YANG Hua
(LawSchoolof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81,China)
The unilateralism position of lois d’application immédiate has broken through the presuppositions of Saigny’s theory. The rise of lois d’application immédiate is not an accident, it’s the self-reflection and self-adjustment of continental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order to follow the trend of the times at a certain stage, and so it is a self-redemption and self-improvement of the traditional continental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face of survival predicament. The shift of paradigm, the evolution of value orientation, the flourish of functionalism, and the decline of ordre public together provide arguments of legitimacy for lois d’application immédiate.
paradigm; value orientation; functionalism; ordre public
2015-12-25
楊華,男,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國際私法學.
D997
A
1672-769X(2016)02-01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