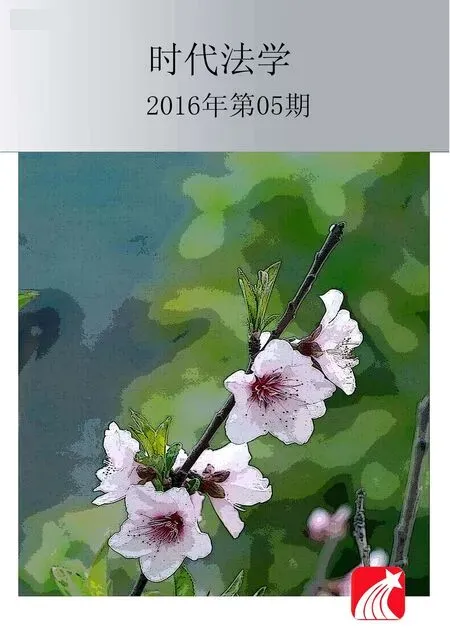迷局與反思: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主體定位*
喻術紅,李秀鳳
(武漢大學法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迷局與反思: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主體定位*
喻術紅,李秀鳳
(武漢大學法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我國《社會保險法》沒有規定誰是社會保險人。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因組織設置、權能配置方面的不足不能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它可以是社會保險行政訴訟的一方當事人,但不能成為獨立法人,致使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與社會保險人主體身份分離。長期以來,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實際履行著社會保險人的職責,立法需要明確定性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著重從主體、組織和財務三方面將其塑造為獨立于社會保險行政部門、獨立于同級地方政府的獨立法人。
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社會保險法律關系;社會保險人;事業單位法人;財務自主
我國《社會保險法》第1條明確規定該法的調整對象是社會保險關系。社會保險關系是社會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在社會保險服務過程中產生的一方提供社會保險供款,另一方提供金錢與服務給付的社會關系。社會保險人和被保險人是社會保險關系最為重要的兩方主體,是社會保險法律關系的核心。《社會保險法》第7條和第8條分別規定了社會保險的行政管理主體和提供社會保險服務的主體,前者是各級政府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即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后者是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但誰是社會保險人并未明確,整部法律中也沒有(社會)保險人這一法律術語。《社會保險法》仍然沿襲勞動法和社會保障管理的思維,主體仍然定位于勞動者(職工)與用人單位,而不是保險人、參保人、及被保險人,對于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同樣缺乏細致的規范和動態地考察。就社會保險法律關系而言,社會保險人是最為關鍵的主體,誰是社會保險人?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能否作為獨立的社會保險人?如何把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塑造成真正的社會保險人?厘清這些問題是社會保險法制化建設的基礎和前提。文章依據社會保險的制度機理,在解析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現實處境、社會保險人主體的真實身份、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與社會保險人身份分離原因的基礎上,根據我國的制度環境和現實需求,著重從主體獨立、組織獨立和財務獨立三個方面將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塑造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保險人。
一、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身份之謎
“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官方正式表述最早見于1993年國務院批轉國家體改委《關于一九九三年經濟體制改革要點的通知》第十部分“加快勞動、工資制度和社會保險制度改革步伐”,首次指出“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具體承辦社會保險業務并承擔資金保值、增值責任”。其后,“社會保險經辦機構”雖經廣泛使用,但并沒有明確的含義界定。1994年頒布的《勞動法》第74條僅對社會保險基金經辦機構進行界定,規定社會保險基金經辦機構是依照法律規定收支、管理、運營社會保險基金并對基金負有保值增值責任的主體,而對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沒有定義。2001年,《社會保險行政爭議處理辦法》從實務角度對經辦機構的含義進行了界定*《社會保險行政爭議處理辦法》第2條。,并把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作為社會保險行政爭議的一方當事人,從而確立了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獨立的行政訴訟主體資格。2010年的《社會保險法》把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定位為提供社會保險服務的主體,并專列于第九章對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設置、經費保障、管理制度和職責等方面進行了細致的規定。然而,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是否就是社會保險人這一點現行立法并未明確,現行體制中的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能否擔當社會保險人這一點還需詳盡剖析。
(一)從組織體制看,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無法獨立地擔當社會保險人
我國的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分為中央和地方兩個層級。中央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險事業管理中心,由原勞動部社會保險事業管理局、衛生部全國公費醫療管理中心、民政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管理中心、人事部中央國家機關及其在京事業單位社會保險管理中心4個單位合并而來,屬部屬財政全額撥款事業單位,人員參照公務員管理,擔負綜合管理、指導和監督之責,不經辦社會保險具體業務*曹洋.我國社會保險業務經辦的現狀、問題與對策[J].中國勞動,2015,(4):62-68.。地方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由各統籌級別政府對應設置,包括省、市(地)、縣三級,省、市兩級擔負指導和經辦雙重職責,縣級機構主要負責經辦工作,在一些鄉鎮和城市社區還設有社會保障事務所,作為業務的平臺,從事社會保險經辦工作*孟昭喜.社會保險經辦管理[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5.18.。各地的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不論名稱如何差異(“中心”、“局”或者“處”),基本上屬于同級政府主管部門直屬的、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機構人員參照公務員管理*張榮芳,黎大有.論我國社會保險人的法律地位[C].珞珈法學論壇,2014,(13).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68-79.。
我國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設立直接起始于行政管理體制變革中的“政事分開、官辦分離”改革。為轉變政府職能、提高管理和服務效率,改革對政府承擔的行政管理職能與事業單位承擔的公共服務職能進行明確地劃分和歸位,將政府職能部門承擔的技術性、服務性的社會職能劃歸事業單位,改變“以政代事”的局面,將事業單位承擔的行政管理職能回歸政府職能部門,祛除“以事亂政”的現象。具體到社會保險管理體制改革,即是社會保險行政管理部門擔負的“宏觀上的政策、制度、標準管理”職責,而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具體承辦社會保險業務并承擔資金保值、增值責任*國家體改委《關于1993年經濟體制改革要點的通知》第十部分。。這樣,社會保險行政主管部門的“政”與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事”從理論層面上得以明確的劃分,但是,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組織設置無法助推這一理念的實現。
根據我國立法規定,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設置、人員編制、管理人員的任命以及辦公經費都由同級統籌級別社會保險行政管理部門批準或由同級政府財政按規定予以保障*《社會保險法》第72、73條。。也就是說,雖然理論上實行政事分開,但是實際運作的制度卻不足以支撐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獨立性,經辦機構的人事管理、經費支持及社會保險具體事務的部分決策權能都由社會保險行政主管部門實際掌控。首先,經辦機構的人事管理及物質配備與其行政主管部門幾乎無異。經辦機構的主要負責人由行政主管機關任命,工作人員參照公務員管理,占用由主管機關批準的額定編制。經辦機構的內部事務決策范圍由社會保險行政主管部門根據法律授權決定,內部事務管理實行首長負責制,用人單位和被保險人均無權參與*張榮芳,黎大有.論我國社會保險人的法律地位[C].珞珈法學論壇,2014(13).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68-79.。其次,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人員經費和運行、管理經費受制于行政主管部門。立法規定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人員經費和運行、管理經費由同級財政按照國家規定予以保障,實踐中,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為社會保險行政主管部門的一個內部機構,同級財政的預算、決算以社會保險行政主管部門為一個基本單位,經辦機構的經費數量由其主管部門整體核定而非單獨預算列支。在這種組織設置中,經辦機構如同社會保險行政主管部門的手足,主要負責人由主管部門任命,普通工作人員經過社會招錄后參照公務員管理,機構人員組成與被保險人利益無直接關系,缺乏獨立擔當社會保險人的利益鉗制機制,因此,只能定位于社會保險具體業務的執行部門,而非獨立的社會保險人。
(二)從權能看,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不能成為獨立的社會保險人
由于中央一級的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主要擔負綜合管理、指導和監督之責,并不具體經辦社會保險業務。根據立法規定,地方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職責主要包括社會保險登記、社會保險個人權益記錄和檔案管理、社會保險信息咨詢服務、社會保險待遇支付、社會保險稽核、公布和匯報社會保險基金收支、節余情況、接受有關社會保險舉報和投訴及其經辦機構的內部管理*《社會保險法》第57、58、70、73、74、80、82條。。仔細分析可以看出,經辦機構的這些法定職責僅限于社會保險的技術性、服務性業務,而最能彰顯社會保險人主體地位的核心權能——如社會保險費率的核定權、社會保險事故的認定權及社會保險基金的所有權等——經辦機構并不享有。
一般而言,社會保險人作為一個獨立的風險承擔主體,應當擁有獨立的保險費率核定權。由于社會保險承載著特殊的政策功能,雖然保險費率不能由保險人單方決定,但即使主要由政府決定的保險費率也是在保險精算基礎上盡量地滿足保險人的參與需求,也就是說,對保險費率核定的參與權是社會保險人的保險費率核定權的最低要求。這一點,我國的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不能做到。同時,根據我國法律規定,社會保險事故的認定權也由社會保險行政機關享有。
社會保險基金始終是社會保險的熱門、敏感話題。雖然《社會保險法》占用大量篇幅并專列第八章規制社會保險基金,但是,對于社會保險基金的核心問題——產權歸屬問題——立法采取了回避態度,從而致使社會保險基金的產權歸屬一直是國民高度關注而立法未予明確的問題。從世界立法例來看,作為自治性公法社團法人代表的德國,社會保險基金由社會保險人自主管理;實行公司制法人的智利,立法明確規定個人賬戶基金的所有權歸屬于參保人。而由行政機構擔當社會保險人的國家,大多出現了社會保險基金與社會保險人分離的現象,社會保險基金成為信托財產,社會保險基金實行信托經營。在社會保險基金信托經營模式下,國家會通過立法規定的配套措施保證社會保險基金能夠收支平衡,如社會保險人的社會保險供款請求權等。我國雖然也出臺了《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管理辦法》,明確了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信托經營,但是僅能對基金的投資管理環節起到約束作用,而無力作用于基金的來源環節。社會保險基金的來源環節對基金安全保障同等重要。在實施社會保險費的體制下,社會保險人應當掌控著社會保險費的源頭,應當賦予它相應的社會保險供款請求權,并承擔相應的責任,這樣才能從源頭上保障社會保險基金的安全。現實是,雖然我國的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可以以自己的名義成為行政訴訟的一方面當事人,但是社會保險基金并非其責任財產,經辦機構的責任財產限于政府財政劃撥的經費,因此,經辦機構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獨立的責任財產,也就無法獨立的承擔因業務經辦而致的責任。再加上經辦機構并沒有明確的社會保險供款請求權,追繳欠費的責任自然地也被大打折扣。
綜上所述,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不能構成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保險人,而是承擔技術性、服務性職能的業務執行機構。
二、誰是社會保險人
在對社會保險人主體制度進行審思之前,誰是我國社會保險制度中的社會保險人這一問題必須首先提及。如同前文所述,我國目前的現狀是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并非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保險人,那么,究竟誰是社會保險人?這一問題需在目前的制定設計中獲得釋疑。
從立法上的分工看,縣級以上的社會保險行政部門負責社會保險的管理工作。具體地說,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負責全國性的社會保險管理工作,縣級以上的地方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社會保險管理工作。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負責擬訂統籌城鄉的社會保險政策和標準、社會保險基金的管理和監督辦法等,包括醫療和生育保險服務管理、結算辦法、津貼標準及支付范圍。地方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在各自行政區域內根據規定在授權范圍內制定具體的實施細則,如醫療保險的定點醫院范圍、統籌級別、大病醫療保險的報銷比例等都由地方社會保險行政部門根據地方實際狀況具體擬訂。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負責提供社會保險服務,具體為社會保險登記、個人權益記錄、社會保險待遇支付等事務性工作*《社會保險法》第8條。。這樣,雖然社會保險行政部門作為管理部門原則上僅肩負著管理和監督之責,但卻履行著實質上的決策職能,成為社會保險事務實質決策的“大腦”,而社會保險保險經辦機構本來可以成為獨立的社會保險人,卻沒有社會保險事務的決策之權,充其量只是實施社會保險行政部門決策的實際“手足”*關于“大腦”與“手足”的比喻描述參見鄭曉珊.工傷保險法體系——從理念到制度的重塑與回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232-233.。另外,統籌級別地方政府的角色還不容小覷。雖然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經辦、管理社會保險基金,但并不享有基金的產權,也不承擔基金的經營責任,基金出現支付不足時,由統籌級別政府財政予以補貼*《社會保險法》第65條。。此處的“財政補貼”并非社會保險責任中政府的最終擔保責任,而是本由基金經營人承擔的經營不善的法律責任,或者說應是因應社會保險財務自主原則要求而由社會保險人自主承擔的不利后果責任。
由此可見,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險人主體制度形成一個怪異的格局:擔負管理和監督之責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同時負責著部分決策,管理著社會保險基金的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并不承擔基金經營不良的法律責任,統籌級別政府承擔基金支付不足時的財政補貼責任,國務院確定每年的基本養老金上調標準,社會保險經辦機構雖然只是負責執行社會保險的具體事務性工作,但卻是社會保險爭議訴訟的一方當事人。因此,從表面上看,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承擔著具體的社會保險經辦業務,又擔當著社會保險爭議訴訟的一方當事人,應作為我國的社會保險人,但實際上它既沒有自己獨立的意思,也沒有形成自己獨立的需要充分保護的利益,更沒有能夠獨立擔負責任的獨立資產獨立地擔負社會保險事務經辦不善的責任,充其量它也只是類似美國的社會保障署為方便業務執行在各地設置的地區局和分支機構,是社會保險行政主管機關設置的附屬的業務執行機構,與想象中的那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保險人角色相去甚遠,只有政府,擁有強大的行政決策權的政府,才是那個隱藏在背后的、真正的社會保險人*鄭曉珊.工傷保險法體系——從理念到制度的重塑與回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232-233.。
三、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與社會保險人身份分離的原因解析
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設立與我國的行政體制改革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在“政事分開、官辦分離”原則指引下將政府職能部門的社會保險行政管理職能與業務經辦職能分離,分別成立社會保險行政主管部門和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但這種分離并不徹底。把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以事業單位定性并不能掩蓋其實質上行政機構的運作屬性,經辦機構形式上的獨立地位無法割斷行政主管部門的實質管制。一方面,社會保險行政部門掌控著經辦機構的核心權能;另一方面,經辦機構并無獨立的人事任免權和責任財產,因此,經辦機構只是“政事分離背景下承擔‘技術性、服務性’職能的行政事務執行主體”*李文靜.醫療保險經辦機構之法律定位[J].行政法學研究,2013,(2):42-48.,把其定位于行政機關的內部機構而非獨立的事業單位似乎更契合目前的實際。
從行政法學角度分析,這種承擔“技術性、服務性”職能的行政事務執行主體可以成為廣義上的行政主體進而確定為社會保險行政訴訟的一方當事人,卻因不具備完全的權利能力而不能成為獨立的法人。
行政主體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的行政主體是指“行政法上享有權利、負擔義務,具有一定職權且得設置機關以便行使,并藉此實現行政任務之組織體……廣義之行政主體,不以具有公法人地位為條件,凡公法上之獨立組織體,有特定職權得設立機關或置備人員,以達成任務者,均屬之。”*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增訂8版)[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116.這樣,社會保險行政主管部門屬于狹義之行政主體,擁有公權利,具有權利能力與法律人格,具備公法人資格;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屬于廣義上的行政主體,雖然形式上是獨立的組織體,有限定的職權,但只具備部分權利能力,不擁有獨立的法人地位。
具備部分權利能力的組織成為廣義上的行政主體但不是獨立的法人與法理并不矛盾。雖然部分權利能力的應用理論在私法上并未形成通論,但在行政法學上則普遍承認存在部分權利能力的行政組織,具備部分權利能力的公法組織可以為行政主體,但并不是公法人;也就是說,公法人具有完全的權利能力,而行政主體則并不要求具有完全的權利能力,行政主體著眼的是統治權作用形式中的行政權,即“行政所由出的主體”*〔17〕〔18〕李洪雷.德國行政法學中行政主體概念的探討[J].行政法學研究,2000,(1):76-95.。
社會保險行政主管理部門的公法人資格指示的權利能力嚴格說來是一種實體法上的外部權利能力*權利能力有外部權利能力、內部權利能力和程序權利能力之界分。在實體法上,外部權利能力的特征在于可以作為權利義務的最終歸屬主體(執掌者),從而除部分權利能力的例外情況外,一般被視作法律上的人格。內部權利能力是指能夠成為內部法律規范的調整對象,承擔內部權利義務的資格,從而只為權利義務的部分歸屬主體,其所享有的權利義務的最終執掌者為具有外部權利能力的主體。而行政程序權利能力,即行政程序參與能力,即個人或組織以自己的名義參加行政程序,享有程序權利、履行程序義務的資格和能力。李洪雷.德國行政法學中行政主體概念的探討[J].行政法學研究,2000,(1):76-95.。隨著國家內部存在法的觀點得以認同,國家內部的機關、單位、職位成為擁有內部權利能力的主體,僅限于在法人內部以自己的名義享有權利義務,對外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只能作為法律人格者的機關,產生的法律效果最終歸屬于其所屬的法人〔17〕。特別是隨著訴訟法學的發展,訴訟法上的權利能力與實體法上的法律人格也相對分離,程序主體的地位得到進一步確定和提升,使得個人或組織的行政程序權利能力成為可能〔18〕。以這種理論考察,目前的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實質上就是一個僅擁有內部權利能力的主體,由于沒有獨立的責任財產,除能夠參與訴訟程序外,享有的訴訟權利和履行的訴訟義務都受到極大的限制,所以,最終的責任歸屬主體只能是社會保險行政主管部門,更準確地說是統籌級別政府。正因如此,“承擔‘技術性、服務性’職能的行政事務執行主體”的定位更符合目前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實際,相反,“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事業單位”定位*2011年3月23日,《關于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意見》(中發[2011]5號)指出逐步將承擔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的行政職能劃歸行政機構或將該事業單位轉為行政機構。也就是說,根據此文件精神,承擔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將不復存在。葉靜漪,肖京.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法律定位[J].法學雜志,2012,(5):82-87.則會產生新的疑惑。
從字面分析,“行政”一詞本身含有“經營、管理和執行的意義”,因此,就此意義而言,行政不僅存在于國家或政府事務之中,在私組織或行為中也能發現*翁岳生.行政法(上冊)[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1.。但是具體到“行政管理職能”時,往往限定在公共行政的特定語境中使用,牽涉公權力的行使。我國的事業單位改革已經明確指出將承擔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逐步轉為行政機構或將其行政職能逐步劃歸行政機構,并根據職責任務、服務對象和資源配置方式的差異將事業單位分為公益一類和公益二類*《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意見》第8條。。也就是說,按照改革意見,“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事業單位”以后將不復存在,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要么是行政機構,要么是事業單位。至于哪個選擇更優,只能根據理論的發展和實踐的需要而定。從國際立法例看,承擔社會保險經辦之責的既有行政機構,又有具有自治性質的公法人團體,還有按私法運營的公司法人。不管哪種形式,都非十全十美,關鍵在于適應國情需要,關鍵在于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能否為一個獨立的法人主體。說到底,將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置于權利義務的機制之中、而非從管理與被管理的角度——塑造為一個獨立的法人是社會保險經辦能力建設的關鍵,是推進社會保險改革、完善社會保險制度的關鍵。
四、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保險人身份塑造
“法律規范對社會秩序的調整,是通過設定權利義務來實現的,但法律設定權利義務的前提是確定權利義務的歸屬者和承擔者。”*李洪雷.德國行政法學中行政主體概念的探討[J].行政法學研究,2000,(1):76-95.社會保險人是社會保險法律關系中最重要的主體。社會保險人的準確定位和獨立的主體地位是社會保險關系有序運行的根本保證。
(一)主體獨立——把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締造為真正獨立的事業單位法人
通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設置沒有統一范式,但具有強烈的路徑依賴,受歷史傳統、政治體制的影響尤為深厚。長期以來,在我國的社會保險體制改革中,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一直充當著提供社會保險公共服務的角色,是“依據法律授權,執行社會保險政策、承辦社會保險事務、管理社會保險基金、協同多元主體向參保人提供社會保險供給服務”*胡曉義.社會保險經辦管理[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11.6.的主體,在實踐中履行著社會保險人的職責。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主要履行著提供社會保險公共服務的職責,這正是我國制度語境中“事業單位”的基本職能。根據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的規劃,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基本職責應是提供不能或不宜由市場配置資源的基本公益服務,即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屬于公益一類的事業單位。這與國家社會保險事業管理中心的事業單位定性相符。為保持社會保險經辦系統的一致性,根據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實際運行現狀,地方性的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也應定位于公益一類的事業單位。
事業單位的定性并不能必然導致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獨立性。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獨立”是指獨立于政府部門或其他組織,目前來說,主要是獨立于政府部門,把政府部門的行政管理職責與具體保險經辦業務真正分開,把屬于社會保險具體經辦的職責真正賦予經辦機構,讓其擁有完整的權能,從而成為真正的社會保險人。如果政府主管部門仍然實際掌控著部分社會保險人的權能(如社會保險供款請求權等),則會導致運動員與裁判員身份集于一身,將“無法避免政府從自身的財政利益出發,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選擇”,從而出現普遍的“惜付”的情形*張榮芳,黎大有.論我國社會保險人的法律地位[C].珞珈法學論壇,2014(13).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68-79.。
法人,簡單地說就是法律擬制的人,是具備人格的組織,團體性和人格性是其基本特征。團體性是指它是人或財產的集合體,而非單個的自然人;人格性是指它能夠依法以自己的名義獨立地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馬俊駒,余延滿.民法原論[M].4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11.。社會保險利用保險機制將團體成員的預定風險通過團體成員的供款轉稼于保險團體獨立承擔,保險團體的法人地位成為保險團體的內生性需求。社會保險人由參保的團體成員共同組成,社會保險人擁有征繳參保成員的供款作為自己責任財產的權利;與之相應,當團體成員發生預定風險時,社會保險人應當履行按照法定標準提供相應給付的義務。團體性和人格性既是社會保險人的基本特征,也是社會保險人作為獨立的風險承擔主體應當具備的特質。我國立法以法人活動的性質為標準,將法人分為企業法人、機關法人、事業單位法人和社會團體法人四類。從制度發展的路徑依賴性分析,企業法人顯然不適宜于我國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定性;機關法人的定性則不利于社會保險行政管理職能與具體經辦業務的清晰劃分;從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決策、運營、執行以及救濟程序的適用現狀看,社會團體的定性也不吻合。因此,就目前來講,我國的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應定性為事業單位法人*最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民法總則專家建議稿(征求意見稿)》將法人分為機關法人、社團法人和財團法人,事業單位法人沒有出現。社團法人又分為營利性社團法人和非營利性社團法人。此種分類中的非營利性社團法人比較類似于德國制度中的公法上社團法人(如基本社會保險中“保險基金會”)。從制度語境和行政法學理論的發展來看,非營利社團法人的定性更加契合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本旨,更有利于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獨立法人地位的確立。中國法學會民法典編纂項目領導小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民法總則專家建議稿(征求意見稿)第三章[EB/OL].[2016-03-27].http://www.lawinnovation.com/html/xjdt/13721.shtml.。
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獨立法人地位意味著它能夠以自己的名義獨立地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一般來講,依據保險機理,保險人會根據精算法則確定可保風險的保險費率及保險待遇的給付標準,保險人擁有對保險對象、保險費率、保險待遇標準、保險基金管理等事項的決定權,國家以監督者的身份履行外部監督之責。但是,由于社會保險承載著特定的社會政策目標,社會保險人的權利受到限制。社會保險的本旨在于為全體國民提供基本的經濟安全保障,特別在維持國民擁有合乎人性尊嚴的生存條件、促進社會經濟弱者積極融入社會及實現社會經濟弱者的實質自由與平等方面意義尤為突出*與旨在排除國家權力侵害和干涉為權利內容的自由權等第一代人權不同,以社會權為內容之一的第二代人權更加關注社會經濟弱者融入社會的權利、免于貧困的權利,社會權的產生與發展能夠防止傳統的自由權保障流于空洞化和形式化,以實現社會的實質正義和公平。許慶雄.社會權論[M].臺北: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13;汪習根.免于貧困的權利及其法律保障機制[J].法學研究,2012,(1):194-208.,因此,社會保險機制通常通過強制承保來防止“逆選擇”。一般情況下,社會保險人并沒有承保范圍選擇權、費率決定權和待遇給付標準確定權,這三項權利屬于法律保留事項,由立法機關決定。但是,作為一個獨立的風險承擔主體,社會保險人有責任保證承擔風險的責任財產處于安全狀態,有權利向社會保險供款義務人請求及時、足額地履行供款義務,亦即社會保險人擁有社會保險供款請求權。與此同時,社會保險基金作為責任財產,社會保險人亦有權選擇適當的經營管理方式保值增值。除此之外,社會保險人還可以根據提供服務的需要選擇適當的治理機制實施內部管理,社會保險人擁有內部事務的管理、決策權,國家主要通過立法活動實施干預和監督。選擇適當的治理機制實施有效的內部管理是社會保險人提高服務能力的需要,也是社會保險人的基本義務之一。
在我國的社會保險實踐中,社會保險的承保范圍選擇權、費率決定權和待遇給付標準確定權往往授權或委托政府行使,部分內容甚至直接授權統籌級別的地方政府行使。統籌級別的地方政府為了降低承擔社會保險基金支付不能的最終責任風險,“惜付”便成其“理性”的選擇。與此同時,我國立法規定的政府的社會保險財政責任只限于財政補貼責任。立法只是模糊規定了當社會保險基金支付不能時政府的財政補貼責任,但補貼的范圍、標準、資金來源及相關責任都沒有明確的規定*以財政與社會保險的二元分立為起點,政府財政基于補償改革成本、實現特定社會政策目標和制度擔保責任等原因補助社會保險時應當遵循法定的標準和程序。熊偉,張榮芳.財政補助社會保險的法學透析:以二元分立為視角[J].法學研究,2016,(1):110-126.。我國社會保險基金的來源主要由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雙方繳納,政府沒有直接供款責任。即使對于財政的補貼責任,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并不擁有對政府的社會保險供款請求權。這樣的制度設計實際上架空了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基本權利,致使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成為僅承擔“技術性、服務性”職能的行政事務執行主體,不能成為真正的事業單位法人,從而制約了社會保險制度的整體運行效率。以后的改革應徹底改變這種現狀,明確政府、單位和個人各自的財政責任,把屬于社會保險人的基本權利真正賦予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將其塑造為真正獨立的社會保險人。
(二)組織獨立——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獨立于社會保險行政部門
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組織上隸屬于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其機構設置、人員編制、管理人員的任命以至辦公經費都由社會保險行政部門或同級政府按規定予以保障*《社會保險行政爭議處理辦法》(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令第13號)第2條將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明確為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所屬的工作機構。《社會保險法》第九章規定經辦機構按統籌地區設立,其分支機構和服務網點的設立需經所在地的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和機構編制管理機關批準。由此可見,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實際掌控著經辦機構的組織設立。,人、財、物的關聯與控制使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很難脫離社會保險行政部門的實際掌控,難以形成獨立的利益、以獨立的法人主體身份獨立自主的提供社會保險公共服務,難以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和自求平衡,只是“法律、法規授權的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所屬的專門辦理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等社會保險事務的工作機構”*《社會保險行政爭議處理辦法》(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令第13號)第2條。。這種組織上的隸屬性不但直接制約著經辦機構的經辦能力建設,還進一步凝結著統籌級別政府的固有利益,形成更為嚴重的地區利益和地域差異,進而阻礙著保險類別的整合和統籌級別的提高。這種“官辦不分”的組織體制很難將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締造為能夠自主運營、自求平衡的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保險人。
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獨立法人主體的塑造必須首先破解社會保險行政部門組織上的實際掌控。社會保險作為政府實施風險管理的一項政策工具,擁有獨特的運行機理,已經形成一個獨立的運行系統。這個系統一方面承載著國家賦予的提供特殊的公共服務的職能,一方面沿著社會保險的機理在反復的失衡與平衡中不斷地尋求自洽、并實現發展。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是這個獨立系統的運營者,因此,把它構建成一個自上而下的實施垂直管理的體系并不違背社會保險的運行機理,相反,更能保障和提高制度的運行效率*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曾建議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應實行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鄭秉文.中國社保經辦服務體系亟需深化改革[N].上海證券報,2013-12-27(A03);鄭秉文.中國社會保險經辦服務體系的現狀、問題及改革思路[J].中國人口科學,2013,(6):2-16.。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實行垂直管理,自成系統,可以祛除社會保險行政部門的從屬和管控,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法人實體,從而將社會保險行政部門的“管”和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辦”真正分離。
(三)財務獨立——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獨立于同級地方政府
財務獨立與自主是社會保險區別于其他社會福利制度的基本標志。社會保險基金是社會保險人承擔團體風險的物質載體。社會保險人的財務獨立即意味著社會保險基金僅是社會保險人承擔風險的責任財產,社會保險人應在遵循保險機理的基礎上依據精算法則首先自求財務平衡,當國家通過立法委托賦予社會保險人承載額外的社會政策功能時應圈定明確的資金來源,而不能以社會保險基金概括承受,否則將會破壞社會保險基金的精算平衡,并危及社會保險運作的可持續性。因此,不管社會保險人的主體類型如何,社會保險基金都獨立于政府財政。以自治性的公法社團法人為代表的德國、法國,社會保險基金歸各保險基金會或行業協會所有,由其自主運營;以公司法人制為代表的智利等拉美國家,由于個人賬戶制的存在,個人賬戶基金雖歸被保險人所有,但由AFP接受委托經營;即便在政府作為社會保險人的美國和英國,社會保險工薪稅入庫后會被分流形成專門的社會保險信托基金,獨立于政府財政,由專門成立的信托基金受托人董事會管理運營。在政府作為社會保險人的國家,社會保險信托基金雖有“第二財政”之謂,但畢竟不同于正宗的政府財政——“第一財政”。之所以作出這種制度安排,時任總統羅斯福的說法是“可以防止立法者濫開空頭支票導致將來的財政赤字,將使社會保險的花費永遠不超過其預定的收入”*Larry DeWit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curity in America, 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Vol. 70, No.3, 2010, pp.1-25.。
我國社會保險基金的財權歸屬一直存在“財政資金”和“參保人共有財產”的爭論,2013年后又對社會保險基金的特質不予甄別將其一概并入全口徑預算的范圍,模糊了社會保險基金與財政資金的邊界*關于社會保險基金財權歸屬的爭論以及社會保險基金并入全口徑預算管理的困惑可參見張榮芳,熊偉.全口徑預算管理之惑:論社會保險基金的異質性[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5,(3):159-169.。2015年8月,《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管理辦法》明確將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視為養老基金委托投資的委托人*《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管理辦法》第13條。,進一步混淆了社會保險基金與財政資金的界限。就社會保險基金信托而言,委托人向受托人轉移信托財產所有權的前提條件是委托人在實施信托行為時對信托財產擁有所有權,既然《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管理辦法》把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作為委托人,那么即意味著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是養老基金的所有權人,這樣,將其與全口徑預算管理的做法結合來看,政府顯然已將社會保險基金作為政府財政的一部分看待。將社會保險基金混同于政府財政,無異于橫越了雙方的界分與藩籬,一方面導致政府的政策目標向社會保險基金過分讓渡和擴張,社會保險基金的“外部負擔”過于沉重,從而破壞了基金自身的精算平衡;另一方面虛化了社會保險的保險性,深深激勵著參保人員對社會保險的非理性期許,致使政府由“制度擔保人”變為“最后付款人”*“制度擔保人”和“最后付款人”的解析參見熊偉,張榮芳.財政補助社會保險的法學透析:以二元分立為視角[J].法學研究,2016,(1):110-126.,結果是社會保險基金的責任和政府財政的責任都被無限地擴張,進而深度破壞了社會保險制度的獨立性。
我國社會保險經辦機構運行經費支出保障的制度設置*我國《社會保險法》第72條規定社會保險經辦機構運營所需的人員經費、物質保障經費以及管理經費都由同級財政按照國家規定予以保障。從另一側面加深了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對同級政府的隸屬和依賴。從世界立法例看,社會保險人運行經費的支出保障既有由社會保險基金支出者,也有通過財政專項預算解決者。一般情況下,社會保險稅制模式下以財政專項預算解決社會保險經辦經費的做法比較普遍,而在社會保險費制模式下,對于第一層次的社會保險由中央集權管理的情況下,也會存在由中央財政預算解決經辦經費的情況,如日本*吳震能.日本社會保障制度之研究——以權利救濟為中心[D].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2009.93.。但是,既使在這些國家,基本只是第一層次的基本保險由中央財政預算解決,不由同級地方政府財政解決,而對于大多數實行社會保險費制的國家,仍然秉承著俾斯麥保險模式的自我負責精神,在社會保險精算中計入社會保險人的運行經費,這樣做的優勢在于能夠確保社會保險人的自生系統獨立地循環平衡,社會保險人獨立的主體地位得以保障。我國的社會保險立法將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運營經費與同級政府財政掛鉤,當地方政府的“財權”和“事權”并不匹配和對等的狀況下,當社會保險經辦事務還沒成為地方政府的當務之急之時,地方政府當然會根據執政的需要作出有利于自己的“理性”選擇,社會保險機構的經辦能力不足也在預料之中。
因此,為了順利推進社會保險制度的改革與發展,明確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獨立的社會保險人地位乃是當務之急。就目前而言,將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塑造為獨立的事業單位法人,使其成為獨立的責任承擔主體,組織上獨立于社會保險行政部門,財務上獨立于同級地方政府,讓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成為一個能夠真正自行循環、自求平衡的相對獨立的系統,從而割斷對同級政府和同級社會保險行政部門的隸屬,為社會保險關系的順利轉續和基礎保險統籌級別的提升創造條件。
The Puzzlement and Reflection:the Orientation of Social Insurance Agencies
YU Shu-hong, LI Xiu-feng
(Law School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In Social Insuranc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ocial insurer is not pointed out definitely. The social insurance agencies can not take on the role of the insurer because of the absence of independent and self-financed and they are simply executive agencies major in technical and service functions, and can be one of the parties in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but not independent legal persons. The social insurance agencies have actually been performed the function of the social insurer for a long time, so the role of the social insurance agencies should be defined, and constructed into a truly independent public institutional legal person separating from the social insuranc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terms of independent subject, independent organization and independent financial.
the social insurance agency; the social insurance relationship; the social insurer; the public institutional legal person; self-financed
2016-06-11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我國社會法的范疇與體系研究”(項目編號:13BFX143)的階段性成果。
喻術紅,女,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李秀鳳,女,武漢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濟南大學政法學院教師,主要研究方向: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
D922.5
A
1672-769X(2016)05-00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