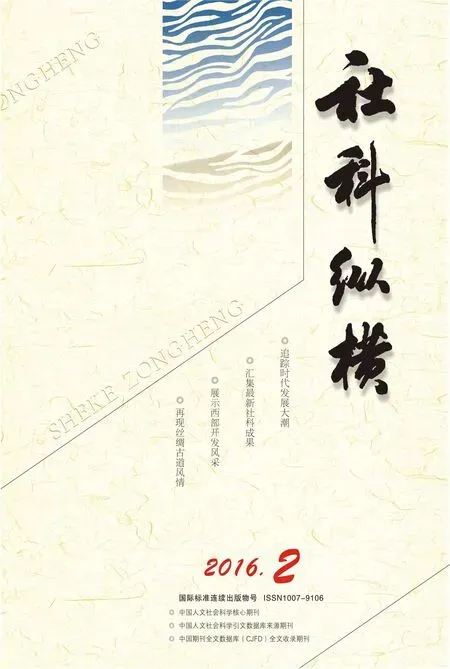“勤勞現象”的倫理反思
劉永春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北京 100872)
?
“勤勞現象”的倫理反思
劉永春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北京100872)
【內容摘要】勤勞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美德。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有些被視為勤勞的行為由于缺乏自由意志的積極參與,喪失了道德上善的性質。為生存處境所迫的勤勞受制于生命必然性法則的支配,有悖于個體的真實意志;被視為生活常態的勤勞是一種缺乏理性反思能力的從眾行為,而且混淆了勞動與生活的關系;被利用的勤勞是一些人為了實現自我利益,打著勤勞是美德的口號,欺騙人類中的另一些人為自己辛苦勞作。注意區分以上三種勤勞的現象,有助于我們深刻理解和把握作為美德之勤勞的道德內涵。
【關鍵詞】勤勞美德自由意志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傳統美德的繼承創新與實現中國夢研究”。
勤勞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中國人自古以來就以勤勞聞名于世,創造出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在當代社會,繼承和發揚這一傳統美德對促進我國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要正確認識和理解作為美德的勤勞,需要特別注意區分其與以下三種缺乏道德屬性的勤勞。
一、為生存處境所迫的“勤勞”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孝道倫理對中國人的觀念和行為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斷子絕孫被視為最大的不孝,“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相反,多子多孫、人丁興旺、兒孫滿堂被認為是孝順的體現。受這種觀念的影響,古代中國社會出現了人口的膨脹,但是“龐大的人口對生產資料的巨大壓力所產生的社會后果就是無力進行資本積累,如此多的人口需要吃、需要穿、需要住,無論中國人如何節儉,一年到頭也難以有什么剩余。”[1](P74)面對這樣的處境,在生產力不發達的自然經濟條件下,人們只有依靠辛勤勞動才能夠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計。美國傳教士何天爵在《真正的中國佬》一書中寫道,他所雇傭拉纖的船夫,為了掙幾分錢和幾頓飯,要走超過波士頓城和紐約市之間的路程;經常會看到,幾十個大人和小孩,為了爭得路邊的一堆馬糞而爭執不休,他深感到:“對于中國大部分的民眾來講,如果一天不勞動或者失去了工作,那將不可避免地意味著一天沒有飯吃。”[2](P228)亞瑟·亨·史密斯也有同樣的感觸,他在《中國人的德行》一書中指出,“在中國這一人口稠密的國家中,生活的水平之低,是名副其實的‘生存斗爭’”[3](P180)。
在現代社會中,這種為生活處境所迫的“勤勞”依舊屢見不鮮。商品經濟的繁榮,使得生活于其中的每個人,都必須依賴于通過自己的工作進行交換而維持生存。因此,工作在個體中的地位也就越加重要。而隨著物質產品的繁榮,新產品的層出不窮,人類的欲望便被物質所引導,而金錢在社會中不僅扮演著購買新產品的工具,更是一個人成功的標志,是一個人尊嚴地位的象征,貧窮是可恥的,富裕才是榮耀的。這種觀念迫使人們努力追求財富,一份高報酬的工作在他們心中的地位就越加重要。所以,當面對金錢至上的社會潮流、層出不窮的物質誘惑時,就會選擇越加拼命地工作,工作在生活中和觀念中的地位就愈加突出。
這種被迫的勤勞充分展現了人類不被惡劣環境所屈服和壓倒,在競爭中謀求生存和發展的奮斗精神,就這一點而言,勤勞是值得贊揚的。但是在道德上這種勤勞仍然是有所缺陷的,因為它不是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基礎之上,它是人們出于生存所迫而做出的無奈選擇,換句話說,要是人們不用勤勞可以免于生存處境的壓迫,那么,便很少有人心甘情愿地繼續辛勤勞作。因此,這種勤勞是建立在一種必然性之上,是被一股外在的力量驅使著人們去從事某些事情,個人的自由意志并沒有充分參與其中。
換而言之,出于外在因素而非內心自愿選擇的勤勞,是不具有道德屬性的,因為根據康德的觀點,具有道德意義的行為首先應當是基于自由意志而產生的。在德國哲學家赫斯看來,“如果勞動是在外力的驅使下進行的,那就是一種貶低和壓抑人的本性的重負,是一種僅僅為了可鄙的罪惡報酬才去干的惡行,是一種雇傭勞動和奴隸勞動。一個人假如除了其勞動本身以外還為他的勞動尋求報償,那么,這個人就是一個為他人的目的而活動的奴隸,是一部被驅趕的無生命的機器。”[4](P169)換而言之,勤勞如果不是出于一種主動的內在的力量,而是被一種外在的力量所驅使,那么,這種勤勞為了避免更大的痛苦,無法獲得真正的快樂。因此,被生活處境所迫的勤勞在嚴格意義上還不能稱之為美德。
二、被視為生活常態的“勤勞”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勤勞而不是休閑才是生活的正常狀態,人總要處于忙碌狀態才被認為是合理的。在中國一些偏遠的農村中,還保留著這樣的一些風俗習慣:男人沒事可做的時候,也不能成天呆在家里,總得找些事情來做,否則會被認為是“懶漢”;那些坐在一起閑聊的農婦,手頭總得拿些針線活來做,即便不需要做,也得拿來做做樣子,免得被人說是“懶媳婦”;就連兒童也被要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干些拔草、放羊、喂牛之類的農活,這樣才會被認為是一個懂事的孩子。正如史密斯所指出的,即便是那些富有得不用干活就可以生活得很舒服的富人,也像貧困的人一樣辛苦地工作著,商人、工匠都是在天未亮就趕到了市場與職場,在朝廷辦公的大臣每天凌晨兩點多就要從家里出發,皇帝也要早起晚睡,日理萬機,這樣才算是一個合格的公務人員。[3](P19)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缺乏休息的觀念,“他們早出晚歸,勤奮勞作。歲歲年年,既無星期天也沒有其他節假日。一年之中,他們只有三個約定俗成的所謂休息日。”[2](P71)忙碌才是生活的常態,勤勞是被各個階層共同踐行的生活方式。
這種“勤勞”的可貴之處是,較少地含有功利性成分,將勤勞視為目的本身來對待,這種為義務而義務的道義精神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問題在于行動者的勤勞不是建立在對自身行為的理性反思之上,而是僅僅因為以往人們都如此行動,于是對傳統習俗不假思索地繼承和效仿,這種對自我的勤勞缺乏清醒認識和反思的狀況與螞蟻、蜜蜂的勤勞并沒有本質上的差異,都是一種無意識的行為,不同的是前者是基于生物本能,后者基于文化上的從眾行為。因此,這種勤勞是一種與道德無關的行為。
在現代社會中,勤勞也是人們生活的常態。當代社會已經逐漸淪為一個“工作的社會”,工作在人們的整個生活中占據核心地位,一切人圍繞工作而生活、交際、自我構建,在考學、擇偶、交友等日常活動中,工作的好壞是人們重要的選擇標準。更為重要的是,隨著互聯網的飛速發展,工作已經開始向日常生活各個領域開展了全面的滲透。特別是移動互聯網的發展,讓工作與休閑、上班與下班的界限很快變得模糊了。工作者隨時都可能接受到來自電話、短信、電子郵件、qq、微信的呼叫,無論你是在上班還是在下班,無論你是在家里休憩、還是在夏威夷度假,無論你是睡著還是醒著,時刻都得注意老板的指示,隨時可以傳達到你耳邊,馬上就得轉入工作狀態,每一個人已經成為潛在的24小時都處于上班狀態。與此同時,休閑的時間已經被壓縮到少之不能再少的地步。對于“一些人的工作,生命就是他們的全部。工作所需的核心,填滿了所有的圓環圖,其它事情的空間所剩無幾”[5](P76)每日的生活,除了工作就是工作,還是工作。正如弗洛姆所言:“我想,世上再也沒有什么事,甚至包括犯罪行為,會如同這永無休止的工作一樣與詩、哲學,以及生活本身背道而馳。”[6](P187)
這種勤勞的問題在于沒有擺正勞動與生活的關系,將勞動視為生活的目的,為勞動而勞動,喪失了生命更為重要的意義。除過勞動之外,生活中還有很多富有意義和價值的事情,比如休閑、交友、家庭生活等等,勞動并不能構成人類生活的唯一目的,它只具有工具性的價值,人們渴望通過勞動實現生活的幸福,在勞動中實現自我的價值,使得人生變得富有意義。如果將勞動視為生活的全部,一生毫無目的地忙忙碌碌,無限享受生活,那樣的生活是很難稱得上幸福的。歐洲人早就意識到,讓工作支配一個人的生活是愚蠢的選擇,所以他們寧愿選擇少拿一點工資,也不愿犧牲和家人、朋友聚會的美好時光。缺乏親情、友情、愛情為勞動所充滿的生活是灰色的,豐富多彩的閑暇時光才是生活的常態。
三、被利用的“勤勞”
在古代社會里,勤勞是被統治階層所極力稱頌和倡導的美德,事實上,統治階層只是將其作為維護政治統治的道德工具,為自我創造財富而增強民眾勞動積極性的重要手段。羅素就指出,在古代社會中,勤勞是奴隸性質的道德。土地所有者為了獲得安樂懶散的生活,利用殘酷的剝削制度與生產資料的獨占,壓迫人們不得不辛勤勞動。后來,他們發現誘使人們信奉一種道德,相信辛勤勞動是他人的義務。即“把生產得來的一部分分出來供養那些閑散之人意味理所當然。”[7](P203)依靠這種方法可以大大減少管理的成本,使得底層的百姓自覺自愿地為統治者創造更多地財富,因此,勤勞便得到了贊美。
在現代社會中,勤勞是美德的觀念被一些資本家所利用,作為追求經濟利益的重要宣傳工具,在一些企業中得到了發展和繁榮。其中加班現象便是對這一現象的集中體現。北大社會調查研究中心《2012年度中國職場人平衡指數調研報告》顯示,國內職場人日均工作8.66個小時,其中三成職員超過11小時。許多企業大力提倡勤勞光榮的口號,鼓勵員工加班加點,對那些堅持長期加班的員工給予褒獎,對那些按時下班的員工則予以批評,“以加班為榮”已經成為一種工作倫理文化,成為在一些工作領域中奉行的潛規則。在這種強大的社會壓力之下,面對稀缺的工作崗位,很多人不得不選擇忍受身心的摧殘,長時間拼命于工作之中,久而久之,導致身體狀況惡化,以至于過勞死現象頻頻發生。對勤勞的過度利用,還造成另一部分人的失業。正如羅素所指出的,“一個人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相當于一個人干兩份工作,導致工作崗位減少,使得更多的人找不到工作。”[7](P203)
齊格蒙特·鮑曼對勤勞被資本家利用的狀況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在他看來,勤勞觀念是在工業社會中得到極力的提倡,并不是偶然的現象,是資產階級有目的有計劃的改造活動,其目的是根除和摧毀那些阻礙現代化工業發展的傳統習俗,讓那些過去習慣于自己設定工作目標,控制進程,分配工作財富的人們習慣于現在“運用他們的技術與勞動能力去執行那些由其他人設定和控制”,[8](P36)缺乏工作意義的任務。“不用理會榮譽和榮耀,理性和目的——只管努力工作,日復一如,分秒必爭,盡管你并不能看到自己這種工作節奏的意義和原因,也無法解釋自己這種努力的意義何在。”[8](P36)
現代企業家對勤勞的倡導正是對“勤勞是美德”觀念的綁架,從觀念上馴化自己的員工,讓員工拼命于枯燥無味的工作,試圖塑造一群不知疲倦且永無怨言的習慣于枯燥單調重復工作的工蟻,“以工作生活具有高貴的倫理為名義,強迫工作者接受一種既不尊貴又不能與自己的道德價值相匹配的生活。”[8](P38)通過將另一部分人訓練成心甘情愿工作的奴隸,通過他人的辛苦勞動來滿足自己閑暇奢侈的消費生活,將他人的勤勞視為增進自我財富的工具。以這種欺騙的姿態鼓吹勤勞,這恰恰是對勤勞的褻瀆。
勤勞不是要求人類社會中的一部分人用自己辛勤勞作創造的財富去無償侍奉另一部分人,也不是一些人企圖通過對它的贊美去奴役另一部分人的宣傳工具。以勤勞為旗號卻試圖在逃避勞動,享受他人成果的做法,不僅是對他人的欺騙,也違背了公平正義的倫理原則。勤勞作為一種美德,不是僅僅對勞動人民的道德律令,是所有人在工作中應當主動踐行的美德。
綜上所述,以上三種勤勞的狀態,或者不是基于自由意志的選擇;或者是將勤勞視為生活的全部,以一種不假思索的態度來行動;或者勤勞的行為是在被欺騙和利用狀態下做出的。總之,在道德上都是有所缺陷的。在這三類狀況中,個體對自身的勤勞行為都缺乏清晰的認識和理性的反思,不是以一種積極主動的狀態來對待勞動,而是以消極被動的態度來面對勞動,人的主觀能動性沒有通過這種勤勞釋放出來,人的真正價值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也沒有通過這種勤勞得到真正實現。因此,作為美德的勤勞不是在這三種情況下而言的,以這三種情況來否則勤勞的美德屬性,是對作為美德之勤勞的誤解。
參考文獻:
[1][美]古德諾.蔡向陽等譯.解析中國[M].國際文化出版社,1998.
[2][美]何天爵.鞠方安譯.真正的中國佬[M].北京:中華書局,2006.
[3][美]史密斯.陳新峰譯.中國人的德行[M].北京:金城出版社,2005.
[4][德]赫斯.赫斯精粹[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
[5][英]漢迪.江慧琴,趙曉譯,空雨衣[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3):76.
[6][美]弗洛姆.健全的社會[M].孫愷詳譯,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4):187.
[7][英]羅素.文良文化編譯.俗物的道德與幸福[M].北京:華文出版社,2004.
[8][英]齊格蒙特·鮑曼.仇子明,李蘭譯.工作、消費、新窮人[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
*作者簡介:劉永春(1983—),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中國傳統倫理思想。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9106(2016)02-0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