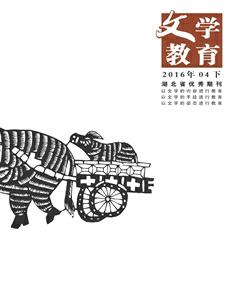試論地域文化對劉震云創作的影響
董穎
內容摘要:地域文化對作家的性格氣質、藝術風格、思維方式、審美情趣等因素有重要影響。許多作家群體與文學流派都是在地域文化的作用下產生的。河南作家劉震云的文學創作就不可避免的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他的作品著眼于鄉村的人情世態及經濟變革背景下的歷史滄桑,具有濃厚的地域色彩。因此,研究地域文化對劉震云創作的影響,可以更加全面的探究劉震云的創作理念和歷程。本文從精神文化、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等方面,探析了地域文化對劉震云創作的影響。希望以此增強劉震云創作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統性。
關鍵詞:地域文化 劉震云 影響
所謂的地域文化主要是指在特地區域內,具有悠久歷史和特色,且至今仍發揮重要作用的文化。包括傳統、生態、習慣、民俗等元素。這些元素具有鮮明的地域色彩。地域文化隨著時代的變遷不斷豐富和變化,但在一定時期內具有相對穩定性,對人們的生活、生存產生多方面影響。在當前的全球化背景下,全面展示不同地區的文化,不僅可以有效豐富世界文化,還可以為我國文化發展增添動力,并增強地域文化的認同性。文學作為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不可避免的會受到地域文化的影響。豐富的中原文化與廣闊的鄉土世界為中原作家群的發展提供了資源。河南作家劉震云在文學創作中就受到了故鄉經歷與中原文化的影響。中原地區農業文明歷史悠久,這使人們具有濃重的鄉土意識,儒釋道精神根深蒂固,同時,戰爭也使生存于這片土地上的民眾具有突出了“官本位”意識。劉震云在這種地域文化影響下,形成了獨具色彩的創作理念和文學成果。
一、域精神文化對劉震云創作的影響
河南在古代是王都的首選之地,屬于中心地帶,被稱為中原,是古都數量密集之地,長期被作為經濟、政治、文化中心。這種深厚的文化積淀和地理優勢,使生活于這里的人們產生了一種自高自大的優越意識,但與此同時,在戰爭及封建頑固思想的影響下,中原人的精神心理也屢屢受挫。尤其在儒釋道等傳統思想的影響下,中原人的臣服依附心理逐漸加強,服從忍讓精神也相對較強。生活于中原大地上的作家劉震云也不可避免的受到這種精神文化的影響,他曾說:“曾在農村生活的人,其世界觀勢必受到農村生活的影響。”親身經歷的農村生活,讓劉震云更加真切的感受到生活在重重重壓之下的底層人物所經歷的種種苦難,并對之報以深切同情。中原歷史文化中的大遷徙、自然災害、文革、戰爭、大躍進等,以及那些被無情摧殘的生命個體,都成了劉震云文學創作的重要資源,他運用自己獨特地創作筆觸揭示了這些文化背后的歷史性與人為性因素。在劉震云的文學作品中,既有源自于歷史文化的歷史苦難,也有被許多人忽略的現實苦難。透過其文學創作不難發現,他在內心深處對生活于中原地區的底層民眾始終抱有濃濃的溫情,也正因為如此,他才會對民間苦難持續關注和書寫。劉震云在創作中往往透過身體苦難和生活苦難,揭示隱藏在深處的精神和心理淵源。他的新歷史主義小說就生動的呈現了諸多歷史苦難的情境。例如,《一九四二》就形象的展現了中原民眾遭受自然災害,在死亡邊緣拼命掙扎的現象。小說中,人們飽受饑餓的煎熬,更加殘酷的是他們還需向軍隊繳納飼料,這些飼料甚至比他們吃的食物還要好,若不按時繳納就會被打死。而當時的執政者蔣介石則“不相信災情這么嚴重”,他有許多軍國大事要處理,這些事物事關他的統治地位,而中原地區數以萬計百姓的性命則被視為草芥。河南作家劉震云稱自己正是這些“慌亂下賤的災民的后裔”,因此,他認為自己有責任去回憶和書寫那段苦難的歷史,這不僅是對中原歷史的尊重,也是對民間苦難的悲憫情懷。
二、地域物質文化對劉震云創作的影響
除了精神文化,物質文化也是中原文化的重要內容,對作家的創作同樣具有重要影響。“去國懷鄉”的思想是中國人永恒不變的意識和書寫主題,尤其是生活在中原農村地區的人們,具有更加濃重的鄉土情結,時常在創作中抒發對故鄉的追憶。受中原物質文明的影響,劉震云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民本觀念,其小說創作也以鄉土世界為背景,但與閻連科、莫言不同,他并未書寫張揚在中原土地上的生命強力,也沒有像沈從文一樣,構建一個獨立于城市文明之外世外桃源。劉震云對故鄉的情感更多的是排斥,而非接受。就地理概念的本質屬性而言,中原文化更加強調對土地的堅守。作為重要的糧食產地,中原人民具有更加悠久的土地情結,對鄉土的留戀之情更加濃烈。劉震云在談到故鄉時曾說:“故鄉是一個與回憶、情感、情愫有關的概念,在每個人出生之時,故鄉就會教給你丈量這個世界的基本東西,諸如愛與恨、大小多少、東西南北等。” 《大廟上的風鈴》中的趙旺、《塔鋪》中的 “我”、以及《栽花的小樓》中的紅玉等人。都對故鄉具有濃重的負罪感或懺悔情感。即便是在《一地雞毛 》、《單位》、《官人》等“城市系列”的小說創作中,劉震云也是透過城市生活展現人們對城市與鄉村的雙重失落,而以《被水卷曲的酒簾》、《塔鋪》、《大廟上的風鈴》、《罪人》等為代表的“鄉村系列”小說則更是鮮明的展現了中原農村人們的物質生活狀態。以《頭人》為代表的“故鄉系列”都是以劉震云的故鄉——河南延津為敘事背景,生動展現了農村民眾的生活境況,以及在時代變遷過程中,鄉村居民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轉變。在“故鄉系列”之后,劉震云又創作了《手機》、《一腔廢話》、《一句頂萬句》等“說話系列”作品,他開始嘗試從“都市”角度,展現人們當前的生活狀態。透過其文學創作不難發現,劉震云對土地具有復雜的情感,這有一定的內在因素,隨著經濟文化的不斷發展,中原地區的人們逐漸從傳統的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化,這促使生活與這片土地上的人逐漸脫離了土地,開始向往城市生活,追求金錢利益。我國著名文學家魯迅就通過“離去——歸來——離去”視為模式,對人們的故鄉情結進行探索,受物質文化的影響,農村地區的人們試圖逃離精神匱乏、物質貧困故鄉,但之后卻希望在精神返鄉中尋求靈魂的安身之處。劉震云的創作無論是在表層的現實層面,還是在深層的異質層面,都彰顯了自己對故鄉的多種探究和思索。
三、地域制度文化對劉震云創作的影響
中原地區歷來被視為軍事要塞,在這片土地上,不斷的上演權力之爭,長期的封建統治使得生長于這片土地上的民眾形成突出的“官本位”思想。作家劉震云曾生活于社會底層,因此他對制度文化的浸染具有更加直觀的感受,對私欲和權力的合謀也有更加清醒地認識,同時,他也更加真切的感受到中原民眾對權力的敬畏。權力不僅僅是衡量一個人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桿,還是人們進行權錢交易的通行證,是獲取物質財富的平臺。因此,在這會發展過程中,人們普遍存在權力崇拜的意識。中原人飽受戰爭之苦,因此具有更加濃重的“官本位”思想,不管是權力的承受者,還是權力的擁有者,都認為權力不具備道德感和正義感,為了取得權力可以運用一切手段,甚至不顧禮義廉恥,失去基本的人性,淪為權力的奴隸。劉震云曾說:“我的故鄉是很看不起我的,故鄉的人們以為我出門在外這么多年,原本應該混個臉面回去的,但卻沒想到只是混了個青年作家。在我們的國度里,你是否混得好,要看你的地位,地位就是一切身份。而做沒做官,做多大官,是和地位有密切聯系的。大家全都怕官,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怕。”中原地區的民眾對權力同樣具有無限的渴求,他們為了實現這種權力欲望不斷進行盲目的探索和追逐,這充分展現了人性在權力土壤中逐漸被腐蝕的現象。劉震云在創作中揭示了,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和龐大的丑惡群體,是形成人性丑惡的根源,正是封建專制統治導致了人性的異化。劉震云在小說《故鄉天下黃花》中塑造了孫、李兩個馬村較有實力的家族,他們不斷進行殺戮,由權力引發了一系列的斗爭與沖突。例如,賴和尚、孫殿元、衛東、衛彪、李老喜、趙刺猬、許布袋等都是權力追逐者,他們利欲熏心在權力的腐蝕下逐漸喪失了做人的底線,為了爭奪權力他們無恥卑鄙,獲得權力之后則肆無忌憚,徹底成了權力的奴隸。劉震云運用生動的筆觸展現了鄉村荒野的生存狀態。
總之,勞倫斯在《經典美國文學論》中曾指出:“在地球表面,不同點折射出不同的光彩,不同的振幅和化學氣體,又與不同的恒星形成特殊的關系。”可見,不同的地域文化對作家的創作個性同樣具有重要影響。生活于中原地區的河南作家劉震云同樣要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他從事文學創作幾十年,作品受到廣泛好評,他的小說具有濃厚的鄉土氣息和鮮明的中原文化色彩。這主要是由于他受到了中原地區精神、物質、制度文化的影響,劉震云在文學創作中多角度描繪了中原土地上底層人物的生存狀態,盡力還原鄉土本色,為讀者展現一個豐富的社會生活圖景。他一方面對社會現實進行無情的批判和揭露,另一方面則展現對故鄉的無盡熱愛。呈現出鮮明的人文主義情懷。
[課題項目:2014年度河南省高等學校青年骨干教師資助計劃項目,名稱《河南文化與河南鄉土文學》,編號2014GGJS-144]
(作者單位:新鄉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