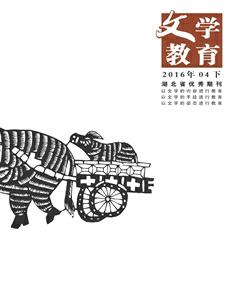論沈從文筆下湘西女性的人性美
王佳煜
內容摘要:在沈從文創作的豐富文學中,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既有稚嫩清純的少女,又有飽經滄桑的鄉村婦人,甚至有生活在社會底層倍受欺辱壓迫的河街妓女,這些女性形象無不體現著善良淳樸的人性美:純凈自然的人性美;淳樸頑強的人性美;真摯熱烈的人性美。他從人性的角度,以其獨特的審美眼光,對湘西女性加以理想化的描寫和由衷的贊美,使一系列鄉村女性各具形態,在文學史上有著獨特的藝術審美價值和認識價值。
關鍵詞:沈從文 湘西女性 人性美
沈從文說:“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為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這句話道出了沈從文獨特的文藝觀。沈從文在他所構筑的“湘西世界”里就充分展現了湘西人民那種特異而原始的生命形式和生活狀態,為人們展現了一幅完全不同于都市文明的人性畫卷。而在這幅風俗淳厚的畫卷中,湘西女性形象更是晶瑩純凈、光彩照人。這些女性無不體現著獨特的人性之美,同時又因其各自的生活環境不同,其人性美也形成了多樣化的特點,顯得更加光輝耀眼。
一.純凈自然的人性美
沈從文塑造的清新純凈略帶土氣的湘西少女格外引人注目,她們如同出水芙蓉,天然麗質,靈秀無邪。沈從文在塑造這些少女形象時也多用自然界的景物,尤其是動、植物加以比擬,更加使得這些天真活潑的少女們融入了湘西那秀美神奇的自然景色中。如《邊城》中的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只小獸物。人又那么乖,如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的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做了拳頭大丈夫的小媳婦”的蕭蕭“風里雨里過日子,象一株長在園角落不為人注意的蓖麻大枝大葉,日增茂盛。”;單純而又任性的三三則“苗條的如一根筍子”,而那如同姐姐一樣的阿黑就更是如此了,當五明“把笛子一吹,一匹鹿就跑來了。笛子還是繼續吹,鹿就呆在小子身邊睡下,聽笛子聲音醉人。來的這匹鹿有一雙小小的腳,一個長長的腰,一張黑黑的臉同一個紅紅的嘴。來的是阿黑。”這些或是明喻或是暗喻便使讀者在感受這些少女形象的同時,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了這些少女所生活的環境,而這環境卻不單是一種社會環境,更多的是一種自然環境。
這些少女不僅外貌形象上具有這種自然純凈之美,她們的行為及語言更是洋溢自然天真、和諧單純的美。當翠翠“平時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對她有所注意時,便把光光的眼睛瞅著那陌生人,作成隨時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但明白了人無心機后,就從從容容的在水邊玩耍了。”而三三在看到別人在釣她家邊小溪中的魚時,會毫不猶豫地沖那人喊道:“不行,這魚是我家潭里養的,你到下邊釣去罷。”她們天真可愛的行為及語言讓人清晰地感受到那種迥異于社會女性的自然的人性之美。這些少女“是一種生命的現象,是一種本能的和自然融會一體的氣質,是跟風、跟日、跟樹、跟綠水青山一樣的一種生命。”
這些少女身上具有的自然純凈之美與她們的生活環境必然戚戚相關,她們集中了湘西獨具特色的自然、民族、風土人情中最為優美的成分。然而這些體現著完美的人性之美的少女們其家庭卻是殘缺的。擁有著相似的命運,翠翠的父母慘死,三三在三五歲的時候死去了父親,蕭蕭和阿黑則從小沒了母親。她們在缺少一種人倫關懷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沒有了家庭的束縛與制約,她們的成長依然是快樂的,并沒有因為家庭的殘缺而變得陰暗沮喪,她們是“沒有沾染人世間的一切功利是非思想,與自然融為一體的境界,是不含渣滓純凈透明的世界。”這一切使得少女們在對待愛情的抉擇時也完全是出自一種生命的本能。翠翠愛上儺送,是被儺送開朗熱情樂于助人的品格和颯爽英姿所吸引,做了童養媳的蕭蕭冒著被沉潭或遠嫁的風險與花狗私合,并且生了孩子,這是她的自然欲求向傳統道德習俗的一次無意識的挑戰。其結果是這些天真無邪的少女獨自承受愛情的挫折所帶來的苦痛。她們對待這份苦痛與不幸卻沒有表現得大悲大痛,只是默默地承受著,似乎所有的苦痛都如大自然中的一場風雨一樣自然而和諧。在這些少女身上自始至終都洋溢著這種自然純凈的人性之美。
二.淳樸頑強的人性美
沈從文筆下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的鄉村婦女形象,這些鄉村婦女具備著中華民族勞動婦女的傳統美德:勤勞、節儉、善良、寬厚。如三三的母親楊太太,玉家菜園的玉太太,《泥涂》中的婦人等。這些婦女形象給讀者最大的印象便是辛勤地勞作。楊太太有自己的碾坊,玉太太則經營了二十畝菜園,不僅善于種菜,而且還能把白菜用各種方法制成不同風味的菜肴。這樣的勞動自然是艱辛的,但這些婦女絲毫沒有表現出對這種生活的抱怨,對生命的厭倦,反而愈加開朗樂觀,而這也正是沈從文想要表達和贊美的——堅強的意志和頑強的生命力。
從作品中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婦女們的命運是十分悲慘不幸的,她們有的失去了丈夫,如《三三》中三三的母親、《菜園》中的玉太太、《泥涂》中的婦人,有的則失去了子女,如《王嫂》中的王嫂,可見,她們同樣是生活在一種殘缺當中。但生活的殘酷無法澆滅她們對生命本體的渴望。她們通過辛勤的勞動把自己的理想追求寄托在家人身上,使自己的殘缺有了一種精神上的彌補,家人的幸福似乎就是她們畢生的事業。楊太太始終在碾坊勞作,用其特有的母性關懷哺育著三三;玉太太則憑靠經營菜地使兒子去北京讀書;《泥涂》中的婦人則靠辛勤的勞作來維持兒子的生命。她們用堅強的意志和樂觀的性格去面對自己生活的殘缺,體現出一種感人至深的頑強淳樸的人性之美。
沈從文在塑造這些婦女形象時,并沒有刻意去表現生活的艱辛、命運的不幸給這些婦女帶來的痛苦,而是側重對生活的正面謳歌,看到的是個人與社會融合的一面,人性中的自然性與社會性始終處于自在自適之中,并竭力表現這種和諧自適中的審美意趣。在作品中沈從文多從生命的角度,人性的標準去欣賞她們所表現出來的獨特的淳樸頑強的人性美,并且在欣賞的同時,對這些婦女表達出一種尊重、贊美和感激之情。
三.真摯熱烈的人性美
沈從文在其豐富的小說創作中,同時也塑造了一些妓女形象,在塑造妓女形象的過程中,對其身上體現出的獨特的人性美加以表現和贊美。
這些畸形女性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缺乏生活的自立能力,她們在非家庭狀態下的特有生存方式是賣身求生,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了妓女暗娼。“這種求生方式只屬于物質生存現象,不包含這類女性的精神屬性,即使她們的生存壓力使她們的身份帶有某些商品化的特征,但卻不帶有精神上的純物性特征。”她們的命運悲慘而凄苦,雖然做了妓女,她們決非金錢至上,她們同其他女性一樣,渴望源于生命本能的感情,并且努力誠懇地追求著。但逐漸變為畸形的情感。在表現上,也有其獨特的形式:《丈夫》中為生活所逼,被迫離開丈夫出來做妓女的老七,逢丈夫來探親時,既要招待客人,又怕冷落了丈夫。有時把丈夫的煙管同火鐮搶去,塞給一支“哈德門”,有時塞一小片冰糖在“丈夫口中”,并且記得丈夫的愛好,為其買了一把胡琴。而《柏子》中吊腳樓的婦人對桅子上唱歌的柏子的愛近乎是一種咒罵式的,看似潑辣蠻橫,實則愛的真摯濃烈。這些妓女的愛的方式不但不讓人反感斥責,反而同情其愛的辛酸和悲苦,不但沒有因其做了娼婦而感其淫蕩,反而讓人體會到她們身上放射出的一種人情美、人性美。
沈從文筆下的妓女形象,因其生活的畸形而導致其愛情的畸形,而這種畸形的愛情也正是她們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在表現上體現出一種獨特的熱烈而又真摯的人性美。沈從文在一種極為狂野粗獷、淳樸自然的鄉村氛圍中書寫著人性贊歌的另一種形態,作品中對河街妓女的生存方式根本不做倫理上的衡量,相反,她們身上所帶有的原始蠻性的情感與生命欲望,在作者的人文價值判斷中具有了審美意義,那便是情感的奔放與生命的莊嚴。在沈從文看來,她們的生命感和情感的非倫理性特征,正是構成了她們形象的“自然”屬性,體現成為極為真摯、熱情的人性美。她們的生活方式是違反傳統的道德觀念的,雖在封建思想頑固的社會形態下,也會受到世俗強烈的批判。但在沈從文筆下的湘西女性一種底層。因此,在分析沈從文筆下的妓女形象時,不應從道德的角度去評判,而是應從一個生命的角度去分析。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沈從文筆下的女性形象雖然都是生活在一種殘缺環境中,很顯然,沈從文正是要把這些女性的特殊的生存境遇與人的生命與環境的對立,人與環境的矛盾便突顯出來,成為人物生存發展所面臨的最大最直接的障礙,人物的命運便取決于對這種矛盾的解決上。但無論其命運如何發展,這些女性則始終洋溢著植根于湘西古老民族文化土壤的樸素的人性美,這種與自然相契合的獨特的精神氣質與人物的生存環境,性別年齡、命運發展相結合,便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人性之美
從沈從文大量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對女性的命運的探討一直是重要的主題之一。在沈從文的作品中,還塑造了一些上層社會的女性形象,如《都市一婦人》中將軍的遺孀,《紳士的太太》中的姨太太等。她們雖身處上層,衣冠楚楚,卻輕佻淺薄,極端的自私利己。這些庸俗虛偽的上層女性與質樸純潔的鄉村女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更加表現出湘西女性人性美的獨特和可貴。沈從文從人性的角度,以其獨特的審美眼光,對湘西女性加以理想化的描寫和由衷的贊美,使一系列鄉村女性各具形態,體現著沈從文獨特的審美感受。
(作者單位:牡丹江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