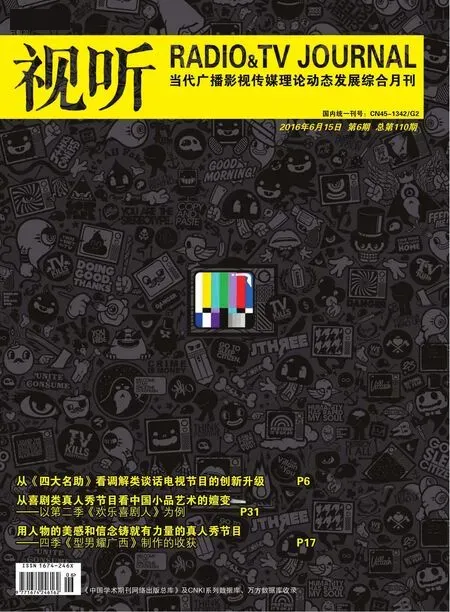影片《永生羊》獨具民族特色的意境美
□鄭潔
?
影片《永生羊》獨具民族特色的意境美
□鄭潔
摘要:《永生羊》是一部講述哈薩克族人民生活故事的電影,展現(xiàn)出民族文化與人民生活的密切關(guān)系,表達(dá)出影片獨有的民族心理與民族信仰的精神。本文圍繞民族特色的意境美,從借景抒情傳達(dá)意境,以實求虛、虛實結(jié)合,“景外之景”“象外之象”等三方面闡釋哈薩克族電影《永生羊》所帶來的意境美。
關(guān)鍵詞:永生羊;哈薩克族;民族特色;意境
電影中的意境主要體現(xiàn)為環(huán)境與人物的交融,在有限的場景中升華出無限高遠(yuǎn)而空靈的境界。在少數(shù)民族的電影中,哈薩克族題材電影與其他的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相比,數(shù)量不多,呈現(xiàn)的發(fā)展趨勢也是相對緩慢的,但通過以哈薩克族的民族特色為主體,展現(xiàn)其獨特的民族文化與生活,突出其所特有的民族心理與精神的影片卻是值得探索與思考的。
《永生羊》是一部哈薩克族的電影,改編于哈薩克族作家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的散文《永生羊》。影片中70%的敘述畫面是在后續(xù)改編劇本中新加進(jìn)去的故事內(nèi)容,將哈薩克民族傳統(tǒng)游牧的生活方式與影片中的情和新疆的美麗圣地喀納斯的景相融合。這種方式的表達(dá)更加突出了哈薩克族的思想性、地理性、民族性和傳奇性。影片是采用哈薩克語同期聲拍攝的彩色故事片,名為薩爾巴斯的綿羊由散文中的主人公轉(zhuǎn)變成一種線索性的電影敘事提示,一種抽象的“薩爾巴斯精神”,融民間信仰、民族儀式文化與生存哲學(xué)于一體。
一、借景抒情傳達(dá)意境
關(guān)于意境,情景說中強(qiáng)調(diào)的是景為情設(shè)、情因景觀、情景交融,情為主導(dǎo)敘事線索的明線,景則為不露斧鑿之痕的輔線。在《永生羊》這部影片中,男女之間的愛情是由草原大戶人家蘇丹的女兒烏拉庫巴將被強(qiáng)行許配給母親的娘家人為導(dǎo)火索,多情的烏拉庫巴不甘于自己的幸福被他人主導(dǎo),在追逐自由愛情的路途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挫折與磨難。就在烏庫巴拉走后的那一夜,夜襲的狼群咬死了很多只羊,其中也有那只曾經(jīng)被遺棄的弱生綿羊薩爾巴斯。這只被遺棄的弱生綿羊是人生命運的一種喻示,在喻指凱斯泰爾遭遇“無望之愛情”的難以承受之痛,同時也隱約預(yù)示了烏庫巴拉私奔后的坎坷命運。
這種景、情、人三者充分運用了自然環(huán)境的表現(xiàn)力,有機(jī)地將人物的思想情感交織在一起。情與景諧,物我情融,《永生羊》中意境的形成便是從“情景交融”開始,情在草原的景中,景在哈薩克族人的情中,景融入情,情里隱含著景,情景達(dá)到和諧統(tǒng)一。草原的遼闊無垠,注定給人的心中種下不羈的豪情,烏庫巴拉的為愛私奔以借景抒情來予以表達(dá)。雖然這一愛情觀在影片中以悲傷的結(jié)局而呈現(xiàn)出來,但卻將情景交融的意象顯現(xiàn)出來,借以展現(xiàn)哈薩克族女人不甘于被掌控的命運,讓人引發(fā)想象,揭示人生哲理,從而產(chǎn)生了較大的藝術(shù)魅力。電影意境就在某個特定的場景中被感知,營造出這個場景所要表達(dá)的真實意境。
二、以實求虛、虛實結(jié)合,呈現(xiàn)空靈跳蕩的電影影像
在《永生羊》的影像表達(dá)過程中,“羊的永生”通過一種以實求虛、虛實結(jié)合的方式,將哈薩克族人對生命輪回的尊重在諸多儀式的象征轉(zhuǎn)換里呈現(xiàn)出來。在哈薩克族人的生命中,生與死都是一種尊重,并都具有同等價值,所以,生就是死,死亦是一種生。只有在生死的等值中,羊才能夠永生。影片的敘事結(jié)構(gòu)并不是遵循時間的線性發(fā)展來布局的,而是在春、夏、秋、冬四次遷徙轉(zhuǎn)換牧場的空間結(jié)構(gòu)的銜接中體現(xiàn)出來的。
在春天里,當(dāng)哈力還為孩童時,牧場中獲得初生羊羔薩爾巴斯的喜悅之情,給人的感覺是暖心的。“孤兒”薩爾巴斯的到來是一種生命初始的象征。在夏天里,哈力在族人的見證下完成了成人禮,并祭羊獻(xiàn)神,此時象征著哈力的成長邁向新生,同時發(fā)生的還有烏庫巴拉與花旗王阿赫泰私奔,薩爾巴斯被狼咬死的事件。在秋天的牧場里,新寡烏拉庫巴被花旗家族驅(qū)逐并實施水罰,奶奶莎拉救下烏拉庫巴,并撮合她改嫁叔叔凱爾斯泰。烏拉庫巴在奶奶的施救下雖獲得重生,但失去了照顧兩個孩子的資格。冬季里的牧場是艱難的,哈力與叔叔凱爾斯泰共同救下了另一只新生的薩爾巴斯,并殺死了一只凍僵了的母羊來獻(xiàn)祭。獲救的薩爾巴斯被烏庫巴拉出于母愛之情悉心照料,烏庫巴拉不畏懼暴風(fēng)驟雪尋找羊奶。冬去春來,隨著四季的輪回,奶奶也離開人世,哈力成家育子,殺羊獻(xiàn)祭。在哈薩克族人中,生與死都是絕對價值的,它們之間是不存在分離的,生的存在是現(xiàn)實生活中的喜悅,死亦是一種道德的完善。在電影的輪回轉(zhuǎn)場中,多次出現(xiàn)獻(xiàn)祭的形式,如影片開始時巖畫上再現(xiàn)這一儀式。哈力成長儀式上,在族長的主持下,凱爾斯泰實施獻(xiàn)祭;路遇凍死的綿羊,哈力與凱爾斯泰再次實行了獻(xiàn)祭;奶奶沙拉去世時,哈力實施了羊的獻(xiàn)祭。一次次的獻(xiàn)祭中,都少不了一句關(guān)鍵話,即祭祀秘語:“你死不為受罪,我生不為挨餓,原諒我們”。
當(dāng)一個民族對一種物的重視程度遠(yuǎn)遠(yuǎn)超過常態(tài)的對待,那么這種物也就是這個民族特有的代碼,就會給他者帶來視覺的沖擊力。“永生羊”的永生在獻(xiàn)祭的過程中,實現(xiàn)了一種人與羊的生死交換。影片通過提供“實”的信息,使觀眾展開聯(lián)想和想象,感受到哈薩克族人把人與羊的地位等同,實現(xiàn)了人羊集體被認(rèn)同的關(guān)系。羊成為替代人的一種物體,也是生命輪回的一種象征。
影片中一些空鏡頭的呈現(xiàn)也是一種意境的表達(dá),精神時空都超越了一般時空,喻示著人的情感體驗和人的生命歷程。草原的美景,可以說是美不勝收,藍(lán)天、白云、蒙古包、連綿的青翠山峰,如畫如詩。這些具有代表性的景色的呈現(xiàn),進(jìn)一步抒發(fā)了民族特色的人物表達(dá)和創(chuàng)作者的主觀感受,實際上包含了創(chuàng)作者想要表達(dá)的一種人生感悟,同時更體現(xiàn)一種中國民族特色文藝所追求的獨有、空靈、跳動的意境之美。
三、“景外之景”“象外之象”探尋銀幕視像之外
電影創(chuàng)作者創(chuàng)造出意境,在抒發(fā)自身獨特審美情懷的同時,也將創(chuàng)作視角指向未來的接受者,也必將引起接受主體的聯(lián)想。接受主體通過對空白的填補(bǔ)與創(chuàng)造,與創(chuàng)作主體進(jìn)行著心靈的對話,同時也創(chuàng)造、延伸和擴(kuò)展了“空白”,從而獲得“韻外之致”“味外之旨”。
影片通過一種“虛實相生”的方式接通有限與無限。具有生命價值的個體存活的時間是有限的,而在自然中生命的綿延是一種無限的輪回。對于草原土著的哈薩克族人而言,草原不僅僅是一種供給他們生養(yǎng)的自然環(huán)境,更多的是賦予了一種生命的象征,羊、駱駝、馬并不是作為物化財產(chǎn)歸屬于人類,它們早就和草原上的人們成為親人、家族和部落,人與草原真正的關(guān)系是密不可分的。在草原上,動物對于生命的的意識影響著游牧民族哈薩克人對生命意義的思考,面對困惑、面對傷感、面對自己的認(rèn)識,通過影片中的“景外之景”“象外之象”,抒發(fā)他們對于整個人生的感受和理性的思考。在描繪具體的情與景之外,構(gòu)成了一個令人馳騁遐想、回味無窮的藝術(shù)空間,象征了一種難以用語言文字表達(dá)的心靈境界和精神志趣,創(chuàng)造出一個似有實無、似無實有、若有如無、亦有亦無、有無相生的境界。
意境是由景與情、形與神、意與象、思與境等因素構(gòu)成的,不是對應(yīng)于片中實景實物孤立的表層意義,而是來自影片的整體情景、結(jié)構(gòu)、氣勢、手法和語言,透露著影片的整體審美效果,是一種“整體質(zhì)”。在作品中,只有當(dāng)那些因素有機(jī)統(tǒng)一為一個整體時,才能表現(xiàn)出特定的意境。《永生羊》這部影片所具備的意境是民族化的色彩,作為我國首部的哈薩克語同期聲彩色故事片,更深刻地展示出哈薩克族基于自身特定的歷史文化和宗教民俗而表達(dá)出的生命體驗和生存哲學(xué),獨有地勾勒出人文新疆的形象。
四、結(jié)語
通過敘述的推進(jìn),創(chuàng)作者將紛繁復(fù)雜的要素緊密地連接在一起,觀眾借助完整的故事情節(jié)體會影片所表現(xiàn)的生命意義、生命哲學(xué)與生命輪回。當(dāng)今時代,人們都在探尋人生的意義和人生的終極價值指向。《永生羊》在尊重藝術(shù)文化的主題選擇前提下,充分呈現(xiàn)了民族文化的豐富性,促進(jìn)了民族文化的迅速發(fā)展,達(dá)到了較高的文化層次方向,是獨特的具有少數(shù)民族文化特色意境美的影視作品。
參考文獻(xiàn):
1.宇波彰.影像化的現(xiàn)代——語言與影像的符號學(xué)[M].成都: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2014.
2.馮嶺.多種文化視角下的影視創(chuàng)作批評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4.
3.鄒贊.“羊”的邊緣書寫與民族風(fēng)情敘事——讀解電影《永生羊》[J].藝術(shù)評論,2012(8).
4.胡靜,張劉婷,夏小花.新世紀(jì)新疆哈薩克題材電影的區(qū)域形象建構(gòu)與傳播策略[J].名作欣賞,2014(6).
5.張冬.簡論電影敘事與意境美[J].牡丹江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4(1).
(作者系河南大學(xué)新聞與傳播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