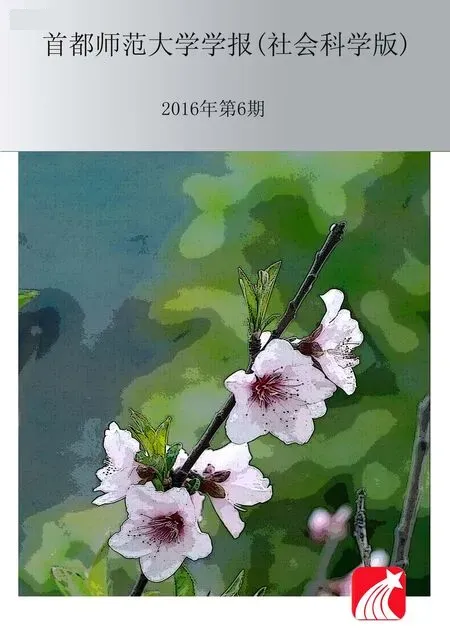緬懷齊世榮先生
李華瑞
一、我與齊先生的交往
2014年10月6日,學校舉行建校60 周年慶典,齊世榮先生代表見證學校六十年成長歷程的老教授發言,先生講話言簡意賅,情深誼長,思維之清晰、聲音之洪亮實令人難以想象是一位88歲高齡的老人在講話。然而真是歲月無情,僅僅過去了一年多時間,先生竟遽歸道山,留下了幾多哀婉,令人心痛。
我雖不是齊先生的學生,現在從事的專業也不是世界史,但是知曉齊先生的大名還是比較早。我在讀本科階段比較偏好世界史,四年級的畢業論文選題就是齊先生的強項:二戰前英國的綏靖政策,做論文時也翻閱過齊先生的相關大作。可是當時英語學得不好,加之當時世界史碩士點很少,于是臨考研究生階段放棄了世界史,而改考宋史。后來知道齊先生很早就帶世界史碩士、博士,還曾幻想如果當年能考上齊先生的碩士,也許我的專業道路會是另一番景象。
第一次見到齊先生是1991年六七月間,漆俠師與鄧廣銘先生在北京主辦國際宋史研討會,在籌辦會議間歇,漆俠師帶領我們一行四人,到北京師院看望于善瑞校長。于善瑞是民國風云人物于鳳至的侄女,1983年至1990年在河北大學任校長,從校長位置退下來后,于善瑞校長要去美國與親人團聚,作為過度于校長被安置在北京師院任副校長。當時北京師院的校長就是齊世榮先生。漆俠師在北京師院有好幾位朋友:戚國淦、謝承仁、寧可和齊世榮。那天于校長個人招待我們,于校長也告知了齊先生和謝先生,齊先生因公務繁忙在會客室只坐了十分鐘就告辭了。在席間,于善瑞校長講起她剛到北京師院上任,當齊世榮先生得知她來自河北大學,就向她問及漆俠師的近況,于校長說你們做的不是同一專業還很熟嗎?齊先生說我們認識很早,然后齊先生說我不僅認識漆俠,還相當了解他:“漆俠,學問好,脾氣大”,于校長聽后感慨“您真是了解漆俠先生”。漆俠師聽到于校長講到這很高興,很認同齊先生對自己的六字評語,而后笑著對于校長說齊世榮是以他的特點說我,“他也是學問好,脾氣大”。今年1月16日在齊先生追思會上,聽到來自齊先生的好友、同事、學生對齊先生性格特征的描述,我感到齊先生與漆俠師有太多相似的地方,剛正不阿,正義凜然,耿直率真,豪放幽默,對后進和學生愛護有加。而且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治史方面也是有共同的堅定信仰和學術操守。
再次見到齊先生已過了10年,2001年4月下旬,我第一次代表河北參加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評審會議,那時的中國史評委都是戴逸、李文海、林甘泉、張豈之、劉家和、陳高華、隗瀛濤等著名學者,在會上見到齊先生,齊先生當時是世界史的召集人。評審會在京西賓館,早飯后評委們大多都在賓館大院內散步,我瞅準時間近距離接觸齊先生,自報家門,并提及1991年曾見過先生,齊先生重提漆俠師“學問好,脾氣大”的話題,說漆俠師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很高,希望我好好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2002年再次參加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評審會時,齊先生見到我主動向我詢問漆俠師病逝的情況。2001年11月2日,漆俠師為緩解哮喘輸液,因保定庸醫給藥不當而突然仙逝,當時曾震驚國內史學界。我給齊先生仔細講了漆俠師病逝的經過,齊先生一再表示嘆惋。這年五月參加中國史學會與云南大學舉辦的“21世紀中國歷史學展望學術研討會”,又見到齊世榮和寧可先生。齊先生發言強調新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治史的重要性,聲音洪亮,氣場很大,所以印象深刻。
2003年以后社科規劃辦規定連續擔任三屆和年過75歲的老評委就不再擔任。那年徐藍教授被特邀參加評審會,方知道她是齊先生的高足,這是我與徐藍教授第一次見面,但我們只是互相詢問過后再沒有交談,后來到首都師大工作才知徐藍教授很健談。
2003年底,我因內子家庭的原因準備調入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后得到寧可先生的支持。歷史系主任宋杰兄讓我在2004年四月下旬到系里試講,試講包括兩部分,一是給系里老師和同學上一節課,二是給系學術委員會做一次學術報告,都限定在半小時之內。那天給學術委員會作報告,齊先生和寧先生都在場,我做了一個“改革開放以來宋史研究進展”的報告。齊先生聽后問我為什么沒有介紹日本和臺灣的宋史研究狀況,我說時間不夠,齊先生說日本和臺灣的宋史研究水平很高,我當時很驚訝,齊先生的確不愧是大家,世界史做得好,對中國斷代史研究狀況也很熟悉。這讓我想起了坊間所傳齊先生提倡做世界史要關心中國史研究的消息,看來齊先生是身體力行。
2004年調入首師大后,雖然齊先生已很少招學生,到系里來的次數也不算多,加之我也不常去系里,除了到齊先生在師大校園的住家專門拜訪過兩次,實際上見齊先生的機會并不多。但先生一直沒有忘記我,先生每次出版新作都會簽名送我一本,先后收到先生贈送的有《20世紀的歷史巨變》《世界史探研》《15世紀以來世界九強興衰史》《史料五講》以及譯作《蒙古近代史綱》。我自己出的書《唐宋變革論的由來與發展》《視野、社會與人物》《宋代救荒史稿》也贈送齊先生指教。
說來有點慚愧,2007年齊先生主編教育部的部編初中歷史教材,請瞿林東先生主持中國史的編纂工作,雖然是初中教材,齊先生要求各斷代要有優秀學者親自執筆。一天,瞿先生給我打電話說,齊先生親自點名初中教材宋元部分由我來執筆。我當時聽了很感動,這不僅是對我的專業業務能力的充分肯定,也是對我的信任。我欣然接受了任務,可是我從未編過初中歷史教材,一接手才發現要寫好初中教材其實不容易,不僅要求內容準確、史實無誤,而且語言要生動,不能太學究氣。我在寫作過程中覺得絲毫不比做一篇論文容易,幸虧有葉小兵先生幫助潤色才勉強交稿。追思會上許多老師都提到齊先生編寫大學、中學教材是有很崇高的社會責任感的,參與這次編寫工作也算是有所體悟。
二、齊先生對《學報》的關愛和支持
2012年7月,學校調我任《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主編及編輯部主任。到學報工作以后,曾專門給齊先生打電話致意,請先生賜稿支持學報。那天電話打了半個多小時,具體內容已記不清了,但有兩點印象很深:一是先生強調刊發的文章要言之有物,有創意,讀者愿意看;二是校對要精,一定要避免出現低級的硬傷錯誤。其實,齊先生一向對學報工作特別重視,先生在《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5期撰文祝賀學報創刊20 周年《艱難的歷程——從〈文史教學〉到〈首都師范大學學報〉》,在這篇文章中齊先生對于學報的發展作了簡要的回顧,實際這是一段很珍貴的學報發展史料:
《首都師范大學學報》于1974年正式出版(當時名《北京師范學院學報》),到今天已經二十周年了。二十年來,我們刊登了一大批文章,其中一些是很有分量的文章,在讀者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為已經取得的成績感到高興的同時,我不由得想起創業的艱難。我校是在1954年創建的。建院初期,從領導到一般教師,都有人忽視科學研究,甚至認為積極搞科學研究的教師是在走白專道路。但那時也有一些有志于科學研究的中青年教師,對這種現象很憂慮,覺得長此下去,不僅科學研究本身將被埋沒,而且教學質量也會日益下降。1958年,借著“大躍進”的機會,劉國盈同志(時任中文系總支書記)和我(時任歷史系總支書記)冒著被戴上“走白專道路”的帽子的危險,一而再、再而三地找當時的院領導鮑成吉同志,建議辦一份學報。領導上認為時機尚不成熟,但允許先辦一份內部發行的刊物。事情總算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劉國盈同志和我決定先辦一份《文史教學》,由中文系的廖仲安同志負責中國語言文學稿件的編輯,歷史系的謝承仁同志負責歷史稿件的編輯。在沒有一個專職人員的條件下,《文史教學》上馬了,一共辦了三期,我校的名譽教授、著名明史專家吳晗先生還熱情地投了稿。不料,1959年形勢一變,許多刊物下馬,我們這份好不容易爭來的刊物也就短命夭折了。1974年,終于有了公開出版的《北京師范學院學報》,但十幾年的寶貴光陰已經浪費掉了。
齊先生在文后對學報提出了殷切期望:“科學研究貴在有創造性,我們一定要努力做到‘唯陳言之務去’,對于那些了無新意的文章千萬不要登。我祝愿,我也相信,《首都師范大學學報》將會辦得越來越好,成為讀者喜歡保存的一份刊物。”我想齊先生的殷切期望和教誨對于今天辦好刊物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一定將“對于那些了無新意的文章千萬不要登”的警語作為辦刊的宗旨。
2014年,學校迎來建校六十周年,學報也迎來了創刊四十周年的紀念,在此之前我打電話給齊先生約請他給學報寫一篇紀念文章,齊先生欣然答應,題為《再接再厲,不矜不限——祝〈首都師范大學學報〉創刊四十周年》,再次回顧了學報的發展歷程,并在文后附記:“北京師范學院創辦的1954年,我即來校任教,當時才28歲。明年2014年建校60 周年,我已是88歲的老人了。今年是學報創刊40 周年,學報要我寫一篇紀念文章,作為一個老員工,義不容辭。但耄耋之年,體腦兼衰,實不成文,姑以應命,尚希見諒。”看到齊先生的附記,很是感動,那種關愛之情溢于言表。
齊先生先后發表在學報的文章初步統計是15 篇,追思會上《世界歷史》編輯回憶說齊先生發表在《世界歷史》有14 篇文章,看來齊先生一生在《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發表的文章最多。齊先生晚年德高望重,他的論文是很多刊物求之不得的,但是齊先生把晚年最有心得的幾篇文章交給了學報,最近新出的《史料五講》中的后三篇《談小說的史料價值》《談日記的史料價值》《談私人信函的史料價值》都交給了學報發表,這是對學報的莫大支持。齊先生的《史料五講》結集出版后,在史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瞿林東先生與他的學生從史學史的角度敏銳的觀察到齊先生大作的學術價值,并撰文給以很高的評價,瞿先生也把文章發給了我們,這是一段頗有意蘊的唱酬佳話。
齊先生最后一篇文章《中國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也交給了學報。2015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在家里突然接到齊先生的電話,先生說,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他寫了一篇論文問能不能用。我回答說您發給我們,我們隨時給您留著版面。先生又說現在還不能給,他要看看習總書記在9月3日紀念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的講話,看看自己的論述與習總書記的講話精神是否有沖突。我說好,那就讓歷史編輯杜平隨時與您聯系。對于齊先生的慎重,我覺得是具有高度政治責任感的反映,也是一個老黨員應持有的立場。追思會上有幾位學者都談到世界現代史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現實性,歷史問題往往與政治問題綰結在一起,齊先生總是能正確處理學術與政治的關系。其實齊先生是最早系統闡述中國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貢獻和地位的權威專家,齊先生之所以慎重是他多年養成的風格,無論何時都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9月20號左右杜平從齊先生家里取到手稿,連夜打出來發給我,我讀后頓感大氣磅礴,擲地有聲。如果不是先生發病住院,我們本應在2015年第五期發出來,齊先生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大作。可是齊先生發病住院,先生又極其認真,一定要親自核校杜平打的稿件,一再延遲付梓。起初杜平問我是否請齊先生的女兒代為核校和簽字,但是我知道齊先生的脾性,堅持由齊先生簽字認可,所以一直到十月中旬齊先生昏迷過去,才由葉小兵教授代為核校,由齊先生的女兒齊衛華女士代為簽字。我之所以這樣做,除了知道先生的認真和嚴謹外,還基于2014年10月看到先生那樣硬朗地參加學校建校六十周年慶典時表現出的精神狀態,覺得先生能夠挺過這次發病,然而人算不如天算,2015年12月3號凌晨齊先生就離開了我們,先生在學報上發表的文章也成了他最后的遺作。
我們一定銘記先生的教導,辦好刊物,以實際行動紀念我們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