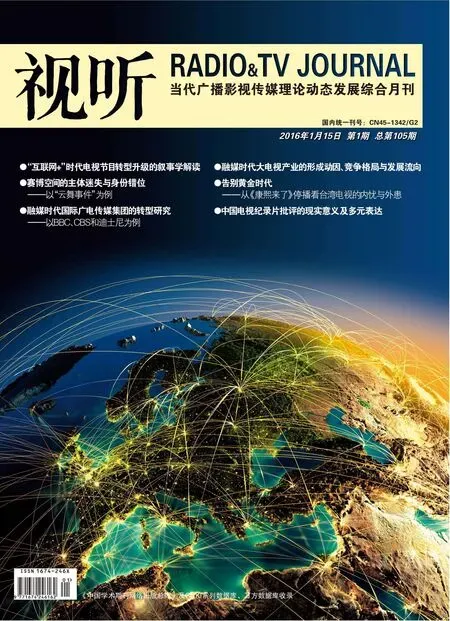賽博空間的主體迷失與身份錯位——以“云舞事件”為例
□賴黎捷 衛彥瑾
?
賽博空間的主體迷失與身份錯位——以“云舞事件”為例
□賴黎捷衛彥瑾
摘要:在以互聯網為主體的賽博空間里,人的主體性意義被賦予了虛擬化色彩。真實交往與虛擬世界的身份邊界被打破和消解。本文以江西省鷹潭鐵路醫院33歲女護士方某自殺,引發的關于“云舞事件”的探討為著力點,分析了“云舞”在經歷現實生活坍塌與虛擬化身的重建過程中,呈現出的行為動機與心理軌跡。“云舞”在沉溺虛擬/擬態/仿像世界完美形象的建構中,僭越了觸手可及的現實生活的種種邊界,理想與現實的對峙與沖突加劇了主體迷失與身份錯位,最后走向精神斷裂。
關鍵詞:云舞事件;賽博空間;主體迷失;身份錯位
2015年9月21日,江西省鷹潭鐵路醫院33歲女護士方某被發現在宿舍自殺。據鑒定,方某系自殺,死因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時間為17日凌晨。隨著消息的發布,事件引發網絡熱議。百度貼吧、大連某高校貼吧、天涯論壇、鐵血社區等均有大量網友參與,而在新浪微博,截至10月8日17時,“男獲遺產后分手女輕生”話題閱讀量高達268萬次①。方某生前是網絡游戲《夢幻西游》江西區女兒村排名前三的高手,同時也是一個游戲直播平臺的音頻女主播,擁有數十萬粉絲,網名“夢幻云舞”。方某在網絡空間的男友也因其自殺事件與之密切相關而遭到“人肉搜索”。這場被廣泛關注的事件被稱作“云舞事件”。
在新媒體甚囂塵上之際,以互聯網為主體的賽博空間呈現出了多元化、異質性、虛擬狀的特征。在這個空間里,個體的主體建構和身份認同充滿著無限可能,自我在網絡空間變動不居的場景中得以重新塑型。與此同時,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身份邊界被打破和消解,網絡空間正在建構一種新的“現實世界”。在轉型期社會變革語境下,青年網民群體如何建構多重自我,如何應對瞬息萬變、碎片化的網絡空間,是否面臨網絡空間的主體迷失與身份錯位,日益成為無可回避的重要問題。本文以“云舞事件”為例,對上述問題作一探討。
一、現實自我的坍塌與虛擬化身的重建
“云舞”的死亡跟職業無關,與她的網絡經歷息息相關。在現實空間里,她是一名護士;在賽博空間里,她是《夢幻西游2》游戲的玩家。現實空間與虛擬空間身份的差異可以說是導致“云舞”自殺的一個重要因素。
(一)現實自我的坍塌
學者麥基卓、黃煥祥曾將自我劃分為真實我、理想我和現實我。真實我指嬰兒的基本天性和人格特征,包括個人生命的所有潛力。但在成長過程中,為了取悅父母,必須修正自己的行為,背離真實我,于是形成了理想我,即可以得到接納和認可的自我。在大多數情況下,真實我的欲望必須屈服于理想我的要求,二者達成某種妥協,發展為現實我。人的成長,充滿了遺棄真實我而產生的自我憎恨,會累積越來越多的負面情緒,感到空虛無助,即本體焦慮。
現實的境遇使“云舞”離心目中的自我越來越遠。兒時的“云舞”喜歡獨自埋頭畫畫,同學們給她取了個外號“鴕鳥”。也喜歡熱鬧,好客,和男同學嬉戲,邀同學到家里一起做作業,把自己的畫作贈予他人。這一階段的自我是安靜的、熱情的,是陽光、外向、有才氣、專注的。
然而,隨著歲月推移,“云舞”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境遇又讓她不得不面對另一個自我:家境平常,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父親罹患癌癥,早早去世,母親沒有工作。這一自我不僅讓她孤獨、自卑,而且給她的心理制造了諸多的壓力。特別是父親去世后,沒有了父親庇護,加上母親對她的警惕設防又寄予重責,使她壓力倍增。從“云舞”和同學的交流中可知,她的理想自我的定位是趨近于父親的,性格和善,淡泊功利。“云舞”工作單位和所在城市平淡無奇的狀況也令她對現實極度失望:醫院、食堂、宿舍三點一線的生活,稀少的病患。這種狀況的高度確定性、趨于一成不變加劇了“云舞”的本體焦慮,即現實我與理想我的距離不斷加大,使主體感到強烈的失落與恐懼。
現實自我的持續惡化,終于隨著父親的離世轟然坍塌。父親的離世使“云舞”感到現實空間中的孤立無援:她拿著電話卡到醫院一樓大廳外的IC電話上撥通了一個個親戚、長輩和朋友們的號碼,一個個地說“我爸爸去了,麻煩來一下醫院”。接到電話,有人會安慰她,“別太傷心了”,也有人只是說,“好,馬上來”。母親幾乎崩潰,總是“怪她不爭氣不上進”,對她警惕設防,云舞自己描述道:“想盡可能地從我這里搜集錢,老了就可以不用擔心我不養她”。心臟病犯了,難受得昏天暗地,也不愿告訴母親,因為她“不了解我需要什么,胡亂強加給予”②。從這些描述不難看出,現實空間里的“云舞”,缺乏親朋好友的關愛,母親在自我定位上又與之截然對立。在現實空間里,“云舞”是孤立無援、不被人愛護和理解的。
此后的十年,一面是網絡空間里虛擬化身的輝煌熱鬧,一面是現實空間里加劇的孤獨與焦慮,“云舞”試圖用虛擬的自我替代現實空間里坍塌的自我。
(二)虛擬化身的重建
所謂虛擬化身,我們可以理解為在虛擬空間或者虛擬場景中將主體意識投射到虛擬角色中,摒棄現實我,重構新自我,將理想的自我形象投射到虛擬空間的生活、工作、戀愛等虛擬行為中。在以互聯網為主體的賽博情境中,“云舞”通過編制一套極具表演性、戲劇性的符碼,試圖打造一個擬象化、理想化的自我,彌補現實生活中的種種缺憾,從而追尋馬斯洛心理需求理論所指涉的最高層次的自我價值實現。
美國學者歐文·戈夫曼認為,我們的日常生活處處粘附著表演痕跡,無論是休息棲居,還是日常對話,都是“向他人呈現我們自己”的一種表演行為。“表演就是圖謀顯示出他的精神、力量以及其他的各種優良的特性。”③在互聯網世界里,“云舞”試圖通過嫻熟運用游戲這一表演形式,展示其優秀品質,成為游戲/虛擬世界的焦點人物。她不僅建立了理想中的社交圈,而且出類拔萃,成為眾人追捧的女神。現實空間中的社交活動對她的吸引力遠遠不及網絡空間,玩網絡游戲成為她重要的生活部分。大伙聚餐,她早早離去,理由是參加“幫戰”。所謂幫戰就是在《夢幻西游2》里,每周五、周六、周日晚上固定的項目,是由系統隨機分配,兩個幫派之間進行的對戰。
每一場表演,都離不開“前臺”的支撐。戈夫曼認為,“前臺是個體在表演期間有意無意使用的、標準的表達性準備”④。前臺是表演的聚集地和展示場所。在“云舞”的表演過程中,《夢幻西游2》無疑就是她完成展示表演的“前臺”。《夢幻西游2》是一款時下流行的網絡游戲,是基于互聯網平臺、支持多人在線、每個游戲參與者都可以通過控制游戲中的虛擬身份而相互溝通、相互影響的虛擬數字社會的體驗過程⑤。操作很簡單,玩家只需無限重復一個點鼠標的動作,跟隨游戲情節設置,獨自或組團隊打怪升級做一系列的任務。游戲中還可以與其他玩家語音聊天,互動交流。玩游戲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玩游戲,在這其中,現實世界里的友情、愛情、煩惱、快樂等,都仿真地得以再現。正是這樣一個“前臺”,成為了“云舞”自父親去世后的十年陪伴。在網絡游戲中的虛擬交流活動逐漸代替了她在現實中的社交活動,在網絡游戲中的社交圈也漸漸取代了現實中的社交圈。
在游戲的表演中,“云舞”獲得一種現實生活無法得以實現的替代性滿足,建構一個迥異于真實世界的理想化的“虛擬自我”。她不再是三點一線的普通護士,而是一位穿戴奢華、實力強大的美麗女子。她的錦衣奢華靡麗,由30個“彩果”染色而成;她的級別已經達到頂級,是175級;她的寵物也是優質寵物:“粉色泡泡”;她的所有技能也都是滿級。“云舞”的自我在這里得以完美重建:才華橫溢,光鮮亮麗,受人尊崇。
網絡游戲具有虛假性表演,不僅為用戶提供虛擬場域,而且為受眾賦權,令其在其中重拾話語權。在米歇爾·福柯看來,話語權具有較強的權力意味,它是權力的一種象征和符號。而在自媒體時代,話語權逐漸下移,人人都可以成為話語傳播者。在游戲世界里,“云舞”不僅可以自由支配游戲裝備,而且還可以選擇現實生活難以滿足的“虛擬婚姻”。游戲中設置有“結婚”這項虛擬制度,抬花轎、新人拜堂、賓客致禮、發放喜糖等現實生活的各種儀式植入了互聯網精神,甚至連生孩子、過日子,都可以虛擬化。起初的云舞是審慎而理性的,在游戲里堅持單身多年。她在QQ上曾掛過這樣一句簽名:“網絡太近,現實太遠。實在不適合投放太多情感”。2013年底“云舞”在游戲中結識了角色名為“附送折磨”(以下簡稱“折磨”)的男子。“折磨”加入了云舞所在的團隊,與她一起在團隊里執行各種任務。2014年“云舞”在一個擁有數十萬粉絲的游戲直播平臺中擔任女主播,“折磨”開始在直播平臺觀看“云舞”的直播,并為她刷虛擬禮物示好。甚至把自己的名字改為“云舞的小甜心”。漸漸熟悉之后,二人感情升溫在游戲里結婚。“婚后”在該游戲的服務器上,二人更是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游戲,并肩作戰,佳績連連,成為游戲里為人稱道的“實力派夫婦”。這時“云舞”的心態發生了轉變,把所有的感情都傾注在了虛擬世界里。“云舞”在網絡游戲中重建了一個理想我,即實現其關于自我的諸種想象與理想的我:富有才氣,受人尊敬和追隨,終得如意伴侶。
二、超媒體自我及其對現實世界的僭越
現實生活的壓抑與無奈促使“云舞”轉向網絡空間。網絡空間中理想自我的建構不僅重塑了自我,而且重構了生活方式。虛擬的化身與虛擬的生活方式促成了超媒體自我幻象的“完美現實”,這一幻象替代了現實空間的虛空,并漸居主導,僭越了現實世界。
(一)超媒體自我的建構
游戲是人類自兒時起認識自我、建構自我的一種重要方式。游戲將現實同化于活動本身。按照心理學家皮亞杰的劃分,網絡游戲屬于象征性游戲。象征性游戲具有把真實的東西轉變成人們所想要的東西,從而使自我得到滿足的功能。互聯網是虛擬性的完美表現。互聯網具有多線程技術特征,由此它在時間上可以不同步,在空間上可以無限拓展。借助互聯網,人們可以選擇性地進行多維展示,由此建構具有無限可能性、開放性的超媒體自我。互聯網對于用戶而言,主要是為了進行符號交換和自我表現,盡管具有虛擬性,但是它確實具有特殊的現實效應。這些用來展示自我的符號可以與其指示物完全分離開來,用鮑德里亞的術語,它們都是擬像,是沒有原作的拷貝。在互聯網的虛擬世界中,人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程度而不是現實所是)“變成任何你想充當的人”⑥。這樣,人們仿佛逃避了現實世界的所有沖突。
法國社會學家讓·鮑德里亞認為,我們生活的世界正在進行著一場前所未有的消費運動,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滿著消費性。消費本身是一種自主性的體現。這種自主性的實現“通過景觀、表演、生活、自戀的循環,將自我生活與媒體景觀融為一體,建構以自我為中心的獨特理解圖示。”⑦“云舞”通過網游消費,將游戲表征、生活模式以及虛擬自戀融為一體,開啟了集榮耀、理想、虛幻于一體的自我建構模式。“云舞”將自我的故事置入網絡游戲的新語境中,并與現實境遇相融合,生成關于自我的擬像,并把自己與其化身的虛擬品質相認同。虛擬身份的建構實際上是對主體所擁有的各種資源的選擇和重組。現實中某些被隱匿的身份資源在虛擬身份的建構中成為核心資源。在現實生活里,“云舞”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護士,低調,離群索居,其甜美的歌喉、頑強的競技精神和團隊合作中的指導才能在病患甚少的急診崗位上難以發揮,而在虛擬身份中,這些資源得以發揮。“云舞”憑著甜美的嗓音在比賽中脫穎而出,被聘為《夢幻西游》江西區唯一一位官方主播,向廣大玩家傳授各種玩法。每晚八點,《夢幻西游》的游戲直播平臺上,許多粉絲都靜候著她的聲音。她成了網絡世界的明星,受人追捧。
在網絡游戲中,玩家與其他角色處于同一時空的感受被強化,并進而表現為強烈的虛擬社群歸屬感。在現實世界里,“云舞”的社交圈幾近空白。在虛擬世界中,“云舞”熱衷于幫派戰爭,與幫派玩家一起執行各種任務,共同遵守幫規。在幫派中,“云舞”處于管理高層,有著較高的地位和較多的追隨者。幫主南宮還是她無話不說的閨蜜。單身、喪父、不受關注等現實生活中的種種不如意被隱匿或者過濾。甜美的愛情、完美的婚姻、高級的裝備、高超的玩法、甜美的嗓音、批量的粉絲等,這些聚合了“云舞”關于理想我的種種元素建構了其超媒體自我擬像,并在“云舞”的生活中占據了重要位置,日漸取代現實生活中的真實自我。
(二)虛擬空間僭越現實世界
借助互聯網建構的超媒體自我實際上是一種擬像。在此意義上,身份變成了一種空虛的構造,因為在表現身份的符號系統背后不存在任何東西。這種符號過程與自我故事的生成語境是日益分離的。因為把故事重新置入新的語境中正是互聯網的典型特征。⑧
起始,她保持著現實和虛擬的平行,但漸漸虛擬空間逐漸與現實世界交叉融合,進而僭越了現實世界。在寫給表哥的遺書中,“云舞”寫道:“媽媽去世后,一直是他(玩家‘折磨’)陪著我,鼓勵我堅強,可我還是做不到,但我很感激遇到他,才讓我堅持了這么久”。網絡空間中的“相公”在“云舞”心目中履行了真實丈夫和朋友的職責。她將幾乎全部的情感和付出投入到虛擬空間。
“云舞”喜歡打簡簡單單的小怪獸,并以此賺取游戲幣和游戲道具、裝備。運氣好的時候,一個月賣道具裝備能賺一兩千塊。這跟她在現實中的工資相差無幾。虛擬空間帶來的現實感和實實在在的收入使“云舞”將兩個空間逐漸混為一體。她的好友“南宮”發現,“云舞”玩游戲的心態發生了變化,目的性越來越強,一個人開了5個號,“天天都在拼命打,把得來的東西賣錢,把賺的錢都打進那個男的賬戶”(即“折磨”,她在虛擬空間中的夫君)。
雖然游戲身份是虛擬的,但玩家的主體意志卻是真實的。持續推進的虛擬場景的設置和高仿真的人際交往使游戲主體的行為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云舞”在游戲中的行為與現實中的行為風格日趨一致。盡管在網絡游戲中,結婚可以轟轟烈烈,設置有抬花轎、新人拜堂、賓客致禮、發喜糖等隆重的儀式,也可通知好友前往觀禮,但是“云舞”與“折磨”的網絡婚姻選擇了低調和悄無聲息。熟識其為人的幫友意識到,她可能將此婚姻視同現實婚姻了。
不僅如此,虛擬空間甚至僭越了現實空間。當“折磨”提出與“云舞”分手后,“云舞”向單位請了半個月的假,飛往大連,提出要和吳青(“折磨”的真名)再見一面,“想知道當初到底是發生了什么事情,我覺得我有權利、有資格知道這些。”“云舞”不顧請假誤工帶來的損失,用現實世界的行為解決虛擬空間的沖突,已經將虛擬空間的種種置于現實世界之上。在大連的半個月里,二人度過了短暫的情侶般的小日子,這令“云舞”加劇了對愛情和婚姻的想象和夢幻。她選擇了虛擬空間表達這種認同:七夕節那天,在劍俠情緣里為“折磨”放了“一個海誓山盟的煙花”。她用這種情侶間在游戲里表達愛意的道具,將其愛情展示給游戲中的玩家而不是現實中的親友。
虛擬身份并非無條件和完全虛空的,也有其內在的實現機制,依托于主體表現來自現實世界的真實的主體意志。網絡空間去除的只是身份的物理形式,而在心理層面,虛擬身份依然保留著真實生活中一些身份特征的印記。
在現實生活中,“云舞”是孤獨、缺乏關愛和真心伴侶的,在虛擬空間里,“云舞”試圖彌補這些虛空。“云舞”給網友安然發了一封信,寫道:“沒有誰會長長久久地陪伴我,屬于我一個人,除了我的愛人。”對游戲玩家而言,虛擬空間中自由的想象與高仿真的實踐比真實的還要真實。玩家的生活變成了虛擬與真實并存的多重結構。這種真實感隨著虛擬空間對現實世界的介入程度加深變得異常強烈。
三、雙重空間的主體迷失與身份錯位
交流是從自我城堡中徒勞的突圍⑨。在人際交流的層次上,主要的障礙是雙方的意圖錯位:每聽見一句話,我們自然而然地會認為,說話人所指的意義,是我們自己使用這些詞語所指的意義。事實往往背道而馳。網絡游戲制造了無數可以隨時轉換或同時存在的身份場所。在一個游戲空間中的有婦之夫,在另一個游戲空間可以假定為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年。網絡用戶之所以長時間、高強度地粘合在游戲中,與虛擬身份的自由流動和隨意轉換不無關系。
在云舞事件中,玩家“折磨”起初是“云舞”所在幫派的一個幫友,還是“云舞”主播節目的忠實粉絲。隨著互動推進,游戲空間的“折磨”愛上了“云舞”,甚至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云舞的小甜心”。在“云舞”的心目中,“折磨”從一個追求者成為夫君,同時也是一個可以交心的朋友,對他寄予了虛擬空間與現實世界的雙重期許。然而“折磨”卻與她不同,沒有太多的社會經歷,網絡游戲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承擔的主要是消遣和娛樂功能。“折磨”真名吳青,現實中只是一個1994年出生的遼寧大男孩,是大連一所高校的學生,比方某整整小了十歲。
在網絡游戲之中,常常存在著兩種對立的身份混合:一種是把網絡游戲看作是真實社會網絡的組成部分,把網絡游戲中的身份當作是其所聲稱的身份,“作為其所是”,另一種是僅僅把網絡游戲當作是一種“游戲”或“扮演”,是一種“幻想”世界中的行為,網絡游戲中身份只是其所幻想的身份。
交流意圖的錯位源自兩個主體對自身身份定位的差異:“云舞”試圖在虛擬空間實現理想我,“折磨”只是將真實我的種種欲望在游戲中釋放。當“云舞”以夫妻之道要求“折磨”時,“折磨”卻抽身離去,在另一個游戲空間里與玩家“半夏”結為“情緣”。當“云舞”質問“折磨”為什么在另一游戲中另覓新歡,“折磨”回答道“我從來沒愛過你,沒拿你做過女友,你做的那些事都是自愿的”。“云舞”是在與“折磨”虛擬主體交往中尋求到了比真實還真實的夫妻身份認同和心理歸屬感,彌補了現實社會自我身份實現的缺憾。當有人打破這種平衡時,她便喪失了主體意識中無比重要的歸屬和依賴,她的雙重期許落空了,導致其迷失現實我,又暫時無法重新建構,陷入主體迷失狀態。
盡管“折磨”意識到“云舞”將網絡游戲的身份混同于現實世界之后,先是以“寢室的網不好,晚上11點后就要睡覺”“父母反對”為由,冷淡地對待“云舞”,后明確提出分手,試圖結束這段交往,但“云舞”堅持用現實世界的行為方式試圖挽回這段感情。她與虛擬空間中的“第三者”對質,將所有的財產進行公證,將絕筆信發給對方,寄出以“夫妻之實”名義希望對方繼承的銀行卡、遺囑公證書、筆記本電腦等。雙方的交流一次次陷入各行其是、背道而馳的僵局。
玩家?戀人?網友?丈夫?云舞事件中的當事人在虛擬空間與現實世界的相互交織中重構了多重自我,沉浸于虛擬時空又無法逃離現實世界的主體意志發生錯位。不同身份定位的兩個玩家,借助虛擬化生存,排遣現實生活中與身份角色相關聯的社會化特征帶來的壓力,同時也因互聯網超鏈接、多元化并存的場景化模式而遭遇身份迷失與主體惶惑。
互聯網作為一種信息方式正在改變我們的世界,值得關注的是,它更重要的影響莫過于個體在虛擬與現實的交錯中被置換成一個多重、播撒的主體,并被不斷質詢為一種不穩定的身份。如何在互動、重疊與轉換主體建構與身份塑造中尋求自我,對于尚不具有成熟、穩定價值觀的青年群體而言,顯得尤為重要。
注釋:
①中國青年網.女主播遭拋棄后燒炭自殺負心男友遭人肉[EB/OL].2015-10-9,
http://d.youth.cn/shrgch/201510/t20151009_7188994_2.htm
②羅歡歡,李志健,閔珍琪.網絡女神的死亡游戲[N].南方周末,2015-10-29
③④[美]歐文.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M].馮鋼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214,19
⑤何旭東.第九城市網站分析與發展戰略[D].上海交通大學,2002
⑥⑧[荷蘭]約斯.德.穆爾.賽博空間里的奧德賽——走向虛擬本體論與人類學[M].麥永雄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181,184
⑦殷樂.電視娛樂:傳播形態及社會影響研究[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292
⑨[美]彼德斯.交流的無奈-傳播思想史[M].何道寬譯.華夏出版社,2003:16
(賴黎捷系重慶師范大學傳媒學院副院長、教授,衛彥瑾系重慶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