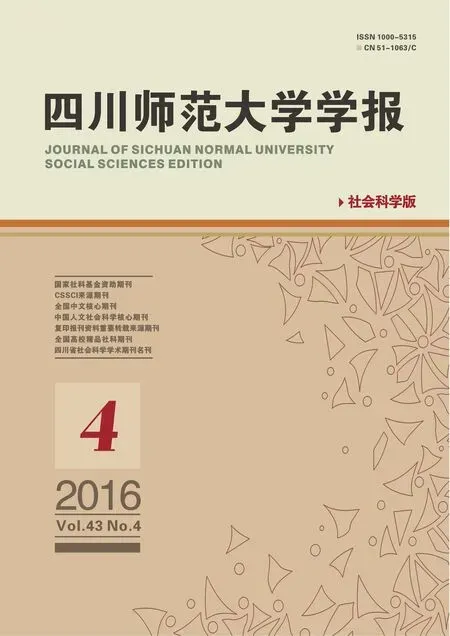走出“自我中心”的困境
——論民族區域教師培訓的普遍無效現象及其消除
雷 云,楊 歡
(四川師范大學 教師教育與心理學院,成都 610066)
?
走出“自我中心”的困境
——論民族區域教師培訓的普遍無效現象及其消除
雷云,楊歡
(四川師范大學 教師教育與心理學院,成都 610066)
摘要:民族區域教師培訓者陷入了“自我中心”的困境。他們無視參訓者的教育知識與實踐狀況,獨斷地設計培訓目的與內容,致使民族區域教師固守“自我”的世界,“理解”無從可能而培訓普遍無效。培訓者唯走出“自我中心”,以“尊重”為前提,借助“傾聽”、“對話”等旨在增進理解的培訓方式,才能消除普遍無效的培訓現象。
關鍵詞:民族區域教師;教師培訓;普遍無效;“自我中心”
近年來,關于教師培訓有效性的討論不絕于耳。人們多從“目的設立”、“內容安排”、“方法選擇”等方面分析評論,提出相應的改進策略。應該說,已有研究頗有助于改善主流文化區教師培訓狀況。但若以此推論民族區域教師培訓,則不免失察。我們認為,當前民族區域教師培訓已陷入普遍無效的困境;而這一困境的產生緣于培訓者受“自我中心”之制約,無視民族區域教師的教育實踐與知識狀況。培訓者唯以“尊重”為前提,借助“傾聽”、“對話”等旨在增進理解的培訓方式,方可走出“自我中心”,消除普遍無效的培訓現象。
一民族區域教師培訓的普遍無效及其癥結
何謂有效的教師培訓?圍繞“有效”(或“實效”)概念,學界提出了不少值得關注的觀點。有論者將“有效”分解為“效果”、“效率”與“效益”,認為“某次教師培訓活動,存在多方利益角逐……立場不同,在他們眼里的效果、效率、效益理解又是必然不同的”[1]。然而,某一培訓很可能在“效果”、“效率”與“效益”諸方面并不一致。例如,要確保培訓“效果”則可能難以兼顧培訓“效益”,如此“分解”似難判斷某一培訓到底是否有效。實際上,更多論者從培訓目的、內容、方法、過程以及結果等方面綜合判斷是否有效[2];還有論者據此構建培訓有效性的評價指標[3]。這一分析思路本身雖無問題,但現實中很難發現在上述各方面都盡善盡美或一無是處的教師培訓;構建指標體系對培訓工作量化評價雖有重要意義,但如何確定各指標所占比重又難有可靠的依據。“分解”有助于認識“有效”的外延,卻無法把握其內在實質。鑒于此,有論者認為,有效的培訓必須對參訓教師返崗后的教育實踐產生積極影響,“必須給工作帶來進步和更好的效果”[4]。這一認識的問題在于,工作是否有“進步”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很難簡單歸結為其所受的培訓。有效的培訓只能為參訓者改進實踐提供可能,而不能直接作用于實踐活動。推而論之,可為改進實踐提供條件的培訓,必然能引起參訓者自覺反思自身,能為其提供一幅新的實踐圖景。在此意義上,有效的培訓應當是一種充滿意義、富有啟發的理解性培訓。
1.培訓的普遍無效
一般而言,由于漢區教師的教育實踐屬于主流教育文化,各類高校或培訓機構按照國家要求對其組織的培訓總存在一定的理解性,不會出現普遍無效的培訓狀況,其問題不過是理解性不高而導致的低效現象,通過調適培訓方式、改善培訓方法就能解決問題。
與此不同,在民族區域教師參與主流教育文化的培訓中,由于文化的不同導致教育生活方式的異質,參訓教師往往將自己和培訓者劃入截然不同的兩個教育世界,培訓者講授的內容不僅被先驗地認為難以理解,而且由于被斷定為“無用”而無需理解。民族區域教師培訓由于缺乏“理解性”而呈現普遍無效的現象,不少學者的調查研究對此都有所反映,筆者在培訓實踐中也深有感觸。有論者指出,“在參加培訓的教師(注:指民族區域教師)中,退學、曠課、遲到、早退現象時有發生,部分教師表現出對培訓缺乏興趣和積極性,甚至于還出現了某些抵觸情緒”[5];“由于接受培訓的少數民族中小學教師學歷背景不同、經歷不同、教育觀念和知識結構不同”,他們對培訓的需求似乎難以滿足[6]。筆者近年來參與了十余項西藏自治區教師培訓項目,培訓中總感覺參訓教師很難融入培訓活動;不少藏區教師坦言,“培訓專家講得很好,但我們的情況與所講的相差太遠”,“我們不過是配合你們的工作完成培訓任務而已”。顯然,調整培訓方式已難改變民族區域教師的培訓現狀,只有深入內里探明癥結方有助于消除普遍無效的培訓現象。
2.培訓普遍無效的根本癥結
表面看來,民族區域教師對自身實踐以及培訓內容的認識和理解,是導致培訓無效的最主要原因。似乎是民族區域教師將自己定位于不可通融的另一個教育世界,是他們主觀地認定培訓內容無用,培訓者只能望之興嘆。不過,這只是問題的表象而非癥結。民族區域教師的這種認識和理解,其實是培訓行為的被動反應,問題的癥結應在培訓方探詢。已有論者對民族區域教師培訓的諸方面進行過頗為中肯的批評,認為“拋開經費、資源、機會”問題,民族區域教師仍然存在著培訓觀念的城市化、培訓內容的理論化、培訓方法的單一化、培訓過程的形式化以及培訓者的集權化[7]。盡管這一評論頗切要害,但所述問題仍然是“無效”的表征,還須透過問題表征追問更深層的緣由。我們認為,更深層的緣由在于,當前民族區域教師培訓,從培訓觀念至目標、內容再至方法、過程,諸方面無不反映出以主流教育文化自居的培訓者陷入了“自我中心”的困境。培訓者擁有新課程改革的話語權,自恃掌握了“主流”的實踐方式與“先進”的教育知識,而“少數民族地區受地理和經濟等因素的制約,基礎教育水平普遍落后”[8]。民族區域教師似乎只有全盤放棄自身的教育經驗,接受先進的教育知識,才能盡快地趕上當前主流文化語境下的教育改革的步伐。由于培訓者不自覺的“自我中心”的培訓設計,加之參訓的民族區域教師又不可能放棄自身的教育經驗,逃離自身的教育處境,于是,兩者處于不同教育世界的意象逐漸形成,先驗地破壞了培訓的可理解性。
二“自我中心”困境下的培訓設計
預設“先進”與“落后”。培訓者的“自我中心”主義鮮明地體現在培訓前對自身和培訓對象的教育知識與實踐狀況的預設。調查發現,培訓者大多不假思索地將自身的教育知識與實踐視作“先進”,而將培訓對象標定為“落后”。他們的預設邏輯如下。首先,以經濟發展水平推論教育發展水平,認為民族地區經濟普遍落后,其教育發展水平也必然落后。盡管經濟發展狀態和教育發展水平并沒有本質聯系,一些經濟發達地區之所以能先行發展,大多是受惠于國家的政策支持,其教育發展水平未必與其經濟發展水平一致,但培訓者并不愿深究而大都籠統地作此推斷。其次,以教育發展水平推論教育認識水平,認為民族地區教育發展水平落后,民族教師的教育理解能力、認識水平也必然普遍低下。顯然,如果經濟發展水平可以通過量化來排列先后,那么教育發展水平則很難依此判斷優劣。每個文化區域的教育都有其獨特的使命,每個民族區域教師都可以利用其依存的文化賦予他的理解方式去探索教育實踐。民族區域教師在認識和理解教育方面都有值得稱道的“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問題是培訓者如何看待他們的知識。再次,以政府部門的培訓安排證實自己為“先進”,完成培訓之前的預設。或許政府部門的培訓安排并沒有劃分先進與落后之意,但這絲毫不妨礙培訓者執意將兩者勾連起來。培訓者正是通過這一個又一個微弱的邏輯推論實現預設,并根據這一預設完成了一系列的培訓設計。
1.獨斷的目的與內容
目的是培訓活動的核心要素。培訓預設首先反映在目的的擬定上。所謂獨斷的培訓目的,是指培訓者按自身所掌握并預設為“先進”的教育知識話語,擬定民族區域教師培訓的目的,并根據所擬定的目的選擇民族區域教師并不一定真正需要的培訓內容。正如有論者所言:“受傳統課程觀念及基礎教育現有課程體系的影響,民族地區教師培訓主要是集中圍繞國家課程的教學要求開展”,“培訓的目標幾乎完全趨同于內地城市的教師培訓”[9],“沒有充分考慮各地的實際情況,仍按照統一的標準進行”[10]。培訓者并非不明白培訓需求調查的重要性,但尊重民族區域教師的需求設計培訓很可能與“預設”相悖。因此,盡管不斷有論者批評培訓目的沒有針對性,內容脫離民族教育的實際,但并未多少實質性的改變。在此,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按常識理解,有效即培訓目的的達成,獨斷的目的若能實現,培訓是否仍可稱作有效甚至是高效?答案是否定的。這種獨斷的培訓目的盡管可能實現,但培訓本身不能為參訓的民族區域教師改變教育實踐提供條件,這種看似“有效”的培訓最終是“無效”的。由此不難看出,以“目的達成”來理解培訓的有效性有其難以克服的局限,相較而言,將“有效”界定為“充滿意義與啟發而富有理解性”似更合理。顯然,在獨斷的目的和內容設計下,民族區域教師培訓很難有什么理解性,必定呈現出普遍無效的培訓現象。在這場無效的培訓中,參訓教師不過是培訓者完成培訓任務的工具,通過培訓他們獲得的只是一些不知所云的、碎片化的教育術語。
2.陌生的知識與經驗
獨斷的培訓目的和內容選擇,導致民族區域教師培訓中充斥著參訓者無法理解的陌生知識與經驗。其實,這些知識與經驗并非不可理解,只是理解需要前提和基礎。民族區域教師培訓中,參訓者的理解前提與基礎便是其已有的教育經驗,他們本可“依托自己已有經驗獲取知識和技能”,已有的經驗是“最寶貴的資源”,在教師培訓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11]。然而,培訓者已預先將民族區域教師的教育經驗設定為“落后”,并通過諸種設計使其在培訓中無法發揮作用。參訓的民族區域教師在培訓者所編織術語網絡下不自覺地接受了培訓者對其所作的“落后”的預設,他們本可作為理解培訓知識與經驗的基礎被強制取消,對自身已有經驗發生了“暫時性遺忘”。陌生的知識與經驗讓參訓的民族區域教師置身于一個陌生的教育世界,這個世界與其自身的教育實踐相距甚遠,格格不入。參訓教師十分明白,他們不過是這個陌生的教育世界的過客,因此培訓所獲得的知識和經驗對自身的教育實踐沒有效用。由于培訓中陌生的知識與經驗未經理解,沒有內化成自己的教育觀念,參訓教師回到自己的教育世界后,不可能據此改變自身的教育實踐。至此可見,陌生的知識與經驗在培訓中所發揮的作用不過是進一步確證“先進與落后”的預設,并借此取消民族區域教師以自身經驗參與培訓的可能性。
3.被動的參與和實踐
應當承認,近年來為了提高培訓實效,民族區域教師培訓做了不少新的嘗試,增加了一些新的內容,其中參與式培訓與注重實踐觀摩尤值一提。參與式培訓強調參訓的民族區域教師卷入培訓過程中所設置的任務或實踐活動,通過認知、情感與行動的投入,獲得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教育知識。不僅如此,在參與式培訓中,參訓教師還可以通過與其他學員的交流來獲取知識。按理說,這是一種十分有助于其掌握新知識、理念,形成新的教育教學技能的方法。然而,由于培訓者所設計的教研任務遠離民族區域教師的教育實踐,參與式培訓變成了被動執行培訓者的指令。同時,參訓的民族區域教師共同完成一個不熟悉的任務項目,相互之間的交流與學習的可能性便大為減少,即便順利完成了培訓任務,他們從活動中獲得的經驗也并無多大意義。實證調查的結果印證了我們的分析。根據對參訓的近百名藏區教師的調查,近85%參訓教師并不歡迎參與式培訓,不愿意完成培訓者布置的各種任務。一項原本旨在發揮參訓者的主動性的培訓方式,由于參訓者“被動”地卷入而失去了應有的意義。與參與式培訓相比,實踐觀摩是比較受參訓民族教師青睞的一種培訓方式。培訓方盡力安排最能反映當前改革趨勢的學校供參訓老師觀摩,力圖通過優質學校的觀摩鞏固培訓所學,擴展視野。吊詭的是,優質學校的觀摩在確證主流教育文化的同時,又使民族區域教師更加堅信他們“處于另一個世界”。于是,主動觀摩往往變成被動游走。
三預設批判與“他者”的意義
1.“先進”與“落后”預設的批判
“先進”與“落后”的預設,乃是培訓者不自覺地進行和完成的。應該說,前述對這一預設的揭示實際上已經對其進行了批判。只是這種批判不夠徹底,還有必要進一步從學理上探明其局限與問題。稍加分析不難發現,“先進”與“落后”預設若要成立須有其前提,即不僅要求預設對象能被納入某一參照標準所確立的秩序之中,更為重要的是,這一參照標準不能是外部強加的,而應該是判斷對象主動納入作為自己的發展尺度,否則便難免遭到強制與霸權的詬病。據此理解,返觀民族區域教師培訓,培訓者的預設包括教育實踐與教育知識兩方面。先論教育實踐預設。根據當代比較教育研究成果,任何教育實踐模式都根植于某一社會境遇,不可與孕育該模式的社會境況相剝離。就此而論,民族教師的教育實踐與培訓者的主流教育實踐各有不同的社會環境,兩者難以找出一個共通的發展標準,以其中任何一種實踐模式作為參照標準都必然會強制另一種教育實踐脫離其自身的社會境遇。培訓者所依傍的主流教育實踐與參訓教師的教育實踐兩者存在差異而非差距,“先進”與“落后”的預設是不成立的。再析教育知識的預設。判斷此預設是否成立的關鍵在于,是否存在一個參照標準能將不同教育知識置諸其下進行衡量。可以設想,如果存在這樣的參照標準,參照標準本身不僅也是教育知識,而且具有普適性。教育知識以教育實踐為對象,既然沒有普遍通行的實踐模式,則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教育知識。這一預設也是難以成立的。
2.作為“他者”的民族教師及其實踐
根據預設批判可以得出,參訓的民族區域教師所在的社會文化與培訓者往往有很大差異,他們在教育實踐與認識方面對于培訓者而言是一個有益的“他者”。這一理解蘊含著如下幾方面重要意義。首先,“他者”標明了一個與“自我”不可通約、不可同論的存在者。作為培訓者應當認識到,民族區域教師的教育實踐有其獨特性,其對教育的理解與主流民族有相當大的差異,若僅以主流民族的教育實踐方法、經驗作為培訓內容,將很可能導致整個培訓活動缺乏理解性,出現普遍無效的培訓現象。其次,“他者”是一個與“自我”有所關聯、相互參照的存在者。“他者”總是“自我”的他者,是與“自我”有著一定聯系而非毫不相關或完全未進入視線的存在者。可以說,“他者”和“自我”只有相遇才能完成相互界定,并進而可以相互參照。培訓為代表主流教育文化的培訓者與民族區域教育提供了相遇的契機,民族區域教師的教育實踐若能在培訓中顯現出來,便可成為培訓者理解“自我”的一個重要的“他者”。再次,“自我”與“他者”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參訓的民族區域教師及其教育實踐相對于培訓者而言是“他者”,培訓者相對于參訓的民族區域教師而言也是“他者”。但是,在民族區域教師培訓中,培訓者掌握了話語權,其相對于參訓教師而言的“他者”形象已經建立起來;與之相對應,民族區域教師未能在培訓中表達自我,其對于培訓者的“他者”形象尚未建成。
3.“他者”與培訓者的自我認識
“他者”是“自我”的一面鏡子,不僅是自我認識不可缺少的參照,甚至可以說是形成更加合理、健全的“自我”的基礎。一個從未經過“他者”中介過的,“自我”大多是一個虛幻的“自我”;一個未能認識“他者”作為自己限制的“自我”,也必定是一個過度膨脹的“自我”。民族區域教師培訓中,參訓教師本可以為培訓者更好地認識主流教育文化與知識,提供一個有益的“他者”。具體來說,民族區域教師及其教育實踐可提供在另一種不同文化下的行動方案,培訓者可以借此看到另一種可能的教育實踐,這本來十分有助于培訓者理解主流的教育實踐與知識的特性、有效范圍以及局限性等。然而,由于參訓教師的教育實踐被預設為“落后”,在培訓中未能有效地形成一個相對于培訓者而言的“他者”,使培訓者深陷“自我中心”而不能自拔。處于“自我中心”的培訓者極度膨脹,認為自己掌握的教育知識是絕對真理,民族區域教師完全不必質疑,也毫不在意培訓中傳授的教育知識的有效范圍是否包括民族區域教師的實踐。然而,正如有論者所言:“這里(注:指民族區域)的孩子靦腆、害羞,漢語表達不流暢,像合作學習、探究學習都很難有效展開,形成一套做法在這里應用,處境非常尷尬。”培訓者自以為具有普遍適用性的教育實踐模式(如“合作學習”),其實往往難以運用于其他少數民族地區,主流民族的教育知識在此觸碰到了適用的邊界。
4.“他者”的缺位與理解的缺失
表面看來,問題不過是民族區域教師沒能在培訓中表達“自我”,實質上卻是作為培訓者的“他者”的缺位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問題,最終導致培訓理解的缺失。具體說來,參訓的民族區域教師在培訓中的“失語”對于培訓者的自我認識和反思極為不利,未能據此形成適恰的“自我”,也未能由此反思自身的教育實踐與知識的局限。培訓者無法形成健全的“自我”,作為民族區域教師的“他者”便是不健全的,“他者”的不健全又必然會影響到“自我”的形成。所謂理解的缺失,一方面是指,由于民族區域教師“自我”未能彰顯,導致培訓者沒有一個可供理解的“他者”,理解現象顯然不可能發生;另一方面是指,培訓者與民族區域教師都以不健全的“自我”參與培訓,自然不可能出現富有生氣的對話與交流,無法實現相互理解。可以看出,培訓者與民族區域教師都陷入了“自我中心”的困境,培訓者處于一種主動的、自大的“自我中心”境地,參訓的民族區域教師則處于被動的、退縮的“自我中心”境地。如果兩者都不能走出“自我中心”,那么培訓必然由于理解的缺失而呈現出無效的狀態。事實就是這樣。在民族區域教師培訓中,培訓者以為自己掌握了“先進”的教育實踐方法和知識理論,不屑于理解參訓教師;參訓教師則認為自己的教育實踐境況不被了解,完全處于另一個世界,是培訓所講、所觀觸及不到的。雙方都不承認對方為“他者”,培訓中飄蕩著一個個虛幻的“自我”。
四走出“自我中心”的民族教師培訓
1.須以“尊重”為前提
民族區域教師培訓中的“尊重”,不僅要求培訓者主動關心參訓教師生活與文化上的適應情況,更為重要的是培訓者應當主動反思和破除“先進”與“落后”的預設,以平等的心態對待民族區域教師的教育實踐與知識,在各個培訓環節對其予以足夠的關注。這里有必要著重強調如下幾個方面。其一,培訓者須樹立一種平等的交往心態。培訓者不可以自身作為主流文化教育實踐者與認識者自居,而應主動了解民族區域的教育實踐現狀和知識經驗。其二,培訓者應注重參訓的民族區域教師這一課程資源。參訓教師自身的教育經驗是一種重要的課程資源。培訓過程中,有必要設計一些民族性、地方性的教育活動與任務,使參訓教師能夠真正投入培訓,實現相互交流與學習。其三,培訓者在選擇課程內容時應具有一種文化敏感性。文化敏感性,指培訓者對參訓教師文化背景和生活經驗的感知程度,以及在此基礎上采取適恰的方式幫助參訓教師實現學習和理解的意識。具有文化敏感性的培訓者,注重將培訓活動根植于參訓教師所在地區的歷史文化和風俗習慣,強調對課程內容開展文化分析,開發文化課程資源[12]。其四,培訓者應以參訓教師的教育實踐與知識經驗為參照反思“自我”。民族教師培訓中的“尊重”,不僅表現在課程內容和培訓形式的安排上,而且更為深刻地反映在將參訓教師的實踐經驗尊為重要“他者”,進而以“他者”為參照,重新構建一個更加健全的“自我”,真正走出“自我中心”的泥濘。
2.應注重“傾聽”他者
培訓者的“自我中心”主義往往表現在培訓中“只說不聽”。他們具有不可遏制的言說欲望,總想在有限的時間里將自己的所有“先進”知識和實踐方式講授出來;對于民族區域教師“落后”的知識經驗以及具體實踐,他們毫無興趣。要走出“自我中心”的困境,必須扭轉這一局面。培訓者應當從“只說不聽”轉變為“先聽后說”、“聽說結合”。所謂“先聽后說”,指在培訓之前應當通過各種渠道了解民族區域教師的教育實踐現狀,調查他們對自身教育的理解和認識水平,對參加本次培訓有何期望,有何批評建議。“先聽后說”不僅可以了解培訓需求,根據參訓教師的訴說設計培訓方案,而且培訓者的主動傾聽向參訓者表達了一種“尊重”的姿態,受到尊重的參訓民族教師必將欣然投入到培訓中來。“聽說結合”,主要是指在培訓過程中要善于引導民族區域教師參與到培訓實踐中來,在培訓中表達自我、理解他者。應當注意的是,培訓者所涉及的論說主題應當是民族區域教師所關切的,具有強烈的言說欲望的,而不應是從自身的教育實踐方式和知識理論中引申出來,這樣的主題將導致參訓民族教師的被動參與。“傾聽”為民族區域教師在培訓期間提供了“訴說”的機會。“訴說”有助于民族區域教師形成“自我”,從而使培訓者獲得一個理解自我的“他者”,因此“傾聽”可助培訓者走出“自我中心”,主動理解參訓民族教師。
3.要多開展對話交流
若要改變培訓者與民族區域教師處于兩個不同的教育世界的狀況,就有必要在培訓中開展對話。“對話”使兩個具有不同視界的人走出自我,走向他者,是促進培訓者與民族區域教師相互理解的重要途徑。培訓者的“自我中心”主義往往使其以為民族區域教師缺乏與培訓者對話的基礎,他們只需多學前沿知識,多看先進的實踐。培訓者的這一不自覺的設定是在大量培訓實踐中固化,要糾正這一認識并非簡單地轉變觀念就能成功。其中的困難在于,在培訓過程中民族區域教師由于文化、生活習性以及教育經歷等多種原因,大多不善于表達自我,開展對話交流有相當大的難度。面對這種情況,培訓者除了選擇恰當的對話交流的主題以外,還有必要創新多種對話形式。其實“對話”并不限于口語交流,如果民族區域教師的口頭表達有困難,個人組織語言口頭講述有難度,可采取小組集體交流,然后再與培訓者對話,或者直接改用書面交流形式。近年來,多有論者提出,教師培訓應注重引導參訓者多寫,將自己學習中的所思所想所得寫下來。寫的時間相對充足而且不用緊張,“寫的方法是最簡單易行的”,這種方法不僅“可以使思路更清晰和有條理,可以幫助思考趨于縝密和深入”,而且方便參訓民族教師之間、參訓民族教師與培訓者之間交流想法,“是引發更大學習興趣的秘訣之一”[13]。
4.務以“理解”為目的
未能實現理解的民族區域教師培訓是無效的。培訓者只有走出“自我中心”理解民族區域教師,才能提高培訓活動的理解性,最終為參訓者改善自身的實踐狀況提供條件。“理解”,既是民族區域教師培訓的起點,也是其最終的目的。如何才能促進民族區域教師培訓中的理解性?首先,培訓中的理解是一個相互誘發的過程,培訓者必先理解民族區域教師的教育實踐及其知識經驗,根據理解調整其培訓設計,如此才有可能引發民族區域教師的理解。民族區域教師培訓中,培訓者主導著整個培訓活動,他們不能等待被參訓教師理解,而應主動理解參訓的民族區域教師,以為其理解培訓提供鋪墊。其次,民族區域教師的教育實踐與知識經驗是培訓理解的出發點。培訓者的理解,主要是走出“自我中心”,走向民族區域教師的教育世界;參訓教師的理解,主要是以自身的教育實踐和知識經驗為基礎,整合主流民族教育實踐與知識的有益成分。培訓者不能輕視民族區域教師已有的教育知識經驗,要以此為出發點,引導他們理解主流教育文化。再次,民族區域教師培訓中的理解應當以實踐運用為取向。真正徹底的理解乃是在實踐運用中完成的。民族教師培訓以引發參訓教師的理解為目的,以促進其反思調整已有教育觀念為核心,以激勵其運用知識改變教育實踐現狀為旨歸,只有運用所學知識變革現狀,才能徹底理解所學知識。
參考文獻:
[1]王彬.教師培訓有效性評價的幾個基本問題[J].上海教育科研,2015,(2):63-66.
[2]王晨.提升教師培訓有效性的策略研究[J].天津教科院學報,2014,(1):46-48.
[3]陳霞.教師培訓有效性的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研究[J].中小學教師培訓,2008,(10):9-11.
[4]鐘祖榮.教師培訓實效產生機理研究[J].中小學教師培訓,2015,(12):1-4.
[5]于影麗.對新疆少數民族雙語教師培訓工作中的文化自覺性思考[J].民族教育研究,2014,(3):104-108.
[6]李曙光.新疆中小學少數民族教師培訓的基本路徑[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3):49-50.
[7]李丹.教師培訓:針對教師的系統教學過程——對民族貧困地區教師培訓的調查與思考[J].中國民族教育,2008,(1):20-22.
[8]張新賢,焦道利.西部少數民族地區教師培訓的發展研究[J].現代教育技術,2009,(10):58-61.
[9]張華,王亞軍.民族地區教師培訓的實踐檢視與理念突圍[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6):78-83.
[10]劉陽.少數民族地區中小學教師培訓問題研究[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7,(24):13-14.
[11]鄧友超.論教師學習的性質與機會質量[J].教育研究與實驗,2006,(4):55-59.
[12]茍順明,王艷玲.民族地區教師的文化敏感性與教師培訓的重構[J].當代教育與文化,2014,(2):25-30.
[13]王躍.關于互動參與式培訓的思考[J].中國遠程教育,2012,(12):79-83.
[責任編輯:羅銀科]
The Common Invalid Condition of Regional Ethnic Teacher Training and Its Elimination
LEI Yun,YANG Huan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6, China)
Abstract:In the regional ethnic teacher training, the trainers usually get into a dilemma of “egocentricity” as they ignore the education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condition of trainee teachers and assertively design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contents so that the trainees stick to their “self”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others. As a result, this kind of training is invalid. The only way for trainers is to step out of the “egocentricity”, based on “respect”, and with the help of “listening” and “dialogue”, which aims to enhance understanding, so as to eliminate the common ineffectiveness in teachers training.
Key words:regional ethnic teachers; teachers training; common invalid; egocentricity
收稿日期:2015-12-20
基金項目: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二五”規劃課題“民族教師培訓的有效性研究——基于文化人類學視角的考察”(SC13E037)。
作者簡介:雷云(1980—),男,四川大竹人,四川師范大學教師教育與心理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教育基本理論與教育哲學; 楊歡(1989—),女,四川德陽人,四川師范大學教師教育與心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教師教育理論與實踐。
中圖分類號:G45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5315(2016)04-01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