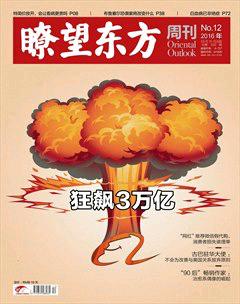“營改增”試點全面推開,深意何在
李克強總理所作的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本年度政府將采取三項措施以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5月1日起,建筑業、房地產業等四大行業將實施“營業稅”改征“增值稅”,市場目前較多將這條消息理解為大利好,但也有不同觀點聲音。由點及面,全面鋪開,“營改增”的推進究竟有何深意?
“營改增”不是“政府補貼”
張連起(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學家、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管理合伙人)
全面實施營改增可促進服務業率先發展和制造業轉型升級。消除重復納稅,接通抵扣鏈條,優化產業分工,有利于服務業與工業深度融合及 “專注、專業、專門、專才、專精”的創新主體競相涌現。這是繼2015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半壁江山”之后,財稅改革不失時機提供的有力支撐。
此外,不動產納入抵扣范圍,標志著規范的消費型增值稅制度浮出歷史地表,有利于企業擴大投資、增強內生動力,用普惠性降稅的“減法”,換取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加法”、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的“乘法”、企業不動產投資負擔的“除法”。
更為重要的是,全面實施營改增為“十三五”時期經濟發展大棋局布下了先手棋、“當頭炮”。營改增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稅種轉換,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政府補貼”,也不是定向返還的“芝麻鹽、胡椒面”。它是一項創新驅動、動力支撐、財稅引領、產業催生的重大制度變革。
營改增改革年化減稅超過5000億元。這意味著,這部分資金活水能更有效地成為實體經濟“潤滑劑”、創新驅動的“信號源”,推動產業結構、需求結構和就業結構不斷優化,為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保就業、強預期提供“四兩撥千斤”的財稅動力。
自2009年我國實施從生產型增值稅向消費型增值稅轉型的改革,到2016年5月1日起允許企業購買的不動產進項稅抵扣,標志著現代增值稅制度初步定型。簡化稅種、公平稅負、降低成本、統一稅制,不僅倒逼政府提高稅收征管能力,還客觀上強化了因隱瞞交易導致的偷漏稅行為的內在約束力。
能有效減少二手房投機,“溫和”調控房價
謝皓宇(華泰證券房地產行業首席分析師)
房地產格局的重大變化,幾乎都和稅制掛鉤。1994年,中國啟動分稅制改革,將地方財權上收,大幅提高中央稅種的比例,再通過轉移支付還給地方。后來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土地出讓、土地抵押、房地產稅收)的依賴與此頗有關聯。
2015年全國財政收入12.5萬億元,其中營業稅1.9萬億元,包括房地產貢獻的6104億元,建筑業5136億元、金融業4561億元,后兩個行業的相當一部分也跟房地產掛鉤。
營業稅外,土地相關的稅收總計9873億元,其中,契稅3899億元,土地增值稅3832億元,土地使用稅2142億元;再次,個人所得稅8618億元,這其中還有部分來自于房屋交易。
當前的“營改增”改的是房地產稅收。營業稅占地方稅收比重高、特別是地方政府加足了平臺杠桿的省市需逐步出臺應對措施。據統計,2007-2011年,有9個省市對營業稅十分依賴,營業稅占地方稅收比重都超過了40%,其中包括北京,達到41%。
對房企來說,“營改增”稅負減少,這種變化和影響是積極的。但要做好地價支付增加的準備。因為事權和財權不匹配,地方政府會借由土地出讓收入和土地抵押的繼續增加來抵消稅收減少的影響。
由于增值稅稅率一定高于營業稅,所以增值越多、稅收越多、對投機的抑制越多。當前營業稅為固定稅率5%,假設增值稅稅率為11%,則當房價上漲超過83%時,增值稅將開始超過營業稅,按照百城價格指數進行計算,北京、深圳等9個城市的稅負可能會增加。
但當前的二手房市場賣方說了算,所以短期內,這些成本將被轉嫁給買方。從長期來看,“營改增”無疑會減少新入市投資性需求,使得價格變化更為平穩。
稅收倒逼,解決行政體制改革的反彈問題
喬新生(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稅收制度是改革的重中之重。我國尚未進入福利社會,但企業的稅負已與部分發達國家大致相同。今年政府決定全面實施“營改增”,減輕企業負擔,這意味著中國實體經濟的春天來了。
但“營改增”的全面推進勢必帶來連鎖反應。考慮到今年的中央政府財政赤字安排,如果不加快行政體制改革步伐,大幅降低公共開支,那么正在實施的稅改方案可能會因政府的剛性需求而不得不調整。
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方法是,一面堅持減輕企業稅收負擔的改革不動搖,確保營業稅改為增值稅之后企業的稅收負擔不增。另一面必須加快行政體制改革步伐,盡快合并重組機構,減少行政公務開支,使我國的稅收體制改革不會因為行政負擔過重而出現反復。
政府機構改革必須雙管齊下:首先,對那些直接面向市場的政府機構應加緊綜合性改革,把市場監管機構包括金融市場和非金融市場監管機構的職能合并起來,在此基礎上借助于互聯網絡的信息共享技術,建立精簡的市場監管部門。
其次,這些年來某些領域的行政事業機構不斷膨脹,這要求我們在行政改革過程中,既要充分發揮行政事業單位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也要充分發揮政府財政預算稅收制度的引導性作用,充分利用稅收倒逼機制解決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反彈問題。世界各國行政體制改革的經驗和教訓是,與其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只要中央政府下決心徹底減少部分行政事業單位撥款,行政機構改革必會進入快車道。
減稅救經濟顯出誠意
馬光遠(經濟學家、民建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不同于過去多年的“結構性減稅”的提法,行業稅負只減不增是“全面減稅”,是從總的稅負比重上設置一個政府稅收收入的上限,這和過去的“結構性減稅”比,對改變政府收入增長快于居民收入的局面,將宏觀稅負控制在合理區間,具有轉折點意義。
為什么要全面減稅,其意義不僅在于為企業減負,而是通過全面減稅,構建起一個企業負擔合理、不影響中國經濟競爭力并有利于創新和民生的稅制結構。宏觀稅負過高,不僅增加企業負擔和制度成本,削弱了中國稅收制度的競爭力,影響了企業創新。
減稅是救經濟的最有誠意、最能真正見效的舉措。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今年減稅的舉措有三:一是全面實施“營改增”;二是取消違規設立的政府性基金,停征和歸并一批政府性基金;三是將18項行政事業性收費的免征范圍,從小微企業擴大到所有企業和個人。
通過這些舉措,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5000多億元。這三項舉措,針對性很強,如果真的落到實處,對于減輕企業的負擔,效果無疑很顯著。
但這只是第一步。要真正實現全面減稅,建議制度設計更進一步:
一是通過預算法律,宏觀稅負上限作出明確規定;
二是清理各種非稅收入,很多企業不怕稅,但怕各種莫名其妙的收費,各種名目繁多的收費才是亂。從國際上看,稅收才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渠道,而非稅收入只是一個補充,但目前,各級政府非稅收入所占比例至少都在10%以上,有些地方政府的非稅收入更是高達50%以上;
三是將國務院的稅收立法權盡快回收,并加快很多稅種的法律立法工作,實現稅收從條例到法定的重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