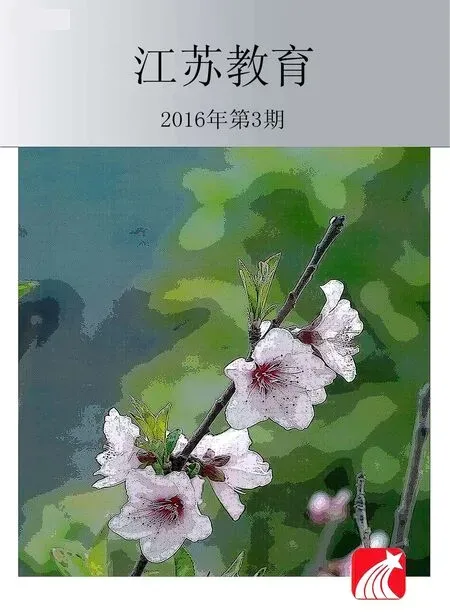“文之藝”與“藝之術”
——對高等書法教育“重技輕道”現象的思考
李彤
“文之藝”與“藝之術”
——對高等書法教育“重技輕道”現象的思考
李彤
目前高等書法教育存在一個較為突出的問題就是“重技而輕道”。本文認為造成這種重技輕道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在當下的社會和文化環境中,許多人對于書法藝術認識的偏頗;其次是教學評價機制以及教師自身素質的缺失;再次,急功近利的工具理性導致了學生在學習中對于“技”與“道”的厚此而薄彼。
高等書法教育;重技輕道
如果說,劉海粟先生在上世紀20年代聘請方介堪、來楚生等人到上海美術專門學校(南京藝術學院前身)講授書法篆刻課程,使得書法篆刻藝術由此走進了現代高等教育的大學殿堂,那么,1963年浙江美術學院(今中國美術學院)設立書法專業,則第一次通過專業的設立,將書法專業納入高校系統,確立了書法在高等教育中的學科地位。自此以后特別是近20年來,高等書法專業教育的發展勢頭迅猛,成績喜人——不僅為書法藝術的發展培養了大量的專門人才,同時,由于高校自身作為研究機構的屬性,也使得它越來越成為當代書法學術一個不可或缺的研究重鎮。在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績的同時,目前我國書法高等教育所存在的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
近10多年來高速發展的書法高等教育可謂一派紅紅火火,但在這熱鬧、繁榮的背后,是不是也有盲目和“大躍進”式的不切實際呢?首先,這幾年設立書法專業的高校日益增多,據筆者的不完全統計,已有100多所,而且還有繼續上升的趨勢;其次就是盲目擴招,據說有些高校的學生人數已達到每個班級近百人,而由此凸顯的問題,不僅是師資的不足,從而使教學水準難以達到高校本應達到的標準,同時,學生生源質量在兇猛的擴招面前也難以得到保證。當然,這些問題并不是我們作為一個書法專業教師所能改變的,相信隨著高校注重抓教學內涵建設,這些問題會逐步得到改善。本文也不打算對此進行更多的評述。
對這些由于宏觀政策以及諸多社會因素所帶來的問題姑且不論,僅就高等書法教育本身來看,也存在著諸多的問題,其中一個較為突出的問題就是“重技而輕道”,這一點,不論是從書法教學的課程設置、教學的評價乃至學生對于各門課程的學習的重視程度都有相當明顯的體現。以至于不在少數的書法本科畢業生,在經過了4年的高等教育以后,除了在書法技法上取得了一些進步,不僅缺乏作為一個書法工作者必要中國傳統文化素養,甚至連基本的專業理論修養也難以達到較高的水準。這決不是筆者夸大其詞,可以說,這樣的情況在當今的書法高等教育中已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一個書法本科畢業生不會寫專業論文已經不再是什么稀罕事,而即便是有些有志于書法的學生,考研究生時在專業理論課考試上所表現出來的水準有時也會令人瞠目。不論是在書法專業碩士還是在博士研究生的考試中,非書法專業畢業學生的書法理論素養高過書法專業畢業生,已經不是個別現象。雖然,所有的學校都更愿意招收理論素養好,且又有相當書法技法水準的書法專業畢業生,但結果在面對書法專業畢業生糟糕的理論素養的情況下,只能選擇非書法專業的學生,這種在考研時,本專業學生競爭不過非專業學生這一在其它學科中少有的現象,在目前全國書法專業的研究生招生中卻不在少數。
造成這種重技輕道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在當下的社會和文化環境中,許多人對于書法藝術認識的偏頗;其次是教學評價機制以及教師自身素質的缺失;再次,急功近利的工具理性導致了學生在學習中對于“技”與“道”的厚此而薄彼。我們認為,這種現象如果不得到糾正,長此以往,不僅有礙于高等書法教育自身的發展,同時也會給書法藝術的發展帶來負面的影響。
一
書法藝術是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朵藝術奇葩。從書法藝術的形成和發展來看,我們可以毫不隱諱地說,書法一直就是文人的藝術,這一點不僅和世界上其它一些藝術門類不同,也有別于中國其它的一些傳統藝術。可以說,不論是在書法藝術觀的形成上,還是在書法藝術獨特藝術語言產生和發展上,抑或是審美品評標準的建立上,都無疑會打上傳統文人的烙印,體現著中國傳統文人的價值觀和審美觀,書法藝術這一文人化的特征,就使得它具有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而當下許多對于書法藝術的誤讀甚至歪曲,無不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缺失有關,而書法藝術之所以有其自身的意義和價值,其實恰恰就在于它蘊含和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如果剝離了文化,如果書法淺薄得只剩下“有意味的形式”,那么,這至少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書法。因此,要真正地理解和學習書法藝術,自然就不能撇開中國的傳統文化。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目前我們的高等書法教育中,重藝術而輕文化,重技法訓練輕文化素質的現象十分普遍,認為只要字寫得好,在書法家中執這樣觀念的人大有人在。其實,在古人看來,只有被稱之為書法家的人,所寫的字才能被稱為書法,僅僅有技法,能將字寫得好,充其量不說是字匠也就是個善書者,唐代有諸多“作字得楷法之妙”,“為輩流推許”的經生,就技法而言,其水準誠如啟功先生所言:“校以著名唐碑虞、歐、禇、薛,乃至王知敬、敬客諸名家,并無遜色”。但即便是《靈飛經》這樣“結體精嚴,點畫飛動,有血有肉,轉側照人”的唐代經生作品,如果不是冠以鐘少京名頭,恐怕都難以書法的名義在書史上留傳下來。更何況,當下的文化生態環境,較之古代,已經有了很大的變異,身處幾乎可以稱作異質文化的我們,假如沒有傳統文化作為根基,可能連對書法的理解都會出現偏頗,又怎么能將字寫得好呢?一幅字就能造就一個書家,甚至會用毛筆寫字就自稱書家,只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神話;然而,正是這一由于對書法和書法家理解上的偏頗所導致的神話,讓許多人把修煉技法看成是成就一個書法家的全部。應該說這是目前高等書法教育重技輕道的最主要觀念上的原因。
二
相對于高速發展的高等書法教育,師資的短缺已成為制約教學質量的主要障礙,許多新近開設書法專業的學校,可以說,是在師資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借著高校規模化的東風匆匆上馬的,師資的的缺乏使得他們只能靠引進和外聘,對于那些沒有書法專業學科基礎的學校,其師資主要有三個來源:引進書法專業的博士碩士研究生;調動或請本校其它專業有一定書法藝術水平的教師任課;外聘社會上的書法家擔任專業教師。應該說,不論是那種類別的教師,只要真正具備書法專業教師水準都是可以勝任的。如果說,剛剛畢業的書法專業的研究生走上高等書法教育的崗位,雖然具備作為一個專業教師的基本素養,但在教學經驗上還有所缺憾,那么,有些后兩類教師的不專業性,至少是在作為一個書法專業教師所應該具備的較為全面的知識結構和技能水平上的某種欠缺是在所難免的。有些人雖然在書法創作上有造詣,但即便是一個一流的藝術家也不一定就可以成為一個一流的教育家,因為藝才不等同于師才,“傳道、授業、解惑”的良師之所以難覓,就在于一個名副其實的藝術教育家不僅要具有一流的藝術水準,更要有淵博的知識和對專業學科全面而深入的認識作為教育的保證,以及具備作為高校教師的教學和科研能力。更何況,由于種種原因,一些社會上的,僅僅能寫一手蠻好看的毛筆字,甚至連字也不能算好看的所謂“書法家”也借著高等書法教育教師短缺的窘迫走進了高校的講壇,再加上外聘教師難以全身心地投入的客座性質。因而,這樣的教師構成,必然會對高等書法教育的質量帶來影響。除了一些有書法學科基礎的高校,從年齡結構來看,大多數書法教師都基本是出生在上世紀60年代以后的,眾所周知,從這一年齡階段所受到的教育和知識結構來看,基本已不可能有較好的中國傳統文化基礎,不要說和老一輩書法教育家方介堪、潘天壽、沙孟海等人相比,就是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從事書法教育,出身于60年代之前的那一輩相比,也有著不小的差距,因此,在對于書法藝術的理解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素養在高等書法教育重要作用的認識往往不夠,甚至有些人自己就認為“書藝”就等同于“書技”,因而,這是目前高等書法教育中存在重技輕道的又一原因。
三
正如前文所說,由于藝術類考生對于文化成績的要求相對較低,一些考生將報考藝術院校當成是上大學的捷徑,因而,有些學生只是沖著大學的文憑而無意于書法本身。就是有志于書法藝術的同學,相對來說,文化素質偏低也是客觀事實。再加上,由于高考指揮棒的作用,讓他們在準備報考書法專業伊始,就有了藝術專業對文化素質要求不高的錯覺,這種無意的誤導,不能不說對他們日后的書法藝術的學習有一定的影響。加之“書藝”就等同于“書技”時風的影響,如果再沒有好的教師的正確引導,在學習過程中的重技輕道也是難免的。
急功近利的工具理性可以說是現代商業社會的一個通病,雖然古人云“字無百日功”,但只要在技法上下一番功夫,進步應該說還是比較快的,如果再在展覽上拿上一個獎,說不定就能帶來個名利雙收,而專業素養、理論研究方面的提高相對于寫字來說,顯然收效要慢很多,寫一百天的字,可能會像模像樣,但讀一百天的書,就想寫出一篇有價值的學術文章基本是不可能的。至于中國傳統文化素養,至少從表面上看,與技法的提高沒有太大的關系,而且收效不明顯,更不能帶來名利,因此,在書法被看成是一個謀取名利或者是稻粱謀的手段或工具時,重技輕道也就理所當然了。同時,重技輕道之所以也被學校乃至教師認可,也緣于這樣做容易快速體現教學成果,使教學質量能較快得到認可,從而在這種默認和默契中助長了重技輕道之風。
以上,我們從三個方面對目前高等書法教育中存在的重技輕道的風氣進行了一些剖析。我們認為只要本著對書法藝術和高等書法教育負責的態度,就應該對此有清醒的認識。
有人在比較中西方藝術時,曾經用了六個字精辟地概括了西方和中國傳統藝術的差別——“藝之術”和“文之藝”,也許,在西方文化為中心的當代,要真正弘揚中國的傳統藝術書法,如果只重技而丟掉了“文心”,那么,書法也就不再是書法了。
J292.1
A
1005-6009(2016)30-0018-03
李彤,南京藝術學院(南京,210013)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藝術學院美術學院黨總支書記、副院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西泠印社社員、江蘇省教育書法協會常務理事,“青藍工程”江蘇省高校中青年學術帶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