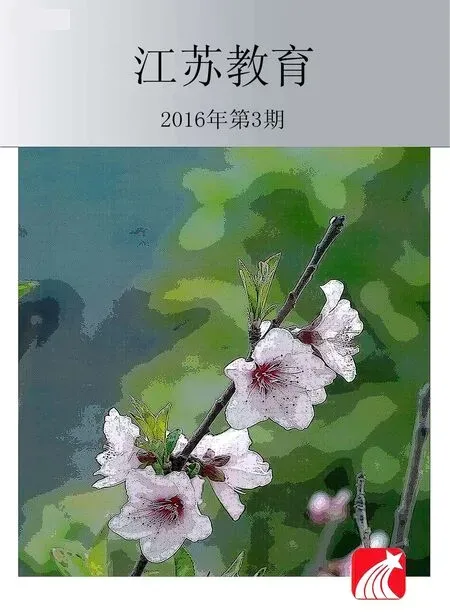論書法教材在實施書法教學過程中的作用
劉研
論書法教材在實施書法教學過程中的作用
劉研
當代書法教育的現實背景下,書法教師必需要在承繼古代書法教育先賢經驗的同時,糾正書法教育固有的誤區,深入研究教材(古代經典碑帖),解決書法教育過程中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合理有效地組織書法教學過程,從而促進書法教學目標的達成,實現教學效益最大化,并實現書法教育的可持續發展。
書法教材;教學過程;教學目標;教學效益;可持續發展
一、書法教學之起源——承續文脈
中國書法以旺盛的生命力,經久不衰,綿延數千年。各個歷史時期的書家燦若晨星,大師巨匠層出不窮。書法本身也逐漸從實用文字的書寫中脫胎出來,成為一種特殊的抒情達意的藝術樣式。這其中固然于歷代書法藝術家們的辛勤耕耘,勇于實踐探索密不可分,我們也更應該看到古代書法教育的不朽功勛。
書法一定是寫字,寫字不一定是書法。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論題。關乎書法教育教學指向性的核心問題,即書法教育教學走向何方?對這一論題的理解是否深刻,決定了書法教育是走向單一的技能技巧的書寫訓練,還是走向“成教化、助人倫”的心性培養的路徑。
回溯到古代教育思想的整體結構中尋求價值,即從一個教育家的角度來看待書法教育。書法教育不僅僅是給學生灌輸書寫技能,增長才藝,更在于以對的心性培養為主體,一以貫之。書法教育只是人文教育的一部分,關乎學生的品格、修養、禮儀與風度,培養嚴謹的學風。培養人的良知,才是人文教育最核心的目的。這等同于學校教育中,不單單只重視知識學習,更重要的是對于“人”的成全。
然而,一切藝術學習皆從模仿開始。技進乎道的境界必先始自于“技”的訓練,書法教學尤其需要讓學習者從書寫技能、技巧上加以操練,并在此過程中達到培養審美、陶冶心性、成全“人”的最終目標。
郭沫若先生在甲骨片中發現練字的骨片,一行十分規整,而另一行則明顯稚嫩,而在其中又有幾個像是老師在旁邊指導或捉刀示范的,這或許就是最早的師父帶徒弟,培養下一代“貞人”的貴族子弟教育方式。殷商時期的“貞人”是其時史官,正是“貞人”的記錄,才使得商代文明得以保留,因而其他貴族子弟才有了學習“典冊”,識字、書寫的機緣。
師徒授受是早期的書法教學樣式,對后世的影響十分深遠,并一直保留至今。在其后的西周、東周、秦漢等各個歷史時期,書法教學呈現不同的樣態,父子之間口傳手授、親友之間相互傳承借鑒,為書法承繼和發揚做出了巨大貢獻。
秦統一六國以后,始皇帝嬴政命丞相李斯對六國古文“罷其不與秦文合時者”,廢除異體,簡化字形,于全國范圍內推行規范文字,作為推行識字教育、書寫教育的教材,頒行全國。這不僅推動了文字的統一,同時也成為漢后諸朝兒童識字習書的先驅。
整個一部書法史,不僅是一部漢字使用與演變的歷史,也是一部書法教育傳承的歷史。
書法發展史是隨著書體的不斷演進,在使用過程中由實用主義逐步走向藝術的自覺,并在不斷承繼的同時,發展創新,從而逐步建立起恢宏的藝術格局。這格局包括筆法、結構、章法等書法作品本體,還包括書法家、書法史、書法美學、書法哲學等書法理論體系,從而形成了環環相扣、互相交叉又互相牽制并井然有序的龐大的立體構架,從而構成了真正意義上的“書法學”。
二、書法教學之目標核心——心性培育
一切教育樣態都以成全“人”為這最終目標,書法教育教學的真正旨歸依然指向教學對象——“人”的成全。在兩千多年的傳統教育里,書法是很重要的教學內容。孔子所言“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書便是其中之一。
書法教育作為民族文化復興的重要途徑,有其必要的社會擔當。書法教師首先要回歸教育家的立場,書法教育的重點在于“成教化,助人倫”。通過書法教育育人,以學生的心性培養為核心。
現在書法教學的方法、形式和手段是多樣化的,形式看好,教育部門也十分重視,仿佛已然萬事俱備了。但實際上它的核心問題卻令人堪憂,首先是社會對書法這個學科的理解有很大偏差,普遍把書法教育看作是一種興趣愛好或者是技能才藝展示,成為附庸風雅的面子“工程”。這種教學目的性使書法的教學的狀態顯得非常尷尬。一方面從實用的角度來說,毛筆書寫已不實用,同時,學生對繁體字與簡體字轉換有隔閡;另一方面,以此來體會傳統文化,很多書法教師又無法以傳統文化之道,一以貫之到學書過程中。
書法教育教學的實施行為必須直接指向書法教學的目標核心。在根據不同教育對象組織教學過程的前期準備階段,書法教育教學內容(教材)的編排便是一個重中之重的問題。教學過程組織因不同施教對象而有所不同,這就是書法教育教學過程中必須要牢牢把握的因材施教的問題。因此,教材的組織編排就要具有循序漸進的科學性,從而順利實現教學行為作為最終的核心目標服務。
中小學階段書法教育是書法教育系統工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最基礎的工程,這是從事書法教育教學工作者的普遍共識。“沒有中小學書法教育,就沒有中國書法的未來。”
書法教育靠的是書法教師。書法教師除了必須具備精研歷代經典法帖的專業素養,還必須具有研究教材、教法的專業技能。在固有的師范院校書法培養目標中即有“三筆字”(即毛筆字、硬筆字、粉筆字)的書寫技能達標。但是,這種純粹以技巧訓練為目標的所謂達標,將書寫純粹理解為技能,而沒有提高到文化的認識高度。書法教育教學必須從靜心習書、培養審美、陶冶性情著手,努力培養教學對象正心誠意的為學處事作風,在細心、認真、專注書寫一手工整秀麗的字跡之外,塑造美好的中國心靈,承繼華夏的文化血脈。
三、書法教學目標達成之載體——教材
為了使這一目標能在組織教育教學過程得以圓滿實現,必然涉及諸如書法作品(碑帖)研究、書法家個案研究、書法技法研究、書法家個體研究、書法美學知識體系研究、書法理論研究、書法史學研究、書法哲學研究等一系列教學內容,即“教材”。
書法教材的設計編排依據,即是幫助不同教學對象在不同階段掌握不同的書法學基本內容的理由。書法教師首先必須具有精研古代碑帖的專業素養和能力,從浩如煙海的碑帖中遴選出適合不同施教對象所需要的教學內容,并能根據遴選出的碑帖合理有效組織教學過程,即“教法”。
對學生而言,“怎么寫”是他們首先想要解決的問題,這要求他們勢必從教材中找到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于是,書法教材研究問題便是呈現給書法教師的第一步問題。歷覽我們學書過程中所見的書法碑帖,都需要教師對這些經典碑帖進行深度剖析、整合、拆解和重新建構。
當然,這樣的做法與“書法教材要超越形而下的技巧解析,傳播傳統文化正道”并不矛盾。即使回溯到古代書法教育思想的整體結構中尋求價值,也要從一個書法教育家的角度來看待書法教育。如果沒有起碼的書寫技巧、技能,何談心性培養?整個書法教學過程的組織實施便是在培養學生不畏難的意志品格,正心誠意的修養、禮儀與風度、一絲不茍的書寫正是在培養嚴謹踏實的學風。教導一個學生的書寫要端莊正確,就意味著教導做人做事要有規矩有分寸,要知書達禮,要行為雅正。如果心性的培養這條主線沒有貫穿下去,所有的書法教育都是片面的。假如脫離書寫技巧技能的操練,書法教育便無異于“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即使是在書法承繼的歷史上影響巨大的書法教材,其呈現的弊端也十分明顯。20世紀80年代,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葉圣陶先生題簽的《中學生字帖》,相信對眾多書法愛好者,甚至是目前奮戰在書法教學一線的書法教育工作者,都曾產生深刻的影響。
這套“四大楷書”教材分別是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碑》、顏真卿《勤禮碑》、柳公權《玄秘塔碑》、趙孟頫《膽巴碑》。這套教材在我國中小學書法教育史上曾起到過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然而,當初筆者作為書法愛好者使用這套教材時就十分困惑,待大學本科四年的教學階段,乃至走上工作崗位之后,這些困惑逐漸隨之迎刃而解。
1.多數學書者都受這一固有觀念的影響:學書先學楷。
書法教材楷書熱銷,篆隸備受冷落,遑論行草。其實,從整個書法史的演進來看,楷書形成于魏晉,盛行于唐代,若要按照這一理論,楷書產生之前的學書者莫非要有足夠的耐心等待楷書產生或成熟之后?而且,楷書的用筆方法甚為繁復,對初學者來說尤為不利,學習過程應該是由淺入深、由簡及繁的循序漸進的過程。
陳忠康在《書法學習的核心問題》中也談到:漢代到魏晉這幾百年中,成熟的書體不是楷書,而是草書。也就是說,魏晉人學書法,面對的是一個成熟的草書系統,而不是如宋以后,面對的是一個成熟的唐楷系統。這樣差距就出來了。草書對于楷書來說,更加自由開放,從草書化到行書,行書必定具有草書的品格。所謂古法,就是一套從草書中化出來的筆法系統。而宋以后,學書先學楷書的做法成了書法的常識,也可以說是偏見。
2.楷書的筆法系統甚為繁復,包括此套教材在內的諸多書法教材中,大家印象深刻的莫過于對筆法教學進行圖示的筆鋒行進路線圖。從雙鉤的筆畫中間加一條帶有筆鋒行進方向的虛線,筆鋒轉換處還有重重的黑點加以提示。然而,稍微具有基本書寫技能技巧的教師應該對此深感疑惑。筆鋒的連貫運動是要結合提按進行的平動和立體運動的結合,這種運筆的運行軌跡都是平動的細線,假如按照其運行軌跡行筆而不加筆鋒提按的教學示范,必然是滿紙“墨豬”。相反篆隸筆法相對簡單易操作,為何趨簡而就繁,舍本逐末,事倍而功半呢?
3.筆畫訓練目標即是在有經驗的書法教師指導下得以順利實現,接下來的筆畫訓練與單字之間的承接關系之弊端便更加明顯。主要表現在單字范例的選擇上:如“橫畫的訓練”單元,其范字選擇盡量不要涉及尚未學習過的“豎”“點”“撇”“捺”等。然而,我們所見的內容卻并不理想,如“橫畫訓練”單元范字練習中出現了“上”“下”“言”等字例,相信大家在年少發蒙習書時曾經因此而倍感苦惱。本來這節課的訓練內容是“橫畫練習”,結果習題中卻又出現了“豎”“折”“點”等尚未學習的筆畫,雖然這樣方便教材編寫,但卻著實苦了一線教師。
教學過程中的一整套嚴謹有序的涉及方案是具有其符合教育教學規律的內在邏輯規定的,而這種草率的范例選字造成了教學過程的秩序破壞,從而使教師的課堂教學效果不能按照既定方向合理、有序、有效進行,學生們也因陌生技法的干擾影響整體的習書效果,使得技法學習的思路變得模糊,不利于本單元教學目標的順利達成。
4.不管是哪一種碑帖的教材編寫,勢必破壞作品的整體章法,不利于學生對作品整體氣象的把握,同時,古代碑帖范本原拓,一般是可以句讀,具備可識讀性的完整文章,即使因為歷史久遠、風雨剝蝕、自然破壞漫漶而缺失或殘損,但仍有大部分內容可以給學習者以美的熏陶和感染。結構拆解后的重新梳理雖然有助于學習者對筆法、結構的訓練,但勢必會破壞原帖的精神風貌,因此,要求書法教師應當具備相應的專業素養,能做到整合、拆解運用自如,并能根據教學進度,合理有序安排教學過程。
綜上所述,書法教育教學的目標能否順利、有效達成與教材是否按照科學的邏輯順序編排具有十分密切的關聯,這勢必要求書法教師在理解、把握碑帖的整體精神風貌,能動地把握好將碑帖拆解、整合成有效教材上,提出了更高的專業要求。有經驗的教師可以嘗試自編教材,并根據施教對象的不同,合理安排教學過程,有效提高學生的學習效果,實現教學效益最大化,進而實現書法教育的可持續發展。
[1]汪永江.中小學書法教育要以心性培養為核心[V].中國美術報,2016.4.18.
[2]黃惇.中小學書法教育之我見[J].江蘇教育(書法教育),2016.1.
J292.1
A
1005-6009(2016)30-0061-03
劉研,江蘇省錫山高級中學(江蘇無錫,214000)書法篆刻教師,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教育學會書法教育專業委員會會員,江蘇省國畫院書法藝術研究院特聘書法家,江蘇省教育考試院書法水平等級考試委員會高級培訓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