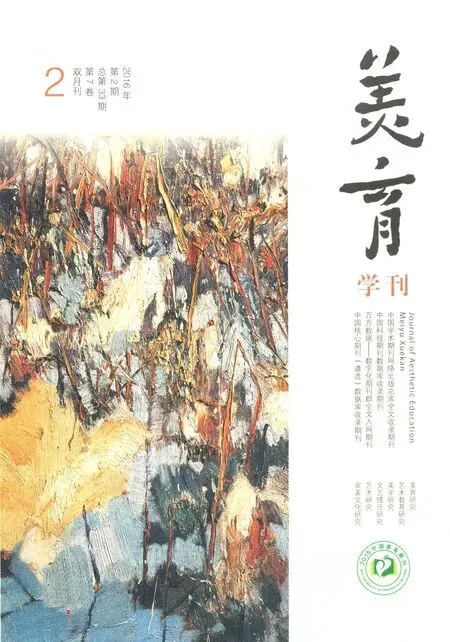論席勒的“游戲說”
羅 雙
(武漢大學 哲學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
論席勒的“游戲說”
羅雙
(武漢大學 哲學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摘要:游戲是席勒美學思想的核心語詞。席勒通過對游戲的規定和闡述形成了他的“游戲說”,成為西方思想史上關于游戲最經典的言說。在《審美教育書簡》中,席勒在人性的基礎上建立了游戲的特殊規定,游戲不僅是自由的游戲,還是審美的游戲。席勒根據這一規定把游戲應用到審美王國和審美教育之上,使游戲指向自身以外的人和世界。然而,也正是由于這一規定使游戲形成了自身的邊界,我們必須在界限之內正確看待席勒的“游戲說”。
關鍵詞:席勒;游戲;美;人性;審美教育
一、何為席勒的“游戲說”
游戲是人類共有的一種存在現象和生存狀態,為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所關注和研究。一提到游戲,人們通常會聯想到兒童的嬉戲和玩耍,在這個意義上它成為童年時代的標志性活動,孩子們在其中感到無拘無束和無憂無慮。推而廣之,只要擁有和兒童玩耍時一樣的心靈狀態,人生的任何一個階段和時刻都可以描述為游戲,甚至整個人生都能被看作游戲的人生。不僅人的世界充滿著游戲,物的運動也能給人以游戲的感覺,成為人欣賞的對象,甚至在最高的層面和最大的維度上,宇宙萬物的生命活動也能貼上游戲的標簽。然而,不管游戲以何種形態呈現出來,它們都能給人帶來游戲的感覺,也就是說它們的活動始終要和游戲的內涵保持一致。
正因為游戲的諸多存在形態賦予了自身以多重的語義和應用,才引起思想家們對它的內涵進行規定的興趣,這樣就形成了各種各樣關于游戲的言說。在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把游戲規定為人工作之余的休息,使之成為持續和高效工作的手段。近代,康德把游戲規定為人的認識能力之間自由和諧的運動,即人在審美時呈現的自由狀態。現代,斯賓塞把游戲規定為人出于本能的對于過剩精力的發泄,認為游戲有益于個體和民族的生存。直到后現代,伽達默爾改變了傳統的從游戲者即人出發論述游戲的方式,提倡回到游戲自身,把游戲規定為游戲的自我表現和存在方式。不同的“游戲說”展開了游戲的不同層面,有從游戲的對立面來界定游戲,有從理性的認識或非理性的本能來規定游戲,也有從游戲自身的存在來闡明游戲,但思想家的言說不是為了掩蓋而是揭露游戲的本質,他們是在游戲的基礎上建立起自己的“游戲說”。
游戲的形態是多樣的,但游戲的本質是唯一的。為了直觀地呈現游戲的本來面目,以便理解游戲的本質規定,我們有必要對“游戲”這一語詞作詞源學的解釋。在漢語中,游戲一詞由“游”和“戲”構成。游和水中的魚有關,表示“一種隨意的和自如的身體活動”[1];“戲”主要是指人的嬉戲活動,同樣有著身體和心靈的自由。游戲超越了現實和思想對人的限制,使人宛如水里自由游動的魚。在西方,“游戲”在英語中被表述為play,在德語中被表述為Spiel,都有玩耍的基本語義,玩耍是一種游戲規則較隨意的自由活動。除了含有玩耍的意義外,游戲還特指賭博和競賽,它們沒有玩耍的隨意性,必須遵守嚴密的游戲規則,但在規則之內仍然有選擇的自由。可見,自由始終伴隨著游戲,沒有自由可言的游戲不是游戲。如果把自由界定為游戲的本質,就有了自由游戲的表達,于是“游戲”在英語中就被變為free play,在德語中就變為Freispiel。可見,游戲的世界是一個蘊含著無限可能性的自由世界,自由是人在游戲中最渴望得到的感覺,也是游戲最明確的內涵。游戲也正因其自由的本性,吸引著思想家們的注意和興趣。
對于一生追求自由的席勒來說,游戲自然成為其思想的重心。席勒對游戲的規定和闡述就構成了他的“游戲說”。席勒的“游戲說”既是康德游戲思想的直接繼承,又構成了斯賓塞游戲思想的前身,因而它在游戲的思想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文本來說,席勒對游戲的言說雖然聚集在《審美教育書簡》的第十四封信、第十五封信和第二十七封信中,但一個完整的游戲說必須依托于《審美教育書簡》這個思想整體。整體的思想道路造就了席勒“游戲說”的獨特性和明晰性,使之在游戲的解釋脈絡中不被遺忘和替代。在《審美教育書簡》中,席勒一方面把游戲置于人性的歷史語境中,使游戲成為實現人性完滿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又把它和美聯系起來,使審美教育成為改造人和世界的主要手段。在人性的背景和審美的光環下,席勒對游戲有著特殊的規定,不僅最為接近游戲的純然本質,而且最大程度地發揮了游戲的功能。席勒的“游戲說”奠定了游戲在社會和藝術中的地位,導致對游戲的分析在現代思想中越來越受歡迎。
本文以席勒為思想的主體,以游戲為思想的線索,圍繞游戲的起源、本質和功能,通過揭示席勒“游戲說”的基礎、核心和應用來探究席勒“游戲說”的思想脈絡,指明席勒“游戲說”的思想界限,從而使席勒“游戲說”的完整面貌得以真實地呈現。
二、席勒“游戲說”的基礎:為何游戲
席勒的“游戲說”不是憑空出現的,它的產生經歷了一個順理成章的思想過程。人是席勒思考游戲的出發點,因為人要游戲是游戲存在的內在根據,而且這種需要不僅是人性的先驗要求,更為重要的是人性的現實需求。席勒的思想主要來源于康德,尤其是他的“游戲說”直接繼承了康德對游戲的規定。他們把思想立足于人性的考慮,但與康德把人性理解為人的心意諸功能的活動不同,席勒對人性的運用則超出了心靈的范圍,人性被視為人的現實狀況和本然狀態,即人性的分裂和完滿。
(一)人性的現實需求
席勒首先從人性的現實狀況出發,并以希臘的人性為參照,發現了現代社會不可避免的人性分裂現象。希臘人是席勒理想人性的代表,因為他們“同時擁有完美的形式和完美的內容,同時從事哲學思考和形象創造,同時是溫柔而剛健的人,把想象的青春性和理性的成年性結合在一種完美的人性里”[2](第六封信)。由此可見,希臘人擁有完滿和完美的人性,他們雖然就個人而言是作為個體而存在的,卻能以其完整的人性成為一個時代及其民族的代表。與此相反,現代人由于科學和勞動的分工,導致了人性的內在結合被撕碎,從而“永遠被束縛在整體的一個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就把自己培養成了碎片”[2](第六封信)。每個人只能分有人性的碎片而成為單個的存在,也就失去了作為整體存在的可能性。
人性的分裂現狀產生了對人性重歸完滿的需求。此時,席勒把游戲作為治療人性分裂癥的良方加以推出,因為“只有當人是完整意義上的人時,他才游戲;而只有當人在游戲時,他才是完整的人”[2](第十五封信)。游戲意味著人性的完滿,可以讓人體驗到實際生活所欠缺的生命充盈的滋味,是造就完整的人的必要條件。希臘人無須借助游戲的外在力量就能成就完整的人性,因為他們的生活世界本身就如同游戲的世界,游戲內在于他們的自然本性之中。現代人的游戲本性卻被自身所遮蔽,游戲的缺席使人的感性和理性相分離,人被培養成為一個孤零零的碎片,因而迫切需要外在的游戲活動來喚醒人的游戲本性。在席勒的思想中,這一外在的游戲活動表現為以藝術或美為對象的審美活動。“藝術的游戲允許世人,聚集破碎的力量,在微末中成為某個整體,一種全部,即使僅在短暫的瞬間和有限的藝術美的領域。”[3]游戲使人容易發覺和經驗到自身的完滿性,因而游戲的過程就是整合人性碎片的過程。隨著游戲活動的不斷發生和日益深化,對自身完滿的經驗就會慢慢變為一種享受和沖動,促使游戲成為人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甚至全部,從而徹底激活人的游戲本性。游戲本性在人身上的激活,也就意味著人性又回復到完滿的狀態。
可見,席勒把人性特殊化為人的游戲本性,所以人性的分裂就是游戲本性的遮蔽,人性的完滿就是游戲本性的顯現。游戲始終伴隨著人性歷史變化的全過程,希臘人的人性是游戲本性的顯現,現代人的人性是游戲本性的遮蔽,而游戲本性在游戲中的覺醒又意味著人性復歸完滿,所以人不但不能離開游戲,而且還要主動參與游戲,在避免人性分裂的同時提高人性的完滿度,以求達到希臘人那樣完美的程度。
(二)人性的先驗要求
人對游戲的需求不僅有著歷史和現實的原因,還源于人性的先驗結構。在論證游戲的先驗存在時,游戲被表述為游戲沖動。席勒“游戲說”的主體就是關于游戲沖動的論述。沖動是推動人把自己的本性對象化為現實的內在動力,游戲沖動就是人對游戲活動的欲求和渴望,它根植于人的游戲本性,并影響著人的思想和行動。
人性對游戲的先驗要求來源于席勒對人性的先驗劃分。席勒認為人身上可以區分出兩種不同的天性,分別是固定不變的人格和變動不居的狀態,由此產生了對人的兩種相反的要求:一個要求把世界的物質多樣性歸入統一的形式中,這是人的理性和道德本性,由人格所規定;一個要求把形式的一致帶入物質世界的變化中,這是人的感性和自然本性,以狀態為根據。當這兩種本性試圖對象化為現實時,形式沖動和感性沖動便應運而生,驅使著人分別去滿足這兩種本性的要求。因此,形式沖動要求保持人格的恒定,感性沖動要求推動狀態的變化,人在同時滿足這兩種沖動時就會遇到矛盾,畢竟恒定和變化是對立的兩極。所以,由于兩種沖動自身的限制和規定,僅憑它們不可能實現人性的完滿,甚至還可能導致人性的分裂。
雖然這兩種沖動的要求看似對立,不可調解,但席勒認為“這兩種沖動從本性上并不是相互對立的;如果它們無視這點而依然顯得對立,那么只是由于它們本身誤解了自己,并搞亂了各自的范圍,因而任意違背了本性才出現這種情況的”[2](第十三封信)。所以,形式沖動和感性沖動本應是安分守己的,它們在各自的邊界內從事規定好了的活動,一般不會相互爭奪和碰撞。形式沖動雖然要求保持人格的恒定,但并不要求狀態也一同固定不變;感性沖動雖然要求推動狀態的變化,但并不要求變化擴展到人格的領域。但是,界限的模糊和混亂導致了二者的越界和斗爭,當一方超出界限占領對方的領地并成為決定性的沖動時,沖突和強制就產生了。如果形式沖動成為決定性的沖動,人就要受理性和道德的強制;如果感性沖動成為決定性的沖動,人就要受感性和自然的強制。因此,為了擺脫人的雙重強制,實現兩種沖動之間的和平相處,必須要有一個確定并保持其界限的存在。
這時,“理性出于先驗的理由提出要求:在形式沖動和感性沖動之間應該有一個集合體,這就是游戲沖動,因為只有實在與形式的統一,偶然性與必然性的統一,受動與自由的統一,才會使人性的概念完滿實現。”[2](第十五封信)游戲沖動作為形式沖動和感性沖動的集合體,它的任務就是通過在形式沖動和感性沖動之間設置一個和平相處的中間地帶,避免兩種沖動的直接碰撞,讓它們在游戲的范圍內自由地實現對象化。因為游戲沖動同時滿足了它們的要求,因而它們所有的對抗性特征得到拋棄,互補性特征得到保留。于是感性和理性作為互補的兩種天性,感性沖動和形式沖動作為互補的兩種沖動,在人身上和諧地并存,實現了人性的完美結合。“游戲沖動是人性先驗概念必然調和的結果,是抽象概念在自我身上發展的最終旨歸,正是依靠和諧這一概念,席勒才將人性的先驗分析引向了美學領域。”[4]
即使這兩種沖動沒有發生越界和沖突,如果人僅僅單獨地滿足一種沖動,或者相繼地滿足兩種沖動,那么人也不是完全意義上的人,因為人性在某一時間內只有人格或狀態,而不是人格和狀態的結合。無論在哪種情況下,人性的完滿都會在人身上喚起游戲沖動,以便讓另外兩種沖動在它之內同時發生作用和同時得到滿足。所以,如果沒有游戲,無論是先驗的人性,還是現實的人性,都會發生分裂的狀況。而有了游戲的本性和沖動,人就有了完滿和完美的人性。
三、席勒“游戲說”的核心:與美游戲
游戲對人性的積極作用是游戲存在的內在根據,這構成了游戲說的基礎,席勒由此展開他對游戲的論述。但游戲之所以能成就完滿的人性,既來源于人性的需求,又根植于游戲的本質,而后者更為根本。因為游戲的本質支撐起游戲的存在和價值,所以席勒對游戲的本質規定構成了游戲說的核心。席勒對游戲有其特殊的規定,游戲不但是自由的游戲,而且是審美的游戲,純粹的游戲只存在于美和藝術之中。席勒認為以物質對象為目標的現實游戲不是理想的游戲,理想的游戲根植于理想的美,只有與美的結合游戲才是真正的游戲。
在感性沖動和形式沖動中,人是身不由己的,他不是遭受自然法則的強制,就是遭受理性法則的強制,沒有自由可言。但是,作為感性沖動和形式沖動集合體的游戲沖動,就會同時從感性和理性上強制心靈。正因為它使心靈在兩方面都受到強制,因而同時也在兩方面揚棄了強制,從而使人不僅在感性方面而且在理性方面都達到自由。反過來說,也正因為游戲沖動消除了感性沖動和理性沖動的強制,才使它既與感性的興趣相調和,也與理性的觀念相一致,從而使二者在游戲領域內結合起來,實現人性的完滿。馬爾庫塞也認為游戲“并非旨在同某物嬉戲,毋寧說,它是生活本身的游戲,它超越了匱乏和外在的強制,它是沒有恐懼和煩惱的實存的顯現,因而就是自由本身的顯現。”[5]因此,游戲作為自由的顯現,超越了感性和理性的對立和強制,不僅把人的完整性歸還給人,還恢復了人的自由。
游戲沖動能把感性沖動和形式沖動結合起來,除開歸功于自由的本質之外,還因為游戲內含美的因素。席勒通過沖動的對象把游戲和美聯系起來,他認為感性沖動的對象是生活,即一切呈現于感官的物質存在;形式沖動的對象是形象,即一切呈現于思維的形式特性;而游戲沖動的對象是生命的形象,即一切廣義上成為美的東西。美作為游戲沖動的對象,同時也是感性沖動和理性沖動的共同對象,因而生命的形象既有感性沖動的生命力,也有形式沖動的形象感。游戲作為同時容納感性和理性的場所,它使人的生命取得理性的形式,而形式在他的感覺里活著。“形式不是生命之外的某物,而是生命的核心,它是生命的客觀化形式。反之,生命也不在形式之外,它構成被形式所作用的內容,因而它是關于形式的間接的認識。”[6]212所以,在美的東西中,他的形象就是生命,他的生命就是形象。生命和形象在作為對象的美中的結合,從而導致感性沖動和理性沖動在游戲沖動內的結合。
為了實現人性的完滿,席勒強調“人應該僅僅與美進行游戲”[2](第十五封信)。美作為生命的形象,既不可能是生命的全部,也不可能是純粹的形象,因而是生命和形象的完美融合。美的這一雙重屬性擺脫了單一屬性的強制,既通過形象顯現了生命,也憑借生命豐富了形象,使美以自由和諧的面貌表現出來。“與美游戲”是席勒同時對美和游戲作出的規定:一方面,審美不是嚴肅的活動,而是自由的游戲;另一方面,游戲不是人與人或人與物之間的現實活動,而是特指以美為唯一對象的審美活動。審美和游戲的同一彰顯了二者的共同本質,即自由,所以“美和游戲沖動之間的兩座實在的橋梁就是,它們都具有擺脫實用目的的共同自由”。[7]在游戲、美和自由的三者關系中,自由是聯系游戲和美的橋梁,游戲是審美的自由活動,而美就是游戲的自由顯現。
在席勒的思想世界,自由是游戲和美的共同規定,而游戲和美是相互規定,由此可見自由與美是游戲的雙重本質規定。這也是席勒的獨到之處,雙重的規定構成了對游戲的雙重限定。其中,自由割斷了一切對游戲的束縛之網,顯示出游戲在生活世界的超然地位;美則劃清了純然的游戲和日常游戲的界限,表達了游戲的審美特征。它們最大限度地清除了游戲的雜質,使游戲呈現出純然和本源的面貌。
四、席勒“游戲說”的應用:審美教育
在《審美教育書簡》里,席勒思想的落腳點不是游戲而是審美教育,游戲只是審美教育的出發點。這就如人性是游戲說的出發點一樣,人性的分裂和完滿要由游戲來規定,游戲的功能最終也要落實到審美教育上。不過席勒在這中間設立了審美王國這一過渡,使得思想的道路顯得更為通暢。
游戲對于席勒來說是一種審美的游戲,它為了自身的普及和強化,召喚著審美王國的建立。“在力量的可怕王國的中間以及在法則的神圣王國的中間,審美的創造沖動不知不覺地建立起第三個王國,即游戲和外觀的快樂王國。”[2](第二十七封信)“游戲和外觀的快樂王國”也就是審美的王國,因為游戲沖動的對象是美,而美在很大程度上顯現為外觀的美,美的欣賞和體驗必然又會帶來快樂,所以審美王國也是游戲和外觀的快樂王國。這句話包含了建立審美王國的基本要素。首先,它是處在力量王國和法則王國的中間,由力量王國發展而來,又向法則王國發展而去。其中,盲目力量控制的王國是自然王國,是由感性沖動建立起來的;法則控制的王國是理性王國,是由形式沖動建立起來的。正如審美王國和游戲一樣處在中間位置,它的作用也如同游戲的功能,是為了防止兩個王國越過邊界和發生沖突而建立的和平地帶,它們的存在都是為了調節和平衡。其次,它是由審美的創造沖動建立起來的。審美的創造沖動即游戲沖動,它是建立審美王國的力量源泉,這就決定了“在審美王國里,人與人只作為形象來相互顯現,人與人只作為自由游戲的對象面面相對。通過自由來給予自由,是這個國家的基本法則”[2](第二十七封信)。所以,在審美的王國之內,不僅自然物以美的形象向人顯現,而且游戲的人之間也以美的形象相互呈現。審美的游戲使人擺脫了一切力量和法則的束縛及強制,把自由歸還給人。最后,它是逐漸建立起來的,不是一蹴而就的,畢竟游戲沖動和審美意識需要萌芽和發展的過程。雖然我們不知道這一過程最終要經歷多長時間,但審美王國自然王國已瓦解,理性王國未完成時必然產生的過渡形態,是人類擺脫力量和法則束縛的必然選擇。現在席勒把建立審美王國的任務提出來了,我們就應該發現和完善它的存在,發揮它對人性的積極作用。
作為從自然王國到道德王國的過渡,審美王國是對游戲功能的顯現和擴展。游戲的基本功能是調節人性,使人性完滿,所以“席勒所謂人在其中意識到審美體驗的那種審美狀態是康德哲學的調和傾向的一種連續”[6]212。不過,康德哲學的調和作用局限于抽象的人性,而席勒通過審美王國把這一調節作用從內在的人性擴展到現實的王國,從而游戲不僅能改變人性,還能改變現實。游戲功能到擴展現實領域,不是僭越,因為這沒有超出游戲自身的邊界,現實的改變是建立在人的改變基礎之上的,而人的改變是在游戲的職責范圍之內的。因此,審美王國不是由自身建立根據,而是由王國的公民憑借游戲沖動逐漸建立起來,并隨著藝術的發展而不斷拓展疆域。
要進入審美王國,就必須學會如何去游戲,而游戲是與美游戲,所以審美的教育是成為審美王國公民的必要條件。審美王國的公民必然是審美的人和游戲的人,所以審美教育就是通過美的實踐引導人成為審美的人和游戲的人,也就是發現人自身美的本性和游戲的本性。席勒認為,這一實踐的工具就是藝術,人的本性也是在藝術那不朽的典范中開啟的。席勒之所以選擇藝術作為審美教育的實踐工具,是因為它是最純粹的審美和游戲活動,從而也是最有效的教育手段。藝術作為審美的游戲,它擺脫了一切功利和道德的束縛,自身就包含著美和游戲的純然本性,從而能以其純然本性直接喚起人的本性。通過藝術的實踐,人既可以學會以美的形象顯現自身和世界,成為審美的人,也可以學會用游戲的態度對待自然和社會,成為游戲的人。
因為審美和游戲的人是自由和完整的人,所以歸根結底,審美教育的目的就是揚棄人性的扭曲和分裂,培養自由和全面發展的人。這個理想的人不再是康德思想中的抽象的人,而是活生生的人,這使席勒的研究超出了理論的范圍,進入到現實的領域。席勒在第二封信中指出:“為了解決經驗中的政治問題,人們必須通過解決美學問題的途徑,因為正是通過美,人們才可以走向自由。”由此可見,席勒不僅把審美教育作為恢復完整人性的必要手段,而且作為實現人在政治上自由的主要途徑。將審美教育和人性的完整和政治的自由結合起來,這在西方思想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席勒在把審美和游戲應用到現實的同時,也開辟了一個新的教育方式,對近現代教育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審美的教育不同于知識的學習和技能的訓練,不是將外在的東西轉化為自身的內在所有,而是直接喚起內在于人的游戲本性。游戲本性是和諧、自由和快樂的本性,它“能把人性自身的和諧帶入社會,使人無論是在和自然的交往還是與人群的交往中獲得一種真正的自由和快樂,這種交往同樣源于人的天性的自由顯現,而不是一種強制性的義務”。[8]人把游戲本性帶入社會,實現社會交往的和諧,審美教育就有了社會意義,成為改造不完善的人和世界的理想手段,這也是席勒建立審美王國的最終目的。
五、席勒“游戲說”的界限
席勒的“游戲說”是哲學史上第一次對游戲的系統解釋和論述。在席勒的思想中,游戲關聯著生活世界的諸多方面,比如人性的歷史發展、國家的歷史變遷和人的存在狀態等,對人的完善和世界的改造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席勒對游戲的特殊規定,他在把理想的游戲與現實的游戲劃分開來的同時,也不自覺地給自己的“游戲說”確立了界限。
首先,游戲的概念沒有現實的意味。席勒的游戲不是現實的游戲,而是作為理想的藝術游戲。從人的本性和沖動出發,席勒在感性和理性之間直接設定了游戲的存在,并且把游戲的對象限定為美,使游戲無論從其產生過程還是活動本身來看,都不具有現實的意味。雖然藝術和美是現實的,但游戲是人和藝術之間一種理想關系的建立,排除了一切現實的功利態度。所謂的游戲本性和游戲沖動,也是理想的人性的表現。一般而言,人身上都具有感性、理性和游戲三種本性和沖動,它們的綜合統一才構成了完整的人,但人在某一時間內只會傾向其中的一種,從而區分出特殊的人性。因此,席勒對人性的劃分合情合理,但現實的人不必執著于此,我們所要做的就是通過藝術的游戲完善自身。
其次,游戲和美的王國不是普遍地存在于現實生活。從人的生活世界出發,席勒在自然王國和道德王國之間構建了游戲和美的王國。審美王國被席勒看作游戲的理想環境,因為既沒有任何對人的限制,也排除了一切對對象的束縛,人與對象的關系只有一種——游戲或審美的關系,這一關系給予了人最大的自由。然而,真的存在這樣一個美的王國嗎?席勒回答道:“按照需要,它存在于任何一個情緒文雅的心靈之中;而按照實際,就像純粹的教會和純粹的共和國一樣,人們大概只能在一些少數精選出來的社會團體之中找到它。”[2](第二十七封信)從空間上說,審美王國雖然為人性所需要,存在于理想的心靈中,但現實中并不存在一個普遍的審美王國,它只能在理想的精英團體出現。從時間上看,我們不是每時每刻都能處于游戲的狀態,也就不能在審美王國中長久居住,生活世界還有其他的組成部分。既然席勒的審美王國是由審美的創造沖動建立起來的,也就意味著審美王國在沒有創造沖動的支撐下是無法存在的,現實的生活不總是審美的。
最后,審美的教育不能普遍地解決一切現實問題。在席勒之前,人的培養全部憑借知識的積累和技能的訓練,這是對人性的強制和束縛,也是導致人性分裂的主要因素。在席勒提出審美教育之后,西方教育開始注重培養完整的人,藝術課程逐漸進入教學的視野,人性有了自由發展的空間,這就是席勒美育思想的現實影響。即使如此,審美教育也不可能解決所有的現實問題,至少不能解決政治自由的問題。藝術的游戲雖然能潛移默化地改善人性,但現實的改造依然需要物質的手段。如果把游戲絕對化為改變現實的唯一方法,那么游戲的霸主地位必然導致審美王國的瓦解,因為游戲和美不是審美王國的全部,除此之外還有更廣泛的生產實踐,它們才是改變現實的直接作用力。
總之,席勒的游戲是人與美的游戲,席勒的“游戲說”是游戲的美學闡釋和美的游戲闡釋,但無論是游戲還是美最終都關乎人的自由。所以,“游戲說”是為了人并通過人而實現人的自由的美學理論,它自身是思想的言說,卻指向自身之外的人和世界。但是,游戲的現實作用畢竟是有限的,我們在關注席勒“游戲說”的創新和影響時,也要認識和保持它的界限,不能把游戲絕對化為拯救現實的救世主。
參考文獻:
[1] 彭富春.哲學與美學問題——一種無原則的批判[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51.
[2] 席勒.審美教育書簡[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
[3] 呂迪格爾·薩弗蘭斯基.席勒傳[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379.
[4] 雷武鋒.論席勒的審美游戲說[J].武漢科技學院學報,2002(4):10-12.
[5] 馬爾庫塞.審美之維[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53.
[6] 維塞爾.活的形象美學[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0.
[7] 鮑桑葵.美學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383.
[8] 盧世林.美與人性的教育——席勒美學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4.
(責任編輯:紫嫣)
On Schiller′s "Theory of Play"
LUO Shuang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Play is a core concept in Schiller's aesthetic thoughts. Schiller has established his theory of play by formulating and expounding it, and it has become the most classical discourse about play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s. In his 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 Schiller establishes the special rules which characterize play as not only free but also aesthetic. By this characterization, Schiller applies play to the aesthetic domain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enabling play to point to the man and the world outside the self. However,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play forms its own frontier which our discussion of his theory of play must not overstep.
Key words:Schiller; play; beauty; humanity; aesthetic education
中圖分類號:B83-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5-0012(2016)02-0019-07
作者簡介:羅雙(1991—),男,安徽合肥人,武漢大學哲學學院美學專業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西方美學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