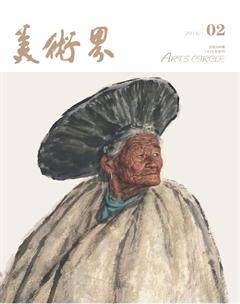“太行山畫派”命題的可行性分析
郭孝波
[摘要]中國古代畫派的界定標準應具備風格相近、傳承關系一致、擁有權威性開派人物三個條件。文章從“畫派”的概念、界定標準等幾個方面進行分析比較后,認為以太行山為創作主題的現代畫家們并不具備形成“太行山畫派”的條件。
[關鍵詞]太行山畫派;傳承關系;開派人物;畫派風格
當代以地域性命名的“畫派”逐漸出現,較突出的有:陜西黃土畫派、黑龍江冰雪畫派、廣西漓江畫派等近20個之多,其現象的存是值得深入研究。可以看出,當今“畫派熱”這種“新的亂象”正是中國文化走向開放、多元化的一種體現。
真正從理論上系統地為“畫派”界定標準的當屬俞劍華在《揚州八怪的承先啟后》(1962年)一文中對“畫派”所作的論述,“系統地總結了中國畫派的形成、發展、滅亡的自然規律,……明清以來的各地方畫派都由史論家加以命名的。”對于畫派的界定標準,周積寅繼承了俞劍華的觀點:“凡是研究中國畫史畫派者,均會將畫派形成的客觀自然規律——開派人物、開派人物與骨干人物的傳承關系、風格相近等寫進定義中,這是最基本的常識。”
本文認為應用發展的眼光去看待“標準”本身,也就是“標準”本身所具有的時代性,脫離時代的特點必然會變得僵死。因此,關于“畫派”的理解,堅持引用上文所提到的“畫派”所具備的三個條件,以發展的、時代的眼光,對“太行山畫派”命題的可行性進行分析。
一、開派人物
“權威性的開派人物”是“畫派”形成的前提。五代荊浩隱居太行山洪谷,成為北方山水畫派的創始人,其傳世作品《匡廬圖》應是以北方太行山地域性地貌特征為參考的,其后以表現太行山為題材的畫家和作品甚少。至20世紀60年代,太行山又進入了畫家的視野,開始涌現出一大批以表現太行山主題創作的畫家和作品,較突出的畫家有賈又福、呂云所、張俊、白云鄉、白聯晟、李明等,他們深入太行山深處,觀察表現太行山的地貌特征,對太行山產生了特殊的情感,將自己的創作重心置身于太行山。所列畫家分別畢業于不同美術院校,早年都學習古代傳統技法,后師法自然,形成了自己的繪畫風格,并不存在相互間的師承關系,應歸為“并稱畫壇的名家”,各位畫家作品風格迥異,在技法表現上多以“積墨法”為主,以反復皴染表現太行之深厚、雄壯之感。至于各位名家門下學生,有的沿襲老師的風格面貌和表現技法,與其師畫風基本一致,缺少創新;有的稍作變化,雖不完全沿襲其師技法,有所創新,但更多則脫離了太行山主題創作。因此,從“畫派”的角度,缺少開派性的領軍人物。
二、傳承關系
以太行山為創作主題的畫家們,皆從傳統而來,相互間基本談不上師承,如果說有一定的師承,那或許都遠承五代荊浩,荊浩、關仝作為“歷時性的畫家傳派”的北方山水畫派的開派者,為其后表現北方山水奠定了理論與實踐的基礎,創造了能表現北方地域性特征的全景式大山大水的構圖樣式,開創性地加入“皴法”(刮鐵皴),開創了“崇山峻嶺、層巒疊嶂、氣勢雄偉而壯觀”的北派山水畫風。荊浩長期隱居太行洪谷,深入觀察并“寫松數萬本”,創作來源于太行山。從五代至20世紀中葉,除荊浩《匡廬圖》之外,皆沒有明確表現太行山的作品。直至20世紀60年代始,太行山主題創作進入藝術家們的審美范疇,他們深入太行山研究和嘗試表現太行山的筆墨技法。如果從傳承角度而言,中國古代的文化傳承方式很重要的便是師徒間的授業方式,言傳身教,可以最直接地將某種文化思想或技藝技能傳授給徒弟。而對比近現代,學院還保留了多少這樣的師徒傳承方式,畫家們接受現代社會的教育模式和利用先進的印刷技術手段,打破了中國傳統相對封閉的師徒傳承方式,開放性的教育模式,可以提供廣泛深入學習各朝各代、各家各派的傳統技法和風格的條件,這也就模糊了嚴格的師承關系的界限。如果“畫派”的標準還嚴格遵守古代那種師徒傳承的標準,那么近現代就不可能再出現某一“畫派”。
從現代畫家表現太行山的作品的整體技法來看,多是以“積墨法”為主,強調筆墨的反復皴染。“太行山”的這種地域性的自然特征,也反過來影。向到以“太行山”主題創作的筆墨形態,筆墨仍以寫實為主,強調筆墨反復勾、皴之后整體的視覺效果或畫面氣息,筆墨線條仍以塑形為主,而不同于南方強調筆墨本身的韻味,這與太行山的雄渾厚重的自然氣息是分不開的。
可以看出,以太行山為創作題材的現代畫家間的師承關系模糊,各家由于個性品格的不同,在觀察和創作時產生不同的審美感受對太行山的抓取點不一致,有的側重整體,有的側重局部,導致作品個性特征突出。要求藝術家從傳統中汲取各種筆墨營養,包括筆墨技法層面的,也有筆墨精神層面的,結合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太行山,并通過自身的審美體驗去探索和創造獨具個性的筆墨語言形式和畫面風格。
總體來看,以太行山為創作題材的現代山水畫家們皆都以五代兩宋的北派山水畫為宗,歷代畫家以及現代各家之間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只不過是淡化了師承某家的痕跡。
三、畫派風格
“風格相近”是“地方畫派”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正是“畫派”間相互區別的重要特征。以“地別為派”正式出現于清代張庚的《浦山論畫》中:“畫分南北始于唐世,然未有以地別為派者,至明季方有浙派之目,是派也始于戴進,成于藍瑛。”“太行山畫派”也是以太行山這一地域性概念命名的“畫派”,理當具有地方畫派相近的風格。
太行山地域性特征明顯,必然會影響到藝術家們的審美傾向。太行山高聳、雄壯、深厚的氣質不同于江南秀美、婉約的品性,這必然帶來創作情感上的差異。前文提到,以太行山為創作題材的現代畫家們屬于“并稱畫壇的名家”而非傳統的師承關系,但受客觀觀照對象太行山這一地域特征的影響,必然會促使作品“風格相近”,表現在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方面。綜合以太行山為創作題材的畫家們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可以看出,作品都是以表現太行山溝壑縱橫、崇山峻嶺、連綿起伏這一地域性特征,以及太行山雄偉深厚、剛健壯美、蒼茫凝重、不屈不撓的形而上的太行精神氣質為主,作品形式上多構圖飽滿、氣勢宏大,筆墨表現注重寫實、筆力剛勁,以“積墨法”為主,多反復皴染。同時,由于個性審美的差異,“畫派”中各作品風格迥然。可以看出這里所提的“風格相近”更多是畫面之外精神氣質上的相近,主要指北方山水畫大派具有的總體風格特征,而這種“風格相近”的范疇并不應局限于幾位代表性的現代山水畫畫家,凡是親歷太行山創作實踐的藝術家便會表現出這種地域性的風格特征,也絕不會把太行山表現得過于秀美。另外,還應注意到無論是“歷時性的畫家傳派”還是“共時性的地方畫派”都應避免創作風格的模式化、概念化,以及陳陳相因的流弊。
結語
綜上所述,以太行山為創作題材的現代山水畫家們并不具備獨立成派的條件,在開派人物、師承關系、風格相近等方面都沒有促使“太行山畫派”的形成。更沒有像西方畫派自覺地提出某種繪畫主張或藝術綱領,畫家間的藝術實踐也是自發、零散的,并未形成某一組織(或許作為一種“畫風”更恰當)。但是,我們也應該注意到,繼荊浩之后太行山這一主題性創作又被藝術家們所重視,他們投身太行山這一地域性特征的藝術探索和實踐,創作表現太行山風貌和體現太行山精神氣質的山水畫作品,這一繪畫現象的時代性特點是具有一定歷史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