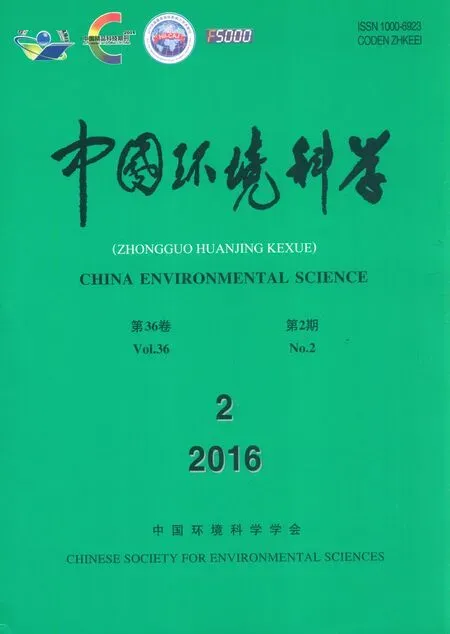基于PSR模型的江蘇海岸帶生態系統健康時空變化研究
寧立新,馬 蘭,周云凱*,白秀玲(1.河南大學資源與環境研究所,河南 開封 475004;2.國土資源部海岸帶開發與保護重點實驗室,江蘇 南京 210024)
?
基于PSR模型的江蘇海岸帶生態系統健康時空變化研究
寧立新1,2,馬 蘭1,2,周云凱1,2*,白秀玲1,2(1.河南大學資源與環境研究所,河南 開封 475004;2.國土資源部海岸帶開發與保護重點實驗室,江蘇 南京 210024)
摘要:以江蘇省海岸帶為例,基于PSR模型構建江蘇省海岸帶生態系統健康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熵權法和層次分析法結合確定指標權重,依據構建的評價模型對近19年間的生態系統健康狀況進行評價與分析.結果表明:研究區各縣市生態系統健康綜合指數在3~6之間,處于一般等級的區域占總面積的54%~66%,處于較差等級的區域占34%~45%,空間分布上表現為研究區中部生態系統健康狀況較好,而南北兩側相對較差;研究區生態系統一直處于一般健康水平,但從健康指數構成來看,研究區壓力、狀態、響應因子值在研究期間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生態健康指數在2002年以后略表現出下降趨勢,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關鍵詞:海岸帶;生態系統健康;時空變化;PSR模型;江蘇省
* 責任作者, 副教授, ykzhou2009@126.com
生態系統健康研究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是當前生態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許多學者對此進行了較為廣泛而深入的研究[1-2].研究內容已從過去的生態系統健康概念探討、評價指標確定、研究尺度、評價模型等方面[3-7]逐漸轉移到各種不同類型生態系統(森林生態系統、農業生態系統、流域生態系統、濕地生態系統、城市生態系統)健康的實證研究[5-11],但對于海岸帶生態系統健康的研究則相對較少[12-15].由于生態系統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相關研究進展還十分有限,目前還未形成一套完整可行的理論體系和評價方法,因此,在實際的健康評價過程中,需要根據研究區域的環境條件和社會經濟特點,選取合適的指標建立符合當地實際情況的評價指標體系和評價模型,據此對生態系統健康進行評價.研究中采用較多的評價模型主要是多因子綜合評價模型,包括“壓力-狀態-響應” (PSR)模型[16]、“驅動力-狀態-響應” (DSR)模型[17]、“驅動力-壓力-狀態-暴露-影響-響應” (DPSEEA)模型[18]、“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 (DPSIR)模型[19]等,其中PSR模型由于具有清晰的因果關系,在各類生態系統健康研究中得到了較為廣泛的應用[16,20-25].
海岸帶是海陸相互作用強烈的復雜地帶,作為一個生態交錯帶,其生態結構與生態過程受到人類活動和環境變化的雙重作用.江蘇省海岸帶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特殊的地理區位,人類活動影響強烈而頻繁.隨著人口的增長和對資源的掠奪式開發利用,海岸帶地區生態環境破壞較為嚴重,其可持續性發展受到很大挑戰[26].本文選擇江蘇省海岸帶地區作為研究對象,以生態系統健康、景觀生態學等理論為基礎,依據PSR模型構建生態系統健康評價指標體系,探討江蘇海岸帶生態系統健康空間分異及其動態變化特征,探求生態系統健康演化的主要驅動因子,以期為合理開發利用當地海岸帶資源、恢復區域生態系統健康提供理論指導和科學依據.
1 研究區概況
江蘇省包括南京市、無錫市、徐州市、常州市、蘇州市、南通市、連云港市、淮安市、鹽城市、揚州市、鎮江市、秦州市和宿遷市等13個地級市,本研究涉及區域為連云港市、鹽城市和南通市中的臨海縣市,具體包括連云港市區(包含連云區和海州區)、贛榆區、灌云縣、響水縣、濱海縣、射陽縣、東臺市、大豐市、南通市區(包含崇川區、港閘區和通州區)、如東縣、啟東市和海門市等12個縣市.地理位置位于31°64′N~35°12′N、118°75′E~121°94′E范圍內,總面積17424.32km2,占整個江蘇省面積的16.98%(圖1).該區地形以平原為主,地勢平坦,海拔0~4m,大陸海岸線長954km[27];光照充足,無霜期達210~224d,年平均氣溫為13.7~14.6℃,地跨暖溫帶與亞熱帶兩個氣候帶;研究區域內保護區數量多,建有鹽城國家級大豐麋鹿自然保護區和珍禽自然保護區、東臺中華鱘自然保護區、連云港云臺山國家森林公園以及南通市啟動長江口濕地保護區,保護區面積達1581.43km2,占研究區總面積的9.1%.

圖1 研究區位置Fig.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2 研究方法
2.1 數據收集及預處理

圖2 研究區各時期(1995,2002,2009,2013年)景觀類型Fig.2 Landscape patterns of study region in 1995,2002,2009,2013
研究使用的數據包括遙感影像數據、社會經濟統計數據以及其他數據資料.遙感影像數據使用的主要是美國Landsat5和Landsat8影像,輔以Landsat7影像,軌道號為118/38、119/36、119/37和120/36,成像時間分別是1995年、2002年、2009年和2013年夏季前后.統計數據主要包括1996年、2003年、2010年、2014年江蘇省統計年鑒.其他數據包括江蘇省地形圖、江蘇省行政區劃圖、土地利用圖及保護區分布圖.
影像處理首先利用ENVI5.1對影像進行波段合成,參考地形圖對影像進行幾何精校正;依據遙感影像的色調、紋理,結合野外考察資料及江蘇省土地利用圖,建立江蘇省海岸帶景觀類型解譯標志,將研究區景觀劃分為耕地、林地、草地、水體、灘涂、建設用地和人工塘7種類型.在ENVI5.1支持下,采取最大似然法進行監督分類,分類后利用人工目視糾正錯分區域,確保解譯精度達到80%以上.將解譯后的影像經過拼接、鑲嵌及裁剪處理得到研究區4期景觀類型圖(圖2),利用Fragstats4.2提取景觀格局指數,并利用ArcGIS10.1進行空間分析和制圖.
2.2 生態系統健康評價指標體系
2.2.1 指標體系構建 評價指標體系的科學合理性是區域生態系統健康評價準確、合理與否的關鍵,也是該評價是否有指導意義的關鍵.其指標的選取應以反映生態系統的主要結構與功能,盡可能采用RS、GIS技術的實時動態監測,具備系統性、完備性、可操作性,并體現人類作用作為基本原則[28].
本研究以聯合國經濟合作開發署(OECD)建立的壓力-狀態-響應(PSR)模型[29]框架為基礎,對江蘇省海岸帶生態系統健康進行評價分析.依據該模型可認為人類的生產、生活會對海岸帶生態系統造成一定的干擾并產生一定壓力,進而引起區域健康狀態發生相應變化,基于此,人類社會會對區域健康狀態的變化做出響應,來減緩環境質量下降.綜合考慮江蘇省海岸帶的社會經濟、環境污染及保護情況,參照目前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最終確定了目標層、項目層、因素層3個層次共18個指標的江蘇省海岸帶生態系統健康評價指標體系(表1).其中部分指標說明見表2.
2.2.2 指標標準化處理 不同指標由于數據類型、數據來源、計算方法、數據特征及量綱不同,無法直接使用上述指標進行直接計算.本研究使用極差法將其進行標準化處理,處理成無量綱數據,取值范圍在0~10之間.生態系統健康評價的指標可劃分為負向指標和正向指標,正向指標與區域生態系統健康成正相關,按公式(1)計算;負向指標與區域生態系統健康成負相關,按公式(2)計算.具體指標趨向情況見表1.

式中:yij為第i年第j項指標標準化后的值;xij為第i年第j項指標的實際值;max xj為第j項指標在研究時段內實際值的最大值;min xj為第j項指標在研究時段內實際值的最小值.
2.2.3 指標權重確定 權重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權衡某指標在整體評價中的相對重要程度,合理的評價指標權重分配可以提高評價結果精度.目前權重確定的方法有專家打分法、層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熵權法等,不同的分析方法具有不同的優缺點.本研究權重的確定采用層次分析法[30]和熵權法[31]分別計算權重再求其平均值而得到,該方法可一定程度上避免層次分析法主觀因素的決定性作用和熵權法純客觀賦權的缺點,將層次分析法的系統性和熵權法的客觀性結合起來.力求主觀與客觀因素的統一.經計算,得到的指標權重見表1.
2.2.4 綜合評價模型 通過綜合指數法計算區域生態健康指數反映生態系統健康狀況是生態系統健康評價研究中經常使用的方法,綜合指數越大,表明生態系統越健康.將江蘇省海岸帶按行政區劃分為多個子區域,因此在具體評價模型建立時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32]:
子區域的評價模型為:

式中:EHIi為第i個子區域的生態系統健康指數;yij為第i個子區域第j項指標經標準化處理得到的值;wj是第j項指標相對于目標層的權重;n為評價指標個數.
項目層因子指數計算模型為:


表1 江蘇省海岸帶生態系統健康評價指標體系Table 1 Indices system for evaluating ecosystem health of Jiangsu Province coastal zone

表2 部分評價指標說明Table 2 Information about some of the indices

表3 不同景觀類型生態彈性度賦值表Table 3 Ecosystem elastic capacities for different landscape types
式中:Ai為第i年項目層某因子指數;yij為第i年第j項指標經標準化處理后的值;wi'為第j項指標的相對于項目層的權重;n為項目層該因子指標個數.
整個研究區的評價模型為:

式中:EHI為生態系統綜合健康指數;EHIi為第i個子區域的生態系統健康指數;wi為第i個子區域的面積權重;n為子區域個數;其他參數意義與式(3)相同.
2.2.5 生態系統健康等級劃分 根據計算出的生態系統健康指數,并參考已有研究劃分的生態系統健康等級標準[35-36],將研究區生態系統健康水平劃分為5個級別,如表4所示.

表4 江蘇省海岸帶生態系統健康等級劃分Table 4 Classification of ecosystem health condi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coastal zone
3 結果分析

圖3 江蘇省海岸帶各時期(1995、2002、2009、2013)生態系統健康空間變化Fig.3 Spatial variations of ecosystem health of Jiangsu Province coastal zone in 1995、2002、2009、2013
根據PSR框架模型和已建立的評價指標體系和評價模型分別計算江蘇省海岸帶各研究單元及整個研究區的生態系統健康指數和生態因子值,結果見圖3~圖7.

圖4 研究區壓力因子變化Fig.4 Changes of pressure factor of study sub-region

圖5 研究區狀態因子變化Fig.5 Changes of state factor of study sub-region

圖6 研究區響應因子變化Fig.6 Changes of response factor of study sub-region
3.1 壓力分析
生態系統健康壓力指標用于表征自然現象和過程及人類的生產、生活對區域生態系統所造成的干擾和脅迫,其指數大小反映生態系統所受壓力的大小,即受干擾和脅迫的程度.

圖7 研究區整體各因子變化Fig.7 Changes of factors of study region
從空間分布來看,江蘇省海岸帶各子區域間壓力差異較明顯,整體上表現為從中部區域向南北兩側壓力因子值變小(圖4),即生態環境面臨壓力逐漸增大.單從人口密度來看,以2013年為例,中部區域(鹽城五縣)人口密度為371人/km2,而連云港三縣和南通四縣人口密度分別為703人/km2和980人/km2.在人口相對密集的連云港三縣和南通四縣的城鎮化率、經濟密度、化肥施用強度也高于鹽城五縣,造成了研究區中部區域壓力值小于南北區域.
從時間變化來看,研究區12個子區域生態系統壓力因子均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在近19年間,除大豐市、東臺市、如東縣三市外,其他9個子區域的壓力因子值呈現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趨勢,即生態系統面臨的壓力增大.其中連云港市區壓力因子值下降最大,由1995年的8.37下降到2013年的5.34,除墾殖指數外,其他指標對壓力的增大都有不同程度的貢獻.19年間,人口密度不斷增加,人口自然增長率加快,人們為了滿足自身發展需求,對區域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強度增大,致使大量農田轉變為工業用地和居住用地,墾殖指數不斷減小;同時,城鎮化率和經濟密度不斷上升,19年間城鎮化率由10.79%增加到20.49%,經濟密度由268.94萬/km2增加到4025.50萬/km2;此外,為了增加糧食產量以滿足生產與生活需要,化肥施用強度也由1995年39.18t/km2增加到2013年的270.03t/km2,由此使得連云港市區面臨的壓力不斷增大.除連云港市區壓力增加最強烈外,其他壓力增加的子區域中,壓力因子增加值由大到小依次是:灌云縣>贛榆市>南通市區>海門市>射陽縣>濱海縣>響水縣>啟東市.與此相反,大豐市、東臺市、如東縣面臨的壓力則有減小的趨勢,由大到小依次為:如東縣>東臺市>大豐市.以東臺市為例,東臺市人口自然增長率在1995年、2002年、2009年、2013年分別是1.12‰、-1.39‰、-0.35‰、0.19‰,人口總數由1995年1.18×106人減少為2013年1.14×106人,由于人口壓力的減小,其他指標也有不同程度的減緩趨勢,如化肥施用強度在此期間由36.61t/km2減小為27.74t/km2,由此使得東臺市面臨的環境及非環境壓力有所減小.
整體來看,研究區4個時期壓力因子值分別為5.81、5.78、5.66、5.41,可以看出,江蘇省海岸帶生態系統所面臨的壓力逐漸增大(圖7).主要原因在于,近19年間,江蘇省海岸帶人口總數量呈增加趨勢,由1.25×107人增長到1.31×107人,化肥施用強度隨之增加,同時經濟高速發展,地區生產總值由6.75×106萬元增長到6.63×107萬元,帶動了城鎮化率的提高,對生態系統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壓力.
3.2 狀態分析
生態系統健康狀態指標是用于表征區域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其指標大小是生態系統狀態的度量,是生態系統健康評價中最重要的指標[34].
從空間分布來看,研究區12個子區域生態系統狀態因子差異較為明顯(圖5).以2013年為例,江蘇省海岸帶中部地區(灌云縣、響水縣、濱海縣、射陽縣、大豐市)以及南部的南通市區和海門市生態系統健康狀態較差,分布在研究區南北兩側的其他縣市生態系統健康狀態較好.究其原因,研究區北部地區山地較多,林地面積比重大且分布集中,人類干擾相對較低,景觀多樣性較為豐富,生態系統的彈性較高,結構相對較好;在南部區域(如東縣、啟東市和東臺市),城鎮化率、化肥施用強度及人口增長率相對偏低,生態系統所承受壓力較小,系統結構相對完整,景觀的破碎化及分離性都較其他區域偏低,而系統的物質生產功能也較高,尤其是水體漁業生產力遠遠大于其他地區,僅如東縣、啟東市兩個地區水產品產量就占到整個研究區產量的33%,以上因素的綜合作用使南部部分區域狀態較好.
從時間變化來看,近19年間,研究區狀態因子呈下降趨勢的子區域有大豐市、東臺市、南通市區、海門市、啟東市.其中下降最大的子區域是南通市區,狀態因子減小1.06,主要是由初級生產力、土壤生產力、分離度指數、生態彈性度的減小造成的.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和經濟的高速發展,大量耕地、林地和草地被用作建設用地,19年間建設用地面積增加了163.76km2,耕地、林地、草地面積分別減少了127.01、0.58、3.64km2;與此同時,分離度指數由1995年5.36降低為2013年4.59,斑塊密度由1.03增大為1.08,生態彈性度也出現一定程度的下降,由1995年的0.51降低到2014年的0.48,使得南通市區的景觀結構遭到破壞,初級生產力降低.而部分子區域狀態因子則出現上升,上升幅度最大的是連云港市,19年間狀態因子增加了1.01,其次由大到小依次為贛榆市>灌云縣>濱海縣>響水縣>如東縣>射陽縣.以連云港市區為例, 19年間,雖然該市耕地、水體、人工塘面積都有不同程度的縮小,分別縮小了17.79、24.29、54.47km2,但是糧食作物產量和水產品產量都出現較大幅度增加,糧食作物產量增加了3.50×105t,水產品產量增產1.0×105t,土壤和漁業生產力的大幅度提高使連云港市區狀態因子上升最快.
整體來看,研究區在研究時段內狀態因子值呈波動變化.1995年至2009年間,狀態因子由3.93降低到3.17,2013年又提高到3.89.2009年之前,研究區人口的大量增加使得生態系統承受的壓力增大,由5.81變為5.66.在人為因素的干擾下,對自然資源進行開發利用,大量耕地、林地、草地被用作建設用地、人工塘用地,導致景觀更加破碎,斑塊密度增大,景觀多樣性減小,生態系統狀態變差;2009年之后狀態因子的上升與政府的重視有關,2010年11月江蘇省委、省政府制定出臺《關于加快推進生態省建設全面提升生態文明的意見》,2011年4月出臺《關于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工程的行動計劃》,2013年編制印發《江蘇省生態文明建設規劃(2013-2022)》,相關法規的實施積極推進了生態保護與建設行動,環境質量有所改善.這一時期,除啟東市狀態因子減小,其他縣市的狀態因子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造成了整個研究區生態系統健康狀態因子上升.以贛榆縣為例,在2009~2013年間,該市狀態因子增加0.742,物質生產能力以及多樣性指數、均勻度指數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斑塊密度有所減小,使狀態因子上升.
3.3 響應分析
生態系統健康響應指標是用來表征生態系統惡化過程中,人類為阻止其惡化并恢復健康狀態而采取的一系列反應,對生態系統健康起積極推動作用,其指數大小是這種反應的度量.
從空間分布來看,江蘇省海岸帶各子區域間響應差異明顯,19年間生態響應因子值總體上都表現為研究區中部區域大,向南北兩側逐漸遞減. 以2013年為例,除研究區南部啟東市響應因子值是6.7,其他縣市響應因子呈現出從研究區中部區域向南北兩側逐漸減小,中部區域的射陽縣和大豐市響應因子值分別是5.48、7.14,而其他縣市都在2~3之間,生態響應較小.究其原因,研究區各子區域環保意識水平都處于較低水平,教育支出占公共財政總支出17%~27%之間;更主要的是射陽縣和大豐市保護區面積比處于較高水平,鹽城市大豐麋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坐落在大豐市,面積26.67km2,鹽城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一大部分分布在射陽縣,面積約為446.10km2,另有563.19km2位于大豐市,使得這兩個子區域生態響應值處于較高水平.
從時間變化來看,研究區有6個子區域生態系統健康響應因子值呈現下降趨勢(圖6),下降幅度由大到小依次為濱海縣>射陽縣>東臺市>響水縣>大豐市>灌云縣,變化原因主要為教育支出占公共財政總支出比例的降低引起的.以濱海縣為例,1995年教育支出占公共財政總支出的38.03%,到2013年教育財政支出占公共財政總支出的18.84%,降幅達20%.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教育支出所占比例減小,但實際教育支出的總費用卻不斷增加,19年間教育支出增加了11.25億元,同時公共財政支出增加了61.22億元,造成了教育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的比例降低,因此,當地對于環境保護重視程度還有待提高.與此相反,部分地區生態系統健康響應因子有增加態勢,增加幅度最大的區域是啟東市,其次依次為連云港市區、南通市區、海門市、如東縣、贛榆縣.以啟東市為例,雖然教育投入比例也有所降低,但是廢物綜合利用率和保護區面積比有明顯的增加.近19年間,為防止海岸帶生態環境的繼續惡化和保護生物多樣性,當地建立了自然保護區和生態示范區,在2002年底建立了啟東長江口(北支)濕地省級自然保護區及其附屬自然保護區,保護區的建立減緩了當地生態系統的惡化趨勢;同時,廢物綜合利用率也由1995年的79.85%增加到2013年的98.18%,增加了18.33%.這些積極有效的生態保護措施使當地生態系統健康響應因子表現出上升趨勢.
整體來看,江蘇省海岸帶生態系統健康響應因子呈波動下降趨勢(圖7),2002年最高.原因是研究區的大部分保護區在這段時間建成,2000年鹽城建立了東臺中華鱘自然保護區,2001、2002年南通分別建立了沿海防護林灘涂自然保護區和啟動長江口濕地保護區,使得該地生態響應顯著提高;而之后研究區保護區面積變化較小,但是環境教育投入率有所下降,使得生態響應出現降低.整個研究時段內,生態系統響應因子由1995年3.94降低為2013年3.89,由此可看出,江蘇省海岸帶生態系統壓力和響應的變化未能引起當地政府的足夠重視,雖然已采取一定措施對生態系統進行保護與恢復,但力度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尤其需要增加教育投資在公共財政支出所占的比例,開展生態保護教育,以增強人們的環保意識.
3.4 生態系統健康狀況分析
綜合生態系統壓力、狀態和響應三個方面,根據計算出的權重值,得出江蘇省海岸帶生態系統健康綜合指數(圖3),用綜合指數來表征生態系統的健康狀況,指數越大,表明生態系統健康狀況越好,反之越差.
從空間分布來看,4個時期生態系統健康綜合指數總體上都表現為研究區中部區域大,向南北兩側逐漸遞減.以2013年為例,除南部啟東市健康指數是5.7外,其他縣市健康狀況表現出中部區域高,南北兩側低的分布特征,中部射陽縣、大豐市、東臺市、如東縣4縣市都屬于一般健康等級,其他7縣市健康屬于較差健康等級,且分布在南北兩側.特別注意的是,大豐市在2002年健康指數是6.05,是研究時段內唯一一個處于良好健康等級的子區.其原因在于大豐市廢物綜合利用率和保護區面積比在2002年處于各研究子區在各年度的最優狀態,人口密度、城鎮化率和化肥施用強度等指標均處于較好水平.
從時間變化來看,19年間,研究區12個子區域中有8個區域生態系統健康綜合指數呈現下降趨勢,變化幅度由大到小排名依次是:大豐市>射陽縣>東臺市>濱海縣>響水縣>灌云縣>南通市區>海門市.大豐市健康指數下降最大,19年間健康綜合指數由5.77下降到5.17.由于該地地理位置優越,人口較多,人口壓力大,城鎮化率明顯提高,經濟增長快速.人類的開發利用使得斑塊密度增加,景觀破碎化加大,而景觀多樣性和均勻度減小,造成該區域健康指數的不斷減小.同時,其余四縣市的生態系統健康綜合指數呈上升趨勢,變化最大的是啟東市,指數值增加了1.35,該市地廢物綜合利用率和保護區面積比的增加使生態系統健康狀況逐漸得到改善.
整體來看,江蘇省海岸帶生態系統健康綜合指數在1995、2002、2009、2013年分別是4.33、4.43、4.20、4.20,其整體健康狀況雖然都處于一般健康水平,但在2002年之前,生態系統健康綜合指數有所上升,而2002年以后,生態系統健康綜合指數有較大程度下降,海岸帶地區生態系統健康狀況出現惡化趨勢.2002年之前,研究區壓力、狀態變化不大,而響應因子有大幅度增加,原因是研究區的大部分保護區在這段時間建成,2000年鹽城建立了東臺中華鱘自然保護區,2001、2002年南通分別建立了沿海防護林灘涂自然保護區和啟動長江口濕地保護區,使得該地生態響應上升,生態系統健康綜合指數上升;2002年以后,研究區保護區面積變化較小,但是生態面臨壓力卻越來越大,使得該地整體生態健康綜合指數有所下降.研究時段內,整個研究區域總人口由1995年的1.25×107人增加到2013年的1.31×107人.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人類活動對海岸帶生態系統產生的壓力逐漸增大,使得大量耕地、草地、水體、灘涂被轉變為建設用地和人工塘,遙感解譯數據顯示,近19年來,研究區建設用地和人工塘面積分別增加了658.15km2和258.12km2.同時,在人類活動的強烈干預下,江蘇省海岸帶生態系統結構發生較大變化,景觀破碎化程度加大,生態系統彈性度降低.雖然當地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來防止生態環境的惡化,但力度相對較小,尤其在環保投入和自然保護區建設方面重視不夠,使生態系統健康狀況表現出一定的惡化趨勢.
4 討論
本研究雖立足于江蘇海岸帶實際,基于PSR模型建立海岸帶生態系統健康評價體系和方法,并綜合使用層次分析法和熵權法來確定指標權重,力圖實現評價的科學性和合理性,但由于海岸帶地區是一個自然、經濟與社會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復合生態系統,其影響因素眾多,人類干擾強烈,加之目前生態系統健康研究尚處起步階段,還未形成統一、成熟的評價指標體系和方法,可借鑒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使得本研究所建立的評價指標體系還不夠完善,具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另外,由于對海岸帶生態過程認識還不夠深入,所建立評價指標體系以結構性和功能性指標為主,而過程性指標未予以涉及.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應進一步加強多學科交叉,從多層次、多角度開展海岸帶生態系統健康評價研究;同時,海岸帶生態系統是一個動態發展的、較脆弱的生態系統,應開展長期定點監測以獲得動態變化數據,并注重生態過程對生態系統健康的影響,以實現海岸帶地區生態系統健康的客觀評價與動態監測.
5 結論
5.1 景觀生態學和生態系統健康理論,以多源數據為基礎,基于壓力-狀態-響應(PSR)模型構建了生態系統健康評價指標體系,并對江蘇省海岸帶生態系統健康進行評價.研究結果表明,除2002年大豐市生態系統健康處于良好等級,其他江蘇海岸帶子區域均處于較差或一般健康等級,19年間處于較差等級的區域占總面積的34%~45%,分布在江蘇省海岸帶的南北兩側,主要是連云港市區、贛榆縣、灌云縣、南通市區和海門縣;處于一般等級的區域占總面積的54%~ 66%,主要分布在海岸帶的中部區域,主要是響水縣、濱海縣、射陽縣、大豐市、東臺市、如東縣和啟東市.造成這種空間差異的主要驅動因素是人類活動,在人口密度和經濟密度大的地區,人為干擾對生態系統產生較大壓力,系統的結構受損,而生態環境保護與治理力度相對較小,使生態系統健康處于較低水平;在人口密度和經濟密度較小的地區,生態系統遭受人為干擾相對較弱,生態系統結構相對較好,生態系統的健康狀況處于較高水平.
5.2 江蘇省海岸帶屬于人類強烈干擾區,受到的人類影響較大,對人類干擾較為敏感.近19年間,雖然研究區生態系統一直處于一般健康水平,但從2002年以后,綜合健康指數有所降低.這表明當地生態系統有朝著惡化方向發展的趨勢,應引起當地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加大海岸帶生態系統的保護和管理,以實現當地海岸帶生態系統健康的改善與恢復.
參考文獻:
[1] Lepold J C. Getting a handle on ecosystem health [J]. Science, 1997,276:887.
[2] Ferguson B L. The concept of landscape health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1994,40:129-137.
[3] 袁興中,劉 紅,陸健健.生態系統健康評價——概念框架與指標選擇 [J]. 應用生態學報, 2001,12(4):627-629.
[4] Harvay S, Nancy S S, Paul B.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dicators of ecosystem health in the Great Lakes Basin [J].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2003,88(1-3):119-151.
[5] Peng J, Wang Y L, Wu J S, et al. Evaluation for region ecosystem health: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progress [J]. Acta Ecolobica Sinica, 2007,27(11):4877-4885.
[6] 陳 高,鄧紅兵,王慶禮.森林生態環境健康評估的——一般途徑探討 [J]. 應用生態學報, 2003,14(6):995-999.
[7] 吳建國,常學向.荒漠生態系統健康評價的探索 [J]. 中國沙漠, 2005,25(4):604-611.
[8] Li Y F, Li D. Assessment and forecast of Beijing and Shanghai’surban ecosystem health [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4,487:154-163.
[9] 劉 永,郭懷成,戴永立.湖泊生態系統健康評價方法研究 [J].環境科學學報, 2004,24(4):723-730.
[10] 劉惠清,許嘉巍,吳秀芹.西藏自治區乃東縣生態系統的健康性評價 [J]. 地理科學, 2003,23(3):366-371.
[11] 李春暉,鄭小康,崔 嵬.衡水湖流域生態系統健康評價 [J]. 地理研究, 2008,27(3):565-573.
[12] 孫 磊,孫英蘭,周震峰.青島市海岸帶生態系統壓力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研究 [J]. 海洋環境科學, 2009,28(5):584-587.
[13] 戴亞南,彭檢貴.江蘇海岸帶生態環境脆弱性及其評價體系構建[J]. 海洋學研究, 2009,7(1):78-82.
[14] 唐得昊,鄒欣慶,劉興健.海岸帶生態系統健康評價中物質和生物多樣性的差異——以江蘇海岸帶為例 [J]. 生態學報, 2013,33(4):1240-1250.
[15] 蘇盼盼,葉屬峰,過仲陽,等.基于AD-AS模型的海岸帶生態系統綜合承載力評估——以舟山海岸帶為例 [J]. 生態學報, 2014,34(3):718-726.
[16] 解雪峰,吳 濤,肖 翠,等.基于PSR模型的東陽江流域生態安全評價 [J]. 資源科學, 2014,36(8):1702-1711.
[17] Birgitte H, Hugo F A, Erik S K. Approaches to assess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organic farming with particular regard to Denmark [J]. Agriculture, 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 2001, 83(1):11-26.
[18] Gentry-Shields J, Bartram J. Human health and the water environment: Using the DPSEEA framework to identify the driving forces of disease [J]. The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3,468-469:306-314.
[19] 張繼權,伊坤朋,Hiroshi T,等.基于DPSIR的吉林省白山市生態安全評價 [J]. 應用生態學報, 2011,22(1):189-195.
[20] 朱衛紅,郭艷麗,孫 鵬,等.圖們江下游濕地生態系統健康評價[J]. 生態學報, 2012,32(21):6609-6618.
[21] 帥 紅,李景保.典型年洞庭湖系統健康綜合評價 [J]. 地理科學, 2014,34(2):170-177.
[22] 崔力拓,李志偉.河北省沿海開發活動的生態環境效應評估 [J].應用生態學報, 2014,25(7):2063-2070.
[23] 張軍以,蘇維詞,張鳳太.基于PSR模型的三峽庫區生態經濟區土地生態安全評價 [J]. 中國環境科學, 2011,31(6):1039-1044.
[24] 倪曉嬌,南 穎,朱衛紅,等.基于多災種自然災害風險的長白山地區生態安全綜合評價 [J]. 地理研究, 2014,33(7):1348-1360.
[25] 劉曉曼,王 橋,孫中平,等.基于環境一號衛星的自然保護區生態系統健康評價 [J]. 中國環境科學, 2011,31(5):863-870.
[26] 沈正平,韓 雪.江蘇省海岸帶可持續發展觸探 [J]. 人文地理, 2007,98(6):47-52.
[27] 王 玉,賈曉波,張文廣,等.江蘇省海岸帶土地利用變化及驅動力分析 [J].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 2010,19(Z1):7-12.
[28] 蔣衛國,李 京,李加洪,等.遼河三角洲濕地生態系統健康評價[J]. 生態學報, 2005,25(3):408-414.
[29] 顏 利,王金坑,黃 浩.基于PSR框架模型的東溪流域生態系統健康評價 [J]. 資源科學, 2008,30(1):107-113.
[30] 南 穎,吉 喆,馮恒棟,等.基于遙感和地理信息系統的圖們江地區生態安全評價 [J]. 生態學報, 2013,33(15):4790-4798.
[31] 李雪銘,晉培育.中國城市人居環境質量特征與時空差異分析[J]. 地理科學, 2012,32(5):521-529.
[32] 周云凱,白秀玲,姜加虎.近17年鄱陽湖區生態系統健康時空變化研究 [J]. 環境科學學報, 2012,32(4):1008-1017.
[33] 徐明德,李 靜,彭 靜,等.基于RS和GIS的生態系統健康評價[J]. 生態環境學報, 2010,19(8):1809-1814.
[34] 張寶秀,熊黑剛,徐長春.新疆于田綠洲生態彈性度與景觀環境分析 [J]. 水土保持研究, 2008,12(6):112-114.
[35] 段樹國,系秀梅.塔里木河流域生態系統健康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J]. 云南地理環境研究, 2007,19(5):114-117.
[36] 申艷萍.城市河流生態系統健康評價實例研究 [J]. 氣象與環境科學, 2008,21(2):13-16.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of ecosystem health of the coastal zone in Jiangsu Province based on the PSR model.
NING Li-xin1,2, MA Lan1,2, ZHOU Yun-kai1,2*, BAI Xiu-ling1,2(1.Institut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China;2.The Key Laboratory of the Coastal Zone Exploitation and Protection, M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 Nanjing 210024, China).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6,36(2):534~543
Abstract:Coastal zone is the transitional area between marine ecosystem and terrestrial ecosystem, its ecosystem health is closely related to human activities. This paper took the coastal zone of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assess the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of ecosystem health from 1995 to 2013. A multi-indices evaluation system was constructed to investigate ecosystem health based on the PSR conceptual model, and the index weight was determined with AHP and Entropy weighting metho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cosystem health indices of all sub-regions ranged from 3 to 6. The area with normal status accounted for 54% to 66% of the whole region, and the area in worse condition were 34 to 45%. Spatial pattern suggested that the middle part of the study area lied in better condition than those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area. The values of pressure、state、response factors showed gentle decline of ecosystem health condition, particularly after 2002, which may need more attention for protection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Key words:coastal zone;ecosystem health;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PSR model;Jiangsu Province
作者簡介:寧立新(1991-),男,山東濟南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濕地生態.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41101089,41371450);國土資源部海岸帶開發與保護評價重點實驗室開放基金項目(2013CZEPK05)
收稿日期:2015-06-08
中圖分類號:X8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6923(2016)02-053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