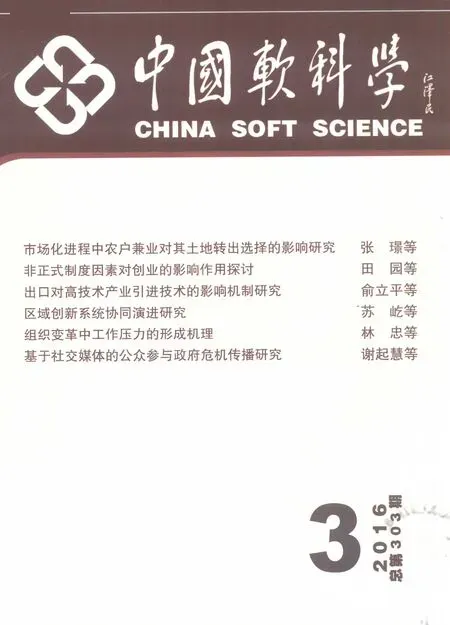農地的“三權分置”及改革問題:政策軌跡、文本分析與產權重構
張 毅,張 紅,畢寶德
(1.清華大學 土木水利學院,北京 100084;2.中國人民大學 財政金融學院,北京 100872)
?
農地的“三權分置”及改革問題:政策軌跡、文本分析與產權重構
張毅1,張紅1,畢寶德2
(1.清華大學土木水利學院,北京100084;2.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北京100872)
摘要:十八屆三中全會后,中央關于農地產權“三權分置”的改革思路日漸清晰,學術界從不同角度展開了討論與研究,但是目前關于“三權分置”問題仍處于眾說紛紜、缺乏共識的階段。在對近年來地方和中央“三權分置”的政策演變軌跡進行梳理,并運用文本分析法分析中央“三權分置”政策中三權和承包經營權的主要特征后,論文深入辨析了學術界關于“三權分置”中承包權與經營權法律屬性方面的共識與分歧,發現在“三權分置”和農地流轉的條件下,承包權仍屬于物權,并且與農地未流轉條件下的原土地承包經營權一樣,是集體成員基于其特定身份而享有的權利;經營權在土地承包經營權轉包、出租和入股方式流轉條件下屬于債權性質,在轉讓和互換流轉條件下屬于物權性質。論文基于上述分析還對我國農地產權重構進行了初步探索。
關鍵詞: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承包經營權;承包權;經營權
一、引言
近年來,我國農地流轉規模日益擴大*據統計,到2014年底,家庭承包土地流轉達4.03億畝,占整個家庭承包土地總面積的30.4%。也就是說,在我國農村約2.3億個家庭中,大約有6000萬個家庭流轉出了土地,占農村家庭的25%。參見:《陳錫文:社會化服務助推家庭經營現代化》,http://www.cirs.tsinghua.edu.cn/zjsdnew/20150506/1120.html,2015年5月8日訪問。。為兼顧農地流出方(農地承包戶)和流入方(農地經營者)的利益,各地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改革探索,如推行兩田制*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和家庭承包經營的前提下,將集體的土地劃分為口糧田和責任田(有些地方叫商品田或經濟田)兩部分。口糧田按人平均承包,一般只負擔農業稅,體現社會福利原則;責任田有的按人承包,有的按勞承包,有的實行招標承包。、農地股份制*以農村集體土地(單獨或結合資金等其他要素)入股,由設立的經濟實體對入股集體土地等要素實行統一經營,并采取按股分紅等分配方式的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經濟制度。和農地信托制*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和承包權不變的前提下,土地承包人基于對受托主體的信任,為了使自己取得更大的土地收益,更加有效、充分地利用土地資源,將其承包地經營權信托給受托人。受托人以實現土地收益最大化為宗旨,以自己的名義對土地經營權進行獨立管理或處分,而土地收益由土地承包者或其指定的受益人享有。等。上述實踐探索為促進區域農地流轉、實現農業規模經營積累了寶貴經驗,但同時也始終存在著農地流出方與流入方土地權利不清晰及由此導致的雙方權益不同程度受損這一瓶頸問題。比如,一方面,農地承包戶原意流轉土地但并不想永久失去土地;另一方面,農地經營者試圖長期經營土地但隨時面臨農地承包戶收回土地的約束,并且農地經營者流轉到手土地的財產權能也并未有效激活。歸結起來,這是一個農地承包經營權權利結構不適應且滯后于實踐發展的重大理論問題,迫切需要中央層面給予頂層設計以破解。
我國目前法定的農地承包經營權權利結構是建立在改革開放后集體土地所有權與土地承包經營權之間“兩權分置”基礎上的,但是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大量勞動力離開農村,農民出現了分化,農地承包戶不經營自己承包地的情況越來越多。如何使農地承包戶放心轉移就業且保留其承包權益,農地實際經營者安心從事農地規模經營且享有一定的土地財產權能,成為政策制定者和與農地經營有關的各方面臨的重大理論問題。
為適應實踐發展的迫切需求,八屆三中全會拉開了包括土地改革在內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關于農地改革的一系列政策舉措陸續出臺。2014年1月19日,中央一號文件中明確指出,“在落實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的基礎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允許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向金融機構抵押融資”,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農戶承包權”和“土地經營權”的概念,這既是對近些年地方農地產權制度改革探索的官方回應,也為未來農地產權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2014年12月22日,農業部部長韓長賦表示,實現土地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農地經營權三權分置,是引導土地有序流轉的重要基礎,是我國農村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創新,從“兩權分置”過渡到“三權分置”是巨大的政策飛躍。至此,“三權分置”一詞成為我國現階段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過程中重大制度創新的集中體現[1]。
關于農地產權“三權分置”,既有學者肯定其意義和價值,也有學者指出其缺陷和弊端。比如,有學者認為,“三權分離”的農地制度具有深厚的歷史基礎,是對現行農地制度的繼承和發揚,能夠實現公平與效率的有機統一[2]。承包權與經營權的進一步分離尤其是經營權的進一步細分,將大大擴展農戶產權配置及其效率改進的潛在空間[3]。 “三權分離”農地制度明確了土地承包關系“長久不變”的制度內涵,即“長久不變”的核心是承包權而非經營權,是土地承包關系長久不變而不是土地經營關系長久不變。放活土地經營權解開了農村集體土地流轉的困境[4]。但是,也有學者認為,集體所有權、承包經營權與流轉經營權之間的法律關系和權利規定是殘缺的[5];耕地流轉實行承包權不流轉的做法,這一政策在設計上存在一定缺陷,如果農民將經營權長期流轉并一次性交租金,就等于出售經營權,這樣一來,農民手中擁有承包權就失去意義[6]。分離之后,承包權與經營權分別負擔農民生存與發展的功能,在兩權歸屬不同主體時,很容易出現“兩權角力,一權虛化”的權利沖突窘境,最終導致農民利益受損[7]。“三權分離”是經濟學主導農地改革政策的形象表述,存在明顯的法學邏輯悖論[8]。
學者們觀點存在分歧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從宏觀視角看,“三權分置”將承包權與經營權分別賦予農地承包和農地實際經營者,似乎找到了有效破解農地承包經營權權利結構不適應且滯后于實踐發展這一理論問題的法寶鑰匙;另一方面,從微觀視角看,“三權分置”中承包權與經營權作為全新的政策用語,其權利內容的邊界如何,兩者有無沖突及遇到沖突時如何解決等關鍵問題并不甚明了。繼而,使農地產權"三權分置"的可操作性大打折扣。
基于此,本文著力研究土地承包經營權一分為二(分為承包權和經營權)且實現承包權和經營權分置并行之后,承包權與經營權的法律屬性和權利內容、承包權和經營權與法定作為用益物權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關系、“三權分置”中“三權”的相互關系等在理論上仍屬空白且法律上無跡可尋的農地產權重構問題。
二、農地“三權分置”的由來:政策軌跡
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農村改革的路徑類似,當前的“三權分置”政策的出臺,也經歷了一個從地方到中央、自下而上的政策過程。截至目前,不論中央還是地方,均沒有專門發布有關中央有關農地“三權分置”的政策文件。中央關于“三權分置”的政策主要分布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以及其它中央文件中;地方關于“三權分置”的政策主要集中在地方出臺的有關發展現代農業,加快推進農地流轉的相關文件中。
(一)地方有關“三權分置”改革政策
上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三權”分離探索已在各地展開。重慶、江西、浙江、安徽、四川等地通過出臺文件,鼓勵集體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離,穩定承包權、搞活經營權,規范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二次分離有強烈的社會訴求和深厚的實踐基礎*參見王立彬:《國土資源部有關負責人談土地承包經營權“再分離”》,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2/29/c_118753978.htm,2015年4月28日訪問。。
1.中部地區
根據現有資料,與“三權分置”有關的“承包權”或“經營權”首次出現之處是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法》(2003年3月1日起施行)頒布之后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政府辦公廳出臺的《關于規范農村土地承包和經營權流轉的若干意見》(合政辦〔2004〕95號)(2004年9月11日),該意見規定:“堅持農村土地承包關系長期穩定。對二輪承包后的人口變動,原則上不予補地。土地經營權流轉應由當事人雙方進行協商,簽訂流轉合同,并經村集體經濟組織見證。任何個人和組織都不得強迫農民進行土地經營權流轉。”該文件雖然沒有提及“承包權”,但卻明確提出“土地經營權”的概念。直到2008年,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政府《關于農村土地承包和經營權流轉的意見》(合政〔2008〕93號)(2008年8月14日)則明確規定:“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應當堅持在穩定農村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不變的基礎上,鼓勵農村集體土地的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相分離。”2012年,安徽省合肥市城鄉統籌辦《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規范管理的意見》(合統籌辦〔2012〕7號)(2012年9月11日)再一次強調:“在穩定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前提下,實行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相分離,堅持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經營使用權,逐步擴大農民承包經營權的權能范疇。”所不同的是,該意見中同時出現“經營權”和“經營使用權”的概念。但是,在2009年,安徽省人民政府《關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若干問題的意見》(皖政〔2009〕13號)(2009年3月16日)中,并未提及“三權分置”的相關內容。
除安徽省之外,河南省焦作市(2009年3月24日)、洛陽市(2009年4月13日)、江西省贛州市崇義縣(2009年5月17日)、湖北省遠安縣舊縣鎮(2009年7月2日)、遠安縣陽坪鎮(2009年7月15日)等中部地區其他省份也都先后發布關于農地產權“三權分置”的文件。所不同的是焦作市和遠安縣陽坪鎮提出用“使用權”代替“經營權”,實行所有權、承包權和使用權“三權”分離。
2.東部地區
在東部地區,最先部署農地產權“三權分置”改革的是浙江省,比如,浙江省嘉興市人民政府辦公室《關于加快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意見》(嘉政辦發〔2007〕106號)(2007年9月24日)提出:“鼓勵農村集體土地的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相分離,穩定承包權,搞活經營權,規范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浙江省寧波市委辦公廳、寧波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做好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工作提高土地規模經營水平的意見》(甬黨辦〔2008〕5號)(2008年1月30日)規定,“堅持穩定承包權、放活經營權的原則。在穩定農村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和土地承包關系的前提下,實行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離”,其中特別強調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特指“農戶家庭承包耕地的經營權流轉”。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的2014年,寧波市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加快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促進農業轉型升級的意見》(甬政發〔2014〕62號)(2014年7月15)進一步明確規定:“堅持依法自愿有償和穩制活權的原則,落實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搞活土地經營權,不斷創新土地流轉形式,健全土地流轉機制,規范土地流轉管理。”但是,2009年中共浙江省委辦公廳、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積極引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促進農業規模經營的意見》(浙委辦[2009]37號)(2009年4月1日)中,并未涉及“三權分置”的有關內容。
除此之外,浙江省余姚市(2008年5月7日)、臺州市(2009年3月7日)、衢州市衢江區(2009年9月14日),山東省青島市即墨市(2009年6月28日)等均先后出臺關于農地產權“三權分置”的文件。可見,東部地區的農地產權“三權分置”實踐探索主要集中在浙江省。
3.西部地區
西部地區農地產權“三權分置”改革主要集中在重慶市和四川省,比如,重慶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加快農村土地流轉促進規模經營發展的意見(試行)》(渝辦發〔2007〕250號)(2007年9月12日)規定:“穩制、分權、放活的原則。農村土地流轉和發展規模經營,要穩定家庭承包經營體制,在不改變土地承包關系的前提下,實行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土地使用權分離,創新流轉機制,探索有效形式,放活土地使用權。”四川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進一步規范有序進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意見》(川辦發〔2009〕39號)(2009年8月26日)。規定:“堅持‘穩制、分權、搞活’的原則。在穩定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的前提下,實行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相分離,堅持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經營使用權。”兩省市意見的不同之處在于,重慶市提出“承包權”與“土地使用權”分離,四川省提出放活“經營使用權”。
由此可見,地方有關“三權分置”改革政策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前,“三權分置”改革在全國東中部多數地區均有部署,且最早出現在中部地區的安徽省合肥市(2004);二是除西部地區的重慶市和四川省之外,東部和中部地區的“三權分置”改革政策均是地市級及其下級政府出臺的,省級層面的相關文件均為提及;三是各地區關于“承包權”的概念表述較為一致,對“經營權”則有“土地經營權”、“經營使用權”和“土地使用權”三種概念表述。
(二)中央有關“三權分置”的政策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有關農地“三權分置”政策的提出經歷了如下過程:(1)201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北考察時指出,深化農村改革,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要好好研究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者之間的關系,這是近年來國家領導人代表中央層面首次提及“承包權”和“經營權”的概念。(2)2013年12月24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指出,“農村集體土地應該由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農民家庭承包,其他任何主體都不能取代農民家庭的土地承包地位,不論承包經營權如何流轉,集體土地承包權都屬于農民家庭”,“土地承包經營權主體同經營權主體發生分離,這是我國農業生產關系變化的新趨勢”,“落實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要加強土地經營權流轉管理和服務,推動土地經營權等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公開、公正、規范運行”。這是近年來中央會議中首次涉及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政策思想,也首次提出“土地經營權”而非“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政策主張。(3)2014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提出“在落實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的基礎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允許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向金融機構抵押融資”。這是繼201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之后,中央首次對土地經營權的權能賦予新的內涵。(4)2014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提出“鼓勵創新土地流轉形式”、“鼓勵承包農戶依法采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及入股等方式流轉承包地”,“抓緊研究探索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土地經營權在土地流轉中的相互權利關系和具體實現形式”和“土地承包經營權屬于農民家庭”。這是中央首次專門發文部署“土地經營權”而非“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5)2014年12月23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指出,要引導和規范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6)2015年1月22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引導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健康發展的意見(國辦發〔2014〕71號)提出,現階段通過市場流轉交易的農村產權包括承包到戶的和農村集體統一經營管理的資源性資產、經營性資產等,以農戶承包土地經營權、集體林地經營權為主,不涉及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和依法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集體土地承包權,具有明顯的資產使用權租賃市場的特征。這是中央首次將(農戶承包)土地經營權流轉納入農村產權流轉的范疇,從而進一步豐富了土地經營權的權利內容。(7)2015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2015年中央1號文件)提出“抓緊修改農村土地承包方面的法律,明確現有土地承包關系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的具體實現形式,界定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土地經營權之間的權利關系”,“引導農民以土地經營權入股合作社和龍頭企業”。該文件在之前一系列文件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不僅再次豐富土地經營權權能(入股),更對尚處于中央政策層面的“三權分置”提出了修改相關法律法規的更高要求。
三、農地的“三權”及“三權分置”:來自政策的文本分析
政策文本分析作為一種研究范式,有著自己的分析技術和研究策略。政策文本分析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比較純粹的文本定量分析,最一般的表現是對文本中某些關鍵詞的詞頻統計,重在描述文本中的某些規律性現象或特點,屬于傳統的內容分析;二是對文本中的詞語的定性分析,多從某一視角出發對文本進行闡釋和邏輯演繹,屬于話語分析范疇;三是綜合分析,即文本的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對文本既有定量描述也有定性闡釋甚至還有預測[9]。
縱觀中央關于“三權分置”之三種權利的政策規定,可以發現具有如下特征:
1.所有權
關于所有權的概念,有“土地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土地集體所有權”和“集體土地所有權”共四種表述,這些概念體現出中央政策對我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肯定和延續。
2.承包權
關于承包權的概念,有“承包權”、“集體土地承包權”、“農戶承包權”和“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集體土地承包權”共四種表述。通過這些概念的表述和文件中的相關表述,不難發現,承包權存在如下特征:一是承包權的承包方式以“農戶”、“家庭”和“農民家庭”(且是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農民家庭)承包為主*家庭承包,是指對具有保障功能的耕地、林地、草地這三類農村土地采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承包方式時,以該社區農民集體成員(農民)人人有份、內部家庭(農戶)為經營單位的承包。參見:丁關良:《工商企業租賃與使用農戶“家庭承包地”的法律對策研究》,《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5),第38-45頁。,并且“其他任何主體都不能取代”;二是承包權的期限“穩定并長久不變”,同時也需要“明確現有土地承包關系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的具體實現形式”。
3.經營權
關于經營權的概念,有“經營權”、、“土地經營權”、“承包土地的經營權”、“農戶承包土地經營權”和“集體林地經營權”共五種表述。通過這些概念性表述,還可以發現中央文件中提到的經營權包括兩種:一是農戶承包土地的經營權;二是集體林地經營權(僅限以家庭方式承包取得)。
另外,通過對與經營權有關的表述分析可以發現,經營權還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經營權的前綴詞是“家庭承包土地”;二是經營權的主要目的是“放活”,既可以“向金融機構抵押融資”,也可以“通過市場流轉交易”,還可以“入股合作社和龍頭企業”*截止2014年底,全國土地流轉面積4.03億畝,占比為30.4%。其中大約58%的土地在農戶之間流轉,大約23%的土地流轉給合作社,大約10%的土地流轉給農業企業,剩下的土地流轉給其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并鼓勵創新土地流轉形式;三是經營權流轉場所可以是“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等“公開市場”,且通過“市場流轉交易”的(土地)經營權流轉具有“明顯的資產使用權租賃市場”的特征。
4.承包經營權
關于“承包經營權”,有“承包經營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共兩種表述,其中只有表述之“土地承包經營權”是我國現行《土地管理法》、《物權法》等法律法規的法律用語,它與表述之一“承包經營權”的存在說明承包權和經營權是可以合二為一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人同時享有承包權和經營權。
5.“三權分置”中的“三權”關系
關于“三權分置”中“三權”關系,中央政策并未有統一的、明確的提法。但從現有的政策表述中,可以歸納出如下特征:一是明確指出“土地承包經營權主體同經營權主體發生分離,是我國農業生產關系變化的新趨勢”*2013年12月23日至24日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指出。;二是明確指出要“好好研究”*201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北考察時指出。、“抓緊研究”*參見:中辦、國辦《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中辦發〔2014〕61號)。并“界定”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土地經營權(在土地流轉中的)(相互)權利關系(和具體實現形式)*參見:2015年中央1號文件。。
綜上可見,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的中央文件中關于“三權分置”中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的概念存在多種具體表述。尤其是承包權與經營權的概念,既有混合在一起的,如(土地)承包經營權;也有分開表述的,如“(農戶)承包權”與“(土地)經營權”。但是,與承包權與經營權的概念相比,關于承包權與經營權權能的表述,就顯得較為混亂。其中,既有關于承包經營權權能的表述,也有關于(土地)經營權權能的表述,而承包權與經營權的邊界該如何界定則并未涉及。比如,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2014年11月20日),提出“鼓勵承包農戶依法采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及入股等方式流轉承包地”。毫無疑問,這些流轉方式均屬于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權利內容*《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法》第32條規定,“通過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依法采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或者其他方式流轉”。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但是,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引導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健康發展的意見(2015年1月22日)則提出,“現階段通過市場流轉交易的農村產權包括承包到戶的和農村集體統一經營管理的資源性資產、經營性資產等,以農戶承包土地經營權、集體林地經營權為主,不涉及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和依法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集體土地承包權”。不難發現,能在市場流轉交易的農村產權中包括土地經營權而不包括土地承包權。中央的政策指向是允許土地承包經營權通過轉包、出租、互換、轉讓及入股等方式進行流轉的,但是,農地流轉流入方得到的只有土地經營權而非土地承包權,土地承包權不能在公開市場上流轉。
四、農地“三權”及“三權分置”的法律屬性:來自學術界的共識與分歧
關于“三權分置”后承包權與經營權的法律地位,學者們眾說紛紜。主要有以下四種觀點:一是承包權是成員權,經營權是債權[10]。二是承包權是物權,經營權為債權。如,根據當前的法律制度安排,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和農戶承包權是物權,而土地經營權是債權,權利的效力差異明顯[11]。三是承包權和經營權均屬于物權。如承包權在嚴格意義上仍是土地承包經營權;經營權是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派生權利,是因承包經營權的部分權能讓渡于經營權而產生的新的權利內容*與該觀點較類似,還有學者認為,受權能分離理論的誤導,將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承包權能等同于承包權,將經營權能等同于經營權,就形成了農村土地三權分離的民事權利。參見:申惠文:《法學視角中的農村土地三權分離改革》,《中國土地科學》2015,29(3):第39-44頁。,并非單純承包土地一種權利資格;土地經營權是一種物權性(財產性)權利[12]。分離后的經營權其定位應為物權,具體性質是用益物權,其權能主要表現為對承包地的獨立占有、經營、收益和處分。承包權理應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權利,具體來說,是一項獨立的物權,性質也為用益物權[13]。四是承包權是物權,經營權未提及。如,經營權從承包經營權中分離出來,可以抵押擔保,但作為物權的承包權依然不能抵押[14]。要強化土地承包權的物權屬性*參見[5]14。。綜上可見,學術界對承包權與經營權的法律屬性問題,分歧比較突出,尚處于討論與百家爭鳴階段。不難發現的是,學者們對承包權的法律屬性認識較為一致,分歧主要體現在對經營權法律地位的認知上。
(一)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物權性質的土地承包權
筆者認為,將承包權界定為成員權較為不妥。理由是,一方面,現有法律法規并未清晰界定成員權的概念、內涵以及取得或喪失成員權資格的條件和程序等內容;另一方面,眾所周知,在我國現有法制條件下,農民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前提是農民是其所在集體的成員之一。否則,集體成員由于其享有的成員權既可以被賦予承包權,也可以被賦予土地承包經營權,而承包權與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先后次序和引致關系仍處于纏繞狀態。如果將承包權界定為物權,雖然按照物權法關于“一物一權”、“公示公信”和“物權法定”的原則,承包權的權益均不能與我國《物權法》法定用益物權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相提并論,我國法律也不能在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基礎上重設承包權做為物權的一種,但是筆者贊同上述學者潘俊的觀點,“承包權在嚴格意義上仍是土地承包經營權,經營權是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派生權利”,并且筆者認為這一觀點成立的前提條件就是土地承包經營權由家庭經營的靜態轉變為流轉經營時的動態。
換言之,在農地未流轉條件下,當承包權主體與經營權主體為同一主體(農戶或農民家庭)時,農戶或農民家庭享有完整的“轉讓、轉包、出租、互換、入股”等權能,此時,家庭承包權內含于土地承包經營權之中。在農地流轉之后,承包權將替代家庭經營條件下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權利職能。所不同的是,此時的承包權權利內容與農地流轉之前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權利內容有所不同。比如,土地承包經營權人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有限處分(與所有權人相比,主要體現為流轉的權利)等權能,而承包權人除了享有部分收益權能和最終處分權能*參見:湖北省農委:《湖北省新時期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狀況》,http://znzg.xynu.edu.cn/Html/?5581.html,2015年4月20日訪問。(與經營權人相比,包括退出、繼承等)之外,其占有、使用、部分收益和部分處分權能均讓渡給農地的實際經營者*土地承包經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進一步融合,就是土地承包經營權中人身性質的權利與財產性質的權利進一步分化和組合的過程。農民依據身份所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應當逐漸向土地收益權的方向轉變,而其中的農地經營權與之再度分割,以便在制度上造成一種能夠完全適應農地市場交易需要的土地產權。參見:揭明,魯勇睿:《土地承包經營權之權利束與權利結構》,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64頁。。因此,按照物權法的一般原理:物權的變更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物權變更,包括物權主體、內容、客體的變化;狹義的物權變更,主要指物權內容和客體的變化,不包括物權主體的變化[15]。由此可知,土地承包經營權衍生家庭承包權,將發生物權權利內容的變更,農地流轉條件下的家庭承包權同樣屬于物權的一種。
(二)土地承包經營權轉包、出租與入股——債權性質的土地經營權
關于經營權的法律屬性,筆者認為,需要分類對待,既不能由于農地流轉時流出方(農戶)與流入方(經營者)必須要簽訂流轉合同并嚴格套用物權的“一物一權”原則,而將其簡單地界定為債權;也不能由于承包經營權是物權,就根據“經營權是因承包經營權的部分權能讓渡而產生新的權利內容”,而將其界定為物權,更不能不明確其法律屬性從而造成農地流轉過程中操作層面的混亂。要做到分類對待,筆者認為,如前文所述,既然土地經營權是農戶將土地承包經營權通過“轉包、出租、互換、轉讓及入股等方式”進行流轉讓渡的,就有必要區分不同方式流轉條件下的土地經營權法律屬性。
1.轉包
轉包是指承包方將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經營權以一定期限轉給同一集體經濟組織的其他農戶從事農業生產經營。土地承包經營權轉包時,農地流入方(農戶)與流入方(實際經營者)簽訂轉包合同并報發包方備案即可*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法釋〔2005〕6號)。。根據《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第35條第2款的規定“轉包后原土地承包關系不變,原承包方繼續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規定的權利和義務”可知,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轉包不會使農地流出方(農戶)喪失土地承包經營權,而只是從物權性質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中分離出部分權能(包括物權性質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中的占有權、使用權和收益權,但不包括處分權)轉移給受轉包方[17]。也即是,在土地承包經營權轉包條件下,受轉包方無法移轉繼受取得物權性質的土地承包權,土地承包權仍由農戶保留,受轉包方實際取得的土地經營權只是原土地承包經營權人讓渡的部分權能而已。
2.出租
土地承包經營權出租,是指承包方將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經營權以一定期限租賃給他人從事農業生產經營。與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轉包較為類似,《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第35條也規定,“出租后原土地承包關系不變,原承包方繼續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規定的權利和義務”。因此,在土地承包經營權出租條件下,出租方與承租方的行為是以發生地租給付義務為目的的法律行為(負擔行為),而非以發生物權變動為目的的行為(處分行為),而“負擔行為,不以負擔義務者對給付標的物有處分權之必要”[17]。物權性質的土地承包權仍由出租方保留,承租方通過與出租方簽訂合同約定并只取得承包地的土地經營權,出租方與承租方之間的農地租賃關系屬于債權關系。
3.入股
《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法》第二章第五節第42條規定,“承包方之間為發展農業經濟,可以自愿聯合將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從事農業經營”。同時,農業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第19條規定,“承包方之間可以自愿將承包土地入股發展農業生產合作,但股份合作解散時入股土地應當退回原承包農戶”。因此可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條件下,雖然土地承包經營權轉化為股權,但是其是一種不完整的股權,也可以稱作為“準土地股權”[18],其與既有股份制理論所定義的嚴格意義上的股權由較大差距。因此,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條件下,農戶讓渡的是土地承包經營權分離出來的部分權能,土地股份合作社取的是承包地使用權*參見[16]第422頁。。也即是,土地承包權仍由農戶家庭掌握,土地股份合作社只擁有土地經營權;一旦土地股份合作社經營失敗、需要解散,土地經營權復歸農戶家庭并與其一直擁有的土地承包權合二為一成為原物權性質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由此不難發現,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條件下的土地經營權具有相對性、暫時性、短期性和意義自治性等特征,是債權性質的權利。需要指出的是,如前文所述,中央政策精神已經明確“三權分置”條件下,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主要通過放活土地經營權的方式,允許其可以“入股合作社和龍頭企業”。
(三)土地承包經營權互換與轉讓——物權性質的土地經營權
1.互換
互換是指承包方之間為方便耕作或者各自需要,對屬于同一集體經濟組織的承包地進行交換,同時交換相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參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第35條。。不難發現,土地承包經營權互換是同一發包方所發包的兩個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互相調換。其結果是互換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戶均沒有喪失土地承包經營權,只是對兩個農戶家庭所擁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所對應的承包地做了調換。因此,土地承包經營權互換條件下,兩個農戶家庭均保留土地承包權和土地經營權,并且各自的承包權和經營權是合二為一,未發生分離的。由此,可以認為,土地承包經營權互換條件下仍有農戶家庭掌握的土地經營權作為其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一部分,也是物權性質的。
2.轉讓
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是指承包方有穩定的非農職業或者有穩定的收入來源,經承包方申請和發包方同意,將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經營權讓渡給其他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農戶,由其履行相應土地承包合同的權利和義務的行為[19]。根據《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第35條規定,“轉讓后原土地承包關系自行終止,原承包方承包期內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部分或全部喪失”,可知,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條件下,原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法律資格和原擁有的物權性質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同時消滅*參見[16]第325頁。。因此,轉讓方在移轉其土地經營權的同時,也放棄了土地承包權;受讓方在獲得轉讓方土地經營權的同時,也在承包期內擁有了土地承包權。并且,與土地承包經營權互換相類似,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之后,受讓方所獲得的是物權性質的,未發生承包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完整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由此可以認為,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條件下的土地經營權作為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一部分,是物權性質的。
五、農地產權重構
既然農地產權“三權分置”之后,不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方式下,土地經營權分屬物權和債權兩種權利性質;土地承包權雖然仍屬物權性質,但在土地承包經營權轉包、出租和入股三種流轉方式下,其與原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所擁有的物權性質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在權能上已有所不同,這些都使農地產權的重構成為可能。需要指明的是,前述研究所涉及的土地承包權和土地經營權均為農地流轉一級市場的范疇,還有必要研究農地流轉二級市場條件下,土地經營權再流轉的機制機理,從而進一步豐富農地產權結構。
(一)土地經營權再流轉:轉(出)租、抵押與擔保
1.轉(出)租
轉(出)租包括轉租和出租兩種形式。轉租是指農戶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出租的方式將土地經營權讓渡給其他農戶或者種植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農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之后,由這些承租方作為出租方將土地經營權再次租賃給他人從事農業經營的行為。農地流轉二級市場上的出租,指的是在土地承包經營權以轉包、入股、轉讓、互換等方式流轉給其它農業經營主體之后,由這些農業經營主體將土地經營權在一定期限內租賃給他人從事農業經營的行為*以北京信托的一單土地信托為例,2014年3月,北京信托在北京密云縣水樟村推出首單土地信托產品,該項目采用“財產權信托+資金信托”雙信托結構。水樟村將約1700畝農地的土地經營權通過股份經濟合作社集中起來,由該土地合作社作為委托人成立財產權信托,委托北京信托管理土地經營權,再由北京信托將土地經營權流轉給圣水櫻桃專業合作社經營,用于種植水果等農作物。參見:《土地經營權流轉潮起》,http://business.sohu.com/20141226/n407297078.shtml,2015年5月10日訪問。。
2.抵押與擔保
我國現行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法》規定,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耕地承包經營權不允許設定抵押。但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并保持長久不變,在堅持和完善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前提下,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為農地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提供了政策依據。并且,2014年中央1號文件進一步提出,“允許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向金融機構抵押融資”。
基于此,筆者認為,以“三權分置”為基礎,在農地未流轉條件下,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是指抵押人(原土地承包經營權人)在物權性質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有效存在的前提下,為擔保自己或者他人(第三人)的債務履行,以不轉移農地的占有,將土地經營權作為債務擔保的行為。在農地流轉*農地轉讓和互換流轉條件下,土地經營權抵押的定義與農地未流轉條件下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抵押相同。條件下,土地經營權抵押,是指抵押人*如果農地流轉方式為轉包,則抵押人為受轉包人;如果流轉方式為出租,則抵押人為承租人;如果流轉方式為入股,則抵押人為農民合作社或農業企業。在通過轉包、出租、入股取得的物權性質或債權性質的土地經營權有效存在的前提下,為擔保自己或者他人(第三人)的債務履行,以不轉移農地的占有,將債權性質的土地經營權作為債權擔保的行為。當債務人不按照約定履行債務時,債權人(抵押權人)有權依法拍賣、變賣債權性質的土地經營權的價款優先受償或以債權性質的土地經營權折價受償。
(二)農地“三權分置”中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定位:“三權”關系的紐帶
在土地承包經營制度建立之初到各地出現農地流轉市場這一時期,土地承包經營權是個“復合的概念”,承包權屬于農民家庭,經營權屬于家庭成員。總體上看,默認土地的承包人與實際經營人為同一主體。但是,隨著農村農地流轉市場的自發與非自發出現,無論土地承包經營權以何種形式流轉,不論農民個人抑或中央政府均不希望農民失去土地承包經營權*從中央政府將15年承包期延長到30年,到后來又提出土地承包關系“長久不變”可見一斑。。現如今,土地承包經營權一分為二,進而承包權主體與經營權主體相分離,正是中央政府在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原則下所做出的農村土地產權重構的現實選擇*參見[1]。。從某種意義上說,要厘清“三權分置”中“三權”的關系,土地承包經營權是不可回避的一種權利(詳見圖1)。
(三)農地“三權分置”條件下農地產權改革與重構機理
承包經營權一次分離激活了“人”(農民)的積極性,推動了農村生產力大解放。承包經營權二次分離將激活“物”(農地)的靈活性,促使農村生產力發展再一次飛躍。從邏輯關系上講,先有土地所有權后有用益物權性質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然后才有土地承包經營權分離后的家庭承包權和土地經營權。而且,在農地流轉的條件下,通過將物權性質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一分為二,可分置為土地承包權(物權性質)和土地經營權(在農地轉包、出租和入股流轉條件下為債權性質;在農地轉讓和互換條件下為物權性質)。
在農地流轉一級市場,土地承包權不論何種方式流轉,均屬于物權性質。并且,土地承包權屬農民家庭/農戶所有,是農民家庭成員基于其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這一特殊身份而取得的。土地經營權則在不同的農地流轉方式下,呈現出不同的權利屬性。在農地轉讓和互換條件下,受讓方(轉讓時)或者互換雙方(互換時)所獲得的是物權性質的、未發生承包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完整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此種條件下,土地承包權和土地經營權實際上是合二為一并內含于土地承包經營權之中。因此,土地經營權作為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一部分,是物權性質的。但是,在農地轉包、出租和入股流轉條件下,土地承包權均仍屬農地流入方(農戶),只有土地經營權屬于農地流入方(實際經營者)。此種條件下,與土地承包權相比,土地經營權由于呈現出明顯的暫時性、短期性、相對性和意思自治性等債權特征,從而成為債權的一種。
在農地流轉二級市場,包括其他農戶或者種植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農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內的農地實際經營者,在獲得土地經營權之后,還可以將土地經營權轉租(轉租方以租賃方式獲得土地經營權時)和出租(出租方在土地承包經營權以轉包、入股、轉讓、互換等方式流轉條件下獲得土地經營權),也可以將土地經營權以抵押擔保的方式向金融機構進行融資。

圖1 “三權分置”條件下農地產權重構簡圖
這樣的產權重構,既沒有改變農地集體所有制和農戶對承包土地的承包權益,又在厘清土地承包經營權、土地承包權和土地經營權相互關系的基礎上,有效放活土地經營權,穩定農地流轉雙方對農地利用的合理預期,從而使農地產權關系更加合理,為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進一步釋放土地改革紅利奠定產權基礎。參考文獻:
[1]高云才,馮華.韓長賦:“三權分置”改革是重大制度創新[N]人民日報,2014-12-22(2).
[2]陳錫文,韓俊.中國特色“三農”發展道路研究[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134-135.
[3]羅必良,凌莎,鐘文晶.制度的有效性評價:理論框架與實證檢驗——以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為例[J]江海學刊,2014(5):70-78.
[4]陳起陽.“三權分離”背景下對于土地承包經營權制度轉型的思考[N]吉林日報,2014-7-15(4).
[5]劉守英.農村集體所有制與三權分離改革[J]中國鄉村發現,2014(3):8-14.
[6]商灝.黨國英:一號文件或倒逼土地承包權交易[N]華夏時報,2014-1-23(17).
[7]鄭志峰.當前我國農村土地承包權與經營權再分離的法制框架創制研究——以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為指導[J]求實,2014(10):82-91.
[8]申惠文.農地三權分離改革的法學反思與批判[J]河北法學,2015,33(4):2-11.
[9]涂端午.教育政策文本分析及其應用[J]復旦教育論壇,2009(5):22.
[10]申惠文.法學視角中的農村土地三權分離改革[J]中國土地科學,2015,29(3):39-44.
[11]陶鐘太朗,楊遂全.農村土地經營權認知與物權塑造——從既有法制到未來立法[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15(2):73-79.
[12]潘俊.農村土地的“三權分置”:權利內容與風險防范[J]中州學刊,2014(11):67-73.
[13]張力,鄭志峰.推進農村土地承包權與經營權再分離的法制構造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15(1):79-92.
[14]馮華,陳仁澤.陳錫文: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底線不能突破[N]人民日報,2013-12-5(2).
[15]王利明.物權法研究(修訂版)上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252.
[16]丁關良.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328.
[17]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68.
[18]黃少安.從家庭承包制的土地經營權到股份合作制的“準土地股權”——理論矛盾、形成機理和解決思路[J]經濟研究,1995(7):33.
[19]房紹坤.物權法用益物權編[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110.
(本文責編:辛城)
“The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of Rural Land and Reform Issues:Policy Track,Text Analysis and Property Reconstrction
ZHANG Yi1,ZHANG Hong1,BI Bao-de2
(1.SchoolofCivilandHydraulicEngineering,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2.SchoolofFinance,RenminUniversity,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Since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the reform idea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n “the seperation of three rights” of rural land is increasingly clear.The academic circle has conducted discussions and researche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However,currently the problem of “the seperation of three rights” is still in the stage of being without consensus.After sorting out the evolution track of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al policy of “the seperation of three rights” in recent years and analyzing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three rights and the contract-management righ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al policy of “the seperation of three rights” by using the text analysis method,the paper further discriminates the consensus and disagreement within the academic circle on the aspect of legal property of the contract right and the management right in “the seperation of three rights”,finding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seperation of three rights” and the rural land remise,the contract right still belongs to the property right,and is the right owned by collective members based on their specific identity,which is the same as the original land contract-management righ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being without the rural land remise.The operation right belongs to the nature of creditor’s righ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ubcontracting,renting and shareholding the land contract-management right,and belongs to the nature of property righ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and remise and mutual exchange.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the paper also makes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China’s rural land property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rural land;seperation of three rights;contract-management right;contract right;operation right
中圖分類號:D91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9753(2016)03-0013-11
作者簡介:張毅(1986-),男,河南三門峽人,清華大學土木水利學院博士后,研究方向:土地制度與政策。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完善我國農村土地股份制制度設計研究”(14BJY090)
收稿日期:2015-09-08修回日期:2016-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