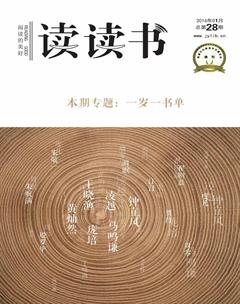《音樂的容器》后記
馬慧元
本書是又一本音樂和讀書筆記。雖然寫了不少和音樂相關的文字,但我從來不認為自己的寫作是樂評,我只是記錄自己讀書、學音樂的點滴而已,至于對音樂家蓋棺論定、好漢排座次的事情,還是留給真正的評論家吧。我也不是書評人,我只希望在讀書的過程中發掘作者的“上下文”,努力實踐一種近于和作者平行的思考軌跡,然后和作者“對照筆記”。這可是個不小的野心,并常常因無知而感到絕望,只能不斷放慢腳步。
因為喜歡管風琴和相關的歷史,我看過不少管風琴的歷史紀錄片,贊嘆之余,也有點怪他們把這一切弄得太完美了,尤其是管風琴演奏的場合,往往是在靜謐的老教堂里,氣氛純美而孤絕,哪怕樸素,也有一種遙遠的驕傲。但真正的歷史樂器、教堂生活哪可能是這個樣子?
容我離題一下——碰巧讀到獲得諾獎的加拿大作家門羅其人,還頗有感覺。我知道這是個寫“家長里短”的人——小說家當然大多離不開市井生活,都不是清高避世的人。不知為什么,我讀一點門羅,竟然想起管風琴的歷史——看上去這是多么極端不同的兩個世界啊!然而管風琴是個長久之物,連接著村莊的一生一世,多少生生死死、人情世故都在那個氣場里。在我眼里,任何歷史場合都是一個“復雜系統”、混沌系統,里面是掃不清的灰塵,清不完的廢物,人與人之間則有無盡的糾葛和誤會,而管風琴的管子里則可能是小動物的樂園!世世代代,村莊、城鎮里,圍繞管風琴的財政、人事、音樂紛擾從未斷絕,表面的清潔之下仍然是俗世的故事。除非你把這一切付之一炬,不然它只會變得越來越復雜。不僅教堂,一所庭院,一個家都是一個復雜系統,雖然我們擁有的語言標簽不斷豐富,但仍追不上世事無常,能做的只是捉住一片“生活”,裹上幾個在絕望中抓住的詞語。歷史就這么傳下來,藏在生活里的話語好比微弱的光線。
書和生活之間的關系,就是這樣可疑,經典尤為可疑。但我至今還是迷信著它們對生活的誠實、和生活的聯系。
其實,我自己讀書寫文章,希望表達的就是這樣的聯系:管風琴、古典音樂、歷史和科學,這都是人的世界,所謂俗和雅只是人為的標簽。各種經典和生活的聯系也不是我的發明,它一直就在那里。
我在一篇小文里寫過這樣一段,又開始在管風琴上彈法國浪漫派作曲家弗朗克的《前奏曲,賦格和變奏》,突然想起以前自己寫過這么一句,“所謂的高雅藝術,不驕傲,不高貴,不冷漠,它來自生活中最艱難的堅持,最誠懇的關懷。而那些最細致的手藝,背后都是卑微的生活。”我的天,那不正是過去彈弗朗克的時候寫出來的嗎。幾年前的一天,我在教堂里練琴,天氣不錯,直到傍晚都很亮,光一塊塊地從教堂的彩色玻璃里潑進來,而管風琴上的增音音箱開開合合,聲音的波動也好比光線進出。音樂柔美,但枯燥的增音踏板開合練習讓我厭煩得發瘋。老師走過來對我說,“時間到了,我們要用琴,你回去吧。”我不知不覺停下來。此刻音樂未冷,而教堂里氣場突變,陰森之感排山倒海。音樂就是這樣,會打開生活中最觸手可及的意象,而此時,弗朗克的余溫和當時的情景合作成一幅特別的畫面,竟然直通“消失”和“死亡”——那是四川大地震的日子,中國人日日聽到殞命和逃生。高雅藝術的背景里就這樣密布著卑微和痛苦,或者說,任何有歷史的精深之物都有受難的印跡,它總是有效地吸收各種哀感。
這個瞬間或許只是巧合,或者只是大腦不邏輯的通感。可我還是感觸良多,因為人類情感的彼此依托,也因為人生的多樣和相似。有時我覺得,前人已經為我們擔當了很多,經典是我們永遠的朋友,可有時又覺得人生懸隔。哀樂悲慨之間,讀懂很難。
所以我只能奢望自己很慢很慢地生活,有記錄,有幻覺,有奇跡面前的驚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