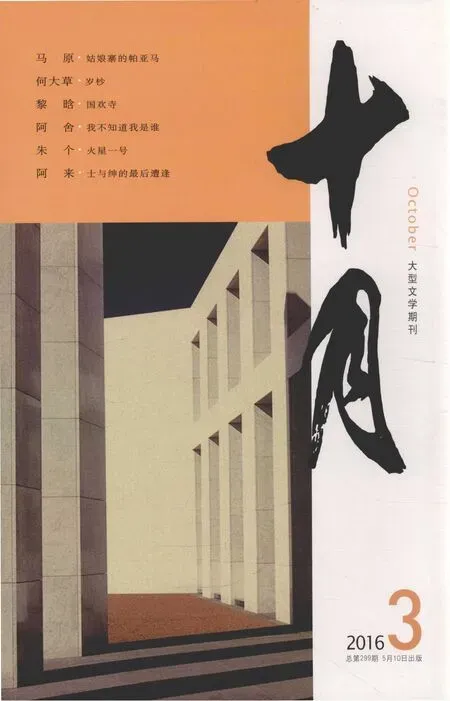摩天輪
朱個
一
阿祖原本不知道,不睡覺的時候也可以穿睡衣。意識到這點(diǎn)時,他已經(jīng)五十多歲了。
從前輪到不上班又得在家待著的日子,他都套著老頭衫和棉毛褲,要么再加件兩用夾克。這些衣服老早就舊了,起初就不是鮮艷的顏色,現(xiàn)在便更加黯淡,黯淡的底子上泛出灰白,是年年如此的痕跡,倒根本也顯不出什么難為情來。
他沒有過那種專門叫“睡衣”的東西,待到睡覺的時候,全部扒光就是了。阿祖從來沒有覺得這樣不大方,也沒有什么不舒服。過不了幾年他就要退休了,五十出頭的男人,別說在家里,就是在外面也不會在乎這些枝枝節(jié)節(jié)的花頭了。
直到這天。他撕開包裝袋,拎起這身在他看來有點(diǎn)兒陌生的衣服。
“家居服!”說話的人是阿祖的小姨子。
“怎么樣,姐夫?”
“這個顏色還行吧?”
“不就是睡衣?”阿祖的太太美萍問道。美萍緊握著茶杯,披著她有點(diǎn)兒嫌小而不怎么穿出去的棉外套,窩在沙發(fā)另一頭。
“家居服。”小姨子美芳說。
美萍探身看看,嘴角輕輕扯開,眉毛輕揚(yáng),沒有爭辯。
美芳似乎著急,聳肩賠笑:“隨便怎么叫,反正就是平時在家里穿穿好了。”
阿祖還沒有收到過這樣的禮物。他的腿開始輕輕地抖,低著頭有點(diǎn)兒不敢看美芳,也不敢看美萍。還好包裝袋很大,蓋在上面也沒人注意。美芳嘴上說“家里穿穿”的衣服有一套,上裝和長褲,暗暗的紅色,印著一個個銅版圖案。阿祖知道這種顏色,他教過的課文里有一篇寫到過這種顏色,好像是叫豬肝紅。那篇課文寫一個人的臉,說像豬肝一樣紅了起來。阿祖年復(fù)一年地教,印象很深,偶爾又不免懷疑,豬肝并沒有那么鮮麗,用來形容紅臉蛋究竟妥不妥,但這樣的念頭也只是一閃而過,他才不愿讓自己被這些無聊的想法糾纏。睡衣的面料有種茸茸的觸感,還夾了薄薄的棉層,為了固定棉層又在表面縫出了菱格的走線,顯得既厚實(shí)又挺括。衣領(lǐng)處的商標(biāo)織著“富貴貓”,下面還有一行小字“精品家居服”。
美芳用著鼓勵的眼神:“姐夫,試試大小,小了可以換。”
“可以換?”美萍問。
“網(wǎng)上購物都有七天退換,”美芳說,“姐夫的尺碼我也是猜的。”
“敢網(wǎng)上買東西,虧你不怕上當(dāng)。”美萍笑說。美萍比美芳大幾歲,又多讀了幾年書,眼光自然是要謹(jǐn)慎一些。大約正是靠著這一點(diǎn),她當(dāng)上局里的辦公室主任,幾屆領(lǐng)導(dǎo)班子下來,風(fēng)氣穩(wěn)穩(wěn)當(dāng)當(dāng),口碑始終不錯。就女人的天性來說,謹(jǐn)慎一些不是壞事,但阿祖有時覺得她過于謹(jǐn)慎了,性格里那點(diǎn)兒含量本就偏少的活潑跳躍的東西漸漸地就被壓制了。她經(jīng)常把在機(jī)關(guān)賴以謀生的素質(zhì)帶進(jìn)家門,這個規(guī)矩、那個當(dāng)心,把整個家弄得風(fēng)聲鶴唳緊張兮兮的。尤其近年來,美萍非常看不慣網(wǎng)購,她認(rèn)為網(wǎng)上賣的全是假貨,都是看不見摸不著的騙子。雖說阿祖也不懂如何在網(wǎng)上買東西,可一件事情在還沒學(xué)會做之前就被禁止掉了,這著實(shí)叫人憋屈不已,還有點(diǎn)兒無所適從。
阿祖換上新睡衣從臥室出來,美芳剛關(guān)上洗手間的門,看到了他,并不很大的眼睛夸張得睜開了,發(fā)出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聲音,這聲音聽起來多多少少有些名不副實(shí)。“精神,很精神,姐你看看,是不是這樣?”
“唔……”美萍的聲音傳出來,人已經(jīng)不在沙發(fā)上,公寓很大,一時半會兒不知道她在哪里。
在軀干上鋪展開來的睡衣,似乎比起先前折疊的時候要鮮活一些,銅版圖案是略微帶閃的印花材質(zhì),襯得阿祖一個黃蠟蠟中年人都有了活泛起來的模樣。
“姐,我說叫姐夫看會兒電視。”美芳陪著笑,淺淺地看阿祖。明明是說給阿祖的話,聽起來都是在跟美萍說。她示意阿祖快坐下來,仿佛因為姐姐暫時離場,而需要她來招呼一下似的。阿祖新衣服上身,又在自己家被款待了,有些不自然,卻也不是不習(xí)慣。
美芳跟她姐姐走動得不頻繁,逢年過節(jié)都是禮貌地坐坐就走的。今天吃了晚飯來,現(xiàn)在八點(diǎn)多了還沒走,又給阿祖帶了禮物。按道理,美萍應(yīng)該開口問問,妹妹是不是有事相求。美芳是百貨公司的一名售貨員,高中畢業(yè)就上班了。去年忽然離婚了,不聲不響地,保密工作還做得特別好,美萍和父母都到最后才知道。至于問她一句為什么,美芳總是像背不出課文的學(xué)生一樣,三言兩語就卡頓了。在這事上,美萍至今有點(diǎn)兒抱怨,態(tài)度也始終不冷不熱的。
阿祖打開電視機(jī)。關(guān)節(jié)彎折的所在,新衣服都還生硬著。美萍不知道在干嗎。
“姐夫,怎么凈看廣告啊。”美芳忽然說。
阿祖一驚,回過神來,探身去拿遙控器。
美芳卻說算了,她從包里掏出了一只黃色塑料盒子。“姐夫,聽聽音樂。”她說。
按動了某個開關(guān),美芳把盒子放到阿祖面前。一陣靜默以后,幾個音符從盒子里細(xì)細(xì)地溜出來,怯生生而孤零零的,還不能完全蓋過電視機(jī)里的廣告。阿祖聽得懂,是一種民族樂器。盒子有個外放的喇叭口,好像在穿過喇叭口的一排排孔洞后,聲音躍入到廣闊天地,才噌地一下變粗了,濕潤、柔滑,迅速高亢勃動起來。
那股旋律阿祖一定是頭一回聽,卻不能覺得陌生。民樂總是這樣的,每一小段音節(jié)的急轉(zhuǎn)回合,都不出所料,正中下懷。
“好聽嗎?好聽的吧!”美芳問。
“這叫葫蘆絲。”她補(bǔ)充。
“俄羅斯?”美萍忽然冒出來,她正從沙發(fā)后面路過。
美芳好像沒有聽見姐姐說話。阿祖本來打算大笑,忍住了。
曲子播放到此刻,背景里出現(xiàn)了電聲伴奏。伴奏把曲子的節(jié)奏強(qiáng)化了,一拍一拍都拎出來,變得有些渾濁,還喧鬧。
“《歡樂的潑水節(jié)》。”美芳說。
這大概便是曲名了。《歡樂的潑水節(jié)》,阿祖腦海里出現(xiàn)姑娘小伙奇裝異服熙攘著亂作一團(tuán)的情景,或許,他可以再往下想想……還有濕透的衣褲緊緊貼著身子。
“美芳,你還聽這個?”美萍問。聽到聲音她出來看看,手指煩躁地敲擊著沙發(fā)后背,胸部以下都在落地?zé)粽找陌堤帯?/p>
“剛開始聽,也沒多久。”美芳答,她好像沉醉其中,隨著曲子擺動起來。
葫蘆絲的曲子已經(jīng)糊成一片,音量四散著覆蓋了整個兒客廳。沒有先前簡單的獨(dú)奏那么分明,阿祖越聽越摸不著頭緒。
當(dāng)他再次朝那個方位看過去,美萍已經(jīng)不在了。
二
阿祖一覺醒來,身上還穿著美芳送的夾棉睡衣。上衣撩到了胸口,一只褲管也蜷縮在膝蓋上面。按入春的季節(jié)說應(yīng)該是有點(diǎn)兒厚了,半夜腳會自動伸到被子外面。跟以前光膀子睡不一樣了,他再也不用介意會著涼。
小臥室門窗緊閉,即使清晨乍暖還寒,積蘊(yùn)的暖意依舊簇?fù)沓蓤F(tuán)。昨晚抽過幾根煙,房里彌漫著床褥被熱量蒸過后,混合著煙和皮膚油脂的熱烘烘的氣味。阿祖朝天躺著,回想起幼年在鄉(xiāng)下,蚊香燃盡的夏季早晨,剛剛被窗口的一絲涼風(fēng)吹過,小孩子不情愿地醒來,手上、腳上、臉面上所具有的,也便是這種氣息。阿祖早出晚歸大半輩子,起床都是匆匆解決,不常想這些,一想便把他想得稍微傷感起來。睡衣的棉布料,穿洗過幾次后,新東西的陌生味兒才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常用的洗衣粉和自己的體味兒,還變得越發(fā)柔軟,貼在皮膚上,說不出的懶惰和安全。從前怎么就不知道穿睡衣。阿祖的胳膊架在腦袋上,深深地吸氣。
阿祖身材矮壯,手腳都粗短,卻只可說短小而不能用精悍形容。一張國字臉,雙眼皮大眼睛,眉毛濃密緊湊,直到末梢也沒有四散出去的跡象,這相貌在年輕時頗使他驕傲過一陣。也僅僅是一陣,并沒有帶來更多幻想中的羅曼史。他跟美萍是經(jīng)介紹認(rèn)識的,單看她的長相,平心而論不如他。那時候他二十出頭兒,剛從師專畢業(yè),分配在縣城下面的鄉(xiāng)鎮(zhèn)初中。下班后,他得騎著一輛遠(yuǎn)房親戚淘汰下來的自行車,穿過十幾里暗黑的田野,去城里找美萍。說不清那時候,他是更愿意望見縣城的萬家燈火,還是更愿意捏到美萍的手。幾個月的相處后,在準(zhǔn)岳父的主張下,阿祖調(diào)進(jìn)了縣城高中,住到了美萍家。
二十多年過去,阿祖身上有種若隱若現(xiàn)的敏感細(xì)膩是美萍所弄不懂的。阿祖究竟是個語文老師,在課堂上,他有很多時刻必得要傳授一些只可意會的情感,而為了這些情感,他是必得將自己培養(yǎng)出某些情緒的。總有些時刻在他走出教室后,這些情緒還絲絲縷縷地黏在心里。比方說,阿祖一直是喜歡“浪漫”這個詞的,這個詞通常壓在他心里很多事情的底下。這個詞代表的意思,讓它只能是一層軟軟的鋪墊,一個名詞,一個形容詞,一個狀語,最多當(dāng)一種修辭罷了。他如果把它抽出來,擺上桌面的話——那么,這種情形他還沒有嘗試過。
他愛養(yǎng)花。他不明白美萍為什么討厭花,即便她的理由很正確——招蚊子,阿祖也不能理解會有女人討厭花。養(yǎng)花是阿祖做過最浪漫的事了。阿祖只養(yǎng)三種花,蘭花、茶花和杜鵑花。他買花,從來只告訴美萍價格很便宜。蘭花不便宜,品種稍好一苗就幾百上千,他拿所有的私房錢都買了花。花是自自然然地生長,很能爭氣,三種花開放起來,氣質(zhì)從優(yōu)雅到雍容到絢爛,有一個指數(shù)級別的遞增。好幾次美萍同事來家參觀,贊不絕口,美萍隨手就送人家一盆,阿祖一般也只能打落門牙往肚里吞,不只心疼鈔票,更心疼在別人手上短命。養(yǎng)花這事,跟其他事一樣,阿祖不敢有怨言。三種花都不是容易伺候的花。蘭花對濕度要求很高,茶花對溫度也很敏感,杜鵑對酸堿度很講究,在阿祖居住的灰蒙蒙的南方小城,它們的葉片總是蒙滿灰霾。可阿祖就是有這樣的耐心,晚飯后他會長久地待在陽臺上,細(xì)細(xì)梳理每一根枝條,擦拭每一片葉子,讓它們彎曲垂掛的每個表面,在光線下都呈現(xiàn)出油亮無瑕,直到夜晚全部降臨,什么都看不見為止。然后,阿祖就點(diǎn)起一根煙,在煙霧里,平心靜氣地看著朦朧的花花草草。
自美芳那晚來家,已經(jīng)過去兩個月。這兩個月里,美芳幾乎沒有來過。今天休息,阿祖起了床就待在陽臺上擦葉子。每片蘭葉都翻著合理的弧度,大口徑的、不過分的弧度,就像那夜的美芳已經(jīng)燙了很久的頭發(fā),直是算直的,又間隔均勻地微微鬈著,每段拐彎的地方都有同樣光亮的色澤。阿祖擦著擦著,心頭的褶皺反倒越來越深,怎么都撫不平整。
今天又要給小迪補(bǔ)課。那么,阿祖想想美芳是很自然的事情。
小迪是美芳的兒子,正讀高三。成績不好,沒考上阿祖任教的學(xué)校。大約已經(jīng)不是一般的不好,連語文都想要補(bǔ)一補(bǔ)。
“語文沒什么好補(bǔ)的……”阿祖這樣說給美芳聽。
也不知道當(dāng)時美芳是不是聽懂。阿祖說了些語文應(yīng)該怎么學(xué)之類的話,上課要好好聽,課后要多看書,基礎(chǔ)知識很重要。這種話每回家長會都能重復(fù)好幾遍,阿祖說起來輕車熟路。學(xué)生們補(bǔ)數(shù)學(xué)、補(bǔ)英語,分?jǐn)?shù)提高得嗖嗖快,沒有人去補(bǔ)語文,那么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阿祖有推辭的意思,可即便是推辭,輪到可以侃侃而談的話題時,也瞬間在美芳面前有了信心似的。
“小迪基礎(chǔ)太差。他們老師這么說他。”美芳關(guān)小了音樂盒子,葫蘆絲的聲音消失了,最后說的幾個字突兀地變響亮了。
她的身體轉(zhuǎn)向姐夫。阿祖看清了那雙水腫的眼皮,這跟美萍是很像的。和美芳交往實(shí)在太少,阿祖跟美萍結(jié)婚時,美芳悶聲不響地坐在人堆里,不像個家里人。每回只有看到美芳的臉,好像才能把她認(rèn)出來。姐姐臉蛋瘦窄,配這對眼皮有點(diǎn)兒拿捏不穩(wěn)。這雙眼睛長到美芳肉乎乎的臉上才協(xié)調(diào)一些,腫眼皮顯得她憨直又和氣,像個慈眉善目的女菩薩,軟乎乎地亟待供奉。阿祖五十多了,最年輕的同事有時戲稱他“阿祖伯”。他們叫起來的時候,從不會怯生生的。被人叫成伯,心大概是同樣的軟,阿祖沒辦法拒絕這樣一雙眼睛的懇求。
小迪坐下來的時候,阿祖又跟往常一樣發(fā)現(xiàn)了他的不靈活。和身材比起來,小迪的屁股有點(diǎn)兒大,癡肥的樣子,不像是擅長運(yùn)動的小孩兒。阿祖整個兒下午都要給小迪分析病句和成語。小迪穿著校服,鼻頭油油的,下巴很短,有幾根胡子碴兒,戳在細(xì)嫩的皮膚上。他是個沉默的學(xué)生,阿祖講得很慢,同時也不很明白他有沒有聽進(jìn)去。
“你媽媽呢?”阿祖放下卷子裝作漫不經(jīng)心地問道。
小迪讀書不好,性子還是乖的,大人問話有一句答一句。
“不知道。”
“不知道?”
小迪放下筆,眼神越過阿祖的肩膀,點(diǎn)點(diǎn)頭。
“哦。”阿祖吭氣,朝他看的方向看了一下。
美萍從里屋出來,她挎?zhèn)€包,穿戴整齊。按照雷打不動的慣例,星期天要去爸媽家。經(jīng)過他倆旁邊,她丟給阿祖一個眼色。
昨晚,美萍忽然問:“小迪自己來,美芳不來的?”
“嗯。”
“她倒是知道省事。”
“嗯。”
“星期天你就走不開了。”
“嗯。”
“你們同事做家教怎么收費(fèi)的?”
阿祖沒吭聲。
“說句話!”美萍走過來,戳戳阿祖手上的報紙。
“我也沒地方去走哦。”阿祖翻起上眼皮,從眼鏡框外面看著美萍模糊的臉說道。她臉上有被遮蔽的慍怒,影影綽綽地閃現(xiàn)。美芳和我的事情,跟你有什么關(guān)系,阿祖想說。想想而已,一個屁都沒放。
小迪已經(jīng)來家補(bǔ)過好幾次課了。整個兒事情,阿祖說不上不好,也談不上很好。差不多的年紀(jì),總不免要拿來與自己兒子比的。阿祖兒子去年讀的大學(xué),考到北京,985院校,美萍擺了十桌,興高采烈。小迪和美芳也在場,坐外公外婆邊上不聲不響。兒子是運(yùn)動健將,讀書又好。阿祖用著兒子淘汰下來的電腦、手機(jī),還穿著幾件兒子的舊衣服,男孩兒的年輕荷爾蒙依稀殘留在衣領(lǐng)、袖口上,怎么都洗不干凈,就像兒子執(zhí)拗地抱著他,而他帶著這股自己早已消散的氣息吃飯睡覺,卻跟兒子離得越來越遠(yuǎn)。兒子輕描淡寫就一路順風(fēng)的人生,實(shí)在跟他爸爸不太相像。于是,反而是小迪。他慢,他拖沓,他既大又不靈便,他每個字都含在嘴里嚼很久,在那些遲緩的被拉長的需要等待的過程里,阿祖體會到了平靜,和不著急總會來的東西。幾回補(bǔ)課下來,他漸漸喜歡上了這個孩子。
阿祖明白美萍那個眼色是什么意思。即使小迪看不到,而他也喜歡小迪,阿祖卻好像不能夠不回應(yīng)。美萍的眼神里含著久違的同盟感,仿佛在說她雖然沒有教課,但她能和阿祖一樣,知道那是個怎樣不招人待見的小孩兒,還有個想占他們家便宜的媽。結(jié)婚以來,她很少流露出尋找戰(zhàn)友的姿態(tài)。他舍不得這難得的同仇敵愾的施予,甚至還有點(diǎn)兒感激,他覺得自己正處在某個平臺上,并緩緩上升到與她相應(yīng)的高度。
他僵硬了零點(diǎn)幾秒,咧開嘴沖美萍笑了笑。
“她大概去跳舞了。”小迪忽然開口。
門口穿鞋的美萍直起身,她似乎嘆了口氣。沒有追問,也沒有回應(yīng),還是關(guān)門走了。
阿祖從平臺掉下來。“誰?你媽?”他問道。
“她很喜歡跳舞。”小迪點(diǎn)點(diǎn)頭。
“嗯?”阿祖問。
“跳舞沒有什么不好。”小迪說。
阿祖放下筆,盯著男孩兒。
“總是有人亂說。”小迪說。
三
葫蘆絲曲子循環(huán)播放著,輪到第三次《歡樂的潑水節(jié)》時,美芳起身說該走了。那時快十點(diǎn)了,阿祖穿著她剛送的新睡衣已經(jīng)坐到十點(diǎn)了。
他也立即站起來,美芳把他按下去,叫他繼續(xù)坐,還把電視機(jī)又打開了。
“我來收拾,這一攤子,不好意思。”她說。
美萍早早進(jìn)了書房,怕吵還把門虛掩了,她說最近很忙,總是把工作帶回家。茶幾上有幾杯冷茶和打開包裝的零食,地上掉落一些瓜子殼。美芳堅持要一道收拾了。阿祖是做慣了家務(wù)的,美芳也不是不曉得。那么,她還是這么殷勤著,阿祖心里便有些松動,微微顫了一下。美萍是不會出來做這些瑣事的,她不會做飯,也不洗碗。阿祖并不抱怨,這么多年他實(shí)在是習(xí)慣了。現(xiàn)在輪到美芳,他就有些不習(xí)慣。
其間,阿祖的手碰到了美芳。他正從茶幾上取回杯子,她彎著腰,披著一件滑雪外套。確切說,阿祖碰到的是美芳的衣服料子。滑雪外套面料冰涼,觸感膩膩的。阿祖陡然心驚,這跟皮膚好相似。
他教了三十幾年的書,眼里的學(xué)生一片又一片。有時候,他們來他辦公室,站到桌前,趴著去默寫課文,或者聽他訓(xùn)話——他訓(xùn)話算是威嚴(yán),雖然語速有點(diǎn)兒慢,用詞也不是很流利,但還是有力量的——那時候,阿祖總會有意無意地把手搭在他們肩上,或者在揮舞著手的動作同時,假裝掠過他們的胳膊、腰肢,或者前臂一小段裸露的皮膚。他太喜歡這么做了,他控制不住不這么做。他這么做的時候是很謹(jǐn)慎的,他老早說服了自己去相信,一切都是不小心的名正言順的天經(jīng)地義的接觸。即便碰到的基本是各種布料,棉布溫軟,尼龍布滑爽,可相同布料在各個人身上依舊呈現(xiàn)出稍微不同的輪廓和走向。“摸來摸去摸什么摸啊,阿祖伯?就摸了幾件衣服,有膽子往里面去啊!”有一回他們辦公室的女同事半玩笑半認(rèn)真地喊起來。阿祖憨頭憨腦地訕笑,耳朵根全紅了。他心知這不是齷齪,可是什么也說不清,大概只要這樣來一下子,他就跟他們具備了某種關(guān)聯(lián),進(jìn)而達(dá)成只有他才明了的默契,微弱卻足以自慰。
他去取第二只杯子,再次碰到了美芳的滑雪外套。這回幾乎是故意的。面料下面還有填充物,填充物下面還有面料,和真正的皮膚組織還有莫大的距離。可阿祖的下半身腫脹起來了,柔軟的觸感契合了他對日常生活的想象。久違的感受如此奇妙,他不露聲色內(nèi)心卻兵荒馬亂。很久以前,他和美萍就不睡在一起了。開始是美萍的事業(yè)處于上升期,每天工作到很晚,而阿祖早睡早起,于是兩人分了被窩。后來換了大公寓,索性就一人一間分了床。分開了就再沒合起來過,這樣也大約維持了將近十年的時光。分居開始的時候,他剛學(xué)會上網(wǎng),到了晚上,一些形跡可疑的對話框就比白天多了魅力,那些框框右上角的小叉叉狡猾地跳躍著,總是逮不住。無論點(diǎn)擊在什么部位,總跳出來一個又一個另外的框,畫面白花花的晃眼,洋溢著十足的腥味,像槍林彈雨,像一張張斑斕大嘴,簡直要了他的命。吃過幾次電腦癱瘓的苦頭后,阿祖對充滿誘惑的事物便有了力不從心,下半身也總維持著軟綿綿的日常狀態(tài),即便一覺醒來,陽具也不再像年輕時一樣變形。失去了晨勃,如同失去了和清晨有關(guān)的事物,所有分明有力的輪廓皆離他而去。他似乎漸漸意識到,當(dāng)下的一切都不是他的,他是一個還沒被這世界用過的家伙,而且世界看起來還沒有一丁點(diǎn)兒想要用用他的意思。
美芳已經(jīng)走下半截樓梯,阿祖發(fā)現(xiàn)她遺忘了她的音樂盒子。他追出去,在臺階構(gòu)成的落差上,他居于高位,向美芳伸出手。美芳仰著臉迎向樓道燈光,簡直會帶來憧憬的誤會。在她接住盒子的短暫一瞬,阿祖還并未松手的那刻,他注意到整個夜晚唯一一次,他們兩個連接在一起。靠的是那只小小盒子,維持住了某種稍縱即逝的聯(lián)系。
阿祖的下腹就在這時,出現(xiàn)了一陣絞痛,久違的腫脹也因此銷聲匿跡。
他有些遺憾,又無法挽留。美萍房里的燈還亮著,一如既往。趁上洗手間的當(dāng)兒,阿祖盡情打量自己,他總算明白豬肝紅這種紅不像紅,棕不像棕,既不刺眼還帶著暖調(diào)的顏色的確最適合五十幾歲的半老頭兒。一只腳踩在中年,一只腳邁入老年,懸而未決地,兩頭都不甘心。水箱里還有進(jìn)水的聲音在汩汩地響動。阿祖掏出陽具,包皮皺巴巴的,夾帶著內(nèi)容物垂掛下來,好像一條布口袋,底兒都已經(jīng)爛穿了。美芳剛剛用過的馬桶,馬桶圈還沒來得及翻起來。阿祖彎腰摸了一把,女人剛剛坐過的地方已經(jīng)涼了。
四
美萍穿了高跟鞋走不快。她落在最后,看著阿祖的兩爿屁股隨著腿根的行進(jìn),一左一右地上下聳動。褲子提得如此高,褲縫活生生地卡在正中間,形狀凸出得活靈活現(xiàn)。阿祖破天荒地堅持請姐妹倆出來玩兒,不知道葫蘆里賣的什么藥。美萍皺皺眉頭,腳下不像有走得更快些的意思。
阿祖前面是美芳,脫下來的外套打個結(jié)拴在腰上。她穿了球鞋健步如飛,馬尾高高挽起,發(fā)梢噌噌左右甩動,這一切都源于她軟綿綿的腰肢。那條愛跳舞的腰就像彈簧,讓美芳的上半身充滿了彈力。和她熱愛的葫蘆絲音樂一樣,今天的美芳整個兒透著一股廣場舞的歡樂。
三個人排成一條線,小孩子們歡呼著從他們旁邊掠過,阿祖提著的包袋差點(diǎn)兒被掀飛。遠(yuǎn)處聳立著一架巨大的摩天輪,眼面前高高低低的人頭,往前延伸,在摩天輪下演變成密密麻麻的雜亂背景,他們走過去,就好像走進(jìn)了更廣大的舞臺,情緒也有了發(fā)展的空間。在家的時候,一堆情緒掩埋在一堆掩埋情緒的瑣事里,買完菜就做飯,吃完飯就看報,獨(dú)自睡覺和醒來,無窮無盡。現(xiàn)在到底不一樣了,阿祖慶幸自己堅持了出門的決定。
游樂園在上海郊區(qū),如果開車的話,從小城到那兒的時間,和從上海城里出發(fā)去一趟花的時間差不多。小城的百姓自然就有錯覺,好像他們也算半個上海人,所以這里一直是小城居民的樂園。美萍來過好幾次,阿祖卻是頭一回來,美芳肯定也是。一路上,開車的美萍沒怎么說話,坐在后排的阿祖不時能從后視鏡里看見她戴著的太陽鏡,遮去小半張臉。開車人不說話,其他人好像也不太敢說,尤其是不會開車的人,總是唯恐鬧鬧嚷嚷妨礙了駕駛員似的。
本來阿祖提議坐一回摩天輪的。
“我不坐,”美萍說,“我坐過的。”她一派所有人都欠她錢而她也無所謂你們還不還的表情。
美芳露出孩子一樣嚴(yán)肅的尷尬神情,民族音樂帶來的歡樂變?nèi)趿耍砩辖拥貧獾奈兜罎u漸飄散。阿祖的竊喜消失。她雙手交互握住胳膊:“我覺得……沒什么好坐的吧。”
每次看到摩天輪,阿祖都會記起一段很傻的話。那段話寫在他們學(xué)校二樓男廁所的第一個馬桶間門上。每個工作日早晨的九點(diǎn),阿祖就走進(jìn)那個隔間。他蹲下來的時候,總能看到門上寫著一行字,以至于后來,只要一做出解手的姿勢,那段話就像淡入淡出的幻燈片浮現(xiàn)在眼前。一定是哪個學(xué)生寫的,可能是某段歌詞。“想帶你去看摩天輪,傳說摩天輪到達(dá)最高點(diǎn),就是能看見天使的時刻,相愛的人會永遠(yuǎn)在一起……”他仰視著眼前的龐然大物,圓形的機(jī)械構(gòu)造精密完美,歷久彌新。任何言語的論斷都跟它沒有關(guān)系,盡管它是人造的物體。它好像就要倒在他身上,它那么大而他這么小,即便倒下來,大概都砸不到他。
阿祖想走得快一些,或者慢一些,那樣他就能趕上美芳,也不會冷落美萍了。可他們還是在影影綽綽的人流里默契地排成直線,仿佛他們不是來玩兒,只是換個地方走路。在阿祖幾乎要支撐不住的堅持下,姐妹倆答應(yīng)了一起去坐船。在游樂園還只是某個村莊的一部分時,這條河就存在了,而現(xiàn)在成了樂園的邊界。在河邊,建筑設(shè)施縮得遠(yuǎn)遠(yuǎn)的,藏在空曠的草地里,在毋庸置疑的春陽下,人群秉持著積極進(jìn)取的態(tài)度,一簇一簇分布得理直氣壯。手劃船有兩排座位,可他們?nèi)齻€只能按照性別分配的原則,阿祖獨(dú)坐了一排,姐妹倆占了對面一排。
河道并不如何曲折,在平原地帶,兩岸的遠(yuǎn)方也沒有山巒。河岸線無聊地向前伸展,三個人都沒有說話。阿祖面對著姐妹倆,眼睛不知該置放何處,只好頻繁扭轉(zhuǎn)了身子去看兩邊的水。船夫踩著船槳,每當(dāng)阿祖動起來的時候,他就會用一種和他那時身份并不合拍的嚴(yán)厲口吻,警告阿祖會翻船。美萍低頭盯著手機(jī),美芳似笑非笑地瞅他,阿祖耳根微微灼燒,但他打算勇敢起來,打算毫不在意,打算擺出一副大丈夫做派。
“叫你不要動來動去,這么不聽話!”船夫迅捷有力地呼出聲,他有滬郊一帶口音,跟小城的方言類似。他喝止阿祖的時候,并沒有起身,船夫依舊半躺著,不緊不慢地踩著槳。阿祖輕輕一抖,攥著的手機(jī)差點(diǎn)兒掉進(jìn)河里。他正對焦漂動在水平面下方幾厘米的藻類植物,而且鏡頭還恰恰能夠掃入一角美芳搭在船舷的手臂。
在至高無上的安全提示下,美萍怒目而視。線條遲緩的水流中,兩邊駛過零星船只。
再沒有話題,不會有交談,更沒有言笑晏晏的想象。所有舉動化為泡影。船夫沒有心情跟同行打招呼,他還在氣呼呼地嘀咕,他倒霉遇上了如此不愛惜生命的顧客,他為這只飯碗承載了如此巨大的責(zé)任而嘆息不止。阿祖感到自己正在過分惹人注意,鼻孔里充盈的陽光漸漸稀薄。他冒冒失失鉆進(jìn)了光線背面,綿密的冷,從每艘別人的游船上,暗地涌來。而美芳偏偏別轉(zhuǎn)著頭,裝著在觀察某些她從來沒有認(rèn)識過的風(fēng)光。她合攏并歪向同一角度的雙腿繃緊了,從側(cè)面看去,股臀部位出人意料的豐滿,和站立時候相去甚遠(yuǎn)。在阿祖眼里這不是失望,幾乎是羞辱,她置身事外,云淡風(fēng)輕,她只管自己在那兒,像周圍的水,有無數(shù)種被掬捧被描述的可能——卻唯獨(dú)從他身邊流過去了。
阿祖胸中無限憤懣,上岸時頭也不回。他聽到有叫喚聲。“取照片,取照片了!快來看游湖的照片!”仿佛被解放出來,他湊了過去。坐在電腦前的年輕人,把阿祖他們的照片打開給他看。顯然都是在三個人不經(jīng)意間拍下的。照片一張張翻頁,阿祖眼睛亮了。
“啥時候拍的?”他問。
年輕人扁著嘴,潦草地指向后方:“看到了?那兒,有個拍照的地方。”
“要不要印?”年輕人問。
“要,要。”
打印機(jī)唰唰開動。“二十塊一張,十張,兩百。”
“買什么?”美萍警惕地出現(xiàn)在阿祖背后。
“照片?”她說,“我看看。”從年輕人手里接了過去。
阿祖掏錢的手僵在半空,美萍漫不經(jīng)心卻又含蓄豐厚的神情,仿佛巨大的引力場,叫他動彈不得。
“這張不好……也不好……這張像什么呀……美芳,你臉都變形了。”
美芳已經(jīng)穿上了外套,聽到美萍的招呼,走過來。當(dāng)她看到美萍口里變形的臉,聲音顯得有些緊張:“嗯……還好,我想還好吧。”
“這還好?”美萍把照片晃在年輕人眼前,“拍成這樣還好?多少錢,一張?”
“二十……”年輕人指著阿祖,“他說全部要的……”
“上海佬殺豬!”美萍低頭數(shù)起照片。阿祖伸手想去拿,美萍很重地甩肩膀,把他避開了。
美芳今天第一次跟阿祖說話:“姐夫,你覺得呢?好像是有點(diǎn)兒,有點(diǎn)兒歪了。”臉上某種纖細(xì)的一直能撫慰人的東西不見了。
那張是姐妹倆的合影,美芳歪斜的頭剛箍進(jìn)畫面一角。阿祖就是見到了這張眼睛才亮起來的。他絲毫意識不到那張臉有變形,就是一張肉乎乎的側(cè)面,怯生生地塞在姐姐背后。那是小城昔日里一直存在的臉,皮下脂肪把皺紋都撐開了,毫不辜負(fù)白嫩二字,確確實(shí)實(shí)地與當(dāng)下的每一寸光線水乳交融。一股氣息在他體內(nèi)穿行,有個噴嚏在鼻腔橫沖直撞,激起了一連串反應(yīng),阿祖真想把那張臉掏出來。僅此而已。掏錢包的手,終究還是軟了下來。他永遠(yuǎn)不會理直氣壯了。
美萍盯著阿祖壓低了嗓門兒:“這種照片,不知道拍什么,這么貴買來干嗎!”她眼神黯淡,隱隱的失望循著后腦勺的中軸線,依稀浮起。最熟稔的失望,始終漫漶于她的前半段人生,這刻又若即若離地撕扯著她。她很想跟阿祖好好說話,她從來都想跟他好好相處。對她來說,從過去到未來,這樣的發(fā)現(xiàn)毫無意義。
“我們不要。”美萍把照片一扔,作勢要走。
“印都印了,大姐,這幾張已經(jīng)塑封了。”年輕人聲音提高了,從柜臺后走上前。幾個無聊游客開始好奇地張望。
一只手把阿祖和美萍撥開。美芳握著皮夾,她的皮夾是桃色的漆皮,紅得發(fā)亮:“多少錢?”然后把兩張紙幣放到桌上,手掌在上頭輕輕拍了一下。
“姐,”她的手穿過美萍的胳膊,攬起照片,“拍得蠻好啊,你看上去苗條得一塌糊涂。我臉太胖,不上鏡。”
美萍不情愿地被她挾帶:“……你不是胖,是拍走形了。”
“胖的!怎么跳舞鍛煉都瘦不下來。”美芳拍拍臉頰,回頭瞥了一眼,把姐姐挽得更緊似的。阿祖又看到她肉乎乎的側(cè)面,那一眼冷淡、輕松,含著捉摸不透真正可怕的勢利,那一眼恐怕直視著阿祖而去,叫他一陣心驚肉跳之后,只剩下無限的空洞。
周圍的鼎沸人聲,某種難以理會的別人的生活,漸次離他而去。在無休無止永動機(jī)一樣運(yùn)轉(zhuǎn)的游樂園里,沉沉泛起的疲倦淹沒了阿祖。
五
牛不知道為什么出現(xiàn)在那里。阿祖看到牛就站在野地的一片杜鵑花里。
杜鵑花不知不覺開得這么旺。他想起家里的兩盆,才冒出幾簇骨朵兒而已。這些杜鵑是小城郊外最常見的品種,半透明的紫紅連成一片,云朵一樣覆滿了平地,稠密卻并不迷人。附近是一處工地,攪拌機(jī)發(fā)出渾濁的咆哮,腳手架搭在半空,晚風(fēng)從更遠(yuǎn)的地方,裹來灰塵的氣息。
那頭牛站在將近昏黃的暮色里,泥土般的脊背在花叢間聳動。一個男人揮著阿祖看不清楚的東西,呵斥著它。美萍正駕車穿越十字路口,再過兩條街,他們就進(jìn)城了。郊區(qū)的道路暢通無阻,美萍腳下使了點(diǎn)力,她想盡快回家,結(jié)束這個乏味的星期天。
“等等!停車,停一下!”美萍聽到阿祖拍打她的座椅,發(fā)出急促的呼喊。她嚇了一跳,一腳下意識地剎車,后方車輛按響尖銳的喇叭呼嘯而過。
“靠邊停一下!”
“姐夫,你干嗎?”美芳從后視鏡里看著他說。
“看到那頭牛了嗎?”阿祖指著外面,牛和男人還在緩緩走動,已經(jīng)落在車子后面了,“你們城里長大的,見過牛沒有?”
“回不回家了,阿祖?”美萍煩躁地敲擊著方向盤。
“你們沒見過牛。這不是水牛,是黃牛。”
“好的,黃牛。走不走?”美萍說道。
“水牛是黑的,角還要長還要彎。”
“姐夫。”
“很久都沒見過牛了,還是頭黃牛。這里怎么會有黃牛?黃牛跑到工地上,那是干嗎?”阿祖的語調(diào)還跟剛才一樣,仿佛美萍和美芳都是聾子,而他不光是和聾子說話,也是在和一大團(tuán)空氣說話。他望向道路那頭,男人手里的家伙,不時擊打在牛背上。牛跌跌撞撞,趔趄著越走越遠(yuǎn)。
二十幾年前,阿祖也搖晃著這樣的腳步,不太靈便地敲開美萍家的門。那是準(zhǔn)女婿初次上門,他拎著美萍準(zhǔn)備的酒水和食品,坐了長途車來到縣城。美萍開的門,她剛做了頭發(fā),卷的,順在耳后,散著吹風(fēng)機(jī)的香氣。老丈人心不在焉點(diǎn)點(diǎn)頭,手中的報紙似乎舉反了。丈母娘在掃地,她笑得像粒土豆。沒人怎么跟他談?wù)撌虑椤0⒆驵嵵囟鴣恚龊昧怂袦?zhǔn)備,那會兒忽然有點(diǎn)危險的預(yù)感,仿佛閃電劃過,短暫的明亮過后,一切依舊暗淡無光。然后,在一陣密密的細(xì)碎聲響之后,阿祖發(fā)覺有東西在他褲腿上蹭。是只貓,瘦得皺巴巴的虎皮貓。阿祖在鄉(xiāng)下見過許多貓,貓大多怕生,這只卻不一樣,他還從沒抱過它們。貓在阿祖腳上蹭得起勁,喉嚨里咕嚕嚕地嗚咽。阿祖就把貓抱了起來,貓開始在阿祖手中奮力掙扎。
美萍笑盈盈地說:“剛給它剪過指甲,很長,老把我抓傷。”還捋起袖子給阿祖看。當(dāng)時的美萍比后來豐滿,兩頰脹鼓鼓的,還有點(diǎn)兒嬰兒肥,她微笑的時候,真是存在著一股子聰明嬰兒的勁頭。
阿祖捉住貓爪子,翻過來,它的利爪果然都被剪了。從根部開始剪得干干凈凈,毛茸茸的肉墊只剩下毛茸茸的肉墊,結(jié)著黑色血痂。他拿手指一戳,貓尖叫著抽回腳爪,從他身上跌落,一瘸一拐,蹦跳著消失了。阿祖端起茶杯去廚房倒水,看到那兒還有個女孩,背對著他,好像在干力氣活。阿祖知道美萍有個沒出嫁的妹妹,那么這就是美芳了。
美芳在廚房劈魚頭,阿祖想從她身旁擠過去倒茶。美芳一定知道他就在后面,也一定知道他是誰,卻沒有絲毫挪一挪的意思。阿祖看到魚頭已經(jīng)切下來,又被她從下頜居中劈開。她還在劈,每一刀還沒劈到底就拔起來,第二刀也不看準(zhǔn)胡亂又劈下去,半個魚頭不久就紅紅白白地洇成一片,在臟乎乎的案板上,像潑翻了漆桶,明艷奪目。貓又不知道哪里鉆出來,從他腳邊擠進(jìn)廚房,在美芳褲管上蹭起來,喉嚨深處漸漸傳出陰沉的咕嚕聲。
“這貓跟你特別好。”阿祖說。
篤,篤。美芳繼續(xù)切魚頭。左肩沉著,右手機(jī)械地一上一下。
“在你們家養(yǎng)多久了?”阿祖說。
“這是我的貓。”美芳歪過頭回答。阿祖看到她胖乎乎的側(cè)臉,眉毛修得細(xì)長,好像還涂過口紅,唇色發(fā)光。篤,篤篤,篤。美芳剁了很久的魚頭。晚餐桌上,大家吃到一條沒有頭的紅燒鯉魚,也沒人問魚頭上哪兒去了。再后來,大家就把這件事忘了。
……
“你們?nèi)ゲ蝗タ磁#俊卑⒆娲蜷_車門。
姐妹倆沒有動,也沒有攔他。阿祖徑直穿過了馬路,追著牛和人往建筑工地深處去。
牛是頭公牛。有點(diǎn)兒瘸腿,陽具軟綿綿地垂在兩腿之間,若隱若現(xiàn)。阿祖想,小時候怎么從來沒有注意過牛的那活兒和身體如此不成比例。既不大又是軟的,那么丁點(diǎn)兒家伙也不能經(jīng)常用,總是浪費(fèi)。男人粗鄙地?fù)]舞著帶枝椏的樹枝,龐然大物被驅(qū)使著,聽話得很。阿祖遠(yuǎn)遠(yuǎn)跟了一陣,便有些氣餒。他走不動了。
他奇怪為什么美萍還沒有強(qiáng)硬地喊他回去。他很懊惱,也有些羞愧。最后他放棄了,蹲在幾塊磚頭上。遠(yuǎn)遠(yuǎn)望見車窗里美芳向他揮手,好像在喊叫什么,聲音全被風(fēng)吹走了。暮色四起,一個更深沉、平衡,更值得等待的夜晚即將展開。阿祖掏出了煙。一整天都沒找到機(jī)會抽煙,現(xiàn)在他想可以點(diǎn)一根了。
責(zé)任編輯 宗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