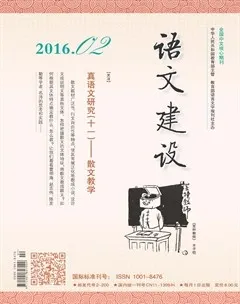散文文體特征與教學(xué)審識(shí)
散文,歷來(lái)是語(yǔ)文教材中比重較大的文體,也是語(yǔ)文教學(xué)構(gòu)成的重要內(nèi)容。在多姿多彩的文學(xué)文體林苑里,如果說(shuō)小說(shuō)是富有人物魅力的殿堂樓閣,那么散文便是精巧雅致的假山亭池。當(dāng)解讀一篇散文的時(shí)候,首先觸動(dòng)我們的,不是像小說(shuō)里展現(xiàn)的紛紜復(fù)雜的人生畫面,而是一顆至誠(chéng)至真的心靈所透出的作者對(duì)人生、對(duì)生活、對(duì)社會(huì)、對(duì)自然、對(duì)藝術(shù)的傾訴與見解,使我們通過(guò)這一扇心靈的“小窗”,獲得許多深刻、新奇的思想與智慧的啟示。因此我們說(shuō),散文是一曲“心靈的歌”,是一種意蘊(yùn)豐厚、益智陶情又具有彈性力度的一種文體。散文這種文體,看起來(lái)既不神秘,也不深?yuàn)W,語(yǔ)言表達(dá)或如平淡的談話,可是,真正理解其中的深刻意味,揭示其中的內(nèi)在意蘊(yùn)和藝術(shù)魅力,卻并不是件易事。散文是“裝著隨便的涂鴉模樣,其實(shí)卻是用了雕心刻骨的苦心的文章”[1],它需要我們?cè)诮虒W(xué)中進(jìn)行多角度、多層面的解讀和審識(shí)。
一、散文文體的主體性特征
長(zhǎng)期以來(lái),語(yǔ)文教學(xué)中對(duì)于散文的解讀,往往多以其“題材廣泛,手法靈活”“形散神聚,不拘成法”等表達(dá)形式著眼,很少?gòu)膭?chuàng)作主體的個(gè)性和人格的視角,從作家散文藝術(shù)思維的活動(dòng)特點(diǎn)上做深層探究。這種忽視創(chuàng)作主體的靜止化解讀方法,導(dǎo)致了對(duì)散文文體特征及其審美特質(zhì)與品格探究的表層化、浮淺化,而不能真正揭示散文藝術(shù)的特征和規(guī)律。
散文是一種主體性很強(qiáng)的文體,它重在作家主體意識(shí)的坦誠(chéng)流瀉,抒寫作家對(duì)人生、對(duì)生活、對(duì)自然、對(duì)社會(huì)的感悟,言我之志,抒我之情,彈撥“自己的聲音”[2]。郁達(dá)夫曾經(jīng)說(shuō)散文最大的特征是作家所“表現(xiàn)的個(gè)性”,朱自清也說(shuō)散文就是要“表現(xiàn)自己”,王西彥更明確地強(qiáng)調(diào)散文要寫出“赤裸裸的自己”。[3]巴金在秋夜翻閱魯迅的《野草》時(shí),就仿佛看見“一個(gè)燃燒得通紅的心”,“先生的心一直在燃燒,成了一個(gè)鮮紅的、透明的、光芒四射的東西。我望著這顆心,我渾身的血都燃燒起來(lái),我覺得我需要把我身上的熱散出去,我感到一種獻(xiàn)身的欲望”[4]。
這些散文大家創(chuàng)作的切身經(jīng)驗(yàn)說(shuō)明,散文是作家在生活感悟中彈撥出的“自己的聲音”。因此,在語(yǔ)文教學(xué)中,我們對(duì)散文的解讀,要注重把握作家主體思維的個(gè)性,發(fā)現(xiàn)作家彈撥的“自己的聲音”,致力于探究散文文體的主體性特質(zhì)。
散文作為主體性很強(qiáng)的文體,重在抒寫主體感受和主體情思,能使創(chuàng)作主體的個(gè)性和人格得到最大程度的表現(xiàn)。誠(chéng)然,各類文體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帶有作家的主觀情感色彩,但在教學(xué)中可以發(fā)現(xiàn),這種情感表現(xiàn)的程度和方式大為不同,其審美效應(yīng)也迥然有異。詩(shī)歌因其高度凝練而不能具體,小說(shuō)因受制于客體而不能直接,戲劇則重沖突而輕抒情,只有散文,因其自由靈活的抒寫方式,可以巨細(xì)無(wú)遺、淋漓盡致地直接抒發(fā)。因此,散文和現(xiàn)實(shí)人生的表現(xiàn)距離最近,創(chuàng)作主體和作品客體的情感投入距離最近,作家直接面對(duì)讀者,面對(duì)人生,真實(shí)直白地表現(xiàn)自我的思想、感情,是位典型的“本色演員”。因此,散文比其他文體作品更容易顯示作者的性格和人格,愛與憎,憂與喜。讀者極易走進(jìn)作品去認(rèn)識(shí)作者眼中的世界,洞見作者的人品、性格和愛好等,并從中領(lǐng)悟到自身可感卻難以言傳的情感反應(yīng)。因此,解讀散文既有理解作者的愉悅,也有發(fā)現(xiàn)自我的喜悅。
閱讀優(yōu)秀的散文,好像與朋友傾心交談,覺得親切、誠(chéng)懇,給人比較誠(chéng)實(shí)可信的印象,這是其他文體難以企及的魅力所在,是散文文體獨(dú)有的審美特質(zhì)。正因如此,散文盡管是文學(xué)林苑里的“假山亭池”,沒有小說(shuō)的巍峨壯觀,但在人格的表現(xiàn)這一文學(xué)基本原則上,卻有其他文體所不可比擬的優(yōu)勢(shì)。它從內(nèi)層的意蘊(yùn)表現(xiàn)到外層的營(yíng)造構(gòu)筑總是隨著作者的情感流向不斷地變化,從而以其最大的藝術(shù)張力和限度來(lái)抒我之情。
根據(jù)散文文體的這種主體性特征,在語(yǔ)文教學(xué)中要注重把握散文主體情感的真實(shí)性。散文抒我之情而且毫無(wú)遮蔽性的審美品質(zhì),使藝術(shù)形象的可信性和主體情感的真實(shí)性成為其獨(dú)具的藝術(shù)魅力。因此,表現(xiàn)至誠(chéng)的心靈和主體的人格與個(gè)性,是散文藝術(shù)的第一生命。在散文教學(xué)中,很多教師往往只把散文的真實(shí)作為作品內(nèi)容的審美要求來(lái)進(jìn)行解讀,而忽略了創(chuàng)作主體的“自我真實(shí)”——即創(chuàng)作主體感情的投入和個(gè)性的體現(xiàn)。我們認(rèn)為,在解讀中對(duì)“散文的真實(shí)”應(yīng)從兩個(gè)層面進(jìn)行把握:一是創(chuàng)作主體自我的真實(shí),二是作品客體形象的真實(shí)。
創(chuàng)作主體自我的真實(shí)源于作家誠(chéng)實(shí)、謙遜的人品,以及真誠(chéng)、自由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作者不避自己的缺憾、喜怒哀樂(lè),毫不掩飾地袒露自我的真實(shí)情感。散文客體的真實(shí),指的是作品真實(shí)地再現(xiàn)自然、社會(huì)、人生,它不僅要求形象本身的真實(shí),還要求形象在社會(huì)環(huán)境背景下的真實(shí)。也就是說(shuō),散文形象要能夠透視本質(zhì),通過(guò)個(gè)別反映一般,通過(guò)個(gè)性表現(xiàn)共性。張若愚的《故鄉(xiāng)與方言》,描述了他既痛恨那些瞧不起鄉(xiāng)野人的習(xí)俗,卻又諱言自己是鄉(xiāng)野人的微妙的情緒,真誠(chéng)地袒露了這種虛榮心,使人聯(lián)想到生活中許多類似的人和事,從而起到升華思想的作用。由此可見,散文雖是最具個(gè)人色彩和主體情緒的精神創(chuàng)造,但它要調(diào)動(dòng)一切藝術(shù)手段,以自己的視野去開拓別人的視野,以個(gè)體的審美意識(shí)去調(diào)動(dòng)群體的審美意識(shí),拓展人們的情感領(lǐng)域。
在散文文體解讀和教學(xué)中,教師往往忽略創(chuàng)作主體自我的真實(shí),也往往忽略生活的真實(shí),不能直面現(xiàn)實(shí)的人生,導(dǎo)致不能揭示主體的自我意識(shí)。散文作為一種文體,雖然應(yīng)當(dāng)而且必須要講究“藝術(shù)的加工”,要作“藝術(shù)化的表現(xiàn)”,但這種藝術(shù)化的表現(xiàn),主要是指藝術(shù)氛圍的渲染、藝術(shù)意境的創(chuàng)造,以及藝術(shù)表現(xiàn)技巧的精妙,并非歪曲生活的真實(shí),掩飾主體情感的真實(shí),抹殺自我意識(shí)的個(gè)性。散文主體情感的真實(shí),建立在對(duì)生活真實(shí)理解的基礎(chǔ)之上,它要富有生活的真實(shí)體驗(yàn)和生命感受,有自己獨(dú)特的藝術(shù)表現(xiàn)領(lǐng)域;它是作家最熟悉、最能理解的生活和情感世界,積淀著作者的經(jīng)驗(yàn)、智慧、修養(yǎng)以及文化構(gòu)成。
我們還要明確認(rèn)識(shí)的是,散文的真情不僅源于生活,也有賴于作家心靈的自由、超越個(gè)人意識(shí)的勇氣以及藝術(shù)表現(xiàn)上的真實(shí),即作家聽?wèi){自己的情感驅(qū)動(dòng),全無(wú)什么情感模式,任情地?fù)]灑感情,馳騁筆墨。魯迅先生曾指出:“散文其實(shí)是大可以隨便的,有破綻也無(wú)妨。”[5]這個(gè)“隨便”并不是信手就來(lái),而是指散文的情感表現(xiàn)沒有什么框式,主體自我的真情和個(gè)性能夠得以充分展現(xiàn)。
二、散文文體的開放性特征
散文是一種“心靈開放”的藝術(shù),散文文體的藝術(shù)焦點(diǎn)在于作家開放的意識(shí)和心態(tài),在于一種出自自我經(jīng)驗(yàn)世界的真誠(chéng)的情感契機(jī),一種對(duì)生活與人生的深層感悟——或者是生活的“瞬間性”和由此在頭腦中時(shí)常出現(xiàn)的令人沉思尋味的“瞬間印象”,或者是對(duì)于各種世態(tài)人事的洞察和由此引起的心靈顫動(dòng)。應(yīng)當(dāng)說(shuō),這是散文創(chuàng)作的本色所在,也是在散文解讀中把握其審美品格的一個(gè)基本方面。
不管是以記敘為主的散文,還是以抒情為主的散文,不管是對(duì)自然世界景和物的靈性透視,還是對(duì)社會(huì)生活中幽微心態(tài)的描述,都無(wú)不是作家的真切感悟。對(duì)散文文體的這種藝術(shù)品格和審美特質(zhì),從其藝術(shù)的表現(xiàn)上說(shuō),在解讀和教學(xué)中我們應(yīng)注意把握它所具有的兩個(gè)鮮明特征。
一是善于從生活中獲取靈感和才思,使散文文體構(gòu)成富有感性因素,產(chǎn)生蓬勃的生機(jī)與活力。生活的氛圍與美學(xué)的境界往往凝注為難舍難分、內(nèi)蘊(yùn)豐厚的藝術(shù)晶體,既具有立體的現(xiàn)實(shí)感,又充滿生活化的藝術(shù)氣息。如余光中的《聽聽那冷雨》采用交叉疊合的藝術(shù)營(yíng)構(gòu),用光、聲、色、味描述出了多姿多彩的冷雨圖,多向匯集“大陸的冷雨”“美國(guó)的冷雨”“臺(tái)灣的冷雨”等不同時(shí)空形態(tài)的生活斷面。它們完全是作者日常熟見的周圍的人和物所勾起的一串串縈思,但這一串串縈思并非人云亦云的陳腔濫調(diào),而是字字珠璣,處處有詩(shī)一樣的象征意蘊(yùn),讀來(lái)耐人尋味,可說(shuō)是一連串透露著深層感悟與靈性的“冷雨之境”。那清清爽爽、細(xì)細(xì)密密、柔婉親切的“冷雨情韻”,產(chǎn)生于“冷雨的感覺”,是“冷雨打在樹上和屋瓦上”的經(jīng)歷,全部的機(jī)心在于作者站立在“淋淋漓漓”的冷雨里,聽那“料料峭峭”“淅淅瀝瀝”“天潮潮地濕濕”的冷雨生息,體察入微地感悟冷雨的情姿、冷雨的靈魂。一次次聽聽那冷雨,帶給作者思戀家鄉(xiāng)的內(nèi)心纏綿之情,一種難以表達(dá)的心冷和苦酸。于是,來(lái)自冷雨的自然圖景與感情體驗(yàn)交融于一體,譜成了一曲“冷雨”的生命之歌,一份從自然圖景中感悟出的生活啟示。
二是順應(yīng)情感自然流動(dòng)的真實(shí)寫作,使散文具有一種興至意足的審美效應(yīng)。凡高明的散文作家,其筆端無(wú)不始終追隨著他的腳步與心靈,描摹情思,真實(shí)地記錄他的情感和意念的律動(dòng)。如林非的《千佛洞掠影》,作者的沖動(dòng)是亢奮的,感情是強(qiáng)烈的:“那些浮動(dòng)和旋轉(zhuǎn)著種種色彩的繪畫,閃耀和流露出種種神情的塑像,讓人感到目眩、迷惑和驚訝。不知道有哪一種笑容,不知道有哪一種靜穆的沉思,也不知道有哪一種悲哀的表情,帶著黃沙,帶著風(fēng)暴,帶著潺潺的清泉,永遠(yuǎn)留在人們的心里。”作者用意味深長(zhǎng)的筆墨,將潛在的情緒和意識(shí)托出,使人思感無(wú)窮。那遍布字里行間、躍動(dòng)的意念,有一股厚重充實(shí)、浸潤(rùn)筋骨的力量襲向讀者的心靈,發(fā)掘著生活的真與偽、美與丑,誠(chéng)切率真地和讀者交流著心聲。
通過(guò)以上兩個(gè)方面的分析可見,盡管散文描繪的人、事、景、物具有客觀性,但是作者在選材、構(gòu)思時(shí),一切客觀事物都必須經(jīng)過(guò)作者主觀世界的篩選和內(nèi)化,從而賦予散文鮮明的個(gè)性色彩。可以說(shuō),個(gè)性美是散文藝術(shù)魅力之所在,也是其藝術(shù)生命之所在。
從散文解讀來(lái)說(shuō),作品有無(wú)個(gè)性美,正是讀者對(duì)散文特有的審美價(jià)值取向。在散文解讀中,只要涉獵一下中外文學(xué)史上的散文佳作就會(huì)對(duì)此有更清楚的認(rèn)識(shí)。蒙田以隨筆式的散文聞名,他的散文題材異常廣泛,內(nèi)容非常龐雜,行文飄忽不定,時(shí)而敘述自己感覺中的“自我”,時(shí)而描寫自己所體驗(yàn)的人生,時(shí)而議論自己所理解的現(xiàn)實(shí)世界,時(shí)而又抒發(fā)起自己的思想情懷。看來(lái)漫不經(jīng)心,然而恰恰是作家這種思想開放、充滿個(gè)性的精神展現(xiàn),在不同的國(guó)度、不同的讀者中產(chǎn)生了持久的啟迪效應(yīng)和審美效應(yīng)。盧梭的《一個(gè)孤獨(dú)的散步者的遐想》,至今被人稱為最能體現(xiàn)作者才華和特點(diǎn)的散文代表作。作品中那些豐富的內(nèi)心獨(dú)白、精辟的哲理議論以及作者坎坷的經(jīng)歷、正義的申訴、真實(shí)的情感、崇高的品德,抒寫得淋漓酣暢、自由灑脫。這既是作者個(gè)性的藝術(shù)展現(xiàn),也是一部豐富的人生啟示錄。可見,不朽的散文作品都是人類心靈中充滿藝術(shù)個(gè)性的獨(dú)特審美感受和發(fā)現(xiàn),是作家充滿個(gè)性的情感剖白。散文文體的這種藝術(shù)品格和審美特質(zhì),是我們?cè)谏⑽慕庾x和教學(xué)中需明確把握的。
三、散文文體的散漫性特征
我們?cè)诎盐丈⑽牡摹百|(zhì)”——即其藝術(shù)品格和審美特性的同時(shí),還必須致力于散文的“體”——即其文體營(yíng)構(gòu)藝術(shù)和表現(xiàn)形式的解析。
對(duì)散文的體式特征,泰戈?duì)栐诮o他朋友的信中曾經(jīng)說(shuō):“詩(shī)就像一條小河,格律就是小河的兩岸,有了兩岸的限制,小河才流得曲折,流得美。而散文就像漲大水時(shí)的沼澤,兩岸被淹沒了,一片散漫。”[6]這個(gè)比喻形象地揭示了散文的體式——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的特征,說(shuō)明散文是一種“最自由的樣式”。對(duì)散文體式的這種散漫特征,古往今來(lái),不少人都做過(guò)論述。宋代散文大家蘇軾認(rèn)為,散文“如行云流水,初無(wú)定質(zhì),但常行于所當(dāng)行,止于所不可不止”[7]。袁宏道曾經(jīng)強(qiáng)調(diào):散文的優(yōu)勢(shì)在于“獨(dú)抒性靈,不拘格套”。這些都是對(duì)散文散漫、自由的文體藝術(shù)特征的精到概括。在散文解讀和教學(xué)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散文散漫、自由的表現(xiàn)形式雖然多種多樣,但可從以下幾個(gè)基本層面來(lái)把握。
一是散文文體的彈性。所謂“彈性”,是指散文筆墨灑脫不羈、變化多端,行文無(wú)拘無(wú)束,具有對(duì)于各種體式、各種預(yù)期能夠兼容并包的高度適應(yīng)能力和博大“胸懷”,具有強(qiáng)烈的開放意識(shí)。這種開放就是所謂的形散特征。“開放”不是散漫無(wú)章,而是說(shuō)散文沒有定格和模式,營(yíng)構(gòu)的是一種闊大的藝術(shù)空間和自由的藝術(shù)天地,追求和創(chuàng)造的是豐富多樣、富有彈性的“形”。這種“形”除了不拘一格以外還有一層含義,就是以博大“胸懷”,對(duì)各種文體的技巧兼容并包,只要意有所至,筆勢(shì)所趨,往往不惜打破文體技巧的藩籬:借助小說(shuō)的意識(shí)流、詩(shī)歌的意象轉(zhuǎn)換和音律節(jié)奏、電影的蒙太奇組接技法、戲劇的對(duì)話、繪畫的色彩、音樂(lè)的旋律等,從而與其他文體形式相互滲透,創(chuàng)造出鮮活的具有高層次價(jià)值的審美特征。
優(yōu)秀的散文在意象組合上,一般都注重意象審美空間的營(yíng)造,特別是散文中的諸多意象群看似“雜亂無(wú)章”,其實(shí)是作家心靈的映射,是根據(jù)作家情思的需要,在某種向心力指引下黏合形成的意象群體。如《荷塘月色》,作者描寫了一組意象:“葉子”“明珠”“星星”“美人”“舞女的裙”,這些意象看起來(lái)有點(diǎn)散亂,其實(shí)意象始發(fā)點(diǎn)是“荷塘”。作者以它為軸向外擴(kuò)散輻射,依次滋生出“荷葉”“荷花”“荷香”“荷波”“荷韻”一系列分意象。作者對(duì)意象的選取靈活運(yùn)用多種表現(xiàn)手法,動(dòng)靜結(jié)合,構(gòu)成了意象的張力聯(lián)系。這種富有彈性和張力的描寫,既勾畫出荷花的形貌,又賦予其靈性,使之人格化。顯然,作者運(yùn)用筆墨伸縮自如,語(yǔ)氣變化多樣,展現(xiàn)了一個(gè)幻化多姿、富有彈性和立體感的荷塘妙境。這就是散文“彈性”的一種藝術(shù)表現(xiàn)。這種散漫、自由的彈性表現(xiàn)是“無(wú)形”,而實(shí)則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有形”,是于“無(wú)形”中求“有形”。
二是散文文體的密度。所謂密度,是指散文在一定的篇幅內(nèi),增強(qiáng)信息的藝術(shù)容量,滿足讀者對(duì)美感要求的藝術(shù)分量。分量愈重,密度自然就會(huì)愈大。散文的這種密度,具體表現(xiàn)在文字的精當(dāng)、意象的繁復(fù)和結(jié)構(gòu)的完密上,等等。文字的精當(dāng)是指全篇文無(wú)廢句,句無(wú)廢字,每個(gè)字都能夠發(fā)揮作用,達(dá)到字字珠璣的程度。意象的繁復(fù)并非是意象的隨意堆疊,而是指它能構(gòu)成復(fù)雜而靈動(dòng)的意象群,表達(dá)豐厚的意蘊(yùn),引發(fā)讀者廣邈的聯(lián)想和想象。結(jié)構(gòu)的完密,是指通篇要有一個(gè)嚴(yán)謹(jǐn)?shù)目蚣埽蛞蓝ǚǘ鴩?yán)整排列、連鎖全篇,或無(wú)定法而縱橫開闔、激蕩成文,其構(gòu)置驅(qū)遣匠心獨(dú)運(yùn)。
如李樂(lè)薇的散文《我的空中樓閣》,無(wú)論在語(yǔ)段上還是在篇章里,都有奇詞、麗句和佳構(gòu)。“山如眉黛,小屋恰似眉梢的痣一點(diǎn)”,勾畫出山和小屋的形象姿態(tài),使山和小屋脫去凡俗。“小屋點(diǎn)綴了山,似飄過(guò)一片風(fēng)帆,掠過(guò)一只飛雁”,顯現(xiàn)小屋點(diǎn)綴山的靜景的美,畫出了“山上有了小屋”才有的生氣和靈動(dòng)的情調(diào),使山光水色平添異彩,生機(jī)勃發(fā)。同時(shí)還寫“山下的燈把黑暗照亮了,山上的燈把黑暗照淡了”,透視出小屋虛無(wú)縹緲的“空中”感。這些詩(shī)化的語(yǔ)言描述,構(gòu)成了緊聚的密度,包涵量大,聯(lián)想性強(qiáng),一句便疊合多層意象。從整篇散文來(lái)看,不僅麗詞佳句俯拾皆是,而且奇譬詭喻讓人目不暇接。審視其“密度”,可說(shuō)是一個(gè)奇妙的文字“方陣”。一千多字的篇幅似乎是由許多顆珠璣串成,而整個(gè)空中樓閣的相關(guān)景物風(fēng)貌,則似乎被倒映在由文字拼成的明鏡里,而且作者在揮灑筆墨的過(guò)程中屢用排比,也是造成作品富有密度和韻味的一種手段。總之,其文字稠密——達(dá)到了字字珠璣的地步;其意象復(fù)雜——忠實(shí)于現(xiàn)代生活的豐富多彩;其意蘊(yùn)豐盈——從縱面上增強(qiáng)了作品的厚度,從橫面上擴(kuò)展了內(nèi)容的廣度。
散文文體所表現(xiàn)的審美意蘊(yùn)應(yīng)當(dāng)給讀者多維的審美體驗(yàn),從各方面強(qiáng)化審美功能,從而提高散文文體的藝術(shù)分量。
三是散文文體的節(jié)奏。凡是優(yōu)秀的散文,不但講究形式的節(jié)奏,而且講究聲音的節(jié)奏,從而使作品所展現(xiàn)的藝術(shù)審美空間更富有魅力。過(guò)去,人們認(rèn)為只有詩(shī)歌和韻文可與音樂(lè)合一,產(chǎn)生視覺與聽覺上的節(jié)奏感和律動(dòng)美;散文則只能形成平面的藝術(shù),沒有什么節(jié)奏可言。其實(shí),散文完全可以同時(shí)利用漢字的形與聲,創(chuàng)造出抑揚(yáng)頓挫、跌宕起伏的音樂(lè)節(jié)奏,并用以充分表現(xiàn)作者所要抒發(fā)的心情意緒。散文是不主常規(guī)、舒卷自如的文體,參差行文,旋律多變,自為佳美。散文的語(yǔ)調(diào)節(jié)奏美主要是指聲調(diào)的抑揚(yáng)頓挫,文句的長(zhǎng)短整散,語(yǔ)流的疾徐曲直,以及它們的錯(cuò)雜相間,從而使作品的聲勢(shì)呈現(xiàn)有規(guī)律的變化。
我們看顏元叔的散文《荷塘風(fēng)起》:“那帶刺的荷莖,纖細(xì)、修長(zhǎng)、勁韌,撐住一頂荷葉,圓似斗笠,葉心是一個(gè)小盆地,向天空攤開,承受雨水,承受夜露,承受陽(yáng)光!”作者對(duì)于雨中荷葉的這段精細(xì)描寫可謂活靈活現(xiàn),這顯然得益于他細(xì)致入微的觀察和精雕細(xì)琢的用詞。“纖細(xì)”“修長(zhǎng)”“勁韌”“撐”“攤”……這些詞語(yǔ)的使用準(zhǔn)確、貼切,使得整個(gè)描寫生動(dòng)、逼真,可見作者對(duì)語(yǔ)言文字運(yùn)用的精致。特別是“忽然一陣強(qiáng)風(fēng)吹來(lái),荷塘風(fēng)起云涌,荷池霎時(shí)變了一番光景”,作者筆下強(qiáng)風(fēng)中的荷葉姿態(tài)挺拔,場(chǎng)面壯觀,氣勢(shì)宏闊,極具荷塘風(fēng)起的震撼力、沖擊力和畫面感。更別出心裁的是光與色的視覺處理恰到好處,陽(yáng)光下耀眼的紫黃、深沉的碧黛交相輝映,共同渲染成一幅荷塘風(fēng)起的動(dòng)態(tài)畫面。隨即云淡風(fēng)輕,一切又都?xì)w于平靜,荷葉的動(dòng)態(tài)之美和靜謐之美也在作者生花的妙筆之下游刃有余地切換。讀者仿佛也是忘我地全情投注,剎那間覺得天地都變小了,“陽(yáng)光,荷葉,輕風(fēng)與人,有那瞬間的多彩的神會(huì)”。光與色的視覺沖擊,動(dòng)與靜的巧妙轉(zhuǎn)換,將這份極具震撼的美感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出來(lái)。其中,作者有節(jié)奏地搭配長(zhǎng)句短句,長(zhǎng)句舒緩流利,短句短促嚴(yán)整,在散句中駢散相濟(jì),或奇或偶構(gòu)成音節(jié)的參差錯(cuò)落,忽急忽徐的語(yǔ)調(diào)也使語(yǔ)氣搖曳悠揚(yáng),產(chǎn)生一種復(fù)雜多變的節(jié)奏感。顯然,這篇散文語(yǔ)詞的精準(zhǔn)運(yùn)用,不僅使靜止的文字頓時(shí)富有動(dòng)感韻律,而且使作者那種疾徐悠深而滿懷慨嘆的神情表露無(wú)遺。
參考文獻(xiàn)
[1]【日】廚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7.
[2]曹明海.在感悟中彈撥“自己的聲音”[J].徐州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92(3).
[3]曹明海.文學(xué)解讀學(xué)導(dǎo)論[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7:361.
[4]巴金.秋夜[M]∥巴金散文精編.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476.
[5][6]徐治平.散文美學(xué)論[M].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0:68,66.
[7]蘇軾.自評(píng)文[M]//蘇軾文集:第5冊(cè),北京:中華書局,1986:2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