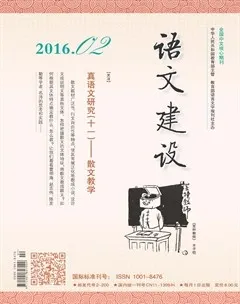你是“路怒族”嗎?
近來,“路怒”一詞在電視媒體與網絡平臺流行開來,引起不少關注。隨著汽車的普及,很多新問題隨之產生,比如交通擁堵,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問題。“路怒”癥的蔓延,正是交通擁堵問題和人們心理壓力癥結的集中體現。請看:
(1)“路怒癥”成為遼寧乃至全國公安重點打擊的對象,對超速、違法搶行、不按規定禮讓、占用應急車道、違法超車等五類危險駕駛行為進行重點整治。(《遼沈晚報》2015年8月3日)
(2)只因綠燈前車未及時啟動,“路怒”司機狂毆前車司機。(《南方日報》2015年8月5日)
(3)出租車擋住道“路怒族”猛踢車(《重慶商報》2015年8月6日)
美國大約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進入汽車時代,人們的心理無法馬上與高速發展的經濟相適應,而基礎交通短時間內無法承載路面上越來越多的車輛,從而導致人們開車時常有壓力,憤怒與暴力行為不斷。針對這種現象,英語中有了“roadrage”一詞,特指懷有壓力與憤怒情緒來開車的行為。漢語新詞“路怒”便源于英語“roadrage”,該詞直譯即為“路怒”。
“路怒”結構上是以“怒”為中心語的偏正結構。“怒”表達了一種病態的憤怒情緒,而修飾語“路”則強調,這種病態的憤怒情緒其行為環境是在路面駕駛過程中。“路怒”在語義上特指交通阻塞情況下,由開車壓力與挫折所導致的憤怒情緒。
交通擁堵,人們情緒失和,稍有影響順暢駕駛的行為都會引發他人的“路怒”行為。“路怒”現象反映的不僅是社會問題,更投射出駕駛者的心理癥結,這引發了我們對群體性心理問題的思考。
(4)曾有評論提出,“路怒癥”是不是病?該不該治?其實,即使把這種暴力行為稱為“路怒癥”,病根也不是在路上。按照“路怒癥”的定義,是指帶著憤怒去開車。如果把交通糾紛中的暴力行為歸為“路怒癥”,實際上已經將施暴者的發怒原因,脫離了事件的本身——因為,本身就是帶著憤怒去開車的。(《人民日報》2015年5月13日)
(5)一些人平時彬彬有禮,可一旦開上汽車就變得不守文明規則,且更易被激怒。這些“路怒族”不僅直接引發了不少事故,有時候也使得矛盾升級,做出非理性行為,造成不必要的人身傷害。(《北京晨報》2015年8月5日)
路面上激增的車輛和愈發擁堵的交通讓人無所適從,哪怕平時彬彬有禮的人,在行車時都可能變成“路怒”司機。交通擁堵,情緒失控,加上天氣等客觀因素,使“路怒癥”蔓延開來。無論是客觀因素誘發還是本身就帶著情緒開車,“路怒”行為可以看作潛伏性情緒病的爆發。可以說,“路怒”是病態的憤怒情緒,不是正常的情緒表達。
因為“路怒”結構本身相對松散,所以“怒”家族逐漸有了新成員,比如“網怒”:
(6)因為可以“潛水”和隱身,生活中積累下來的很多怨氣,讓一些人在網絡上尋找到了一個盡情發泄的途徑,不分青紅皂白、一番謾罵之后就爽了,如此,使得“網怒”成為常態,其最普遍的表現是用詞粗暴、隨意言語或者人身攻擊甚至進行人肉搜索。(《桂林晚報》2015年6月10日)
“網怒”是人們借網絡身份的隱匿性,將現實生活中的不良情緒發泄出來,或隨意謾罵,或爭辯抬杠,甚至侵犯他人隱私隨意“人肉”。這一新用法,更能說明“怒”特指一種病態的不滿情緒,詞義已相對固定,并逐漸具備了新的組合能力。類似“××怒”的詞族,可以泛指懷有病態的不滿情緒,在特定環境或場所中去做某事的行為。“××怒”詞語的出現,是語言為社會弊端發聲。
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路怒”抑或“網怒”現象都好比一個不和諧的音符,亟待人們正視并想出解決之道。職能部門的努力、立法的不斷健全、人們的自我調適,都能夠有效減少這類病態情緒,減少“××怒”給社會帶來的不良影響。我們希望“××怒”詞族少些成員,讓我們傾聽到社會語言的和諧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