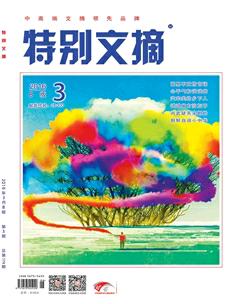方言式微
馮學榮
最近回了一趟家鄉,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親戚家念三四年級的幾個小朋友平時使用普通話交流、很少講家鄉方言了,這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恐怕家鄉的方言已經走上了式微之路。有點惆悵,但是也無可奈何,因為這是經濟規律所決定,大勢所趨。
親戚家的小孩都是本地人,為何互相之間要講普通話?事情是這樣的:由于經濟的發展,家鄉近些年外省人多了起來,造成本地小學的生源多了許多外省孩子,連老師也從外省招聘了一部分,雞同鴨講,無法交流,誰也不愿學誰,結果大家找到了最大公約數:普通話。孩子們在學校講普通話習慣了,就將習慣帶回家里來了。
方言式微的現象并不僅僅發生在我的家鄉,而是發生在全國各地。那么方言為什么會式微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要回顧一下:方言在歷史上是怎樣產生的。我們都知道:古代中國社會是一個農耕社會,農耕人口占人口的絕大多數,他們的雙腿都被拴在土地上,什么時候會離開土地呢?通常只有這幾件事:趕集、告狀、趕考。在古代中國人的人生中,離開家鄉的機會是不多的。在農耕社會,中國人的活動范圍基本上是方圓十里路,人口的流動性極弱,生活環境相對封閉,在封閉的環境里,方言得以形成。所以我們中國自古有“十里不同音”的說法,為什么是“十里”?因為古代中國人趕集所能走的最遠路程,早出晚歸,就是十里路,所以是十里不同音,超出十里地以外,由于缺乏交流,相對封閉,語言就會發生變異。
說到這里,答案呼之欲出了:方言存在的歷史基礎,就是因為人口不流動,而一旦人口發生了實質性的流動,方言存在的基礎就必然崩潰。基礎一旦崩潰,方言死亡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中國過去四十年是工業化的四十年,中國人的生存方式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在過去,中國人是大部分不流動,而現在是恰恰相反:大部分流動,基本上是從農村往城市流動,在城里,大家來自五湖四海,各自說方言根本無法交流,為了選擇成本最低的交流工具,人們只好選取最大公約數:普通話。你不用學我的方言,我也不用學你的方言,大家都說普通話,人人都能懂,將彼此學習語言的時間節省下來,可以馬上開展交易。為什么叫“普通話”?“普通話”的“普通”并不是“平庸”的意思,而是“普天之下人人能通”的意思。
據媒體的朋友說,不少電視臺被禁止使用方言,所以覺得普通話興盛、方言式微是有關部門強制推廣的結果。但是我認為官方的強制性推廣只是起了助力的作用,它并不是這件事的根本,從根本上而言,普通話的興盛和方言的式微,是人口在全國范圍大規模流動的必然結果,換句話說,就算官方不強制推廣普通話,普通話的興盛和方言的式微也是大勢所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使用普通話交易成本最低、各方獲利最大。趨利避害的本性決定了人們總是選擇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交易工具。
香港開埠之前,香港的農村和漁村通用客家話、疍家話和鶴佬話。客家村與疍家村、鶴佬村之間基本不交流,老死不相往來,但是開埠之后,商業繁榮了,都出城了,開始做生意了,要交流了,說哪一種話呢?索性取公約數,大家都講廣東話,這個大家都會講,誰也不用學誰,立馬就能做成生意。香港后來通用廣東話,而客家話、疍家話和鶴佬話作為本土語言,反而式微了。
同樣的故事還發生在新加坡。早期移民新加坡的華人,有的講閩南語,有的講廣東話,還有的講客家話,語言不通,怎樣做生意?最后怎么辦呢?取最大公約數,都講普通話(華語),華語大家都會講一點,就用這個了,交易成本最低。所以移民新加坡的華人原本都不講普通話的,但是普通話成了新加坡第二官方語言,就是因為這個,因為它是最大公約數,交易成本最低。
除此之外,深圳的歷史也是如此,深圳開發之初,移民來自五湖四海,各說各話,各不相讓,誰也不愿意學誰(時間就是金錢,誰也沒工夫學習對方的方言),怎么交流呢?現成的辦法就是取最大公約數,大家都講普通話,所以深圳逐漸演變成一座普通話城市。
(摘自“人文經濟學公眾號” 圖/黃煜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