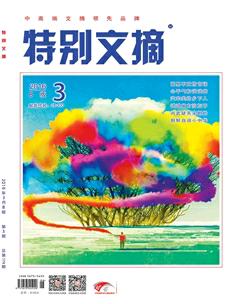朝鮮自詡小中華
雪珥
1644年,李自成的軍隊攻占北京,崇禎皇帝在煤山上自縊身亡。隨后,滿清鐵騎蜂擁入關,席卷大明江山。朝鮮人悲哀地長嘆道:萬里腥膻如許。但軍事上強悍的滿清,似乎在政治上相當寬容:朝鮮可以不必薙發改裝,保持其原先的社會制度和習俗永遠不動搖。
朝鮮人自信地認為:“振興中華”的偉大使命,已經歷史地落到了他們的肩上。他們堅信:“中國有必伸之理,夷狄無百年之命。”朝鮮使節照例到北京向新主人朝貢,但是,他們將記載朝覲細節的報告書《朝天錄》改叫《燕行錄》,北京已經不再是天朝的首善之區,而只是一個別名為“燕京”的旅行目的地而已。滿清統治下中國所發生的一切變化,在朝鮮人看來都是中華文明的大倒退。小到服飾、發型,大到社會主流思想,無一不是禮崩樂壞。當北京人圍觀身著“奇裝異服”的朝鮮使團時,朝鮮人自豪而輕蔑地記載道:這些中國人居然已經不認識天朝衣冠!
朝鮮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其內部文件多將清帝蔑稱為“胡皇”,清使為“虜使”。除了對清公文外,幾乎所有官方文件仍沿用崇禎年號,到南明滅亡,“復明”大業無望,才改用干支紀年和國王在位年號,絕不使用大清年號。朝鮮也試圖用“槍桿子”的方式“恢復中華”。無論是南明政權,還是“三藩”,或臺灣鄭家父子,甚至包括謀求區域霸權的準噶爾蒙古,朝鮮均愿意與之結成廣泛的統一陣線。
1646年11月,日本對馬島主派遣使節訪問朝鮮,表示已經收到臺灣鄭氏政權的邀請,組建聯合軍隊,動員“百萬之眾”,討伐滿清。朝鮮國王李倧大為稱許,派出使節回訪對馬島,敦促日本幕府及早出兵。其子李淏于1649年即位,史稱孝宗。孝宗繼承了其父反清復明的衣缽,秘密倡議北伐。他將駐扎漢城的“御營廳”擴充三倍,從7000人增到2.1萬人,配備攻堅大炮;禁軍從600人增到1000人,還改建為全騎兵部隊;“訓練都監軍”也要擴編1萬人。
三藩之亂時,朝鮮再度興起北伐的熱潮,肅宗李焞(孝宗之孫,1674~1719年在位)雖然在口頭上贊同,實際上對此并不熱心,只見他積極擴軍,就是不真的將軍隊投入反清復明的大業中去。其實,無論孝宗還是肅宗,真正的目的,或者說首要的目的,只是利用北伐動員民意,以便鞏固和加強王室的集權,同時轉移民眾對內政的注意力。
1704年(甲申年),崇禎皇帝自縊甲子紀念(60周年),朝鮮肅宗親詣“禁苑壇”祭祀,同時下令設立“大報壇”,專門祭祀萬歷皇帝,表示不忘其在“壬辰倭亂”時派遣明軍拯救朝鮮的“再造大恩”。這是朝鮮祭奠明帝的開端。1749年,朝鮮國王英祖(1724~1775年在位)決定,將明太祖朱元璋和崇禎皇帝也挪到大報壇上一并祭祀。從此,“大報壇”上供了三位大明皇帝,凡是他們的誕辰日、即位日、忌日,朝鮮國王均會親臨祭奠,世子、世孫隨行,年年如此。與悄悄籌備的北伐不同,祭祀明帝是一場公開的、大張旗鼓的政治秀,與尊清工作并行不悖。1774年,朝鮮英祖再度推出一大創舉:在珍藏明朝賜品的“敬奉閣”旁,建起了一座新的“奉安閣”供奉來自大清國的敕文和賜品等——明清兩朝在朝鮮得到了相同的地位。
出于地緣政治的考慮,滿清對朝鮮采取了綏靖政策,朝鮮王室遠比明朝時期享有更為充分的自主空間。“朝鮮雖是屬國,但向來自主”,這在晚清成了中國政府向列強解釋中朝關系的標準口徑,由此導致了一系列的災難后果。
明清同尊,其實正是朝鮮王室下出的一著妙棋:將大明帝國擺上祭壇,它也就徹底成了“過去時”,又能將那面依然能夠凝聚人心士氣的大明旗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對內可以動員民意,對外可以作為應對滿清的博弈砝碼。一年只需增加區區9天的“國定假期”,在現實利益和歷史道義兩方面,朝鮮王室就取得了物質和精神文明的雙豐收,這是小國“玩轉”大國相當成功的政治運作。
(摘自《國家人文歷史》 圖/黃煜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