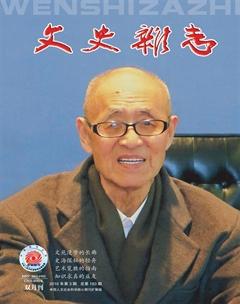古蜀器質(zhì)文明的輝煌與上古歌謠的缺失
鄧經(jīng)武
一
華夏上古時(shí)期的歌謠,即“原始歌謠”,其最早的典籍匯集本,是《詩經(jīng)》的“十五國(guó)風(fēng)”。《詩經(jīng)》分為《風(fēng)》《雅》《頌》三部分,其中《風(fēng)》是從民間采集的十五個(gè)地域的土風(fēng)歌謠,即:《周南》《召南》《邶風(fēng)》《鄘風(fēng)》《衛(wèi)風(fēng)》《王風(fēng)》《鄭風(fēng)》《齊風(fēng)》《魏風(fēng)》《唐風(fēng)》《秦風(fēng)》《陳風(fēng)》《檜風(fēng)》《曹風(fēng)》《豳風(fēng)》。這十五國(guó)風(fēng)所涉及到的地域包括今天的山西、陜西、河南、河北、山東等地。很長(zhǎng)一段歷史時(shí)期人們都認(rèn)為《周南》《召南》是從南方——即江漢流域一帶收集而來。但近來據(jù)一些學(xué)者考證,《周南》《召南》其產(chǎn)地應(yīng)是在東都洛邑。據(jù)此可見,采集十五國(guó)風(fēng)所涉及的地方基本上就是中原一帶,與南方毫無關(guān)系。即使是“漢”水,作為長(zhǎng)江一條最長(zhǎng)的支流,它發(fā)源于陜西省的西南部,流過秦嶺與大巴山之間的漢中盆地后進(jìn)入湖北,在武漢匯入長(zhǎng)江。也就是說,“漢水”有很長(zhǎng)一段是在北方。今天陜西省的“漢中”地名,也可以作為參考。也還需要注意的是,古人將銀河星系也稱作“漢”,《詩經(jīng)》中已經(jīng)有這樣的詩句:“維天有漢,監(jiān)亦有光”,所謂“云漢”“霄漢”等皆是。筆者對(duì)此不擬深加辨析,只是想說說巴蜀上古歌謠在《詩經(jīng)》中的缺失問題。
原始歌謠產(chǎn)生于生產(chǎn)力極為低下、沒有文字記錄的原始社會(huì),為人類社會(huì)出現(xiàn)最早的文學(xué)樣式之一。它源于原始社會(huì)的先民在勞動(dòng)過程中,為協(xié)調(diào)勞動(dòng)節(jié)奏、減輕疲勞、激發(fā)勞動(dòng)熱情,而喊出的勞動(dòng)口號(hào)。后隨先民思維能力、發(fā)音器官和語言能力的發(fā)展,其有節(jié)奏的呼喊漸為有意義的、富于韻調(diào)和節(jié)奏感的語言所代替。《呂氏春秋·古樂》記載了原始先民的精神活動(dòng)情況:“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達(dá)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cè)f物之極。”原始歌謠主要分類有勞動(dòng)(如《彈歌》:斷竹,續(xù)竹,飛土,逐肉。)、祭祀(如《伊耆氏蠟辭》: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婚戀(如《周易》爻辭《屯·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戰(zhàn)爭(zhēng)(如《周易·中孚·六二》: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等。由于上古時(shí)期“國(guó)之大事,在祀與戎”,所以《易經(jīng)》卜辭還保留有:“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來雨?其自東來雨?其自北來雨?其自南來雨?”等。
換句話說,原始先民在勞動(dòng)、祭祀、婚戀、戰(zhàn)爭(zhēng)等特定的場(chǎng)合中,用類似我們今天“吟詠”的拖長(zhǎng)了聲音的方式“說”(唱)當(dāng)時(shí)的情景和內(nèi)心情感,這就是原始的歌謠。在樂器未發(fā)明前,原始人歌舞時(shí)用擊掌或擊石(“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以求增加節(jié)奏感和強(qiáng)化表達(dá)情感的方式,其中一些優(yōu)秀的歌謠獲得更為廣泛的傳遞,并通過口耳相傳來流傳和保存下來。所以人們認(rèn)為原始歌謠是融抒情、敘事、戲劇諸因素為一體的詩,分化發(fā)展為后代所謂的抒情詩、敘事詩、戲劇。
漢唐以來,關(guān)于巴蜀大地民間歌舞盛行的情況,典籍記載頗多。《漢書·司馬相如傳》載“巴渝歌舞”大行于世的情況:“初,高祖用之,克平三秦,美其功力,后使樂府習(xí)之”。說的就是作為戰(zhàn)歌或軍歌的“巴渝歌舞”獲得漢高祖劉邦的喜愛與推廣;杜佑的《通典》卷一百四十六記載了魏文帝受禪后,把“巴渝歌舞”改編為“昭武舞”。唐代劉禹錫《插田歌》詩展示了巴蜀民間“齊唱田中歌,嚶佇如《竹枝》”;宋代蘇轍《竹枝歌忠州作》也有類似記錄,如“連舂并汲各無語,齊唱《竹枝》如有嗟”。又如《新唐書》卷一百六十八所載巴蜀大地民俗“風(fēng)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徘徊,其聲傖佇”等。
二
巴蜀大盆地有久遠(yuǎn)的生命史,自貢大山鋪恐龍群遺址與“合川龍”出土以及“巫山人”和“資陽人”等原始人遺跡,皆可證明。
一年四季的分明、繁復(fù)多姿的美景,鑄造著巴蜀人對(duì)美的敏感心理機(jī)制,決定了他們的審美創(chuàng)造特色。“廣漢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立人像以“基本上符合中國(guó)人的身材比例和一般的藝術(shù)表現(xiàn)采用的造像量度”,體現(xiàn)著對(duì)“人”的真實(shí)生存狀況的關(guān)注。但更重要的是,除了對(duì)人體各部分甚至腳踝的細(xì)節(jié)雕塑寫真外,還突出地使用了彩繪著色技法,在眉毛、眼眶和顳部涂有青黑色,并在眼眶中間畫出很大的圓眼珠,口部、鼻孔以至耳上的穿孔則涂抹著朱色。這正顯示出巴蜀先民偏愛艷濃色彩和華美藝術(shù)的美學(xué)觀念。從這些青銅器和人像繪刻的龍紋、異獸紋、云紋和服飾的陰線紋飾中,從其中表現(xiàn)的絢麗多姿的色彩繪涂中,我們不難看到巴蜀文化美學(xué)對(duì)精美形制和艷濃華美的追求和表現(xiàn)特征。這種美學(xué)追求,既是特定存在的產(chǎn)物,與中原“中和之美”和北方“真善”實(shí)用為美迥然不同,同時(shí)又在地域風(fēng)俗習(xí)慣中被不斷強(qiáng)化和復(fù)現(xiàn)著。古蜀器質(zhì)文明所表現(xiàn)如此精致的造型與色彩運(yùn)用,透射出古蜀先民精神審美活動(dòng)的高度發(fā)展?fàn)顩r。
《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的“巴寡婦清”,應(yīng)該就是華夏大地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個(gè)女企業(yè)家“富婆”。其三代經(jīng)營(yíng)朱砂礦而“富敵祖龍”,致使一代雄豪如秦始皇也不得不“筑臺(tái)懷清”進(jìn)行籠絡(luò)。按當(dāng)時(shí)的科技水平程度,朱砂礦最主要的用途應(yīng)該是印染顏料和化妝品材料。巴寡婦清那宏大的經(jīng)營(yíng)規(guī)模,實(shí)際是由巴蜀民眾對(duì)色彩和顏料的消費(fèi)規(guī)模而決定。正是巴蜀民眾對(duì)色彩艷麗華美的消費(fèi)需求,才有巴寡婦清那富可敵國(guó)的生產(chǎn)盛況。“西蜀丹青”成為秦宮貢品,也正說明巴蜀對(duì)色彩的敏感和顏料生產(chǎn)工藝上所達(dá)到的領(lǐng)先水平。在這樣的基礎(chǔ)上,漢代漆器無論是數(shù)量還是質(zhì)量皆居全國(guó)第一,廣漢、成都被漢朝皇室指定為漆器生產(chǎn)基地并設(shè)專門機(jī)構(gòu)進(jìn)行管理,其基本色調(diào)為紅、黃、黑、棕、綠等濃烈色調(diào),且“花紋精致,色彩斑斕,華而不浮,縟而不艷,輕靈幻美,悅目怡心”,“奇制詭器,胥有所出,非中原燕趙三晉古墓中所有者”,因而受到世人廣泛喜愛甚至遠(yuǎn)銷日本、朝鮮等國(guó)家。20世紀(jì)30年代,朝鮮平壤市樂浪區(qū)(漢代于此設(shè)置的樂浪郡治所)出土的“成亭”制造漆器,漆器的銘文中還有廣漢郡或蜀郡出產(chǎn)地點(diǎn)等字樣。揚(yáng)雄《蜀都賦》曾極盡繁文麗詞地夸耀道:“雕鏤筘器,百質(zhì)千工”、“百位千品”。而漢代就以“細(xì)密黃潤(rùn)”的蜀布行銷全國(guó),甚至遠(yuǎn)至西亞地區(qū),則是人們熟知的例證。
公元2000年在成都商業(yè)街出土的戰(zhàn)國(guó)船棺葬中,發(fā)現(xiàn)色彩艷麗的漆器;1997年秦嶺深處的四川青川縣郝家坪出土的戰(zhàn)國(guó)時(shí)代漆器,成都北羊子山出土的上古漆器,則年代更早。漢代在蜀郡(治所成都)、廣漢郡置工官負(fù)責(zé)監(jiān)造各種涂有紋飾的精美漆器。揚(yáng)雄在《蜀都賦》中描繪蜀郡、廣漢郡生產(chǎn)的雕填、螺鈿、金銀扣等名貴漆器制作的盛況時(shí)寫道:“雕鐫鈿器,萬技千工。三參帶器,金銀文華,無一不妙”。四川漆畫內(nèi)容均為對(duì)鳥和對(duì)獸紋,描繪細(xì)致,有很強(qiáng)的裝飾感。樂浪郡的漢墓中出土的彩繪羽人乘鳳鳥的漆勺和西王母與龍虎的漆盤,所繪物象皆富有氣勢(shì)。羽人乘鳳鳥、西王母與龍虎以及彩繪漆篋上的孝子故事與玳瑁小盒上畫的羽人,都是當(dāng)時(shí)流行的題材。
三
巴蜀以得天獨(dú)厚的自然氣候和地理?xiàng)l件使農(nóng)耕文明達(dá)到極度輝煌的成就,孕育出廣漢三星堆文化、成都金沙文明等煌煌成就。與之相適應(yīng)的,應(yīng)該還有一種同樣輝煌的文學(xué)形態(tài),如像巴蜀神話所呈現(xiàn)的那樣。
“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擊石拊石,以歌九韶,百獸率舞”的原始先民生活方式,“情動(dòng)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情感宣泄方式,應(yīng)該是童年時(shí)期人類共通的表現(xiàn),巴蜀何以獨(dú)缺?人類的天性外顯,需要借助一定的介質(zhì),傳達(dá)內(nèi)心情感,語言是最直接便利的介質(zhì)。巴蜀地區(qū)的四季分明、自然景觀的多姿多樣,直接刺激人的感官,激發(fā)人的歌詠欲望,遂產(chǎn)生出世人耳熟能詳?shù)拿窀瑁纭短柍鰜硐惭笱蟆贰洞ń?hào)子》等。
《詩經(jīng)》中巴蜀原始歌謠缺失的原因,應(yīng)該有如下幾點(diǎn):
1.孔子“刪詩”。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這就是說,周王朝史官曾經(jīng)在華夏大地搜錄有至少“三千余篇”原始歌謠,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詩經(jīng)》只是孔子的一個(gè)“精選本”而非原始歌謠的全貌。孔子對(duì)《詩經(jīng)》原有作品進(jìn)行過取舍整理和刪定,其“精選”依據(jù)的標(biāo)準(zhǔn)是“溫柔敦厚”,“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盡美矣,又盡善也”等。所謂“溫柔敦厚”就是“不偏不倚,謂之中庸”,力求要有“節(jié)制”,也就是“不淫、不傷”即絕不不過分宣泄和極度張揚(yáng)情感。他很自信地宣稱道:“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所選作品內(nèi)容,“絕對(duì)健康”。因此,“蜀地僻陋,有蠻夷風(fēng)”和“巴蛇吞象,三歲而出其骨”的驕狂任性的情感表現(xiàn)方式,自然不符合孔子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巴蜀原始歌謠的缺失,也就是一種必然。
2.地理阻隔難以實(shí)地采風(fēng)。在先秦時(shí)期,由于生產(chǎn)力低下與科技水平的不發(fā)達(dá),要進(jìn)入巴蜀大盆地去實(shí)地采集民間歌謠,不僅是需要極大的財(cái)力支持,更困難的是交通工具的局限。“蜀道難”讓史官們望而生畏,止步不前,所以巴蜀原始歌謠未能錄入“古者詩三千余篇”的范圍之中。此外,在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各方國(guó)各自為政的“軸心時(shí)代”,北方中原大地的史官們能否與方音極濃的“蜀左言”巴蜀民眾進(jìn)行語言交流,收錄與欣賞巴蜀民間歌謠,也是一個(gè)時(shí)代與地域的困惑。即如宋代操山東話的女詩人李清照就指責(zé)過操四川話的蘇軾詞作“不協(xié)音律”。
3.“巴蜀圖語”的遺憾。文字出現(xiàn)之前,人類已經(jīng)有了語言,這是人類進(jìn)入群居時(shí)代的必然。巴蜀先民與其他地域的原始族群一樣,也在生產(chǎn)勞動(dòng)、祭祀、婚戀、戰(zhàn)爭(zhēng)中有著情感宣泄的需要與抒發(fā)情感的表現(xiàn)方式,其中一些優(yōu)秀作品通過口耳相傳得到留存。但直到商周時(shí)期,巴蜀器質(zhì)文明系統(tǒng)中的文字與中原地區(qū)的甲骨金文仍完全不屬一個(gè)系統(tǒng)。這些保留在巴蜀青銅器上的文字,被學(xué)者們稱為“巴蜀圖語”,屬于從原始圖畫到文字的過渡階段。即便這種“圖語”能夠逐漸地“文字化”,也會(huì)因?yàn)榍赝醭诮y(tǒng)一之際實(shí)施的“書同文”制度而徹底消失,附著其中的巴蜀原始歌謠亦會(huì)隨之消散。
概言之,上古時(shí)期的巴蜀大地,產(chǎn)生了奇幻瑰麗的神話和傳說故事,有著震驚世人的三星堆文明與金沙文明等器質(zhì)文明形態(tài),后來又有著巴蜀文學(xué)輝煌的多代呈現(xiàn),于此推想:巴蜀大地應(yīng)該有過原始歌謠的產(chǎn)生盛況。也就是說,巴蜀文化的輝煌是一個(gè)漸進(jìn)的過程而絕非“大器晚成”。春秋戰(zhàn)國(guó)以來巴蜀地區(qū)偏安一隅,極少參加北方中原地區(qū)的政治角逐而常被忽略。也由于地理阻隔和交通落后,尤其是中原正統(tǒng)及中心意識(shí)的偏頗,孔子等人在搜集整理《詩》時(shí)有意無意地忽略巴蜀地區(qū)的詩歌。我們認(rèn)為,巴蜀大盆地久遠(yuǎn)的生命史,上古時(shí)期農(nóng)耕文明的高度發(fā)達(dá),金沙、三星堆等頗具規(guī)模的城市文明,尤其是博大豐富、浪漫奇幻的巴蜀神話系統(tǒng)以及三星堆青銅文化的赫赫成就,都說明巴蜀上古語言形態(tài)的文學(xué)應(yīng)該而且可以有一種輝煌。但我們現(xiàn)在卻只能從零散的資料斷片去梳理了。
巴蜀原始歌謠,僅見于清人沈德潛編《古詩源·河圖引蜀謠》一首,其曰:“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huì)昌,神以建福”;《華陽國(guó)志·巴志》記載“先民之詩”也在盡情歌唱著生活的美好:“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養(yǎng)父。野為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養(yǎng)母”等。唐代在成都的杜甫曾用詩歌講述一個(gè)凄婉故事:“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冥漠憐香骨,提攜近玉顏。眾妃無復(fù)嘆,千騎亦虛還。獨(dú)有傷心石,埋輪月宇間。”說的就是上古蜀王悼念妃子而作《東平》《臾邪歌》《隴歸之曲》等,即《華陽國(guó)志·蜀志》載:“武都有一丈夫,化為女子,美而艷,蓋山精也。蜀王納為妃,不習(xí)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為《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dān)土,為妃作冢,蓋地?cái)?shù)畝,高七丈。上有石鏡,今武都北角武擔(dān)是也。后,王悲悼,更作《臾邪歌》《隴歸之曲》。”
實(shí)際上,從一些典籍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巴蜀原始歌謠繁盛的情況。《華陽國(guó)志·巴志》記載說:“周武王伐紂,實(shí)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曰‘武王伐紂,前歌后舞’也”。這就表明,前往北方參戰(zhàn)的巴蜀8支部落軍隊(duì),在沖鋒陷陣之際,常常是載歌載舞地行進(jìn)。漢高祖劉邦有“巴渝鼓員36人”常伴身邊的事實(shí),以及兩漢時(shí)期皇家宮廷與貴族們宴集中流行的“巴渝歌舞”等,乃至于魏晉時(shí)期“建安七子”王粲記錄的“其辭甚古,莫能曉其句度”的巴渝歌四章等,都可說明巴蜀大地曾經(jīng)有過繁榮的原始歌謠。
“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專家李學(xué)勤教授說得很清楚:“可以斷言,如果沒有對(duì)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構(gòu)成中國(guó)文明起源和發(fā)展的完整圖景。考慮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以及其與中原、西部、南方各古代文化間具有的種種關(guān)系,中國(guó)文明研究中的不少問題,恐怕必須由巴蜀文化求得解決”。
作者:四川省“中華文化與城市傳承普及基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