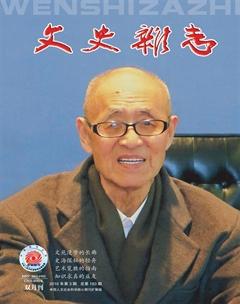彝族傳統醫藥文獻管窺
羅曲

摘 要:彝族在自己的歷史發展長河中,與疾病作斗爭,積累了治療疾病的豐富經驗。這種經驗,有的蘊含于神話傳說中,有的融匯于包括畢摩經書在內的彝文古籍中,有的則作為“專著”形式獨立存在。它們均屬于中華傳統醫學文化的大體系。
關鍵詞:彝族;傳統醫藥;文獻
彝族是西南地區的世居民族,歷史悠久,在享受大自然恩賜的同時,進行著認識自然,探索自然從而創造文化的歷程。在這個歷程中,他們創造了自己的文字,以滿足社會生活的需要。據研究,早在蜀漢建興時期就有使用彝文的依據,[1]在唐代畢摩就開始把彝文用于教學。[2]彝族在與疾病的長期斗爭中積累了豐富的治病療疾經驗,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彝醫藥文化。這種彝醫藥文化,有的蘊含于神話傳說中,有的早已使用彝文以記錄,有的見載于包括畢摩經書在內的彝文古籍中,有的則作為“專著”形式獨立存在。對于彝族的這宗寶貴文化遺產,有必要在學術的層面加以介紹,讓學界從不同角度進行研究,以更好地繼承和弘揚中華傳統醫學文化。
一、見載于彝文古籍中的彝醫藥文化
馬克思科學地考察了人類文明發展后指出,人類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想象力,這個十分強烈地促進人類發展的偉大天賦,這時已經開始創造出了還不是文字來記載的神話、傳奇和傳說的文學,并且給予了人類以強大的影響力”[3]。但是,“任何神話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是已經通過人民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 [4]。所以,彝族的神話傳說,雖然充滿幻想,是一種不自覺的藝術創作,但這是以彝族先民當時的生活為基礎的,是他們以其認識能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包括了彝族先民認識自然、解釋自然,認識人類自身、對人類自身的解釋。在這些認識和解釋中,闡述了天地萬物的起源、人類的起源及演化等事項,其中摻雜著對人體認識及其人的身體保健、疾病防治與大自然關系的內容。這些關于對人體認識及其人的身體保健、疾病防治與大自然關系認識的神話傳說內容,在彝族傳統民間社會以口頭或彝文古籍文本形式流傳著。
流傳于彝族北部方言區的神話史詩《勒俄特依》載,洪水后居木武吾為了重新繁衍人類,要求娶天神之主恩體古子的女兒為妻,但遭到恩體古子的斷然拒絕。于是,被居木武吾救起的動物為了他能娶恩體古子的女兒,大鬧天庭:老鼠鉆到放祖靈位的地方咬壞了恩體古子家的祖靈,蛇咬傷了恩體古子的腳;恩體古子的女兒則被蜜蜂刺傷。恩體古子不得已答應,只要治好自己和女兒的傷,就把女兒下嫁居木武吾。居木武吾派癩蛤蟆到天上,蛇咬傷的以麝香敷之,蜜蜂刺傷的以“爾吾”藥敷之,把祖靈位扶還原。就這樣,居木武吾娶天神恩體古子的女兒為妻重新繁衍了人類。[5]
貴州彝文古籍《物始紀略》是一部記載彝族天文、歷史、文學等內容的文集,有幾篇屬于彝族先民的醫藥文化文本,其中的《醫藥的根源》篇記述說:
病是很古的時候由風吹傳播于人間的。由風吹來的疾病不僅醫不好治不了,而且病根變化快:一病變百病,只有女的能治好病,只有女的能醫好病。一位有知識的女性,以青草治病,以樹皮治病。她到處防病治病,并把醫藥的知識傳了下來。
《人的生死說》篇中敘述道:很古的時候,人的壽命都是很長的,人間美好,人們不愿死,老來也不死。那時的人老了就換新皮,老了又換一層皮,又長新牙齒,不到幾年后,又變年輕了。
《玄鳥給日獻藥》中敘述說:天庭策舉祖有天早起來,差遣玄鳥去巡察天。但還沒到天界,才巡察到一站時,虎來撲咬太陽,把太陽咬得血淋淋。使者玄鳥先幫太陽驅走了虎,然后再向策舉祖稟告太陽被虎咬傷的事。于是,策舉祖用好藥敷在玄鳥翅上,再送去給太陽獻藥,把太陽的傷治好了。策舉祖愛玄鳥,脫下金蓑披在玄鳥身。鳥坐在太陽的腹中,從此太陽出來亮閃閃。
《兔給月獻藥》中敘述說:有一天地上恒度府清早起床后,差遣野兔,去巡察大地。還未到地界,察得一站時,狗來吃月亮。月亮膿滴淋漓,月出也無光。野兔使者,先替月驅狗,再替月傳話,稟告恒度府。度府取好藥,敷在兔眼上,去給月獻藥。月敷藥即好。度府愛野兔,將寬裙贈給兔子穿。兔坐月腹中。管月的野兔,睜眼月亮頭,閉眼月黑頭。月圓與月缺,由野兔掌握。
見載于彝文古籍文獻中的彝族神話文本,在涉及彝醫文化時,有的還反映了彝醫傳統理論,比如《西南彝志》卷四所載《人體的產生恰是一重天的構造》說:
從前人體生來仿佛像天,這話是真的。自有形體和氣以后,又生了五行,人初生于地,經五行變化,向中央涌去。五行屬金的,是人的骨骼。五行屬火的,是人的心臟。五行屬木的,是人的心肝。五行屬水的,是人的腎臟。五行屬土的,是人的脾臟……天空的太陽,是人的眼睛。天上的月亮,是人的耳朵。天空的風,是人的呼氣。天上晴朗,是人的喜樂。天上的云,是人的衣服。天上的霧,是人的墊褥。天上的風,是人的喘氣。天上的吼雷,是人說話。天上的星星,有八萬四千顆。人體的毫毛,有八萬四千根。周天有三百六十度。人體的骨骼,有三百六十節……腎屬水,與耳相連。口能主管雨,又能分辨香味。膽能主管口的作用,口所說的就代表膽的主見。
《西南彝志》卷四所載的《人體大腸小腸論》說:從前人體中,降有青紅色,也知像天樣。宇宙的八方,如人體各部。宇宙的影兒,好比人的身體,又像人的頭部。宇宙的形態,好比人的舌頭;宇宙的精華,好比人的耳朵;宇宙的妖,如人的手膀;宇宙的怪,如人的口;宇宙的哼,如人的眼睛;宇宙的哈,如人的鼻子……宇宙的影子,生了人的腸子……宇宙的形態,生了小腸,長二十四尺,像二十四節氣。宇宙的精,生了人的心。宇宙的華,生了人的腎。宇宙的妖,生了人的胃。宇宙的怪,生了人的肺。宇宙的哼,生了人的膽。宇宙的哈,生了人的肝……天上五行呢,就是中央屬土,南方屬火,北方屬水,東方屬木,西方屬金。又有五行云說,地上的五行呢,就是金木水火土。人體的五行呢?就是心肝脾肺腎……不僅如此,又有頭腦的運行,氣血如江水流行于脾,以通七竅。
從《西南彝志》卷四所載《人體的產生恰是一重天的構造》和《人體大腸小腸論》所負載的信息可知,在關于彝族先民神話思維的作品中,反映彝族先民對人體的認識方面,滲透有五行觀、天人合一觀。
《西南彝志》卷四所載的《人的氣血論》在以天人合一觀和陰陽五行說闡述了對人體生理構造的認識后,又進一步闡述了人體的經絡氣路,而且強調人的經絡氣路也與五行相關:
人死氣定斷,氣生于七竅,大腸和小腸,生在臍底之上。血(清)氣的路有三條,先的一條路,由心內發出,后的一條路,由肺肝通心臟,以流行全身。濁氣的路也有三條,末后的一條,由頭頂,貫入耳朵底,直通到腳跟。次的一條,由腦髓中生,通臂膀四肢,一條由頭頂生,如大水之流行,如河中的波浪,不斷循環著,分布于全體。所有這些,都離不了五行的相生;要是五行相克,人就不能吃飯。這五行即人之五臟,在人體搖動,不停不息的,都是古今相同的。所有這些言論,我只能這樣講,就到這里止。
《尼蘇奪書》是一部彝族創世史詩,由十個神話故事組成,從開天辟地、戰勝洪水猛獸、栽種五谷、發展生產、婚姻戀愛、音樂舞蹈、金屬采煉,一直到民族風情、倫理道德和創造文字為止,以浪漫主義的藝術手法描述了彝族人民歷史發展的過程。其中記載了大量的醫藥衛生知識,強調了醫藥對治病療疾的作用:“若要人不死,要把太醫求,要把良藥吃。娘古阿娘吉,娘別厄母病,天天去求神,日日去卜卦,早晚又刮痧。卜卦卦不利,求神神不靈。樣樣都做遍,病魔不脫身。尋思人世間,人人這樣說,治病要喂藥,吃藥能治病”。
二、見載于彝文祭辭中的彝醫藥文獻
這里所說的彝文祭辭,是指彝族祭司畢摩在相關儀式上念誦的經文。在彝族傳統社會中,喪葬儀式上畢摩念誦經文是必須的內容。在超度祖靈時畢摩是最重要的角色,所念誦的經文是超度必須的儀式。在缺醫少藥的落后社會,不少人得了病要請畢摩舉行相關儀式,在儀式上要念誦相關經文。在畢摩念誦的經文中,不少文本中隱含著彝醫文化。這類文獻主要有以下一些——
《斯色比特依》:在傳統社會里,彝族認為“斯”是神靈,“色”是游蕩,“斯色”即游蕩不定的神靈之意,作為病癥則指風濕類疾病。人們認為凡天氣、山氣、地氣、水氣等所引起的疾病為“斯色”病。
書中比較詳細地論述了“斯色”病的起因、傳播及如何驅趕這些病邪的方法,記載了風、云、雨、雪、霧、雷、電、高山、平壩、土、水、河、森林、蠅蛾、蟬、蚊、老鼠、狐貍等皆附有“斯色補絲”。這些東西不斷繁衍,分支達九十九支,其中森林、巖洞、高山等處是其自古以來的棲息地。
《吃藥好書》:這是畢摩在彝族老人去世后的超度儀式上所念誦的經文,或者是在祭祖大典上畢摩超度祖靈儀式上念誦的經文,所以常被稱為《超度書》。其內容很豐富。有的《超度書》中有醫藥文化內容,比如,在云南流傳的一部《超度書》中有一篇題作《吃藥好書》。這里所說的《超度書》指刻于清嘉慶年間(公元1796-1820年)的木刻本。馬偉光先生于1993年在《云南中醫學院學報》第3期上發表了對該書的研究成果。從其研究看,該《超度書》中的《吃藥好書》篇介紹了藥物25味、治療病癥19種,在動物藥中重點介紹了5種動物肉和10種動物膽的功用。書中所列動物為彝族歷史上狩獵所能捕獲的動物,如野豬、獐子、熊、麂、猴、鷹、烏鴉、魚、蛇等。
《作祭獻藥供牲經》:有的譯稱為《供牲獻藥經》,簡稱為《獻藥經》。《作祭獻藥供牲經》作為祭奠死者時畢摩唱誦的一種祭祀經文,雖然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但其中有一部分內容是樸素的唯物思想的認識和反映。據劉憲英、祁濤于1996年在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彝醫》考證,《作祭獻藥供牲經》抄于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曾廣泛流傳于云、貴、川三省。1947年,著名歷史學家、社會學家馬學良教授在云南省今祿勸彝族苗族自治縣團街鄉安多康村彝族畢摩張文元家調查時發現此書,旋翻譯整理成彝漢對照加注釋的成果《倮文作祭獻藥供牲經譯注》,發表于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上。[6]
《尋藥找藥經》:該經文在描述找藥的艱辛、藥物珍貴的同時,強調認識藥草的是勞動者(牧羊女);而藥草的發現是從對動物的觀察中得到啟發的,反映了醫藥源于實踐,源于對動植物的認識。《尋藥找藥經》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到了宏魯山,因為羊兒病。心中暗焦急,急忙找藥草。掰一枝黃藥,繞向羊兒身,不見羊兒起,這不是良藥。覓到青葉藥,急忙采一枝,繞向羊兒身,羊兒站起來。羊兒蹦蹦跳,這正是良藥”。
《卓莫蘇》:漢譯為《指路書》,據內容有人稱之為《人生三部曲》。據推測,其成書年代在明末清初之際,新中國成立后由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翻譯并于1982年刊印。此書屬彝族喪葬儀式唱誦經書,內容主要是給死者的靈魂指明道路,讓死者的靈魂從當地沿著祖先遷徙來的路線回歸祖先的發源地。在其第一部“追憶亡人”一篇中,有屬于彝醫藥文化的內容,反映了彝族先民在遇到疾病時,不是“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而是積極采藥治療。
《查詩拉書》:這是一本流傳在哀牢山區彝族村寨中較為完整的殯葬祭詞,在系統地介紹哀牢山地區彝族喪葬習俗的同時,論述了不少彝族醫學知識,如對新生兒期、嬰兒期、幼兒期、幼童期、少兒期的生長發育過程進行了全面的描述;而在治病用藥上,則主張大膽使用動物膽類藥,體現了彝族醫藥的特色。在該文本中還提出很多衛生防預及處理措施。
三、彝醫藥專著文獻
彝族很早就有了自己的文字,并運用于彝族的社會生活之中,但使用者主要為畢摩階層。人們對畢摩留下的文獻以畢摩經書稱之。雖然歷史上使用彝文者主要是畢摩階層,但他們生活于彝族社會之中,其活動以彝族社會為基礎,以彝族民眾為對象。所以,在畢摩經書中的彝醫藥文化,除了見載于相關文本中外,還有以彝文撰著的彝醫專著。這類彝醫藥專著文獻,是彝族歷史上身體保健、疾病防治智慧的結晶,也是彝族先民的一種理性化了的生活經驗,因此有極其重要的研究價值。長期以來,在眾所周知的歷史里,彝醫藥文獻未受到應有重視,使之在彝族群眾中的實際使用價值未能得到體現。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拯救民族醫藥的語境下,相關機構和個人開始對彝醫進行調研,并陸續出版了搜集、翻譯的彝醫文獻。這類文獻主要有以下一些——
《元陽彝醫書》:該著發掘于云南紅河元陽縣攀枝花區勐品村畢摩世家馬光福家(馬光富為第四十二代家傳畢摩)。當地曾有“紅河水不干,馬家書不絕”之說。有關專家據其書中對漢語音譯年代的解讀,確認該書成書于大理國明政七年,即公元975年。該書收載了動植物藥200余種,病名80多個以及一些簡易的外科手術,沒有巫術咒語之類表現民間原始宗教信仰的內容,反映了當時的彝族先民對疾病的防治水平,也是了解宋代以前彝族藥物、醫療技術及當時常見病的第一手資料,有特別的學術價值。
《齊蘇書》:書名意即為彝族治病的醫書,又稱《雙柏彝文醫書》和《明代彝文醫書》,是1979年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藥檢所在雙柏縣發掘出的一本古彝文醫書,原件為彝文手抄本,無書名。因其發現于雙柏故稱為《雙柏彝文醫書》,又因其成書于明代所以也稱《明代彝文醫書》。據該書抄本原件“序”所稱,此書成書于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以后歷經清代、民國多次傳抄。該書共有古彝文約5000字,分為76段,記錄了56個病種,87個處方,324味藥物。該書文本以病癥為綱進行編寫,所列病癥、癥狀或體征有60種左右,其內容涉及臨床各科,其中屬內科者約31種,屬外科(包括皮膚科、花柳科)17種,屬五官科者約6種,屬婦產科者5種,眼科1種,傷科4種。
《好藥醫病書》:又稱《醫病好藥書》。該彝文醫書抄于清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冬,于1979年3月在云南省祿勸彝族苗族自治縣團街鄉王李茂家發現。該書記載了內科、外科、婦產科、兒科和五官科的39種疾病,共有317個處方;由單味藥物組成的方劑有171個處方,占54%。全書記有藥物307味,按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分類法大至分為水、火、土、金石、谷、萊、果、木、草及禽類、獸類、魚類和鱗類等13種,但以草類最多。在古彝文醫藥文獻中,該書是內容比較豐富而全面的專著。
《小兒生成書》:又名《娃娃生成書》,抄于清雍正年間(公元1723-1735年),發現于云南省祿勸縣團街區,屬于介紹兒科部分生理知識的專書。該書以樸素、生動的文字將胎兒逐月發育、生長的情況作了描述,對從嬰兒到兒童(1-9歲)的智力、生理變化分為三個部分作了簡單記述:第一部分描寫胎兒從受精開始到降生前的整個胚胎發育過程,第二部分描寫自胎兒出生到1周歲的生長發育、生理變化狀況,第三部分描寫幼兒的生長發育、生理變化情況。
《努苦蘇》:意譯為《醫病書》,1979年民族醫藥普查時,發現于滇西北的祿勸縣團街區自租鄉自租村王學光家。《努苦蘇》和另外的幾部彝醫藥書《可雌崇梭泥》《小兒生成書》《作祭獻藥供牲經》在發掘地點、語言文學、用藥特點方面基本一致,可視為是北部方言區的一個學派。[7]
《啟谷署》:成書年代不詳,但書中留有遺言:“不予公開,只能以男性代代相傳”。該書是貴州省仁懷縣政協秘書長王榮輝先生保存的祖傳彝文古籍手抄本,至王榮輝已傳六代。其成書年代難以考證。據遵義醫學院華有德教授鑒定推測,其成書年代不會晚于明萬歷十八年(公元1590年)。為了不使此書受蟲蛀或損壞,藏書者將它用筍殼包好,再用牛皮紙密封,然后用雞蛋清涂抹烘干藏于“香火”頂上的房屋草內。《啟谷署》記載有5門、38個疾病、263個方劑。其中有傳染性疾病、呼吸系統疾病、消化系統疾病、血液循環系統疾病、生殖系統疾病、神經系統疾病,處方76個。婦科疾病有痛經、帶下、妊娠病、產后病、乳房病、雜病等,處方34個。兒科有傳染性疾病、消化系統疾病、營養性疾病、雜病等,處方12個。外科有癰疽、痔瘡、疥癬、黃水瘡、跌打勞傷、蟲獸咬傷、火燙傷等,處方90個。五官科有耳瘡、眼紅腫、鼻炎、牙痛、咽喉腫痛等,方劑50個。據稱本書所載內容經后人臨床驗證,有效率達95%以上,是研究彝族傳統醫學很有參考價值的一部文獻。
《聶蘇諾期》:“聶蘇諾期”是彝語音譯,其意為醫治疾病的藥。該書是在云南新平縣老產河搜集到的民國10年(1921年)的抄本。對書中所述,相關方面經過數年時間的調查核實,并用現代植物分類學進行了藥物品種鑒定,有的還在臨床上作了驗證。據學者研究,在彝語南部方言區流傳的彝文醫藥書較多,且一般都以“聶蘇諾期”稱之。[8]
《老五斗彝醫書》:該書是1987年聶魯、趙永康二先生在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縣老五斗鄉一帶發現的。據學者考證此書雖然用彝文抄寫于民國3年(1914年),但其最早成書當在清末之時。該書對于研究彝族南部方言區的醫學流派和發展情況是難得的文獻。此書在疾病方面記載了53個,其中內科疾病17個,傷科疾病5個,外科疾病18個,婦科疾病4個,蟲咬傷4個,中毒性疾病2個,兒科疾病3個。本書一個顯著的特點是有針灸,其所載針刺部位有五處:人中、七宣、百會、涌泉、太陽。另有火罐拔毒的內容。從藥物看,記載有動物藥123種,其中多數屬動物內臟:膽類藥13種,肺臟3種,肝臟4種,脂肪類5種,血類3種,腎臟1種,骨灰12種,胎類2種;肉類15種,分泌物18種,卵類8種;昆蟲類藥物23種,皮毛類藥物9種,蛙蛇類藥物9種;又記載植物藥235種,其中樹脂類9種,果子類13種,塊莖類15種;糧食飲食物類5種,草木類194種;金屬化學類藥物21種,方劑301個。
《三馬頭彝醫書》:該書是1986年在云南省玉溪地區元江哈尼族彝族自治縣洼垤三馬頭李四甲家發現的。此書沒有記載具體的成書年代,據考證屬于晚清彝族醫學著作。書中記載疾病69個:內科疾病41個,婦科6個,兒科1個,外科16個,喉科1個,傷科1個,中毒性疾病3個;記載藥物263種:動物藥80種(肉類20種,膽類10種,血類6種,皮毛類14種,脂肪類2種,分泌物8種,胎類3種,昆蟲類9種,蛙蛇類9種),糧食及化學類15種,植物藥168種。從其記載的藥物看,膽類、血類藥較多。
《洼垤彝醫書》:該書是1986年在云南省玉溪地區元江哈尼族彝族自治縣洼垤李春榮家發現的。據考證屬于晚清著作。書中記載疾病48個:內科28個,婦科3個,兒科2個,外科2個,傷科8個,誤吞異物2個,蟲獸傷5個,中毒性疾病3個;動物藥75種,其中腦類2種,脂類3種,肉類6種,內臟類6種,胎類6種,生殖器類216種,魚蛇類6種、昆蟲類7種;植物藥261種,其中寄生類14種,參類12種,樹皮類19種,草木類216種。本書與《三馬頭彝醫書》發現于同一地方,但從記載的疾病和藥物來看各有特色。兩書不屬于互相轉抄的。
《造藥治病書》:彝名漢語音譯為“此木都且”或“此母都齊”,直譯為《造藥治病解毒》”,發現于四川涼山甘洛縣,由沙光榮翻譯,郝應芬、李耕冬校定。該書原本用四川彝文自右向左橫書,共19頁,共約有6000個古彝文字,譯成漢文約1萬字,成書年代在公元16世紀末17世紀初,分為278個自然段落。書中絕大部分是關于醫藥的敘述,夾有少量巫術咒語。該書共收載疾病名稱142個,包括內、外、婦、眼、雜病及許多獸病;記載藥物201種:植物藥127種,動物藥60種,礦物藥和其他藥物14種。從文本所反映的內容看,該書不論用藥方面,還是在治療方法上,都反映了涼山彝醫藥的特點。
《醫算書》:這是有相當研究價值的一部書,發現于四川省涼山州,屬于手抄彝文醫書,成書年代不詳。所謂“醫算”,是古人將天文歷法知識運用于推算人的生老病死內容的一種方法,即根據十月太陽歷和陰陽歷來推算病人的年齡、治病禁日和衰年。其深層意義是對人的疾病與天體運行關系的一種探索,也是對人體生命周期的一種認識。其中關于壽命的測算,疾病的預測,以及生命周期性節律的計算,可謂良莠并存。
該書的“醫算”主要依據太陽歷和陰陽歷來推算病人的年齡、禁日、衰年。關于年齡的推算:以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鼠、牛十二生肖為基礎表述禁日。比如,說屬免的一天禁止針刺什么部位等。彝族稱禁日為“戳戈忌”,意為人體可能發生危險的日子,故在漢語里意為“人辰日”。有專家調研后認為,“彝族先民的針刺有別于漢醫,是一種針刺與放血相結合的療法。彝醫發現人體不同部位對針刺的反應因日子的不同而變化,有時甚至可能發生致命的危險。因此要用歷算來掌握和避開這些日子。這就是在大量觀察、實踐后積累起來的‘禁日’知識。它主要是針對針刺反映而言。所以,也可以說禁日就是禁止針刺人體某些部位的日子。”[9]
關于衰年的推算,是以十二獸紀年法推算生命中的周期性衰弱時間:即人的生命過程呈現一種以八年為周期的節律性變化。所謂“衰年”,是在“十二獸年―陰陽五行―八方位年”這個系統里,所推算出來的生命節律中人體表現衰弱的年份。在這種年份中,機體抗病力下降,容易患病或受傷,且傷病后不易恢復,故衰年又叫危險年。只要衰年一過,人體機能便又恢復正常。按照彝族先民的認識,當一個人出生后,便以十二獸即十二生肖順序排列的“年”增長著歲數。當人滿30歲之后,生命周期開始出現較明顯的節律性變化。這種變化的發生隨個人屬相在生命歷上的位置不同而不同,但第一個衰年的出現總在31歲-38歲之間,此后以八年的周期延續,走到去世。
《醫算書》對針刺的時、日以十二生肖記時法進行記載,比如腳掌心、手掌心、心窩部、頭蓋骨以及胸、腹、腰、背、腿、臂等部位。要進行針刺都必須看日子,看是否是禁日或禁時;如果違反禁時或禁日,不僅治不好病反而會發生危險。
《看人辰書》:該書發現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雙柏縣,從內容看,與流傳于四川彝區的《醫算書》相類。本書系統地記載了某些特定日子為禁日,針刺特定部位會發生危險。在計算禁日時,按每月三十六天計算,逐日有禁刺部位。書中明確指出:
正月、二月、三月,人辰日為豬日、鼠日;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人辰日為蛇日、馬日;十月、冬月、臘月,人辰日為猴日、雞日。凡在人辰日均為禁日,針刺容易發生危險。
《醫病書》:1980年發現于云南省祿勸縣。全書為彝文手抄本,其抄寫時間據書后記為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書中簡明地記載了38種疾病:內科病6種,外科病4種,兒科病2種,眼科病1種;方劑69個:單方38個,復方31個,其中由二味藥組成的方劑20個,三味藥以上組成的方劑11個。全部處方所列藥物97種:動物藥25種,植物藥72種。該古彝文醫書主要是介紹藥物功用和單方、驗方的,對彝藥單方的研究很有價值。[10]
《哀牢山彝族醫藥》:該書是根據前述哀牢山中段新平縣老五斗流傳的彝族醫藥手抄本、哀牢山下段元江縣三馬頭一帶流傳的兩部彝族醫藥手抄本,經調研、翻譯、注釋、整理、編纂而成的專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出版。全書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彝醫發展簡史,包括彝醫的起源和發展,彝醫藥的興衰,彝醫基礎理論;第二部分是臨床各科,即涼山彝族民間常見的一些主要病因、病癥、診斷、治療以及方藥的歸納整理;第三部分是臨床各論,對內、婦、兒、外某些病因、病機、病癥、診斷、治療、方藥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論述。全書記載疾病197個,方劑1364首,載藥1064種,是一部較完整的彝族醫藥著作。
《哀牢本草》:由云南省玉溪地區藥品檢驗所王正坤、周明康等據彝族民間手抄本編譯,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年出版。為了發掘民間彝族醫藥,玉溪地區有關人員,深入哀牢山區彝家村寨,虛心求教賢達,先后在古哀牢屬地發掘到古彝文醫藥典籍手抄本數本。據學者考證,這些手抄本大抵以口碑資料醞釀于元,成書于明,傳于清,轉抄于民國初年。按彝文品名,計有藥材988種:植物藥701種,動物藥244種,礦物藥31種,其他藥12種。書中所列方藥包括了內、外、婦、兒、五官、皮膚、性病、骨傷等多種疾疫病傷所需之藥物;在制、服方面,包括煨、炮、煎、煮、燉、熬、蒸、烊、烘、烤、浸、泡、沖等傳統炮制方法,內服、切皮給藥、灌注、滴人、吸人、沖洗、揉搓、涂搽、包敷、拍打等多種給藥途徑。
文化的創造,有的是屬于“平行創造”,即不同的群體在不同的時空會創造出同一性質或相同類型的文化,或者相似的文化;有的是由于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相互影響,吸收異民族優秀之處完善自己形成的。后一種文化形成在彝族的傳統專著醫藥文獻有明顯體現。比如:前述《醫算書》中所說的衰年周期,與《黃帝內經》中的《上古天真論》對男女生命周期變化的相似:“丈夫八歲,腎氣實,發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三八,腎氣平均,筋骨勁強,故真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五八,腎氣衰,發枯齒槁。六八,陽氣衰竭于上,面焦,發鬢斑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藏衰,形體皆極。八八,則齒發去” [11]。再比如,前述彝醫文獻《齊蘇書》,據專家研究,其內容基本上是一本方書,體例與晉代葛洪所著《肘后備急方》極為相似,很可能受到漢醫學文化的一定影響。[12]
文獻的核心價值是保存人類認識,同時也作為人們進一步認識世界的工具。所以對于彝族專著形式的醫藥文獻加以介紹,讓學界在中華醫學文化的大背景下對其予以研究,對于豐富中華醫學寶庫當有重要價值。
注釋:
[1]據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彝文金石圖錄》第一輯載,在貴州大方縣發現了“妥阿哲紀功碑”。《貴州名勝古跡概說》認為,此碑“相傳為蜀漢時濟火所立,碑上有建興年號”。這一說法和《西南彝志》中的“德施氏源流”的相關論述相吻合。
[2]參見孔祥卿:《彝文的源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7頁。
[3]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第二冊第5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11頁。
[5]參見馮元蔚譯《勒俄特依》,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89-92頁。
[6]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馬學良著《云南彝族禮俗研究文集》收載了《倮文作齋經譯注》《倮文作祭獻藥供牲經譯注》。另,張仲仁、普衛華將《作祭獻藥供牲經》彝文原本重新翻譯,由熊長麟審定,定名為《供牲獻藥經》,于1988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7]參見劉憲英、祁濤主編《中國彝醫》,北京: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頁。
[8][9][12]彝族古文獻與傳統醫藥開發國際學術研討會組委會編《彝族古文獻與傳統醫藥開發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05頁,第77頁,第70頁。
[10]相關內容詳見關祥祖、方文才著《醫病書》一書,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
[11]郭靄春:《〈黃帝內經·素問〉白話解》,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4年,第5-6頁。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云貴川百部《彝族畢摩經典譯注》研究”(項目批準號:14ZDB119)階段性成果,國家民委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彝學研究中心課題”成果(項目批準號YXJDY1405)。
作者:西南民族大學彝學學院教授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特約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