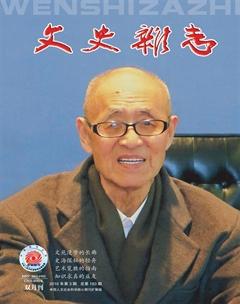蜀族族名含義新探
徐晨
摘 要:“蜀”象野蠶之形或象毒蟲之形的傳統看法缺少有力證據。古代文獻以及戰國竹簡可以證明:“蜀”通獨(繁體“獨”),是獨的假借字;蜀族的蜀的本義是獨立的意思,蜀族是獨立于中原文化圈之外的部族。
關鍵詞:蜀即獨;蜀族即獨族;蜀族族名
對古蜀族“蜀”字的釋義,比較普遍的是將其釋為蠶。《說文·蟲部》釋“蜀”:“蜀,葵中蠶也,從蟲,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段玉裁注:“葵,《爾雅》釋文引作桑。《詩》曰:蜎蜎者蜀,蒸在桑野,似作桑為長。《毛傳》曰:蜎蜎,蠋貌,桑蟲也。《傳》言蟲,許言蠶者,蜀似蠶也。”《廣韻》引此文作蜀,蜀正字,蠋俗字。娟娟,系蠕動曲屈之態。蠋,是蛾蝶類幼蟲的統稱,這里特指桑中之蟲,從而可以得出蜀是桑林中生活的蠶,即蜀蠶相通的結論。由于上述文獻的影響,孫冶讓的《契文舉例》,商承祚的《殷墟對字類編》,葉玉森的《殷契勾沉》以及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解》等都將“蜀”解釋為蠶。一些學者認為“蜀族”是古代從事蠶桑的民族,這種解釋似乎不能全然令人信服。[1]
其實,蜀、蠶,是有區別的。《韓非子·說林下》:“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賁、諸。”《淮南子·說林訓》:“今鳣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高誘注:“人愛鳣與蠶,畏蛇與蠋。”它們皆認為蜀、蠶非一,而蜀(蠋)是一種毒蟲。《說文·蟲部》釋“蜎”:“蜎,肙也,從蟲,肙聲。”段玉裁注:“小蟲也,《毛傳》曰:蜎蜎,蠋貌,桑蟲也。其引申之義也,今水缸中多此物,俗謂之水蛆,其變為蟲。”在殷墟甲骨文中,“蜀”與“蠶”在字形上的區別也很明顯,不可混同。
有學者認為,蜀以蟲為偏旁,這是商代的統治者對蜀人的一種賤稱,說這與歷代王朝在少數民族的族稱用字都加偏旁“犭”或“蟲”,是一致的。[2]細究起來,這種說法也似難成立。從甲骨文看,商代用作方國名和地名者,無一賤稱之例。“蜀”在西周曾被視為“四極”之一,《班簋》載:“乍(作)四方亟(極),秉緐(繁)蜀巢。”其中的三極即秉緐巢和蜀一樣,并未加“蟲”加“犭”,不應視作賤稱。周代的中央王權得到極大加強,遠非殷商王朝與眾方國之間的松散的聯盟關系可比,于是華夏自我中心主義思想相應地膨脹起來,“嚴夷夏之防”,以賤名稱呼四夷少數民族的現象開始出現。“蜀”早見于商代甲骨文,且字不從蟲,從蟲之蜀始見于西周時期的周原甲文,所以,“蜀”起初并非賤稱,到了周代以后才是。[3]
還有一種可能是“蜀”通獨(繁體“獨”),是獨的假借字。1993年,湖北荊門市郭店一號楚墓被發掘,出土竹簡804枚,約有13000字,其時代為戰國晚期,公元前300年左右。郭店楚簡中的《性自命出》篇第7號簡有:“蜀行,猷口之不可蜀言也。”第54號簡有:“蜀凥而樂。”第60號簡有:“毋蜀言,蜀凥則習父兄之所樂。”其中的“蜀”,帛本、今本作“獨”。郭店簡《老子》甲第21號簡:“蜀立不亥。”其中的“蜀”,帛本甲、乙,王本作“獨”。《五行》第16號簡:“君子慎其蜀也。”蜀,帛本《五行》第223號簡作“獨”。 [4]
1994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購得一批戰國時期楚國竹簡,2001年出版了《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2002年出版了《上海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其中上博簡《詩論》第16號簡:“《燕燕》之情,以其蜀也。”上博簡《中弓》第12號簡:“蜀言厭人,難為從正。”蜀言,讀為“獨言”。上博簡《周易·夬》第38號簡:“九晶(三):君子夬夬,蜀行遇雨。”蜀,帛本、今本作“獨”。上博簡《君子為禮》第9號簡:“蜀智,人所惡也。蜀貴,人所惡也。蜀富,人所惡也。”蜀,讀為“獨”。 [5]從對以上楚國的竹簡的釋讀中可以得出,“蜀”是獨(繁體“獨”)的假借字,“蜀”有獨的意思。
除此之外,《爾雅注疏》卷七釋“獨”:獨者,蜀(蜀亦孤獨)。[疏]“獨者,蜀”。注“蜀亦孤獨”。釋曰:“言山之孤獨者名蜀。”《方言》卷十二:“一,蜀也,南楚謂之獨。”《山海經》云:“獨山,多金玉美石。”對《管子·形勢》篇“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一句,歷來解釋可謂眾說紛紜。其實“抱蜀”就是“抱獨”的意思,而“獨”就是“一”,“一”就是“道”。“抱蜀”就是守住“道”;守住了“道”,便可無為而治,廟堂社稷之政務自然也就會鞏固,一切所作所為就會功成名就。[6]
對于中原以炎黃部落為主體的華夏族來說,古蜀國地處偏僻的西南,宗教信仰、風俗習慣與華夏族截然不同。《文選》左思《蜀都賦》劉淵林注引揚雄《蜀王本紀》記載:“蜀王之先名蠶叢、柏濩、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萌椎髻,左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太平御覽》卷一百六十六引揚雄《蜀王本紀》記載:“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折權、魚易、俾明。其時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與中原相比,“左言”為語言之異,而“左衽”則為服飾之異。[7]
先秦時期中原王朝往往以右為尊,而一些周邊少數民族則以左為尊。《文選·六臣注》載唐呂向曰:“侮食、左言,蠻夷國也。”此為釋“左言”之最古者。[7]《禮記·王制》載:“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注:“右學,大學也,在西郊;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禮記·曲禮上》:“獻粟者執右契。”鄭注:“契,券要也。右為尊。”《禮記·檀弓上》:“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注:“喪尚右,右,陰也。”《正義》:“此即兇事尚右。”《老子》三十一章:“兇事尚右。”“用兵則貴右”注:“貴右者,以喪禮處之也。”《禮記·少儀》:“卒尚右”注:“右陰主殺,卒之行伍以右為上,示有死志。”正義:“卒尚右者,言士卒行伍貴尚于右,右為陰,示其有必死之心。”行伍,排列的行列。現行伍的“向右看齊”,仍應為士卒行伍尚右的殘留。[8]
上述“左言”為秦滅蜀前蜀人之言,《漢書·地理志》言:“巴、蜀、廣漢本南夷”,是為實錄。《蜀王本紀》以及相關典籍,還有《辭源》等的記載都是從中原王朝的角度出發的,所說的“時人萌椎髣(當為“髻”之訛),左言,不曉文字”是中原華夏族對蜀人的看法。
20世紀30年代的考古發掘,三星堆、金沙遺址的發掘與考古以及對巴蜀歷史文化的進一步探究,使許多巴蜀文物重見天日并且得到闡釋。有些文物上有巴蜀文字或符號,例如四川新都、郫縣張家碾、峨眉符溪出土的銘文戈以及收集的三角形銘文戈等銅戈都系戰國時器物,其上銘文成行成句,可以認定為蜀族文字。[9]這些古蜀人的兵器常飾以虎紋,以援脊作為吐出的虎舌……蜀國的兵器演變自有脈絡,與中原有別。[10]蜀戈上的銘文無論從文字形體、還是書寫方式都與中原的甲骨文不相同,可以看出古蜀人的文字是中原華夏族甲骨文體系之外的一種獨立的文字,古蜀族是獨立于中原文化圈之外的民族。“蜀”應該是中原華夏族對蜀的稱謂,不是蜀族人的自稱。對古蜀國的文化發展,顧頡剛《古代巴蜀與中原的關系說及其批判》說:“古蜀國的文化究竟是獨立發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戰國以來的事。”[11]
《戰國策·秦策一》有:“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倫也,弊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李白《蜀道難》:“蜀道難,難于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這亦可證明古蜀族是獨立于中原華夏族之外十分獨特的西僻之國,戎狄之長。對于華夏族而言,這個民族是個獨立的、獨特的部族。
古蜀人崇拜虎,從出土的幾件蜀戈來看,其上有虎紋。四川峨眉符溪出土的蜀族虎紋雙髻跪人銅戈,虎身和虎尾在胡部,虎頭在援末部,大大張開的虎口朝向援鋒,緊挨虎口,屈跪著雙手雙腳被縛的雙髻巴人。這個圖像表達的可能是蜀虎吞食巴人,以巴人祭虎的圖像,象征蜀人戰勝巴人的內容。[12]孫華先生說:“巴蜀符號大部分都有虎、羊、心等圖形……蜀地也有崇虎的部落。”[13]廣漢三星堆出土的金虎和青銅虎,造型生動,說明了古蜀人有崇虎的習俗。這與中原對龍的崇拜截然不同,也說明古蜀國的文化是獨立發展的,是一種獨特的文化。
先秦時代,中原王朝判別其他周邊國家是否為少數民族的標準,不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而主要以對中原文化的認同為依據。周邊國家的風俗、語言、飲食等與中原王朝存在很大的差異,這些國家就會被中原王朝認為是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異族國家。蜀國的左言、左衽等與中原王朝的右衽、右言以及甲骨文為主的文化內涵截然不同。綜上所述,我們認為,“蜀”與“獨”通假,蜀族族名的含義是獨族,是獨立于中原文化圈之外的獨特的民族。
注釋:
[1]參見錢玉趾.巴族蜀族族名的由來及含義辨析 .[J].當代電大,1990.
[2]參見童恩正.古代的巴蜀 .[M].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55.段渝.四川通史第一冊 .[M].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36.
[3]參見賈雯鶴.圣山:成都的神話溯源——《山海經》與神話研究之二 .[J].四川大學學報(哲社版),2004.
[4]參見劉信芳.楚簡帛通假匯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66.
[5]參見蒙默.蜀王本紀·“左言”“左衽”辨釋及推論 .[J].文史雜志,2012.
[6]參見朱英貴.釋“蜀”.[J].成都大學學報,2011.
[7]參見洪頤煊輯.《蜀王本紀》見所撰《經典集林》卷十四.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錄洪輯以入其書之揚雄卷,僅增一條,而又未予說明.
[8]參見張靄堂.古漢語左右尊考釋 .[J].玉溪師專學報,1987.
[9]參見錢玉趾.巴蜀文字與神秘文字 .[J].人民日報,1933.
[10]參見李學勤.論新都出土的青銅器 .[J].文物出版社,1987.
[11]轉見屈小強,李殿元,段渝.三星堆文化 .[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15.
[12]參見錢玉趾.巴蜀史與古文字探 .[M].天馬出版社,2010.15-16.
[13]孫華.巴蜀符號初論 .[J].四川文物,1984.
作者:西南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史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