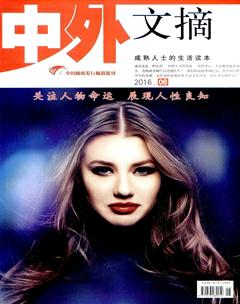臺灣“尊嚴死”合法之后
鐘厚濤
2015年12月18日,臺灣地區“立法院”三讀通過“病人自主權利法”,并將于3年后正式施行。依據此法,未來臺灣18歲以上公民,可以提前作出醫療決定,在后來罹患重大疾病時拒絕治療,選擇有尊嚴地離去。臺“衛生福利部”表示,這是亞洲第一部以病人自主權為主要內容的法律,標志著臺灣在相關法律建設方面走在前列。
這也標志著“尊嚴死”在臺灣合法,所謂“尊嚴死”,即并不提前結束自然人的生命,而是在尊重個人意愿的前提下,不延長自然的生命。而“安樂死”通常是指在醫生幫助下的自殺方式。比如,給予注射藥物或口服藥,提前結束自然人的生命。
病人無權拒絕治療的惡果
對于很多身患絕癥的病人而言,與其茍延殘喘,無奈地存活下去,他們寧愿放棄治療,有尊嚴地死去。但根據臺灣現行的法律規定,病人根本無權作出這種選擇,只能被動地接受治療,因為這是醫務工作者的責任。
臺“醫師法”第21條規定,“醫師對于危急之病人,應即依其專業能力予以救治或采取必要措施,不得無故拖延”。“醫療法”第60條規定,“醫院、診所遇有危急病人,應先予適當之急救,并即依其人員及設備能力予以救治或采取必要措施,不得無故拖延”。
顯然,救死扶傷已經成為了臺灣醫務工作者的一項基本法律義務,如果見死不救,則將被視為是主動傷害,將受到“刑法”追究。臺“刑法”第15條規定,“對于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
若是醫務工作者按照病人的意愿,放棄治療,則等同于是協助其自殺,也將受到法律的懲罰。“刑法”275條規定,“教唆或幫助他人使之自殺,或受其囑托或得其承諾而殺之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謀為同死而犯第一項之罪者,得免除其刑”。
顯然,面對病人,醫務工作者只能全力以赴,加以搶救,不能放棄治療,即使是病人自己打算放棄治療,醫務工作者也不能配合,否則就將抵觸法律,受到嚴懲。也就是說,臺灣的法律并不允許醫務工作者協助病人放棄治療。這一點在1989年3月16日衛署醫字第786649號中有明確的說明:“有關罹患不治之癥病人,如經本人或家屬同意,立同意書后,醫師可否放棄心肺復蘇術之處置疑義,因事涉生命尊嚴、宗教信仰、倫理道德、醫藥技術及病人情況等復雜問題,目前尚有不宜。”
除了法律上明令禁止之外,現今病人的相關合法權益常被家屬的意愿凌駕,一般家屬不會同意“停止對病人進行醫治”。因為如果放棄對病人進行醫治,他們可能會出現深深的心理愧疚和自責,認為自己沒有盡最大的努力。同時還將背上沉重的道德包袱,會被周邊人員認為是“大逆不孝”或者“喪盡天良”。因而家屬會選擇繼續治療來延續病人的生命,但殊不知這也是在加重病人的痛苦。
并非鼓勵安樂死或自殺
“病人自主權利法”全文共19條,核心內容是,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18歲以上人士,可通過“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事先簽署“預立醫療決定”,在未來出現植物人、極重度失智等癥狀、且經醫療評估確認病情無法恢復時,醫務工作者可以按照病人的意愿,停止對其治療或灌食,讓其自然死亡。
為慎重起見,意愿人要想完成預立醫療決定,需同時具備三項條件,一是接受醫療機構提供相關咨詢,二是經公證人公證或兩名以上具備完全行為能力者在場見證,三是在全民健康保險憑證上作出相關記錄。每項認定要由兩位專科醫師確診,并經有關醫療團隊至少兩次照會確認。預立醫療決定后,可隨時撤回或變更決定。
新法還明確規定病人對于病情、醫療選項以及其可能的效果與風險等,應有足夠的知情權。以前有些病人被確認身患絕癥時,醫生通常與其家屬溝通,商議治療方案,有意將病人排除在外。在這種情況下,就構成了雙重弱勢,既要忍受病痛的折磨,又失去了主體權利,喪失了做醫療決定的機會。
很多家屬怕影響病人心情,也刻意對病人隱瞞病情,讓病人誤以為還可以存活很久,最后卻倉促病逝,留下了許多未竟的遺愿。“病人自主權利法”正式實施后,病人將享有更多的知情權力,無疑可以避免上述許多遺憾的出現。
新法也允許病人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病人接受治療時,通常需要有血緣的家屬簽署同意書,但隨著社會結構的改變,許多單身未婚、同性戀人士、沒有配偶子女的人也需要醫療委任代理人,讓病人在生命的最后時刻,能夠讓自己最信任的人而不一定是與自己有血緣關系的人來為自己作出重大決定。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用法律的形式確保病人自主權,并不是要去鼓勵安樂死或者自殺。安樂死是由他人為想實行安樂死的病患注射致命藥劑,而自殺則是一種“生命自我處分權”,等于是提前結束生命。而病人自主權的保護,則并不是要求醫療人員為其注射致命藥劑,也不是要加速病人死亡,而只是確保病人有知情權,有拒絕接受醫療的權利,有安靜離去的權利。
臺灣社會輿論普遍支持
對于新法,臺灣社會普遍支持,認為拒絕醫療不是放棄生命,而是尊重生命。面對心臟停止跳動的病人,不實施搶救手術,其實是“讓病人自然的走”;對于那些只能依靠食管來勉強維持生命的人,放棄治療其實是“讓病人有尊嚴的走”。
臺灣消費者基金會民調顯示,97%的臺灣民眾都表示認可“病人自主權利法”。許多身患絕癥的病人,尤其表示歡迎,認為此法可以讓他們“還我自主權,拒當活死人”。
臺灣社會及政界雖然對該法廣泛支持,但醫學界卻對之一喜一憂,爭論激烈。部分醫學研究者表示歡迎,如臺北榮總醫院醫師林明慧稱,回歸以病人為中心,對病人醫療權有很大進步,病人能預先規劃自己的醫療決策,保障生命最后尊嚴,這具有重要的意義。許多積極推動醫療改革的團體也都表示樂觀其成,認為此法可免去“一路救到死”的困局,也可以減少對醫病雙方造成的痛苦。
與此同時,許多醫學界人士還認為,新法有助于減少無效醫療,大幅節約社會資源。依據臺灣健保資料庫統計,臨終病人過世前一個月,53%都是無效醫療,無效醫療費占加護病房費的80%。據估算,臺灣長期依賴呼吸器的人數比率高達美國的5.8倍,葉克膜使用量更占全球總案例50%。而新法的推行,無疑可以減少無效治療,節約社會公共資源特別是醫療資源,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到更有價值的地方中去。
但也有許多醫學專業人士認為,如果完全按照“病人自主權利法”,醫生可能就會出現見死不救,甚至是放縱病人死亡的可能,這將引發更多的醫療糾紛。
為了降低醫學界的疑慮,新法專門制定了三項規定。首先,醫務工作者因專業或意愿,無法執行病人預立醫療決定時,可不施行。其次,醫務工作者依預立醫療決定執行終止治療時,無需擔負刑事與行政責任。最后,當病人與家屬意見不合時,醫師可以不受干擾,依專業執行病人意愿。
(摘自《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