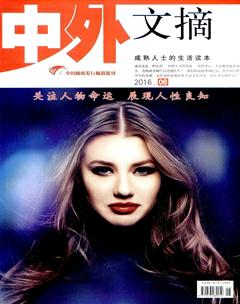一個越“脫”越貧的村莊
袁貽辰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電子地圖上,大垅村和遂川縣城13公里的距離,近得可以忽略不計。把鼠標拖住,不停點擊放大,才能看到一條彎彎扭扭的波浪線。這條2009年正式通車的水泥公路是大垅村與外界聯系的唯一通道。也正是這條5.2公里長的水泥公路,成為大垅村村民揮之不去的陰影——村里的賬單上多了一筆70萬元的欠款。
在這條水泥公路修通之前,進出大垅村的唯一通道是一條泥巴道。村民想去縣里掙點錢,只能用肩膀挑上五六十斤重的蔬菜瓜果,在長滿雜草堆滿大石子兒的泥巴路上走兩三個小時,保準“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因此,當2008年扶貧項目“村村通工程”的消息傳來時,整個村子沸騰了。
經國務院審議通過的《全國農村公路建設規劃》(以下簡稱《規劃》)中白紙黑字地寫著,“十一五”期間,中央政府投資1000億元,對通鄉(鎮)公路、通建制村公路進行路面硬化改造。依據《規劃》,大垅村通村公路項目,可按每公里10萬元得到國家補貼。當時,王建紅在縣城跑運輸生意。鄉里的領導專門找到他,鼓動這個村里的能人回村擔任黨支部書記,負責修路。
“國家有1000億的專項補貼,地方財政再配套一些,修路沒問題。”領導用力拍了拍王建紅的肩膀。后來王建紅才得知,即使領導不承諾,《規劃》中也寫得清清楚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加大對農村公路建設的財政投入”。
眼瞅著村里綠油油的油茶長勢喜人,卻根本賣不出去,王建紅動了心。他放下手頭的生意,回村當了村支書。可當這個致富能手正兒八經領著人打算大干一場時,才發現“問題大了”。他見過的幾個包工頭,給他算了筆賬:“不說水泥和沙子這些材料,光用工費一公里就得六七萬,一公里10萬元哪夠啊?”
幾個村干部一商量,決定“硬著頭皮修”,畢竟還有領導承諾的配套補貼。為解決前期資金不足,他們甚至挨家挨戶給村民做工作,向每名村民收取了50元的集資款。同時,村干部還做通了包工頭的工作:“村子畢竟是集體,即便欠了錢,不還的可能性還是比較低的,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很快,這條總長5.2公里、寬3.5米的水泥路建好了。公路修好后,不少人稱贊王建紅,為村里做了一件大好事。可他卻犯了愁,為修這條路,村里欠債70多萬元,地方財政支持總不到位。
讓王建紅頭痛的還不止此。
2010年,大垅村按照“上級要求”,實施國家扶貧項目“農村飲水安全工程”,水利部門按每人400元的標準撥付工程款。但修好蓄水池鋪設好管道,施工成本赫然變成了每人700元。工程結束,又是一筆30萬元的欠賬。此外,還有危橋改建、村小翻新等扶貧項目,也讓村委會欠了不少債。
時間一長,包工頭不干了,他們一天天催賬。王建紅及其他村干部束手無策,只得安慰前來討債的包工頭:“這是扶貧項目,上級政府一定會想辦法解決的。”“能拖一天是一天。”王建紅說。
村里的情況,王建紅再清楚不過。滿打滿算1400多畝土地,人均不過7分地。村里的集體產業“基本就是個空殼子”。唯獨村委會一樓的幾家門店,能收點租金,一年不過八九千塊錢。靠它還清債務,遙遙無期。
即使在公路修建之前的集資,也讓村干部大費周折。在這個貧困村,“能拿出50元已經很不容易了”。按規定,“農村公路建設不得增加農民負擔……不得采用強制手段向單位和個人集資”。
這些年中,王建紅也從各種文件上看到,按規定,這些扶貧項目一般都應有地方財政配套支持。可大垅村,除了中央政府的財政支持,地方財政配套遲遲不到位。為償還欠債,王建紅等村干部多次找鄉里和縣里,希望協調部分資金,償還欠款。可鄉里縣里,最終也沒給他們一個明確答復。
記者就此采訪了遂川縣交通運輸局局長黃云慶。他表示,村村通工程中,地方財政應配套部分資金,但遂川縣和鄉里的財政都比較困難,確實拿不出什么錢來。作為主管部門,交通運輸局“只能提供一些技術指導”。他還表示,修路不具有強制性,各村“應根據實際情況量力而行”。珠田鄉黨委書記在聽到記者的提問后,就以“正在談事情”為由,掛斷了電話。
即使是王建紅,現在也很難找到這些領導。倒是他,三天兩頭被包工頭堵上,追著要欠款。他已連著幾年沒給家里拿過一分錢了。為了躲年底催債的人,只有到大年三十下午,他才敢回家。
“貧困村”爭奪大戰
幾年來,王建紅都沒享受到交通便利帶來的幸福。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想方設法償還村里的債務。修好公路后3年里,原本給大垅村村干部發工資的轉移支付款項,統統都給了“催錢很緊”的施工單位。
有同樣命運的村干部經常碰頭。另一村的村支部書記的找錢方法,讓王建紅唏噓不已。
這名村干部說,縣里各個部門“手里都還是有點錢的”,對村干部來說,則要“想方設法拿到這些錢”。他周一到周五,一定會出現在縣里,“找各個部門化緣”。前幾年,他還要“陪吃陪喝”,適當的時候再哭哭窮,“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嘛”。靠著這個,這名村支書拿到了部分項目款。
這個方法,王建紅也曾試了幾次,不過收獲并不多。還有個村子,因靠近縣城,得到一筆征地款。大垅村離縣城遠,這條路堵死了。關于還債的辦法,多次被評為優秀黨員干部的王建紅認為,只有“繼續申請貧困村,依靠更多的項目來發展經濟”。他表示,越來越多的村子加入國家級、省級貧困村爭奪大戰,如果評上,還錢就有戲了。
在剛剛過去的5年,省級“十二五”貧困村大垅村,集中解決了公路、吃水、村小翻新、危橋改建等基礎設施建設問題;而之后的5年,村子必須申請上“‘十三五貧困村”,借由新的扶貧項目,來發展經濟,帶動村子致富。“我都選好了油茶種植和蜜柚種植,就等錢和技術了!”王建紅說。只可惜,他的計劃在去年戛然而止。
2014年,江西省“十三五”貧困村評選,在競爭形勢“明顯更激烈”的情況下,大垅村獲得全鄉第三名,落選貧困村。“當時氣得我都想辭職了。”這個身材有些微胖的中年男人臉漲得通紅,回憶起一年前的種種經歷,他依然“咬牙切齒”。
記者就此事向遂川縣扶貧和移民辦公室求證,其領導在聽到記者身份后隨即以開會為由掛斷了電話。留給王建紅的辦法,似乎只剩一個了。“只能繼續走人情關系,去縣里求各個部門啊。”他無奈地嘆口氣,“僧多粥少啊。”
(摘自《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