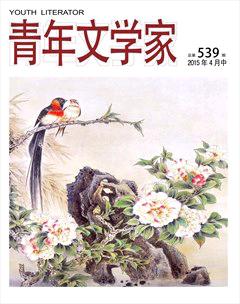論程珌詞中的酒與“遨游”之境
文慧
摘 要:程珌很多詞中都展示了酒的迷醉與遨游天地的自我想象之間的密切聯系。詞人往往借助精神上的天地遨游,抒發世俗苦悶,并從宇宙人生的思考中擺脫苦悶,使其詞在情感內蘊上兼具稼軒的沉郁與東坡的豁達,這在其晚年詞作中尤為明顯。但由于創作上對“雅”的過分追求,使其詞境雖有壯闊氣勢,卻失去了靈動暢達之感。
關鍵詞:酒;遨游;“蘇辛”;理學色彩;壯闊詞境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11-0-02
在程珌的詞作中,出現了很多表現詞人進行上天入地、穿梭遨游的精神活動。在詞中遨游天地的內容背后,程珌是如何表現和塑造這種遨游活動,以及其中包含了作者怎樣的思想意識和審美取向,可做進一步探討。
一、酒與迷醉的 “遨游”之境
在清醒狀態,程珌也有以神游之境表現贊美之意的詞作,多因應酬為之。
常見的是把詠物詞賦予游仙色彩。其茶詞《西江月》中的“歸來滿袖玉爐煙”的仙氣飄飄之境,就用遨游仙境來比擬喝茶之感,并贊美這“歲貢來從”和“天恩拜賜”之茶的高品質。湯詞《鷓鴣天》中也作“飲罷天廚碧玉觴” 來稱贊湯之美味人間鮮有,并感謝 “君恩珍重渾如許”,祝愿君主“天皇似玉皇”。把味覺體驗用遨游仙境來比擬,表現品嘗的美好體驗,通過對君主所賞之物進行贊美,表達對君主的感激;其祝壽詞中也多含神游色彩,但這是南宋文人寫祝壽詞的普遍手段。程珌的壽詞亦多如此,如《步虛詞·壽張門司》,直接給其以“仙官長守仙宮”的情境設定,描繪“群仙拍手過江東”的景象。鑒于這類詞本身具有較明顯的功用性傾向,在情感真實性上就略顯蒼白。
程珌詞中另一類遨游畫面則與應制之詞不同,是在酒精的作用下所進入的一種似夢似幻的精神狀態,這種狀態與藝術創作狀態相似。
“進入藝術構思與創作的虛靜狀態,卻與酒特別是酒帶給人的心理特征很相近,在這樣的時候,人既不受名利雜念的干擾,也沒有榮辱得失之悲,完全沉浸在那個獨屬于自我的美的快樂的境界中了。”
這種由飲酒帶來的迷幻境界在程珌的詞中多以神仙仙境和天地宇宙間的穿梭遨游來表現。詞人清醒時,或身處官場或游歷登臨,除去應酬之詞,便是表達國仇家恨的“騷人愁語”(《滿江紅·登石頭城,歸已月生》)和人生感慨,如《水調歌頭·登甘露寺多景樓望淮有感》、《喜遷鶯·別陳新恩》、《六州歌頭·送辛稼軒》和《沁園春》組詞。而當詩人獨酌之時,便盡拋下官場中的小心翼翼,得到精神上的放縱,發出“人間已夢,我獨危坐玩漫汗”的誑語,進入“駕我浮空泛景,一息過天垠”的天地遨游當中,通過酒來達到“今但入夢青山,云谿深處,煙月生懷袖。”(《酹江月》)的放曠不羈狀態。這種精神狀態的產生幾乎都是以“酒”為契機。或是在“螭殿”與蹁躚而下的仙人們“共吸酒壺干”(《水調歌頭》玉女掃天凈);或是“與君來,蜚玉佩,斬觚瓢”來“醉拍滿缸香雪,寫竭一池濃墨”,未盡興時還要“歸去續松醪”(《水調歌頭》電闋驅神駿);又或是“便折簡,浮丘共酌”(《傾杯》),這些邀仙人共飲的情形,都是詞人飲酒進入似夢非夢的狀態中時所進行的漫游想象。
究其原因,無非是酒往往能使詞人達到個體精神回歸的狀態。或是在醉意中思考人生宇宙,或是希望歸隱擺脫官場煩憂,程珌選擇把這種感情放到自我與神仙、神獸相伴,自在穿梭天地、俯瞰人間的特定情境里,使其詞在視覺上具有一定的新鮮感。
二、迷醉遨游中的多重思想內蘊
后人多把程珌歸為辛派詞人。薛礪若也說“他的詞風與蘇辛為近,但亦時有秀韻的詩句” 。雖與蘇辛風格的相近,但思想傾向上,程珌也有自己的取舍。在表達家國之痛和人生苦悶時,他多不著意渲染其苦痛,對愁緒的表現呈現出克制而隱忍的狀態,他的躊躇滿志,勃郁于心,與稼軒很像。但當面對人生命運的存在價值思考時,其詞表現出的自我寬慰和面對人生的豁達狀態,又頗具蘇軾的神韻,他晚年的詞作中尤為明顯。王國維說:“詩人對于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在程珌所構建神游詞作里,其中的情感內蘊就體現出了一種從對苦悶的隱忍到最后擺脫現實事功糾纏從達到釋然的轉變,具有了多重情感層次。
1. 官場沉浮中尋求放浪不羈的解脫
南宋內憂外患的時代背景,使文人具有高昂的衛國熱情,程珌對辛棄疾的抗金主張有強烈認同性。但同時他又與終身憤懣不得志,沉淪下僚,最后不得不歸隱卻又不曾泯滅希望的辛棄疾有很大不同。程珌一生比較得意,位至高官,是當之無愧的“廟堂詞人”,但史彌遠當權期間,如履薄冰的政治環境,讓程珌晚年屢屢請求告老還鄉。可以說,他對歸隱的向往,是明哲保身,是無心留戀。因此他的情懷比辛棄疾更像蘇軾。
歸隱后的辛棄疾在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而程珌卻是在醉酒中“想昔游依舊”,回望平生“卓筆雞籠,懸天寶蓋,占斷宣徽秀”(《醉蓬萊·丙申自壽》)看似得意,不如“來歲清苕,公家事了,斑衣藍授”就此辭官隱退,遠離宦海沉浮。與蘇軾那份 “且陶陶,樂盡天真。幾時歸去,作個閑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云”(《行香子》)的灑脫頗為相近。
但程珌又很少像蘇軾那樣坦率,他常把感情放在漫游天地的幻想情境下含蓄表達。如《傾杯》中,詞人在“千門人靜”之時孤飲獨酌,幻想“碧云飛下雙鸞影”“迤邐笙歌近笑語”“群仙隱隱”的場面,邀群仙共酌,但“奈天也,未教酩酊。來歲卻笑群仙,月寒宮冷”。都說羨慕仙人生活,奈何仙宮中也不自由,連一醉方休的機會都沒有,詞人不禁也嘲笑仙人,得道升仙也罷,長生不老也罷,最終還是不能放縱而為。雖只字不提詞人情緒,但隱藏在情境里的那種掙脫束縛的渴望,仍不動聲色地流露出來。
《酹江月·丙子自壽》就更像是他思想傾向轉變的縮影,詞開頭憂愁自己不能成為英雄豪杰留名千古,發出“蹉跎歲晚,臨風浩然搔首”的感慨,這與辛棄疾的那種渴望建功立業保家衛國收復失地,但無奈身已老的沉郁之氣如出一轍。而一旦拿起酒杯,酣暢自飲,醉意中“入夢青山,云谿深處,煙月生懷袖”在神游之境中與“坡公”“仇池有約”后,又被東坡深深感染,對世外桃源式的無拘無束產生了深切向往。這里仍然用了酒醉神游的場景設定來揭示其中所隱藏的思想變化,表現出雖也曾渴望建功立業,但無奈歲月不待,身心俱疲,再也不愿被塵世生活所羈絆的態度。
2. 生命短暫的慨嘆中蘊含人生的豁達態度
程珌所受的理學教育,使其這類帶有神游色彩的詞作,不僅包含文人士大夫精神上所共有的老莊精神,更包含著理學的思辨性特征。
他經常抒發“人生易老何哉”(《柳梢香·和齊仙留春》)“千年一息,誰稱彭壽”(《醉蓬萊·丙申自壽》)的感慨。雖感嘆生命易逝,其對生死的態度卻是平靜的,認為來去無非自然。在《滿庭芳·戊戌自壽》中就談到“如今,當此去,十分親切,面問嬋娟。何須看仙槎,海上重還”,不必再年年盼仙槎載自己去仙境一游,“好在金英玉屑, 為我,滿泛金船”,在有美酒相伴的醉意之中得見嬋娟,問上幾句,就是人生的愜意。
他有時也隨性對待人生,“都莫問,鴻鐘勒。也休羨,壺天謫”,平生好“騎鯨游汗漫”,也知道“古來蟾影何曾沒”,所以總有機會能“重約再來時,乘槎客”(《滿江紅·龔撫干示閏中秋》),表現出順應人生造化、自然無為的特點。詞人常做可以隨意穿梭仙界人間的自我設定,在《念奴嬌·憶先廬春山之勝》提到“歸來一笑,尚看看趁得,人間寒食”,一個“趁得”表示出年歲已大,對生命逝去“天教斷送流年,三之一矣”的感嘆,隱含著落寞情緒,但詞人又往往能寬慰自己,表現出“這回歸去,松風深處橫笛”這種對生命不做干預的豁達狀態。
辛棄疾也寫過類似帶有游仙色彩的詞作,如他的《千年調》和《西江月·木犀》就是寫天界遨游。盡管兩人描繪的遨游景象相似,但從深層次的情感內蘊上看,程珌與辛棄疾是有不同的。辛棄疾即使寫仙氣渺渺的景象,也終難脫離現世憂患與自我苦悶,像是喧囂過后,難以釋懷的惆悵就又涌上心頭,產生一種企圖掩蓋傷口卻得不到解脫的憂郁美,陳廷焯認為稼軒“氣魄極雄大,意境卻極沉鬱” 周濟也說“稼軒鬱勃,故情深” 。相比之下,程珌詞中則超出現實事功,流露出對生命存在的思考,在暢游過程中,追尋人生真理,擺脫苦悶情緒,更具有蘇軾的豁達。
三、氣勢洪邁、壯闊蒼涼的遨游之境
程珌詞在描繪仙境遨游時,多營造蒼涼壯闊的環境氛圍。
他在詞中常用數詞的對舉,如“三島眠龍驚覺,萬頃明瓊碾破”(《水調歌頭》玉女掃天凈),“借我萬斛沸銀濤”“寫竭一池濃墨” (《水調歌頭》電闋驅神駿),“一勺流觴何有,萬石橫缸如注”,“蓬萊萬疊忽蜚來,上有千燈照”(《燭影搖紅》);或是運用冷色調來創造寒冷堅硬之感,如“涼月照東南”、“碧氣正吞吐”、“風露五更寒”(《水調歌頭》玉女掃天凈),“燕子春寒渾未到”、“玉樹薰香”、“冰桃翻浪”(《念奴嬌·憶先廬春山之勝》),“更積靄沉陰”、“月寒空冷”(《傾杯》);在詞中也注重煉字, “木鳴山裂盛夏”、“急上瑤庭深處”、“虹氣飲溪干”、“寫竭一池濃墨”(《水調歌頭》電闋驅神駿);當然,仙境的創造離不開道教神話意象的運用。總之,通過這些手法創造出了整體構造宏大又略顯蒼涼的遨游環境氛圍。
但從審美體驗上看,遨游的暢快之感,常被很多晦澀的詞語典故所阻塞,失去了靈動輕巧,變成略顯艱澀的“遨游”。多敘述的語言又淡化了仙境的形象性,代入感不強。確與稼軒有差距,陳廷焯早已說過:“大抵稼軒一體,后人不易學步。無稼軒才力,無稼軒胸襟,又不處稼軒境地,欲于粗莽中見沉郁,其可得乎?”,王國維也說:“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捧心也。”,程珌這類詞作自然不至東施捧心之地,但學到蘇辛精髓又能自具風格,其中之難早已是詞家公認。
相比于其他辛派詞人對詞的“雅化”追求,程珌用理學思想來雅化詞體是其重要手段。在程珌的仙境之旅中,不涉及任何男女之情,既沒有對神女執著追求的情感苦悶,也沒有牛郎織女的遙遙難會,亦沒有嫦娥在月宮中的孤寂凄涼。他在情感表達上顯露出理學思想帶來的弊端,過于克制而真摯不足,達不到稼軒那般隱忍沉郁,又沒有蘇軾灑脫得徹底自由,始終處于一種束縛的創作狀態中。
總的來說,程珌用穿梭天地、遨游仙境、俯瞰人間的隨意視角,加之豪健的手筆,表現出在酒的迷醉中超脫世俗苦悶思考宇宙人生的雅正內容,呈現出一種清醒與迷幻交織的遨游境界。”
參考文獻:
[1]《中國通史》第七卷,白壽彝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2]《宋代文化史》,姚瀛艇主編,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3]《宋代文學史(下)》,孫望、常國武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
[4]《宋詞二十講》,夏承燾、王易等著,彭國忠選編,華夏出版社,2009年版。
[5]《蘇軾傳》,王水照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