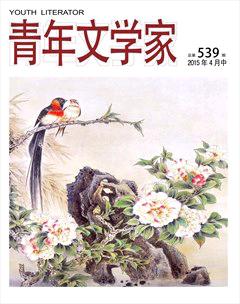納蘭性德是“水做的骨肉”
張穎
摘 要:納蘭性德作為清代最有影響力的詞人,以其自身的遭際與作品相互交融,共同構成文壇上奪目的一筆。一生與水為鄰,詞集以水為名,而作品中處處可見“水”的影蹤;其情綿長深重,哀婉惆悵,生就了似水的柔;而詞人本身更是將傳統文化中的“水德”作為踐行的標準,從“形”到“骨”再到“德”,成就了其“水做的骨肉”。
關鍵詞:納蘭詞;形;骨;德;水做的骨肉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11-0-02
水,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被賦予了生命的哲學載體。上善若水,是君子對自身道德修養的崇高追求,孔子言“水有九德”。而曹雪芹也借寶玉之口道,女子是水做的骨肉,讓人清爽。納蘭性德,是文壇的感傷符號,其短暫的一生為世人奉獻了一本極為厚重的令人不忍卒讀的《納蘭詞》。
一、水之形——納蘭詞中獨特的“水”意象
“納蘭性德把屬于自己的別業命名為“淥水亭”,并把自己的著作也題為《淥水亭雜識》。詞人取流水清澈、澹泊、涵遠之意,以水為友、以水為伴,就在他辭世之時,也沒離開他的淥水亭。”水是其觀照自然,體悟內心后所由衷地生發出的選擇。詞作中處處可見“水”的影蹤,“一片月明如水”(《酒泉子》)“云澹澹,水悠悠”(《酒泉子》“水月影俱沈”(《水調歌頭》)“水浴涼蟾風入袂”(《天仙子 淥水亭秋夜》),而“雨”,“淚”更是其所有意象中極為高頻的兩個,這二者無疑是內心所凝結之“水”的幻化。
納蘭詞中的“水”,乃至經常出現的雨、淚,都是引發其感傷、宣泄其哀情的閘口。以“水”為緣起,便開啟了愁緒的源頭,以“苦雨”做線索,便承續了滿腔的哀傷,以“淚”為宣泄,便觸發了內心交雜的苦楚、無奈。
如《東風齊著力》一詞:
電急流光, 天生薄命, 有淚如潮。勉為歡謔, 到底總無聊。欲譜頻年離恨, 言已盡、恨未曾消、憑誰把、一天愁緒, 按出瓊簫。
往事水迢迢。窗前月, 幾番空照魂銷。舊歡新夢, 雁齒小紅橋。最是燒燈時候, 宜春髻、酒暖蒲萄。凄涼煞、五枝青玉, 風雨飄飄。
“往事水迢迢”,與妻子的恩愛光景似在眼前,一幕幕琴瑟和鳴,歲月靜好的場景浮現,納蘭與妻子盧氏伉儷情深,可妻子卻在婚后三年因難產而死,此后兩人天人永隔,納蘭用情至深以至于“情在不能醒”,每每念及亡妻便泣淚傷心;此刻“風雨飄飄”,都在將癡人的好夢喚醒,訴不盡離恨萬千,物是人非,一時間,人命涼薄又或是緣淺情重,都難分辨,唯有兩行清淚似潮涌出。納蘭即情思,情思即苦雨、清淚,苦雨清淚盡是塑就其生命的那一汪深重的水。
用情至深,也最終讓他泣盡了自己最后的生命, 絳珠仙子曾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無此水可還。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償還得過他了。”大凡有這樣性情的人,這樣細膩的心思,或許都和水有著難分難解的緣分。
二、水之骨——對生命、自然的珍愛與柔情
納蘭性德以其純潔的性靈觀照自然和社會,如一汪純凈的天水,不僅潤澤著他詞中的愛人摯友,甚至塞北江南、一花一木,也都被他賦予了別樣的柔情。
歷來都言納蘭對人生,對外物懷著深深的悲愴之感,以至于滿眼看去皆是一片悲愴之景。而在這背后,到底是什么致使了他這種獨特的風格,前人的論述從詞人的家世背景,天資秉性,后天經歷等方面分析,可稱完備。但是,最重要的應該是他有“水”那自由、純潔,潤澤萬物的秉性,太過熱愛生命,太過純粹和執著地對待生命這個歷程,而這一強烈的有別于他人的對個體存在感的訴求致使他眼中萬物皆有情,都有生命,而這生命又都等同于自己。
當作為一個獨立個體所應追求的親情、愛情和個人理想一一幻滅后,他對生命的反觀也更為深刻了些。不得不說,在這一點上,他也超越了他所生存的時代。
《臨江仙· 寒柳》一詞是他的一首詠物詞,他對生命的感懷和珍重,從中也可窺得一二:
飛絮飛花何處是,層冰積雪摧殘, 疏疏一樹五更寒, 愛他明月好, 憔悴也相關。最是繁絲搖落后, 轉教人憶春山。裙夢斷續應難, 西風多少恨, 吹不散眉彎。
孱弱凄婉的寒柳,身體遭受著冰雪的寸寸打壓,憔悴地迎風獨立,想到那一身的青翠驟然退去,怎能不教人憐憫惋惜,念及那逝去的春天,逝者如斯乎?納蘭所尋的“春”,亦如斯乎?是了,此時的柳便是冰雪壓身的納蘭,他對那“搖落繁絲”的憐惜與嘆惋怎會不傾注全心的熱愛,逝去的當永不復返,而這深深的悲惋和惆悵也不會消散。此時實在該有“柳袋”贈與納蘭,好同黛玉的“葬花囊”一同埋了,雖說納蘭的惜物愛物之情遠不及黛玉的執拗和純粹,可“西風多少恨,吹不散眉彎”置于古今男子行列中,亦可算是極致了,所以,黛玉也似乎理所應當是純粹了的“納蘭”了。
寫物生情,一花一木接有情,而當其筆尖所及的是塞外的雄渾壯闊時,其柔情又將做何處置呢?試看其《浣溪沙》:
冷露無聲夜欲闌, 棲鴉不定朔風寒,生憎畫鼓樓頭急, 不放征人夢里還。秋澹澹,月彎彎,無人起向月中看。明朝匹馬相思處, 如隔千山與萬山。
“冷露”、“棲鴉”、“朔風”、“征人”、“秋月”、“千山”這些意象在邊塞詩里面是尋常的,稍一串聯便是一幅廣袤、雄渾、慷慨悲壯之景,但是詞人把節奏放了下來,讓朔風不再只是掀起大漠的威嚴,而是凝固漫長的寒夜,“畫鼓”可惡,不是因為敲響殺戮,而是牽絆住夢中幻歸的離人,“秋澹澹”似閨閣外寧靜安謐的尋常秋夜,“月彎彎”多了些柔美在輕吟呼喚,奈何竟無人舉頭相望,此時有惆悵生,卻不是為大漠曠野,而是內心無盡的柔情,“相思”便是攻破塞外苦寒和險遠的最柔軟的傷口。正因心中從未放下柔情與愛意,正因對生命太多珍重與寄予,所以他的“征人”比“春閨夢里人”中的“征人”更加沉重,他們應是自由享受生命的主人,而不是被戰爭圈禁的征伐工具。他把邊塞賦予柔情,把平等的關懷賦予與他一樣的征人,又把惆悵留給自己化解。
正如一灣清泉淌過冷峻無聲的大山,當柔軟觸碰剛硬時,他激發出的是別樣的剛柔相合之美,讓他的柔情安放至一個更加無限廣闊的空間,也讓他秉性中似“水”般的“潤澤、柔軟一切”的獨特骨骼得以展現。
三、水之德——志存高遠,不為世濁;平生所交,芝蘭之士
納蘭從小深受儒家文化的滋養,當經年累月的含英咀華之后,已然是一位文質彬彬的儒家君子風貌。而其修養與品性的標準,均是儒家所推崇的德行。納蘭身上便承載著這樣的“水德”,“雖“身在高門廣廈,常有山澤魚鳥之思”。對仕途生活的厭倦,對富貴的輕看,對名利的不屑,使他對凡能輕取的身外之物無心一顧,但對求之卻不能長久的愛情,對心與境合的自然和諧狀態,他卻流連向往。”,“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這便是其可貴之處。
納蘭性德在年少時也立志踐行儒家入世思想,懷著滿腔政治熱情和高度社會責任感、有著遠大抱負和卓越見識。他在《金縷曲》一詞中這樣寫道:“未得長無謂!競須將、銀河親挽,普天一洗。麟閣才教留粉本,大笑拂衣歸矣。”詞中洋溢著書生豪氣和少年壯志,表明了他渴望為國家、民族建功立業的宏偉志向。為男兒壯志“赴百仞之谷不疑”,何其勇哉? 但是皇帝卻全然不顧納蘭的才識和宏愿,僅憑自己興致的“天子用嘉”,讓納蘭充當了殿前侍衛。日日走在與理想向左的道路上,眼見的是官場上黑暗險惡,勢利與污濁,納蘭開始反思青年時期那種追求功名利祿的種種,渴望尋求靈魂的安棲之所,并用沖淡的調子來表現他對人生的淡泊態度,“吾本落拓人,無為自拘束,倜儻寄天地,樊籠非所欲”(《擬古四十首之三十九》),“人生若草露,營營苦奔走;為問身后名,何如一杯酒”(《擬古四十首之二十五》),面對理想時義無反顧的“勇”是可貴,可當現實與自身高遠的志向沖突后,這種心靈上的“折返”更是可貴,身在泥淖卻志存高潔,更是實在難得。
孔子云:“欲識其人,先觀其友”。性德為友“在貴不驕, 處富能貧。”納蘭性德一生中結交了很多的朋友, 感情也比較深厚, 而他與顧貞觀(號梁汾)的友情為最深, 以至有“后身緣, 恐結他生里”的愿望。《金縷曲·淚盡無端淚》一詞便表現了他對朋友的深情和懷念之意:
“酒盡無端淚, 莫因他, 瓊樓寂寞, 誤來人世。信道癡兒多厚福, 誰遣偏生明慧。莫更著, 浮名相累。仕宦何妨如斷梗, 只那將、聲影供群吠。無欲問, 且休矣。
情深我自判憔悴。轉丁寧、香憐易苠苠熱 , 玉憐輕碎。羨殺軟紅塵里客, 一味醉生夢死。歌與哭、任猜何意。絕塞生還吳季子, 算眼前、此外皆閑事。知我者, 梁汾耳。”
上片勸好友貞觀不要為漢槎之事而積憤難平。漢槎之遭遇雖可哀, 造成這種遭遇的現實更是可嘆。接下來開始了對貞觀的叮囑, 望其達觀自愛, 且表現出自己抑郁的心情。這里既有對知己的懷念和牽掛。初見好友,便如故人,其身份相差懸殊,但志趣相投,這首詞直抒胸臆,讀來親切自然,儼然是老友間推心置腹之語。這樣一位滿清貴胄,在初見友人之時便心無芥蒂,幾番囑咐之后,反讓人更覺親切難得。這位顧貞觀,果然成了納蘭一生的摯友,恐怕所有與他較好的漢家文人都被他這種難得的赤誠和坦蕩所打動。在他去世后,他的座師徐乾學之弟徐元文在《挽詩》中贊美道:“子之親師, 服善不倦。子之求友, 照古有爛。寒暑則移, 金石無變。非俗是循, 翳翳糸義士戀。”擔此聲名,納蘭當仁不讓。
納蘭詞處處以“真”貫連,真情、真感、真我。其志趣真純高遠,其待友真摯坦蕩,其為人真誠,善存真我,不雕飾分毫。無怪乎王國維以“北宋以來,一人而已”評價納蘭詞,所推祟的也就是這種“真切”,他將內心情感全部傾注到作品中去。
縱觀納蘭為人,品讀納蘭詩詞,可知“納蘭詞”作為清代一種獨特的文學現象的可貴之處。這樣一位“泥做的”男子,身上沒有半點的“濁臭逼人”之感,反而讓人讀來處處清爽。無論是“水之形”—其詞中大量的“水”意象,還是“水之骨”—其與生俱來的柔情似水,又或是“水之德”—其后天修養的君子品性,高遠志趣,都在支撐起一個形神兼備,德性雙修的“水做的骨肉”。人說他是寶玉的原型,可是,他更該是黛玉的原型,有父母在側,卻與其漸行漸遠,志趣難投,可比黛玉的失怙;終生癡戀一人,為情泣盡一生的清淚,值壯年而仙逝,可比絳珠的泣淚還情;才情秉性,“北宋以來,一人而已”,可比黛玉的超群;托生于帝王側,終身不得自由,可比寄人籬下,欲訴無門的瀟湘妃子;詞風凄涼悲愴,讓人不忍卒讀,便如黛玉的泣血低吟,多愁善感。或許“多情公子”與“世外仙姝”本就一人,只不過一個是困在泥淖中時時散發濁臭的貴胄之軀,一個是養在性靈深處只得與水、荷相伴的仙姝之體,一個困在封建家長和禮教制度之下與命途軌跡“舉案齊眉”,另一個早已飛往念念不忘的至真至純的世外桃源。故而,就其本性,納蘭性德是“水做的骨肉”。
參考文獻:
[1](清)納蘭性德,張草紉(導讀)著:納蘭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
[2]劉德鴻.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3]楊男.論納蘭容若的個性氣質對其詞的影響[J].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