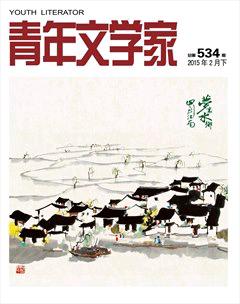顯性革命敘事下的啟蒙意識
盧佳敏
丁玲初到解放區延安時政治意識非常活躍,她懷著對革命對中國共產黨的熱愛積極投身于革命事業和文學創作。但是不久之后,丁玲也發現了革命體制內存在的等級秩序與性別觀念對女性的壓制,慣性的女性意識開始發揮作用,且這一時期的女性意識已從早期莎菲般情緒化的表達沉淀成了理性的思索。于是革命意識與女性啟蒙意識在她心中激烈的博弈著,小說《在醫院中》就是創作于這樣的背景之下。《在醫院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年輕的助產醫生陸萍懷揣著革命的激情來到延安邊區醫院,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投入到醫院的工作當中,但卻屢屢遭受到現實的打擊,到最后選擇離開邊區醫院去繼續學習。在小說《在醫院中》的人物身份設定中,丁玲將小說的主人公陸萍設計成一個剛加入共產黨不久的滿腹革命斗志的女知識分子,對陸萍的身體書寫集中于身體外化的最明顯標志——服飾的描寫,并對安置陸萍身體的地理環境和社會環境也做了詳細的描繪。除此之外,丁玲借由陸萍的視線,對于邊區醫院中的各色人物的生存境遇,特別是婦女在婚姻、自我身份定位問題上給予書寫關注。
(一)服飾與性格——彰顯革命意識
小說一開始在陸萍進入邊區醫院的路上便對她的外貌服飾進行描繪,“那天,正是這個時候,一個穿灰色棉軍服的年輕女子……這女子的身段很靈巧,穿著男子的衣服。”在人類的進化歷程中,男性與女性在外貌形體特征上均存在諸多差異,這也就決定了男性和女性在服飾上的眾多不同。五四時期,許地山曾提出要求女性服飾與男性服飾趨于同化的觀點,目的是減少性別上的差異,他認為女性服飾應該“第一,符合事理;第二,易于操作;第三,不引發欲望。”五四時期出現這樣的觀點,目的是出于提倡男女平等的需要,這在當時只是停留在想象的層面上,并沒有得到完全實行,在解放區延安,革命女性的服裝男性化得到了徹底的普及。服飾在人類文明的不斷發展當中,早已不在充當簡單的遮羞御寒之物,而是一種文化價值的符號,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有著具體的文化指稱,比如黃色的衣物在古代是歷代君王的專屬,象征著等級的高貴。在解放區延安,軍裝是革命工作者穿在身體上的第二個名字,是一個革命工作者身份的顯性標志,在當時的革命工作者看來,服飾的改造代表著一種人生觀價值觀的改造,衣著光鮮必定是小資產階級腐化墮落的典型,唯有艱苦樸素才是無產階級革命者的作風。于是解放區的革命女性唯恐被冠上思想落后的帽子,紛紛學習革命男性的作風,改變自己的女性服飾,以響應解放區延安當時提出的革命隊伍中男女平等的口號,小說中的陸萍便是這其中的一員。丁玲從服飾的書寫上便在陸萍的身體上打上了鮮明的革命的烙印,同時,在陸萍披著革命外衣的身體上還生長著丁玲心中理想的革命者該有的品格:服從黨的指揮,陸萍放棄了自己熱愛的文學而服從組織的安排學習醫學;艱苦奮斗,陸萍在設備簡陋的邊區醫院仍然不忘提升自己的專業知識素養;熱情關心人民群眾,陸萍在醫院中不斷為病人去要求更好的醫療條件。通過小說中陸萍的服飾和性格的書寫,我們不難看出,這一時期的丁玲正不斷用創作來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場,不斷向延安的主流革命意識形態靠攏。
(二)外貌與婚姻——提醒啟蒙
如前文所述,小說《在醫院中》是以陸萍在邊區醫院的經歷為核心線索,借由陸萍的視角來打量邊區醫院的人物風貌。如果說陸萍的身份與性格品質是丁玲延安時期活躍的政治革命意識的體現,那么陸萍視角里延安婦女對于自身、對于婚姻的定位則是丁玲慣性的女性啟蒙意識的再現。到達醫院后,陸萍首先看到的女性形象是這樣的,“她一頭剪短了的頭發亂蓬得像個孵蛋的母雞,從那頭雜亂得像茅草的發中,露出一塊破布片似得蒼白的臉,和兩個大而無神的眼睛。”這是邊區醫院最普通的婦女形象,雖然丁玲只描繪了兩個,但卻倒映出千千萬萬中國舊婦女的影子。丁玲形容兩個除草的婦女的頭發“亂蓬得像個孵蛋的母雞”極富象征意味,聯系這些婦女剛見到陸萍時便理所應當地認為她是來生孩子的情景便可見一斑。這樣的身體外貌書寫向我們傳達了丁玲對于女性命運一如既往的關切,雖然身處解放區,但女性并未得到完全的解放與啟蒙,婦女對于自己的認識還是局限于為丈夫生育后代,這樣作為男性附庸存在的自我身份定位已經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而存在著。即便是醫院中那些醫生、處長的妻子,她們也缺少真正的覺悟,無法走向獨立,她們整日惶恐著自己的婚姻,提防著從外面來的女學生,不斷以“假”工作來讓自己顯得進步。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女性對于婚姻的態度體現著女性對于自我身體控制權的態度,這些婦女心甘情愿地在婚姻中處于從屬被動的地位,并且費盡心機的去維持這種不平等的婚姻關系,表明她們根本無意要爭取對于自我身體的掌控權,或者說處于麻木愚昧的混沌狀態。丁玲對于這些婦女外貌與婚姻的書寫表現出潛在的女性話語立場,暗含著女性主義的視角來關懷和審視女性個體,提醒女性的自我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