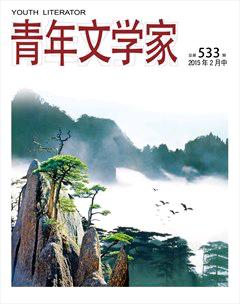出走與皈依
楊惠婷
摘 ?要:90年代后期至今,西藏寫作經(jīng)久不衰。期間,出現(xiàn)許多優(yōu)秀作品,不僅為我們展現(xiàn)了西藏獨(dú)特的自然風(fēng)光,同時(shí)書寫西藏的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化價(jià)值值得我們研究。《日月》是安意如第一部關(guān)于西藏題材的作品,作者為作品預(yù)設(shè)了一個(gè)出走與皈依的主題,同時(shí)作品中所包含的文化價(jià)值,人生哲思仍然值得關(guān)注。
關(guān)鍵詞:西藏文化;出走;皈依
[中圖分類號(hào)]:I2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2139(2015)-05-0-01
西藏,離天最近的地方。純凈,如一位蒙著薄薄面紗的少女,曼妙的身姿,凝雪的肌膚,款款走來,勾起人們無限遐思與意趣。從喧鬧的都市出走,帶著逃離與皈依的性質(zhì),越來越多的人奔向西藏。他們渴望一睹雪域的風(fēng)光,尋求佛光的洗禮。無論老幼,不分信仰,西藏都以極大的包容力,給予來人澄明的內(nèi)心和深切的皈依之感。
伴著旅者紛繁的腳步,近些年書寫西藏的作品激增。像范穩(wěn)的《水乳大地》《悲憫大地》,謝旺霖的《轉(zhuǎn)山》,程怡的《西藏,遙遠(yuǎn)的眼神》等等。這些作品,或展現(xiàn)佛教文化,或書寫藏地風(fēng)情,包含作家個(gè)人游歷西藏的一時(shí)所感,從不同角度瞥見西藏一角。與這些作品相比,安意如的《日月》雖沒有走出情愛的俗套,但卻絕非落俗的癡纏。安意如傾力塑造了“尹長(zhǎng)生”這一角色,作家意欲將他塑造成現(xiàn)世的倉央嘉措,他來詮釋虔誠的信仰對(duì)于現(xiàn)世人們的精神意義與價(jià)值。
《日月》之中,人人懷有“癡念”。長(zhǎng)生癡于聰慧隱忍的尹蓮,尹蓮癡于未被世俗沾染的謝江南(長(zhǎng)生),縵華癡于如宿命般相遇的修道者(長(zhǎng)生),Sam癡于可以把持內(nèi)心的另一個(gè)自己(長(zhǎng)生)。但統(tǒng)歸一處,他們共同癡戀的實(shí)則是至真至純的人心。但一切癡戀必將落空,生性的純潔真摯必將隨年月歸去,回歸那只屬于它的凈土。都市的喧囂,萬難留住人性的純良,真摯清澈充滿靈性的雙眼似乎只屬于西藏這片神秘曠遠(yuǎn)的土地。真正的愛情,也絕非俗世萬種,而是那心靈的默契。行走于西藏,蒼茫絕美的山河,無需山盟海誓蜜語甜言,只需默契和共同的信念。自是深入內(nèi)心的旅程,是尋覓濁世盡頭的永恒光明,共求超越,日月同輝方得圓滿。
在眾多的西藏書寫中,《日月》出彩于作者將自己關(guān)于人生的哲思,關(guān)于藏文化的講述,融于緩緩流淌著的詩化語言當(dāng)中。鉆研藏族文化的作家范穩(wěn)這樣定義一本關(guān)于西藏的小說的價(jià)值:“小說家要做西藏的導(dǎo)游,也有扮演宗教文化之旅的導(dǎo)游。”小說《日月》用藏區(qū)與都市雙線書寫的方式,不僅呈現(xiàn)了一幅曠遠(yuǎn)的藏地美景,一首心靈契合的唯美情詩,同時(shí)呈現(xiàn)了文化的西藏。這不同于背包客用雙腳丈量土地,記錄點(diǎn)滴感悟與觸動(dòng)。作者更是用心靈,用信仰,用虔誠的敬畏之心仰觀遠(yuǎn)脈的雪山,親吻圣潔的大地。神秘的宗教傳說,教派的紛爭(zhēng),宗教的思想流于字里行間。都市文明與藏區(qū)純樸的原始文化的碰撞也多有呈現(xiàn)。對(duì)于北京的書寫,充斥著誘惑和欺騙,背叛與出賣,唯利是圖逢場(chǎng)作戲。回歸藏區(qū),山水人性一切都變得唯美,人人似乎都找到了信仰的支撐。在現(xiàn)代都市,總是人潮涌動(dòng),誘惑不斷,人便顯得浮躁,拜金,失去了對(duì)于信仰,對(duì)于原始人性的追隨與敬畏。而人處西藏,獨(dú)自穿行于高山峽谷之間,許多突發(fā)狀況都將超出個(gè)體所能掌控的范圍,人似乎自然而然的相信了神明,祈求神明的庇護(hù)。藏族地區(qū)的人們對(duì)于神明的敬畏程度不身臨其境似乎不能真正理解。云南梅里雪山海拔六七百四十米是西藏八大神山之一,至今未被人類征服。1991年的登山行動(dòng)還造成17人遇難。當(dāng)時(shí)登山者上山,當(dāng)?shù)氐牟孛窈屠镌谏较缕矶\登山者不要登到頂峰。因?yàn)樵诓孛窨磥恚祟惖牡巧叫袨槭菍?duì)神山的破壞對(duì)神明的極大不敬,將受到神明的懲罰。這有悖于城市文明不斷尋求的征服的快感。作品中,8歲的長(zhǎng)生不習(xí)慣于城市孩子的油滑散漫,不忍于孩子們常玩的逮蜻蜓,打青蟲,捉麻雀的游戲。小小的孩子,對(duì)于自然的敬畏之心已經(jīng)形成,反觀一味趨利的都市人們,不免羞愧。
自從《藏地密碼》占領(lǐng)圖書銷售排行榜頭名,近幾年,西藏題材的文學(xué)作品就一直受到讀者的追捧。《日月》雖使安意如收獲了不錯(cuò)的口碑,但與年齡稍長(zhǎng)的文學(xué)大家相比還有一定差距。最大的問題在于個(gè)人經(jīng)驗(yàn)的局限。作者意欲體現(xiàn)出走與皈依的主題,但仍糾纏于平凡的個(gè)人成長(zhǎng)和愛情牽絆之中難以突圍。平淡的書寫方向的把握,難出真正驚艷的作品。“我將騎著我夢(mèng)中的那只憂傷的豹子,冬天去人間大愛中取暖,夏天去佛法中乘涼。”倉央嘉措的這句詩在作品中多次被提及,這也正是作品的總體敘事脈絡(luò)。幼時(shí)離鄉(xiāng)到大愛中取暖,長(zhǎng)成歸來,領(lǐng)會(huì)佛法精神。宏大的立意,作者并沒有很好駕馭,如若再有一次書寫西藏的機(jī)會(huì),有更加深厚的閱歷積累,或許會(huì)有更加超脫的作品,真正配得起西藏這一神圣的土地。
參考文獻(xiàn):
[1]《日月》 安意如著 湖南文藝出版社 2012年第一版.
[2]《聆聽大家之素材本》 傅光明主編 安徽文藝出版社 2009年第一版.
[3]《記憶拉薩》 戴京著時(shí)事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