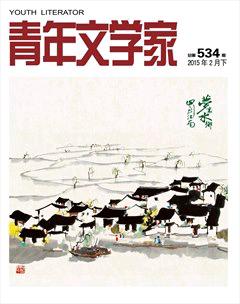感君身世太飄零
石甜甜
摘 要:陸機是西晉著名文士,鐘嶸尊之為“太康之英”,但他的一生卻是在夾縫中艱難求存的一生。在身份上,陸機兼具身事新朝之亡國遺孑和北上中原之江東舊族的雙重矛盾性,這造成了他命運的悲劇走向。即使如此,作為過渡時期的關鍵人物,評寫雙修的陸機仍不失為一代文學之大家。
關鍵詞:陸機;身份;夾縫;《樂府十七首》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06-0-02
引言
公元280年,東吳滅亡,西晉一統天下,結束了漢末以來三國割據的局面。 同年四月,改元太康。太康十年是西晉一朝難得的國泰民安的好時段,在這期間,涌現出一大批詩人,鍾嶸說:“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沐,亦文章之中興也。”①當時文壇的風貌可見一斑,諸人中,鍾嶸對陸機的評價最高:陸機為太康之英。但反觀西晉卻并不是一個文章盛世,“讀西晉人之作,總有一種平庸的感覺,也總括不出一個具有明確特征的詞語來形容他的特點。”②羅宗強的話并不是一家之言,連一向提倡“弱德之美”的葉嘉瑩也認為西晉缺乏優秀的詩人,并深入分析了個中情由,她說:“太康這一時期之所以出類拔萃的詩人極少,是與當時的這些詩人缺乏較強的性格與較高的品格不無關系的,他們大多都被名利祿位所拘囿,很少有人能站出來堅持正義和品節。”③
那么,在整體平庸的情況下,太康之英陸機是如何“木秀于林”的呢?其“寒風掃高木”的結局是意外還是意料之中?本文擬以陸機頗具代表性的詩作《樂府十七首》為文本,結合相關史實,從身份上深入分析陸機書劍飄零夾縫求存的一生,以期能解答上述問題。
正文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抗卒,領父兵為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至太康末,與弟云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薦之諸公。”④史書中短短幾句話揭示出陸機江東世家的身世、亡國遺孑的身份,以及初入中原時的情形。從相關記載來看,由于張華的看重,名實相副的陸機初入洛時頗得稱譽,一切看上去似乎都很和諧,但不和諧的因素也在潛滋暗長。如《世說新語·方正》所載:
盧志于眾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盧毓、盧挺。”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于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魏晉時人極重家諱,晉元帝司馬睿不小心言及賀循父親賀劭的慘烈舊事,也“元皇愧慚,三日不出”⑤,何況他人。江東雖長期割據一方,但陸機所謂“我父祖名播海內”也絕非大言炎炎,盧志之言確實帶有挑釁的嫌疑。深入思考,我們可以推測一下盧志挑釁的到底是什么,想來不過是亡國遺孑這一點。由此,陸機身份的第一重矛盾出現了:一方面他是東吳的舊臣,另一方面,由于被征召,他又需要身事新朝。他處在了新舊政權交替的夾縫中。這當中的諸般苦處,可以從他“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猛虎行》)、“天道夷且簡,人道崄而難”(《君子行》)、“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懼”(《君子行》)等感慨中表現出來。
此外,陸機身份還具有第二重矛盾:中原士族與江東士族的矛盾。這種矛盾源于隔閡,不僅涉及心理、社會、風俗諸方面,還涉及文藝,就連書法,也有“陸機書,吳士書也”的區分。學術方面,唐長孺根據江東流行的《易》學與“天體論”,得出了江東學風比中原相對保守的特征,他說:“吳亡之后,名士企慕中原,于是玄學以及其他風俗習慣亦傳入江南,但仍未深入,所以入洛文士在十年之后仍然沒有能以此見長。所以我們的結論是魏晉期間的江南學風是比較保守的。”⑥由于竹林風氣的浸染,中原玄風漸熾,但山川相隔,間關千里,即使到了陸機的時代,江左依然走著今文經學的路子,文士大多“服膺儒術”。不僅吳姓士族如此,會稽士族更甚,如虞預,“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發,所以胡虜遍于中國,以為過衰周之時。”⑦簡直是視玄學風尚為洪水猛獸了。
關于陸機與玄學,劉敬叔《異苑》有這樣一條記載:
晉清河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郾師。時久結陰,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神姿端達,置易投壺,與機言論,妙得玄微。機心服其能,無以酹抗。乃提緯古今,總驗名實,此年少不甚欣解。既曉便去,稅驂逆旅,問逆旅嫗,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冢爾。”機乃怪悵,還睇昨路,空野霾云,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
一說故事的主人公是陸云。但不管是陸機還是陸云,我們從這則故事讀到的都是江東本無玄學。所以當二陸入洛時,學術上的隔閡凸顯出來,當他們為消除這種隔閡而微染玄風時,出現這樣的故事就不足為奇了。陸機身份的第二重矛盾也由此得到了具體體現:作為北上中原的江東士族,陸機一方面帶有明顯的江東烙印,這從他的著作均與玄談無關可知,另一方面,他又需要入鄉隨俗,極力適應中原士族的生活,同一時期,江東舊友還勸其歸吳。他置身于地域的夾縫中。
有著這樣外在身份上的雙重矛盾,陸機卻依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⑧,并最終因卷入“八王之亂”而被殺害。那么,陸機真的是一個汲汲于功名貪功戀勢的人嗎?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就需要了解陸機的內心。
先來看《樂府十七首》,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君子行》)、“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君子行》)、“人生誠行邁,容華隨年落”(《君子有所思行》)、“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長歌行》)、“四節逝不處,華繁難久鮮”(《塘上行》)。不多幾句就刻畫出陸機感慨于年華易逝功業無成的形象,而關于禍福的論述,更表明陸機對險惡環境有著清醒的認識。但“余本倦游客”(《長安有狹邪行》)的陸機為何遲遲不歸呢?“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猛虎行》)、“何為復以茲,曾是懷苦心”(《豫章行》),諸般苦心,就是陸機遷延不歸的理由。
“苦心”謂何?《晉書·陸機傳》很好的回答了這個問題:“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葉嘉瑩也說:“陸機這個人也并非貪戀功名利祿,因為他出身于東吳的名門貴族,是將相之后,所以他自負有才,一個人‘天生我材必有用,他就感到有責任在亂世之中應特別做些事情。”⑨由此我們知道了陸機堅持不歸的緣由。除去身份上的矛盾,陸機的內心其實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渴望建功立業重振家風,另一方面他又身事暗朝理想失落;一方面,他能夠認清現實,另一方面,他又在如此混沌的現實中沉淪。可是試想,作為一個“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的亡國遺孑,志匡新朝的世難談何容易。所以最終,在各方勢力相互爭斗的夾縫中輾轉求仕的陸機,也死于各方勢力的相互攻伐,諸般苦心皆付水東流。
李世民評論陸機:“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鐘方否,進不能辟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己而難長,死因人而易促。”⑩政治家或許不能完全理解文學家的選擇,但陸機的確是一個進退失據的人,一個在夾縫中彷徨掙扎的人。
結語
上文中,我們探討了陸機身份上的夾縫狀態,事實上,終其一生,陸機都陷在一種進退兩難的死局里。在整體平庸的西晉時代,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講,陸機都無愧于“太康之英”的稱號。可嘆其忍辱負重的志士苦心,依附于書劍飄零的夾縫人生,注定了他悲劇命運的走向。忠而被謗,見疑殞命,不只是陸機一個人的悲劇,也是西晉一個時代的悲劇。
注釋:
①鐘嶸《詩品·詩品序(上)》
②羅宗強《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第三章《西晉士風與西晉文學思想》
③葉嘉瑩《漢魏六朝詩講錄》第五章《太康詩歌》
④《晉書·陸機傳》
⑤《世說新語·紕漏第三十四》
⑥唐長孺《社會文化史論叢》之《讀<抱樸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
⑦《晉書·虞預傳》
⑧《晉書·陸機傳》
⑨葉嘉瑩《漢魏六朝詩講錄》第五章《太康詩歌》
⑩《晉書·陸機傳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