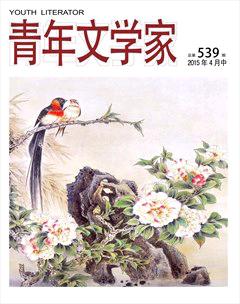迷失的自我:論《小夜曲》中的黃昏(nightfall)隱喻
陳景行
摘 要:《小夜曲:音樂與黃昏五故事集》收錄了五則短篇小說。本文試通過分析不同故事中黃昏時分人物心理變化和情節走向,揭示小說標題中 “nightfall(黃昏)”這一意象代表的日式文化內涵,即在無常的現實面前,個體身份的失落和追逐自我價值過程中的迷失。
關鍵詞:黃昏;自我;身份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11-0-02
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是英國文壇的“移民三雄”之一,1954年生于日本長崎,5歲隨父母移居英國,1989年以《長日留痕》獲得英國文壇最高榮譽布克獎。《小夜曲:音樂與黃昏五故事集》是他的一部短篇小說集,通過五組相互關聯的人物,描寫了一幅音樂人生的浮世繪。由于石黑一雄具有日本和英國的雙重文化背景,他的小說即具有純正地道的英國風情,又流露出日本文化的潛在影響。盡管石黑一雄自認為是一位國際化的作者,不愿提及日本文化對創作的影響,但他筆下那些沉浸在回憶中的“不可靠敘述者”,無論是《長日留痕》中的管家史蒂文森還是《遠山淡影》中的日裔女性悅子,都表現出一種自我認知的“曖昧”,使讀者只能自行判斷回憶和內心獨白的真實性。這種曖昧不清,模棱兩可的表達習慣,正是日本文化最顯著的特點之一。而《小夜曲》書名副標題中的“黃昏(nightfall)”作為小說中五個故事發生的關鍵時間點,則是另一種帶有日式審美情趣,頗具深意的隱喻。在石黑一雄的另一部小說《長日留痕》中,黃昏也曾作為代表帝國時代終結的意象出現,為小說人物回憶平添一份感傷的情緒。
黃昏是一天中太陽收斂光輝,夜幕降臨的時刻。石黑一雄的小說鐘情于描寫“黃昏”,可說是受到了“無常”這一日本文化特有的自然觀和人生觀的影響。
李兆忠在其解讀日本人文化性格的著作《曖昧的日本人》中曾經提到,日本是一個臺風,火山等突發性災變頻發的國家,加之四季分明,景色秀美,瞬息萬變,使得“生存在這種環境里的人,最容易產生‘無常之感”[1]。從燦爛驕陽到夕陽西下,正是萬物生長由盛轉衰規律的象征,最易觸發日本人的“物哀”。落日黃昏自然成為日本文學作品中頻頻詠誦的對象,“在日本人的生命哲學里,一種人生的隕落似乎是無可避免的,明天在哪里?生命會走向何方?”[2]在英語中,黃昏一詞寫作nightfall,不單是指一天中夕陽晚照的時刻,還包括了夜幕剛剛降臨的時間段。《小夜曲》的故事主角都是音樂家或音樂愛好者,對音樂的熱愛和執著支撐著他們的人生理想和信念。然而,當黃昏過去,夜晚降臨后,他們卻都表露出懷才不遇的苦悶,對人生價值的困惑,甚至于在物質和名利的追求中迷失了自我。在石黑一雄的筆下,黃昏的來臨并不僅僅只是提供了一種感傷的氛圍,還暗喻了光明的理想在現實面前的泯滅以及由此造成的自我迷失,具有更深層次的哲學意味。
傷心情歌手
小說第一個故事的敘述者是一名廣場樂隊的吉他手,于偶然間結識了在廣場上喝咖啡的著名歌手托尼·加德納。后者想為結婚二十七年的妻子琳迪獻唱,并邀請“我”入夜后為歌曲伴奏。
托尼·加德納是“我”的母親最愛的歌手。根據“我”的回憶,“我”的母親是一位生活困苦,愛情不得意的單身母親,總是從加德納的歌聲中獲得慰藉與希望。“我”告訴加德納“可是我的母親從來沒有停止相信。每當她傷心的時候,大概就像您今晚這樣,你猜她這么著?她會放你的唱片,跟著唱。”[3](26)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唱出這些感人情歌的托尼·加德納和妻子的婚姻卻已走到了盡頭,因為加德納不甘心自己成為過氣歌手,想要復出,“看看其他人,看看那些成功重返歌壇的人,看看那些至今仍活躍在歌壇的我這一輩人。他們每一個,每一個都再婚了。兩次,甚至三次。他們每一個都牽著年輕的妻子。我和琳迪會成為笑柄的。”[3](34) 正如加德納所說,喜新厭舊,趨炎附勢是演藝圈的規律。琳迪本人年輕時也曾野心勃勃地想要嫁個大明星,并且不惜以第一任丈夫為跳板,最終成功嫁給當紅時期的加德納。后者對此心知肚明,“琳迪明白這其中的道理,比我還早明白”。[3](34)
加德納和他的妻子號稱深愛彼此,演唱結束后,酒店的窗口甚至傳來了琳迪的哭聲,但兩人卻決意分手。入夜的威尼斯,坐著剛朵拉在黑暗的河道上穿行,加德納幽幽地向“我”傾訴心事,“他的聲音時而低得近乎耳語,像是在自言自語。而當路燈或者沿途窗戶的燈光照到船上時,他就會突然想起我,提高音量,然后問‘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朋友?之類的。[3](20)這一切都讓“我”難以理解,“不禁覺得這整件事情也許是一個惡作劇”[3](31)。加德納認為這是因為“我”來自波蘭,不懂得自由的含義,“你怎么可能明白呢,朋友,從那樣的國家來的?”[3](33)但加德納所說的自由并不是造成兩個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無法相互理解的原因,因為自由并不代表個人可以任意自己的價值觀念。“人的生活觀念,并不是從零開始,只能從自己的文化背景中進行選擇。人必然要受制于自己的文化共同體,文化成員的身份會影響個人的認同”[4]。吉他手的困惑反襯出情歌王的價值觀和所作出的人生判斷并不具有普世性,而是在逐名追利中迷失了自我。
大提琴手
小說的最后一個故事從第三者敘述的角度講述了大提琴手蒂博爾的故事。在夏日旅游勝地的廣場上,蒂博爾結實了十一歲后從未摸過琴,卻自稱具有極高音樂天賦和眼力的美國女人麥科馬克小姐。她賞識蒂博爾的才能,認為他具有成為大師的天分,但技巧上尚有所欠缺。到麥科馬克小姐居住的酒店接受指點后,蒂博爾覺得茅塞頓開,“太陽已經快落山了。他犒賞了自己一份摜奶油杏仁蛋糕,喜悅之情一覽無余”[2](218)。然而這個黃昏卻是蒂博爾自我迷失的開始,“大家說那年夏天蒂博爾開始走下坡路,說他頭腦發熱、不知好歹,說都是因為那個美國女人”[2](208),樂隊的其他成員都看出蒂博爾并不具備過人的才能,被人看做天才反而使他產生了不切實際的自我期望。蒂博爾原先一心希望能獲得一份較為穩定的工作,現在卻不情愿到阿姆斯特丹的咖啡廳為客人演奏,“那個女人把他變成了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笨蛋”[2](227)。
蒂博爾最后一次見到麥科馬克小姐也是在黃昏時分,“天已經開始暗了,服務生已經把小玻璃碗里的蠟燭點亮了”[2](234)。在場的還有她的未婚夫,高爾夫球桿商人彼得。麥科馬克小姐告訴蒂博爾她準備回美國結婚。“電梯里,他們脈脈地相視而笑,但沒有說話。他們走出酒店,發現廣場上已經華燈初上”[2](237),兩位“知己”分道揚鑣,但惺惺相惜給蒂博爾帶來的自我期許并沒有就此消除。七年后,往日同在廣場樂隊演出的成員認出了故地重游的蒂博爾,“他穿著西裝——不是什么特別好的,普通西裝而已——所以我猜他現在白天在哪里坐辦公室”[2](240)這時,蒂博爾顯然已終止了自己的樂手生涯。
根據后現代主義論斷,“話語會使受其影響者對某一特定身份產生需要,或者要求他們采用這一特定身份,甚至會把這一身份強加到他們身上”[5]。兩人最初相識時,蒂博爾曾告訴麥科馬克小姐他的導師是一位享有極大聲譽的音樂家,但后者不為所動的態度使之成為兩人互動中的指導者,掌握了話語權。故事中朦朧的黃昏代表了蒂博爾自我迷失過程中的兩個關鍵點: 一旦接受指導,蒂博爾便服從于麥科馬克小姐的音樂話語,相信自己和她一樣都是無法得到發揮的天才;最終這種共同話語體系下產生的身份認同感與現實情況產生了嚴重沖突。才華泯滅和對平庸婚姻生活的恐懼使麥科馬克小姐來到意大利,但最后她選擇妥協,和未婚夫回到美國,接受了現實生活給予的另一種身份。而受她影響的蒂博爾卻不再能接受以謀生為目的的平庸樂手生涯,自我的迷失使他失去了現實生活中的身份定位。
不論下雨或晴天、莫爾文山和小夜曲
《不論下雨或晴天》中的“我”年過四十卻還沒有穩定的居所和收入來源,只得暫居在大學同學查理和艾米莉倫敦的家中,卻意外發現看似圓滿的夫妻關系存在嚴重危機。在夜晚降臨,艾米利下班之前,“我”意識到自己作為失敗者的存在可以反襯出查理的能干,從而化解兩人因對自身和未來的迷茫而產生的感情危機;《莫爾文山》中的大學生夢想成為作曲家,暑期到姐夫姐姐經營的小飯館打零工,偶遇一對生活不如意的樂手夫婦,感受到了現實的困擾。尤其是當他試圖利用晚上的時間寫曲,卻被姐夫認為是影響他人休息,不受理解;《小夜曲》中的爵士樂手明知娛樂圈的愚蠢和無意義,還是受到利益誘惑,進行了整容手術,不得不在酒店修養。他的隔壁房間住著同樣做了整容手術的托尼·加德納前妻琳迪。原本默許并順應娛樂圈規則的兩個人在入夜后大鬧預訂進行頒獎典禮的現場。而當早晨來臨,兩人又回到了之前的疏遠關系,仿佛這荒唐的一夜并不存在。和另外兩個故事一樣,在這些故事中,“黃昏(nightfall)”同樣是人物心理轉折的關鍵點。無論是居無定所的超齡英語培訓老師,熱衷于音樂夢想大學生樂手還是想通過整容包裝自己的爵士樂手,他們都在夜晚來臨時猛然驚醒,意識到音樂理想受到現實消磨的痛苦,甚至在扭曲的心理狀態下,做出吃靴子,將銅像塞進火雞這樣的荒唐舉動。
英語中“nightfall”一詞的原意是“夜幕降臨”,小說中文譯本中的“黃昏”一詞并不足以完全表達出原詞的含義。《小夜曲:音樂與黃昏五故事集》中的主要人物幾乎都是樂手或音樂發燒友,白天時維持著各自的人生軌跡,當夜幕降臨,對現實生活的不滿和懷才不遇的苦悶又成了共同的宣泄目標,由此引發的對自身價值的懷疑和自我身份的失落正是小說一系列故事中反復出現的主題。石黑一雄曾在一次采訪中提到他筆下的人物常常通過自欺面對痛苦,并獲得繼續生存的勇氣,“人類在真正的絕境中挖掘希望的能力即非常悲愴又相當崇高”[6]。小說標題中的“黃昏(nightfall)”既是夜幕降臨前太陽施展余暉的時刻,也是沉淪中的自我面對現實苦苦掙扎的最后時機,可以說是表達石黑一雄口中絕望中求生存之悲涼的最佳意象。
受到日本文化的影響,《小夜曲》中登場人物的串聯就像是一副音樂家們的浮世繪群像,相互關聯,卻又各有各的人生故事。他們來自世界的各個角落,有的人去過許多地方,有的人暫時旅居在異國他鄉,人與人之間只有偶然的相遇,廣場吉他手來自波蘭,大提琴手來自匈牙利,他們都遇到了與自己想法截然不同的美國人;愛好爵士樂的英語老師曾在歐洲各地輾轉,最終又回到倫敦,看望大學畢業后定居在那里的同學;英國大學生歌手遇到的夫婦來自德國;好萊塢娛樂圈紅人琳迪在意大利與前夫分手。不同國家不同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心理在短暫的交集中相互影響,更加重了人物在自我和身份上的迷惑。尤其是波蘭和匈牙利兩個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的設定特別突出了石黑一雄對文化意識多樣性和“國際化寫作”的追求。在《小夜曲》中,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價值觀并無高低之分,也不存在具有絕對影響力和話語權的文化,而是為個體自我的失落提供了相應的文化背景。在石黑一雄的這部作品中,后殖民主義提倡的“混合文化”得到了充分體現。沒有中心和邊緣,也沒有自我和他者,國際化取代了兩元對立的文化帝國主義傾向,同時也帶來了自我身份界定的模糊。小說人物群體性的迷茫心理體現了后殖民混合文化帶來的心態。
參考文獻:
[1] 李兆忠.曖昧的日本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105.
[2] 朱坤.日本文學“黃昏意象”的文化闡釋[J].廣西教育學院學報,2007,(5).
[3] 石黑一雄.小夜曲:音樂與黃昏五故事集[M]. 張曉意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4] 趙稀方.后殖民理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203.
[5] Christopher Butler.解讀后現代主義[M].朱剛譯,秦海花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198.
[6] 李春.石黑一雄訪談錄[J].當代國外文學,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