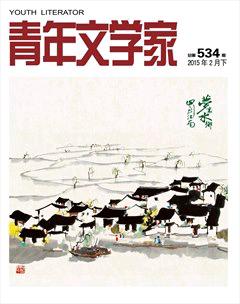簡析《孔雀東南飛》的敘事時空性
摘 要:敘事詩是詩歌中的一種重要的子類型,除了保有其詩歌的本質特征外,與其他詩歌的主要區別在于其敘事性,而研究敘事詩的敘事性,必然要涉及其敘事時空問題。《孔雀東南飛》是中國古典詩歌的精品,對后世敘事詩的發展也有重要影響。因此,本文從始源處立論,通過分析作品《孔雀東南飛》在敘事過程中的時間性和空間性,以期發現其在敘事時空上的獨特品性,以及對現代敘事詩研究的意義。
關鍵詞:敘事詩;敘事時間;敘事空間;《孔雀東南飛》
作者簡介:劉敏(1986.9-),女,漢族,四川內江人,四川廣播電視大學,助教,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漢語教育、教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06-0-03
一、敘事性與敘事時空
敘事學理論源遠流長。在西方,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以及《修辭學》;在中國,則因金圣嘆的敘事研究而使之發展到相當的高度。
在敘事話語中,時間是一個基本因素,“在很多敘事虛構作品中,時間不僅僅是反復出現的主題而且還是故事與文本的組成部分。言語敘述的獨特性在于,時間在其中是由再現工具(語言)和再現對象(故事事件)同時構成的。因此,在敘事虛構作品中,時間可以被界說為故事和文本之間的年月次序關系。”[1]用蘇珊·斯坦福·弗里德曼的話講,敘事,作為講述的形式,是存在于時間之中的,敘事需要時間來講述,敘事講述的是時間中的事件序列。時間性在敘事詩學研究中占據著主導地位,我們在討論敘事詩的時候不得忽視這一重要的因素。敘事時間性研究的杰出理論家利科曾經這么寫道:“確實,我把時間性當成存在的結構,是它通向語言的敘事性;我把敘事性當成語言的結構,這一結構把時間性作為它的終極指設”。[2]此后,H.波特·阿博特在《劍橋敘事導論》中同樣把時間作為敘事的主要特質集中討論。他強調敘事應該是我們人類把對時間的理解組織起來的原則方法。“敘事是一種語言行為(無論是口語、文字,還是其他符號形式),而語言是線性的、時間性的,所以敘事與時間的關系頗為密切。”于此,敘事時間性這一點,基本上已得到國內外敘事學研究者的公認。
敘事研究既存在一個時間維度,也存在一個空間維度,敘事詩中的時間性和空間性,共同構成了敘事詩歌的敘事性特征。如果說,敘事與時間的關系在傳統敘事學中已得到較為充分的研究的話,那么,敘事與空間的關系在傳統敘事學中則幾乎還是一片空白。而事實上,敘事與空間的關系在敘事學研究中非常重要。作為一種“先驗的感性形式”(康德語),時間只有以空間為基準才能考察和測定,正如空間只有以時間為基準才能考察和測定一樣;也就是說,無論是作為一種存在,還是作為一種意識,時間和空間都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物理學家愛因斯坦說道:“空間(位置)和時間在應用時總是一道出現的。世界上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是由空間坐標和時間坐標來確定”。正因為時間和空間總是如此聯系緊密、如影隨形,所以我們認為空間也是敘事中的重要元素,也是敘事學研究的重要維度,而這正是以往的敘事學研究所忽視的。“無視空間向度緊迫性的任何當代敘事,都是不完整的,其結果就是導致對一個故事的性質的過分簡單化。”[3]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敘事正是從空間相互作用的矛盾狀態里建立起來的:是一個“有區分的復雜網絡”和“一個空間的結合型體系”。將空間恢復到與時間完全合作的關系,一起構成敘事發生的力量,能使閱讀在策略上集中于時間的對話性互相作用,共同作為人類思維和經驗的中介組成成分。因此敘事時間性和敘事空間性應該是具統一性的,二者共同作用于敘事詩學研究,才能使我們更好的研究敘事詩作。
二、《孔雀東南飛》中的敘事時間和敘事空間
作為敘事理論討論的一個方面,敘事時間,不僅涉及到故事時間,還涉及到文本時間。熱奈特從順序(order)、進速(duration)和頻率(frequency)三個方面探討了故事時間和文本時間的關系。順序指時間的前后排列次序,小說的敘述時間可以和故事時間的次序相同,也可以不同。前者形成了傳統小說常用的“順敘”法,后者則形成“倒敘”、“插敘”等敘事效果。進速,指敘述時間與故事時間的關系,涉及到敘述的“加速”和“減速”,比如相對于故事時間,敘述時間可以“省略”(無限快)、“概括”(比較快)、“場景”(比較慢)、“休止”(零度進展)。頻率指事件在敘述中的發生次數和重復次數。
《孔雀東南飛》(又名《焦仲卿妻》)一詩首見載于《玉臺新詠》卷一,題為“古詩”,《樂府詩集》卷七十三入《雜曲歌辭》。該作品作為一部表現古代青年男女的愛情長篇,與《木蘭詩》一起被譽為古代民歌的“南北雙璧”,代表著漢樂府敘事詩發展的高峰,也是我國文學史上現實主義詩歌發展中的重要標志。這首被明代王世貞的《藝苑卮言》稱為“長詩之圣”的作品,敘事性特征,非常明顯,就其敘事時間性和空間性而言,《孔雀東南飛》有著自己的特色。
(一)《孔雀東南飛》的敘事時間性
《孔雀東南飛》全詩三百五十三句,一千七百六十五字,它是創始于二世紀的民間口頭創作,集中了人民的智慧,凝聚了人民的血淚。其賴以產生的時代特征、社會環境等歷史條件在作品中都有所暗示,反映出的價值觀念與審美意識也有獨特之處。全詩建構宏大,描寫了焦仲卿和劉蘭芝的動人心魄的愛情悲劇故事,充溢著強烈的反封建色彩,可以說是一篇聲討封建禮教的檄文。
1、故事時間
故事時間,即指一個故事前后相序的發展順序,是故事本身的發展進程的展示。《孔雀東南飛》全部敘事以焦仲卿、劉蘭芝與封建家長的矛盾沖突以及他們夫婦二人的感情糾葛組織起來的,可算是封建勢力壓迫下的愛情悲劇。整首詩,采用雙線推進的方式展開。一條線索由劉蘭芝、焦仲卿夫婦的關系組成,另一條線索由劉、焦夫婦同焦母劉兄之間的關系組成,后者在全詩占主導地位。《孔雀東南飛》一詩寫了劉蘭芝從被遣返回家,到最后劉、焦二人殉情,短短的數月時間之內發生的事情,整個作品敘述的故事,其發展的時間跨度上并不算太大,但卻表現了豐富的內容和意義。該作品的故事時間具體表現為:劉蘭芝向焦仲卿傾訴—母子交流(“府吏得聞之,上堂啟阿母”)—仲卿無奈遣送蘭芝—蘭芝辭別公母小姑—夫妻相別,依依不舍—蘭芝被迫,歸還娘家—縣令遣媒,蘭芝謝絕—兄長逼迫,蘭芝出嫁—夫妻重見,相約赴死—劉蘭芝焦仲卿合葬。這樣一個清晰的故事發展線索,完整地展示了故事的前后相序的關系,從而使得我們能更清楚故事的前因后果,以及造成這種悲劇的特定原因,更易我們理解作品內涵。
2、文本時間
敘事時間通常不一定就是和故事時間完全一致的,這就存在一個文本時間,因而,呈現給讀者的敘事順序可能不同與故事時間的發展順序,這在敘事詩歌中也是常有的事。《孔雀東南飛》該詩其文本時間在全詩表現為:開頭以序言的形式交代了故事發生的背景,簡介了故事的主人公,以及故事梗概,作者以倒敘的形式開始了敘事。正文以“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開始,給文章奠定了基調,敘事正式開始,劉蘭芝對焦仲卿的傾訴,訴說自己從小到大的經歷,“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以及嫁到焦家以后,勤儉持家卻仍然得不到婆婆的喜歡,只能以“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向焦仲卿抱怨。這些內容,從側面展現了一個完美的女子,而這樣的女子都要遭受遣返的命運,更是反襯出社會的不公,封建家長制的殘酷無情。敘事依據作者感情起伏變化,聽完這樣的傾訴,焦仲卿則去稟告母親,自己對蘭芝的心意。然而,得到的卻是母親“槌床便大怒”的回復。封建勢力的強大,即便有心人也無能為力,焦仲卿,堂堂男子,也無力挽救自己的幸福。無奈,“府吏莫無聲”只得回告蘭芝“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第二天,“雞鳴外欲曙”點明了時間,此時的蘭芝收拾回娘家,此處敘事進速明顯慢了下來,對蘭芝回娘家前的敘事非常詳細:
“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裌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蔥根,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
這里敘事者故意慢下敘事進速,則是為了更好地表現出蘭芝的自尊,以及對這個家的不舍,她期待她可以拖延離開的時間,或許婆婆就能改變主意,或許焦仲卿能想出辦法,留下她,對她而言,這樣的敘事方式,豐富了故事的內涵。此后,蘭芝辭別阿母和小姑,再是和府吏相別。這一辭別婆家的部分,作者給予了詳盡的表述,給讀者以深刻的印象。回到娘家,卻是“進退無顏儀”;而后敘述“還家數余日”之后發生的事,兄長逼迫蘭芝改嫁說到“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這樣的兄長使得蘭芝沒有選擇,她被迫答應改嫁,導致最后的悲劇,夫妻二人殉情,結束敘事。總之,敘事者在進行敘事時,對各個部分做出了詳略得當的處理,整個敘述,我們既可以看到“省略”(如“還家十余日”這十余日,作者一句帶過)、“概括”(如“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這一部分內容,則寫得比較概括)、“場景”、“休止”(零度進展)等各種部分在文中都有所表現。在敘事過程中,作者對故事時間進行“加速”、“減速”等處理,讓故事的敘事時間性,更加凸顯,顯示出高超的敘事藝術。
整首詩,敘事時間方面的特點表現為:第一,《孔雀東南飛》的故事時間跨度不大,通過還原文本分析,整首詩歌敘述的大概有一個多月的時間。第二,《孔雀東南飛》敘事時間相對簡單的。第三,《孔雀東南飛》的敘事時間方式比較單一,主要體現在敘事手法上比較單一,主要以順敘為主。作者根據敘事的需要,在敘事時間上,做了相對完善的“加速”以及 “減速”處理,讀來催人淚下,感人至深。通過最后的悲劇收場,達到震撼人心的效果,也反應出了封建家長制度的不合理。
(二)《孔雀東南飛》的敘事空間性
如果說敘事時間是一條靜止的線,那么敘事空間則因其立體性,賦予了故事一個豐富的內涵。敘事詩也涉及到敘事空間的問題,“根據原始神話觀念,宇宙的結構分三個層次,分別為上、中、下三界。在空間上,上界為天界,是以長生天為首的天神所在的地方;中界是地上,是人居住的世界,是英雄們活動的主要場所;下界在地下,是人死亡后去的地方,也是鬼怪居住之地。”[4]在三界中,三界之間不是隔絕的,它們相互聯系而且可以互通。
1、故事空間
物理空間,實際上就是指,故事原本發生的空間位置。因為《孔雀東南飛》寫的對象是百姓生活,并不涉及人神活動,因而人物活動的空間性特征并不著重體現在人物于三界的活動,而主要表現在,人物活動空間的轉移:焦仲卿家—劉蘭芝家—路上相遇—相約地府這樣的空間活動順序。《孔雀東南飛》的空間活動順序,其實簡單、明晰,我們細讀作品就可以看出來。首先,蘭芝的傾訴這一部分,之后“府吏得聞之,堂上啟阿母”這里“堂上”一次則點出來故事發生的地點。緊接著的是焦母與兒子的對話以及母子的沖突,這當然也是發生在焦家的。后來焦仲卿無力阻止母親的決定,只能答應母親遣返蘭芝;蘭芝回到娘家“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此處“家堂”則是指蘭芝的娘家,故事發展繼續展開。此后,“還家十余日,縣令遣媒來”故事繼續在劉家發展,到后來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無奈地答應改嫁;“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新婦謂府吏:“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再后來,劉焦二人殉情。最后“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整個故事以悲劇結束。這樣的空間轉換,讓讀者讀來心里頗有感觸,簡單的故事空間,卻反映出了巨大的社會內容,不能不說是此故事的特色。
2、敘事空間
敘事空間其實是不同于故事空間的。這里主要根據原始神話觀念,提及宇宙三界。作為敘事詩的一個方面,敘事空間主要根據敘述者而定,《孔雀東南飛》反映的宇宙結構三界觀念,其實是比較模糊的,作品以“焦仲卿家—劉蘭芝家—路上相遇—相約地府”這樣的空間順序活動,但從這個轉換的空間場所中,我們仍看到了,所謂的宇宙三界概念。
作品中詳細描寫天界的部分幾乎可以說是沒有的,只是寫到了相關的一些內容,開頭“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給文本敘事奠定了基調。此后又寫到劉蘭芝和焦仲卿殉情后,“兩家求合葬……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敘事寫到華山傍的鴛鴦鳥,這里可以說是蘊含了一種寓意,即蘭芝和仲卿二人成雙成對。這個上界是用地面上的現實和鴛鴦鳥飛鳴的素材虛構出來的,是對圓滿美好的一種憧憬和寄托,這種寫法,滿足了中國文化中喜好大團圓的傳統,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孔雀東南飛》并未詳細提及下界的情況,只是寫到有下界的存在,如作品中寫道:
“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
這里所謂的黃泉即是下界,從而可以看出《孔雀東南飛》對下界的描述,也是個比較模糊的概念。
《孔雀東南飛》的故事空間是比較簡單的,主要圍繞劉、焦兩家為活動的故事空間。寫人活動的中界寫得非常詳細,對整個故事的敘述,敘述者仍然依據感情起伏而組織,對各個部分做了詳略得當的處理。在文本時間上,主要提及地界人的空間活動,天界和地界的概念表現得非常模糊。
三、小結
中國文化以儒家文化為代表,和道家文化共同構成中國文化的獨特品質。因而也就使得中國作品帶有更多的是理想性的。具體而言,中國敘事詩的時間性特點是非常明顯的,整體上看,其時間性特征多是跳躍性的,敘事詩大都依附于作者的情感組織文本。作品大多是依循因果關系或者時間方向 (過去—現在—未來)來組織事件,從而建立其敘事的秩序。空間方面而言,中國敘事詩多因內容簡單、篇幅短小,表現在空間轉換方面都是比較簡單的,跳躍性也不大,呈現的敘事空間性比較單一,多屬于線性式的,這樣就使得敘事詩表現的空間場面通常都不如西方敘事詩宏大。中國的敘事詩,即使敘事也是以抒情為主,這樣的特征,決定了敘事詩不以事件本身為重點,而以敘述者個人情感流動主宰敘事順序的特色。雖然不及西方敘事詩宏大,但是也正因為如此,更能體現中國文化的獨特。
當今世界,國際交流更發達,各國文化交流更勝,面對詩文化的衰退,我們有責任,更有義務,在研究中進步,在探討中向前。讓這些具有悠久歷史的作品,給我們的文化注入更多的養分,才能讓我們的文化軟實力在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文化,一個國家的詩歌也會有它獨有的特色。悠悠千古敘事詩,記錄了一個民族的世事變遷,從稚嫩的童年、懵懂的少年,一路走到今天,我們在這些優美的敘事詩中,真實地感受到了祖輩們的生活,他們親切的身影,以及他們深情的呼喚,這些都將是一個民族不可割舍的歷史,它流淌在我們后輩的血液里,是會永遠延續下去的精神瑰寶,值得我們一讀再讀!我們在學習本民族的敘事詩的同時,也不可忽視其他民族的優秀敘事詩,我們在比較中發現,在發現中探索,在探索中進步,更好的詮釋敘事詩給我們留下的寶貴財富。這是我們對敘事詩進行研究的現實意義。
注釋:
[1]〔以色列〕里蒙—凱南.敘事虛構作品[M].姚錦清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79.
[2]James Phelan Peter J.Rabinowitz當代敘事理論指南[M]申丹,馬海良,寧一中,喬國強,陳永國,周靖波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205.
[3]龍迪勇.敘事學研究的空間轉向[J]江西社會科學,2006:62.
[4]王衛華.《江格爾》與《荷馬史詩》宇宙結構觀比較[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3):105.
參考文獻:
[1]王先霈,孫文憲.文學理論導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85-87.
[2] James Phelan Peter J.Rabinowitz當代敘事理論指南[M]申丹,馬海良,寧一中,喬國強,陳永國,周靖波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205
[3]龍迪勇.敘事學研究的空間轉向[J]江西社會科學,2006:62.
[4]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1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