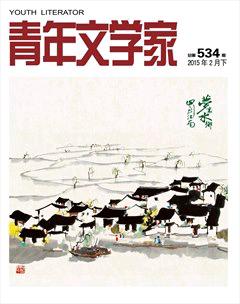淺析李白詩歌中的畫意美
趙穎
摘 要:李白是我國古代盛唐時期偉大的詩人,他的詩大氣恢宏、個性張揚,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國畫,又稱中國畫,是中華民族特有的藝術形式,中國繪畫尚意、重表現、重情感,不受空間和時間的局限。李白的詩歌和國畫的意境在美學上有許多共通之處,詩歌體現了水墨丹青的意境。
關鍵詞:李白詩歌;中國畫;畫面感;意境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06-0-02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這首無數人從孩提時就開始朗誦的《靜夜思》,平淡中帶著深情,寧靜而耐人尋味,當輕聲讀起它時,每個人心中都會升起一輪屬于自己的當年明月,勾起一縷或濃或淡的感懷思鄉之情……
每每欣賞李白的詩,眼前總會浮現出一幅幅絕美的中國畫,他的詩如經典的國畫一樣,詩中有畫,情景交融,所謂詩情畫意,讓人看得見聞得著,醉身其中,流連忘返。李白的詩歌與國畫有許多異曲同工之處。在內容上大多以山水、花鳥、人物為題材,一屋、一舟、一帆皆可如詩如畫;在風格上想象豐富、構思奇特、雄渾瑰麗、豪邁瀟灑,大手筆、大寫意;在表現手法上,夸張、留白、潑墨、寫意、幻彩、虛實結合,均運用自如;在精神上,寓情于景、以詩言志、以物托人,用神來之筆,書寫他的人生、理想和情懷。
清水出芙蓉,生動自然詩中人。談到對人物的描繪,國畫中東晉顧愷之的《洛神賦圖》、五代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宋代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等均是頂峰之作,無論選材自現實生活還是想象傳說,無論是帝王將相、神佛仙道還是社會底層人物,均神態逼真、表現細膩,繪聲繪色、栩栩如生。而李白詩中對人物形象的塑造亦是清新自然、視角獨特。《長干行》是反映商人婦生活的詩歌中最著名的一首。大凡這類“閨怨詩”,多數人會從少婦時期入手寫起,但李白卻別出心裁從童年寫起,且運用形象,進行典型的概括。開篇“妾發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一個額前覆著劉海的小女孩,手里拿著一枝花,站在門前戲耍;一個頭上扎著丫角的小男孩,胯下竹馬,在小路上又跳又跑;兩個娃娃圍在床邊,擺弄著幾顆梅子……多么像一組趣味橫生的民間兒童風俗畫。于是,這“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的一對娃娃結成了后來的小夫妻,引出了“十五始展眉,愿同塵與灰”、“十六君遠行,瞿塘滟滪堆”、“門前舊行跡,一一生綠苔”、“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詩人通過心理描寫和典型的語言、環境突出典型的人物,塑造了一個生活在水鄉、成長在民間,既癡稚又熱情,既溫淳又奔放的“商人小婦”形象,千百年來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而另一首《玉階怨》“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則為人們描繪了一幅情調凄冷的畫面:一個孤獨的少女,在無人的漫漫長夜,久久悄立階下,直到夜色已深,露打羅襪方回到屋中,卻又隔著放下的玲瓏疏簾,凝望窗外的秋月。這是一個被拋棄被壓迫的女子形象,“無一字言怨,而隱然幽怨之意見于言外”,使人對詩中女子油然而生同情與憐憫。
暢游天地間,大氣恢宏山水詩。對于山水景色的描寫刻畫,李白更是信手拈來,一幅幅潑墨大寫意的山水畫卷,甚至讓人懷疑他與“搜盡奇峰打草稿”的石濤、“五百年來第一人”的張大千系出同門。“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這首《望廬山瀑布》與張大千的《廬山圖》、《瀑布》簡直是絕配,仿佛遠隔時空的兩位大師早已是“心有靈犀一點通”,詩是為畫而配,畫是為詩而作。張大千的《瀑布》,充分利用了潑墨、潑彩藝術來表現,瀑布邊緣及以外的物象模糊不清,只突出了瀑布本身的氣魄雄偉;李白則以高度夸張的藝術手法,將飛流直瀉的瀑布,描寫得奇麗壯觀,人們似乎能感受到那撲面而來的瀑布濺起的水花,一幅生動傳神的山水畫卷,手法寫意,筆墨簡煉。再看“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一葉輕舟,在青山與碧水中緩緩飄過,兩岸山中猿聲不絕于耳,遠處一輪紅日浮于水天之間……江山如畫,寄托了作者無限的情思。
筆落驚風雨,不拘一格釋豪放。在詩歌的表現手法上,詩人大量使用了夸張、想象和比喻,主觀抒情色彩十分濃烈,排山倒海、一瀉千里的氣勢,給人以強烈的感官視覺上的沖擊,情感上的震撼。
著名的《將進酒》開篇“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以黃河雄偉的氣勢,烘托形象,制造氛圍,增強作品的感染力;“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你不見有人對著大廳明鏡里的白發悲哀,早晨頭上的青絲晚上就變成了皚皚白雪,將人生由青春至衰老的過程說成了“朝”與“暮”之間的事,流露出詩人慨嘆人生幾何的消極情緒;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又從貌似消極中流露出深藏其內的懷才不遇、渴望施展抱負的積極本質,詩人抱著樂觀、通達的情懷,對自己的才華充滿自信。他那豪氣沖天、呼朋喚友、眼花耳熱的醉態,又再度躍然紙上,好一幅極富感染力的盛宴圖。
《夢游天姥吟留別》帶給讀者的則是另外一幅神奇的畫面,超乎尋常的感官享受。“謝公宿處今尚在,淥水蕩漾清猿啼。腳著謝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巖泉,栗深林兮驚層巔……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詩歌中對天姥山景色的描寫有石濤《搜盡奇峰打草稿》的氣勢,而對眾仙人的刻畫則如顧愷之《洛神賦圖》中“洛神初現、神人對晤”等段的描繪,“翩若驚鴻,宛若游龍”,超凡脫俗。全詩雄偉豪放,瑰麗飄逸,詩人通過夢境的描繪,刻畫出想象中的天姥山奇麗明媚的景象,浪漫而寫意,令人仿佛置身仙境、嘆為觀止。
詩人在創作過程中也會用到繪畫中的留白,以突出主題,彰顯精神。如《敬亭獨坐》,“眾鳥高飛盡,孤云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一般的文藝作品描寫山的時候,為了使山的精神易于顯露,情態更多樣,除了從山勢的高峻,山嶺的連綿,山態的奇詭角度發揮想象之外,還經常借助于譬如云煙變幻、鳥語蟬鳴之類作為襯托。而《敬》詩獨樹一格,不但不需要襯托,反而將所有可襯托的東西統統去掉,單獨寫山。不僅把山人格化,寫出一座有感情、有性格的山,而且將其比作與詩人自己一樣清華脫俗,適度的留白使“皮毛脫盡,精神獨存”,借此吐露詩人對現實生活的看法。繪畫上,白石老人晚年93歲時所畫的蝦可謂爐火純青、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其中一幅《蝦圖》,在大幅的畫面上僅畫了兩只蝦,空白極大,沒有水的痕跡,沒有一絲線條的附加,但蝦的游動、跳躍、嬉戲,流水的生氣躍然紙上……大凡名家吟詩作畫,絕不僅僅是簡單的描繪和復制,都是為了通過作品表達內心一定的思想感情,以物言志,以形傳神。
唐代詩歌是我國古代文化中非常寶貴的一筆遺產,它代表著我國詩歌的最高峰,而李白是盛唐最杰出的、在巔峰上謳歌這個時代的偉大詩人。他的許多流傳千古的佳作名篇,都血肉飽滿,形象生動,以物言志,抒發對時代、對人生、對理想的追求和抱負,盡管也有局限性,但充分體現了他張揚的個性、飄逸的氣度、浪漫主義的情懷,“詩仙”之稱當之無愧。對于李白詩歌的學習和賞析,隨著學習的深入定會帶給我更大的震撼和美的享受。